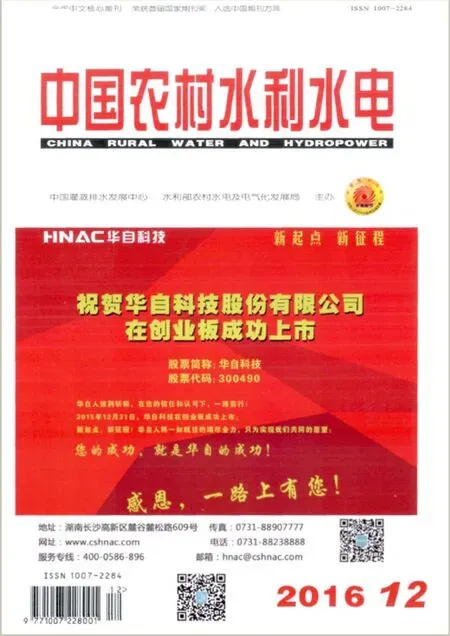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中重金屬形態(tài)分布及其潛在生態(tài)風(fēng)險(xiǎn)評(píng)價(jià)
文 竹,李 江,,王 興,張青青(.貴州工程應(yīng)用技術(shù)學(xué)院,貴州 畢節(jié) 55700;.貴州大學(xué)資源與環(huán)境工程學(xué)院,貴陽(yáng) 55005)
0 引 言
隨著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城市化進(jìn)程的加快,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和處理比例也快速增加,城市污泥中重金屬的含量因城市的工業(yè)布局、地理位置、城市性質(zhì)等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異[1,2]。據(jù)環(huán)境保護(hù)部2010年統(tǒng)計(jì)年報(bào):2010年我國(guó)有城市污水處理廠2 881座,日處理污水1.23×107t[3-5];截至2011年3月底,全國(guó)各市、縣累計(jì)建成城鎮(zhèn)污水處理廠2 996座,處理能力達(dá)到1.33 億m3/d,由此將產(chǎn)生大量的污泥,因此在城市污水處理比例不斷增加的同時(shí),也面臨巨大的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泥(簡(jiǎn)稱污泥)處理壓力[4,6]。由于污泥來(lái)源于各種工業(yè)和生活污水,不可避免地含有一些對(duì)環(huán)境和生物有害的物質(zhì),其中重金屬由于具有易富集、難遷移、危害大等特點(diǎn),一直是限制污泥農(nóng)業(yè)可有效利用的主要因素,污泥中的重金屬污染也是土壤重金屬污染的主要來(lái)源[7,8]。因此,在污泥可有效利用前需獲得污泥中重金屬的環(huán)境效應(yīng)并評(píng)估其潛在的生態(tài)風(fēng)險(xiǎn)。
目前對(duì)于我國(guó)城市污泥中重金屬含量的研究中, 對(duì)于我國(guó)東南部等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理、處置,污泥中重金屬的形態(tài)分布及其對(duì)植物的毒性效應(yīng)或富集效應(yīng)研究較多,而對(duì)于貴州經(jīng)濟(jì)欠發(fā)達(dá)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泥中重金屬元素的相關(guān)研究較少[9,10]。為了掌握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中重金屬污染特征及其潛在生態(tài)風(fēng)險(xiǎn)評(píng)價(jià),本文以貴州省7個(gè)城市(銅仁、貴陽(yáng)、興義、遵義、凱里、六盤(pán)水和畢節(jié))的21家污水處理廠為調(diào)研對(duì)象,采集各廠的脫水污泥進(jìn)行重金屬質(zhì)量分?jǐn)?shù)及養(yǎng)分的測(cè)定,分析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中重金屬分布特點(diǎn),與污泥的相關(guān)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比較的同時(shí),采用修正的BCR法和地累積指數(shù)(Igeo)、單一金屬生態(tài)潛在風(fēng)險(xiǎn)因子(Eir)、多金屬潛在生態(tài)風(fēng)險(xiǎn)指數(shù)(RI)法,研究了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泥的養(yǎng)分和污泥中重金屬的形態(tài)分布特征,并對(duì)其進(jìn)行了潛在生態(tài)風(fēng)險(xiǎn)評(píng)價(jià),為貴州省乃至全國(guó)污水處理和污泥資源化利用中重金屬污染控制提供基礎(chǔ)數(shù)據(jù)和理論依據(jù)。
1 材料與方法
1.1 樣品采集
2015年6-9月分別在貴州省銅仁、貴陽(yáng)、興義、遵義、凱里、六盤(pán)水和畢節(jié)7個(gè)城市選取污水廠采集終端污泥,每個(gè)城市選取3個(gè)污水廠,總共21個(gè)污水廠,21個(gè)污水廠污泥排放量占貴州省污水廠污泥排放量的80%以上,可以代表貴州省目前污泥重金屬的整體污染水平。樣品(采樣點(diǎn))選擇在各污水處理廠污泥脫水車間連續(xù)穩(wěn)定運(yùn)行的脫水機(jī)出泥口,采集不同脫水機(jī)出泥口的樣品并將其混合,混合樣品的質(zhì)量不少于2 kg;根據(jù)多點(diǎn)采樣的原則在污泥堆放場(chǎng)地進(jìn)行采樣,以確保每種污泥采集方法收集的污泥樣品均具有代表性。采集的污泥用錫箔紙包裹放入潔凈密實(shí)袋,迅速帶回實(shí)驗(yàn)室冷凍保存以待檢測(cè)。
1.2 污泥樣品預(yù)處理
1.2.1儀器和試劑
儀器:電感耦合等離子質(zhì)譜儀(ICP-MS,Agilent 7500,USA);微波消解儀(美國(guó)CEM公司);消解罐;聚四氟乙烯坩堝;恒溫電熱板;亞沸蒸餾器(Berghof BSB-939-IR,German);電子天平(German,精確至0.000 1 g);100 mL容量瓶;玻璃漏斗;定量濾紙。
試劑:去離子水;濃硝酸(Q=1.42 g/mL,優(yōu)級(jí)純);超純水儀(Milli-Q,F(xiàn)rance);硝酸(經(jīng)亞沸蒸餾器二次蒸餾酸);氫氟酸(超純,上海試劑一廠);高氯酸(優(yōu)級(jí)純,天津東方化工試劑廠)。
1.2.2污泥中養(yǎng)分的測(cè)定
污泥pH測(cè)定采用1∶2.5水土比浸提pH玻璃電極法;污泥有機(jī)質(zhì)采用重鉻酸鉀氧化外加熱法;污泥全磷用NaOH熔融-鉬銻抗比色法;污泥全氮用全自動(dòng)凱氏定氮法;污泥全鉀采用火焰分光光度計(jì)法[10]。
1.2.3污泥中重金屬質(zhì)量分?jǐn)?shù)的測(cè)定
樣品經(jīng)自然風(fēng)干后,碾磨并過(guò)60目篩,稱取約0.500 0 g加工好的樣品(精確到0.000 1 g)經(jīng)HClO4-HNO3-HF硝化處理,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zhì)譜儀(ICP-MS)內(nèi)標(biāo)法測(cè)定土壤Zn、Cd、Pb、Cu含量,采用冷原子吸收微分測(cè)儀、為ICP配置氫化物發(fā)生器,確保所需儀器的靈敏度。同時(shí)取土壤樣品0.250 0 g(精確到0.000 1g)于25 mL比色管中,加入新配(1+1)王水10 mL,于沸水浴中加熱2 h,其間要充分振搖兩次,冷卻至室溫后加入10 mL保存液,用稀釋液定容,搖勻,該消解液用來(lái)測(cè)定Hg。取靜置后的消解溶液5.00 mL于另一25 mL比色管中,加入50 g/L的硫脲溶液2.5 mL,鹽酸2.5 mL,定容至25 mL,該溶液用來(lái)測(cè)定As。ICP-MS的精確度在2%以下,回收率為95%以上,測(cè)定偏差控制在9%內(nèi),每個(gè)樣品設(shè)置3個(gè)平行樣(測(cè)定數(shù)據(jù)為3次的平均值)[7]。污泥中重金屬質(zhì)量分?jǐn)?shù)的計(jì)算公式[11,12]:
式中:w為污泥中重金屬的質(zhì)量分?jǐn)?shù)(干基),mg/kg;M為所測(cè)定的某種重金屬;c為ICP-MS測(cè)定預(yù)處理樣品得到的重金屬質(zhì)量濃度,mg/L;n為ICP-MS測(cè)定時(shí)預(yù)處理樣品的稀釋倍數(shù);m為污泥樣品質(zhì)量,kg;v為定容體積,L。
1.2.4污泥中重金屬化學(xué)浸提試驗(yàn)
采用修正的BCR法[13,14]分析污泥中重金屬形態(tài)及對(duì)應(yīng)組分含量,此方法將污泥中的重金屬分為5種化學(xué)形態(tài),分別為水溶態(tài)(T1)、酸溶/可交換態(tài)(T2)、可還原態(tài)(T3)、可氧化態(tài)(T4)和殘?jiān)鼞B(tài)(T5)。準(zhǔn)確稱取0.500 0 g過(guò)篩污泥,放入50 mL聚丙烯離心管中,按表1中的浸提條件和步驟進(jìn)行浸提,使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原子發(fā)射光譜儀(ICP-AES)測(cè)定上清液中重金屬濃度。每個(gè)樣品設(shè)置3個(gè)平行樣,每個(gè)批次實(shí)驗(yàn)設(shè)置空白樣品。

表1 修正的BCR連續(xù)提取步驟[13]
1.3 潛在生態(tài)危害評(píng)價(jià)方法
(1)單因子指數(shù)法[14,15]。
Pi=Ci/Si
(1)
式中:Pi為污染指數(shù);Ci為污染物實(shí)測(cè)值;Si為污染物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i代表某種污染物。
(2)N.L.Nemerow綜合污染指數(shù)法[15]。
Pt={[(Ci/Si)2max+(Ci/Si)2ave]/2}1/2
(2)

表2 土壤質(zhì)量分級(jí)標(biāo)準(zhǔn)[14,15]
(3)Hakanson潛在生態(tài)危害指數(shù)法[16]。不同重金屬對(duì)人體健康產(chǎn)生的危害不同,即使在污泥中濃度相同,其產(chǎn)生的危害也有差別。針對(duì)于這點(diǎn),瑞典科學(xué)家Hakanson在1980年建立了一套評(píng)估重金屬污染與生態(tài)危害的方法,將重金屬元素的生態(tài)效應(yīng)環(huán)境效應(yīng)及毒理學(xué)聯(lián)系起來(lái),較純粹采用重金屬元素污染程度更好地反映重金屬元素的潛在危害。其計(jì)算公式為:
(3)
式中:Ei為第i種重金屬的潛在生態(tài)危害指數(shù);Ti為第i種重金屬的毒性響應(yīng)系數(shù)(表3);Ci為第i種重金屬的測(cè)定濃度,mg/kg;Co為重金屬元素的參比值,mg/kg(表3)。

表3 重金屬毒性響應(yīng)系數(shù)及其參比值
不同重金屬?gòu)?fù)合生態(tài)危害指數(shù)(RI)的計(jì)算公式為:
RI=∑Ei
(4)
根據(jù)Ei與RI值大小,對(duì)Hakanson提出的重金屬生態(tài)危害程度的劃分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了適當(dāng)調(diào)整(表4)。

表4 潛在生態(tài)危害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
(4)地累積指數(shù)法(Igeo)[16]。地累積指數(shù)法是從環(huán)境地球化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評(píng)價(jià)污泥中重金屬的污染,除考慮到的人為污染因素、環(huán)境地球化學(xué)背景值外,還考慮到工業(yè)可能引起的背景值變動(dòng)的因素,彌補(bǔ)了同類其他評(píng)價(jià)法的不足,因此在歐洲被廣泛采用,目前也應(yīng)用于土壤中元素的污染評(píng)價(jià)。其計(jì)算公式如下:
Igeo=log2[Cn/(kBn)]
(5)
式中:Cn為元素n在污泥中的含量(實(shí)測(cè)值);Bn為工業(yè)前該元素的地球化學(xué)背景值,取k值為1.5。
2 結(jié)果與分析
2.1 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重金屬含量
由表6可知,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中8種重金屬元素平均含量的大小順序?yàn)镸n>Cu>Zn>Pb>Cr>Ni>As>Cd,其中Mn為115.8~653.2 mg/kg,Cu為152.7~513.4 mg/kg,Zn為75.2~431.7 mg/kg,Pb為92.7~245.7 mg/kg,Cr為91.3~231.8 mg/kg,Ni為43.2~152.7 mg/kg,As為15.4~53.2 mg/kg,Cd為1.5~5.6 mg/kg。其中Mn和Cu占重金屬總量比例最高,Cd占重金屬總量比例最小。污水處理廠污水來(lái)源不同,各類重金屬污染水平差異所導(dǎo)致的,Zn含量高可能與貴州城市排水管道大多采用鍍Zn材料有關(guān),Mn和Cu含量高可能與進(jìn)水中含有電鍍、化工、機(jī)械加工、制革等工業(yè)污水有關(guān)。各城市污水廠污泥重金屬污染程度基本表現(xiàn)為:貴陽(yáng)和銅仁污染程度較高,而畢節(jié)和凱里污染程度較低,這與城市污水廠的工業(yè)廢水有關(guān),工業(yè)廢水中重金屬含量變化較大。通過(guò)分析發(fā)現(xiàn),遵義市污水廠中3次采樣的重金屬含量相對(duì)穩(wěn)定,這與污水廠主要處理生活污水有關(guān),生活污水中重金屬含量變化幅度相對(duì)較小,而貴陽(yáng)和銅仁污水廠污泥中重金屬含量差異較大。

表5 重金屬地累積指數(shù)與污染程度分級(jí)
在互聯(lián)網(wǎng)社會(huì),其最突出的特點(diǎn)就是整合了產(chǎn)業(yè)鏈的各種特色。以運(yùn)營(yíng)商為中心,產(chǎn)業(yè)鏈中的每一個(gè)廠商都有屬于自己的業(yè)務(wù),同時(shí)也在向上游、下游延伸和滲透,每個(gè)廠商的定位越來(lái)越模糊。而諾基亞卻沒(méi)能夠抓住這一點(diǎn),其沒(méi)有主動(dòng)與產(chǎn)業(yè)鏈中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主動(dòng)合作,也就沒(méi)能形成自己的影響力。

表6 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重金屬含量 mg/kg
注:同列數(shù)據(jù)中的不同的字母表示有顯著差異(p<0.05),下同。
《城鎮(zhèn)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biāo)準(zhǔn)》(GB18918-2002)規(guī)定了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控制限值,由表6可知,本研究中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中平均Pb、Ni、Mn和Cd含量超出了限值范圍內(nèi),基本不符合污泥排放標(biāo)準(zhǔn),其他重金屬均符合污泥排放標(biāo)準(zhǔn);對(duì)于不同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泥中金屬污染而言,貴陽(yáng)和銅仁污水處理廠污泥中Cr、Cu均有超標(biāo),而貴州省各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泥平均Mn含量均嚴(yán)重超標(biāo),屬于重度污染;遵義、貴陽(yáng)、銅仁、興義和六盤(pán)水Pb含量超標(biāo);除了凱里和遵義,貴州省其他城市Cd含量均超標(biāo),貴州省各城市As和Zn含量均未超標(biāo)。
2.2 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理化性質(zhì)
依據(jù)《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泥檢驗(yàn)方法》(CJ/T221-2005)測(cè)定pH,w(有機(jī)質(zhì)),w(全氮)、w(全磷)和w(全鉀),貴州省不同城市污水處理廠脫水污泥的理化性質(zhì)和營(yíng)養(yǎng)成分含量見(jiàn)表7,由表可知,貴州省污水廠污泥pH值范圍是5.3~6.3(均值5.8),略顯酸性,符合《城鎮(zhèn)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置農(nóng)用泥質(zhì)》(CJ/T309-2009)要求,污泥中有機(jī)質(zhì)和全氮含量符合《城鎮(zhèn)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置農(nóng)用泥質(zhì)》(CJ/T309-2009),全磷和全鉀含量略低于全國(guó)水平,其污泥呈現(xiàn)高有機(jī)質(zhì)、高氮的特點(diǎn),具備良好的農(nóng)業(yè)和土壤改良的潛在利用前景。
相關(guān)分析可知(表8),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中pH與重金屬均呈相關(guān);有機(jī)質(zhì)含量與Cu、Ni、Pb和Zn呈極顯著正相關(guān)(p<0.01),與Cr、Mn和As呈顯著正相關(guān)(p<0.05);全磷與Ni呈顯著的正相關(guān)(p<0.01),與其他各重金屬含量均沒(méi)有一定的相關(guān)性(p>0.05);全鉀與Cr和Ni呈顯著正相關(guān)(p<0.05);由此可知有機(jī)質(zhì)是影響這些重金屬含量的主要因素,而有機(jī)質(zhì)的這種特性并非適用于所有的重金屬,主要是由于不同的重金屬的化學(xué)性質(zhì)有差異,往往對(duì)其所結(jié)合的位點(diǎn)具有一定的選擇性,即只與其化學(xué)性質(zhì)相匹配的位點(diǎn)相結(jié)合,受此影響,某些重金屬元素與總有機(jī)質(zhì)在分布特征上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聯(lián)系。通過(guò)以上分析說(shuō)明,有機(jī)質(zhì)含量是決定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重金屬元素分布的主要因素。

表7 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理化性質(zhì)

表8 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重金屬與污泥理化性質(zhì)之間的關(guān)系
注:“**”相關(guān)性在0.01水平上顯著(雙尾);“*”相關(guān)性在0.05水平上顯著(雙尾)。
2.3 貴州省城市污泥中重金屬的形態(tài)分布
重金屬的生物毒性不僅與其總量有關(guān),更大程度上由其形態(tài)分布所決定,不同的形態(tài)產(chǎn)生不同的環(huán)境效應(yīng),直接影響到重金屬的毒性、遷移及在自然界的循環(huán)[17]。因此,研究重金屬的形態(tài)分布可提供更為詳細(xì)的重金屬元素遷移性和生物可利用性的信息。根據(jù)歐共體參比司提出的三態(tài)連續(xù)提取法,可將重金屬劃分為酸可提取態(tài)、可還原態(tài)、可氧化態(tài)和殘余態(tài)[18]。其中,酸可提取態(tài)相當(dāng)于交換態(tài)和碳酸鹽結(jié)合態(tài)的總和,這些組分與土壤結(jié)合較弱,具最大的可移動(dòng)性和生物有效性,在酸性條件下易釋放。可還原態(tài)重金屬一般以較強(qiáng)的結(jié)合力吸附在土壤中的鐵錳氧化物上,在還原條件下較易釋放。可氧化態(tài)重金屬主要是有機(jī)物和硫化物結(jié)合的重金屬,這部分重金屬在有機(jī)物被氧化時(shí)有被溶出的風(fēng)險(xiǎn)。殘余態(tài)一般稱為非有效態(tài),因?yàn)檫@部分重金屬在自然條件下,不易釋放出來(lái)[17,19]。本研究采用修正的BCR連續(xù)提取法提取8種污泥中重金屬的形態(tài)(水溶態(tài)T1、酸溶可交換態(tài)T2、可還原態(tài)T3、可氧化態(tài)T4和殘?jiān)鼞B(tài)T5)。其中,T1與T2之和用于評(píng)估污泥中重金屬的遷移性,T1、T2、T3之和用于評(píng)估污泥中重金屬的生物有效性,由于污泥進(jìn)入土壤環(huán)境后,污泥中有機(jī)物會(huì)隨環(huán)境條件變化而轉(zhuǎn)化,與有機(jī)物相結(jié)合的重金屬會(huì)被釋放出來(lái),因此,在評(píng)估污泥中重金屬在環(huán)境中的生態(tài)風(fēng)險(xiǎn)時(shí)除前3種形態(tài)含量外還需考慮T4的含量,T5只有在極端環(huán)境條件下才會(huì)被釋放出來(lái),在自然條件下,T5被認(rèn)為是對(duì)環(huán)境無(wú)污染風(fēng)險(xiǎn)。

圖1 貴州省城市污泥中重金屬的形態(tài)分布
各污泥中重金屬5種形態(tài)百分含量如圖1所示,由圖1可知,貴州省污泥樣品中Cu和Cr主要以酸溶可交換態(tài)形式存在,顯示出污泥中Cu和Cr對(duì)環(huán)境的風(fēng)險(xiǎn)具有一定的累積效應(yīng);Pb和Cd主要以水溶態(tài)形式存在,表明Pb和Cd主要以與污泥中水溶性有機(jī)物結(jié)合形式存在;As和Zn則主要是以可氧化態(tài)和可還原態(tài)存在,表現(xiàn)較高的潛在移動(dòng)性和生物可利用性,極大威脅著土壤環(huán)境的生態(tài)安全;Ni較均勻地分布于5種形態(tài)中,表明污泥中Ni的富集受到了污泥吸附、吸收、有機(jī)物螯合和結(jié)晶化合物固定等物理化學(xué)作用,由于各污泥中Ni前4種形態(tài)(水溶態(tài)T1、酸溶可交換態(tài)T2、可還原態(tài)T3、可氧化態(tài)T4)含量比例均低于80%,且其總量略與土壤背景值相當(dāng),因此,Ni在土壤環(huán)境中生態(tài)風(fēng)險(xiǎn)較Cu、Cr、Zn低。污泥中水溶態(tài)(自由離子態(tài)、水溶性有機(jī)物結(jié)合態(tài))重金屬離子被認(rèn)為對(duì)土壤環(huán)境中植物危害性最大且易污染地表水。圖1中還顯示,Zn和Ni的水溶態(tài)差異較大,表明各污泥對(duì)Zn和Ni吸附吸收作用差異較大;Cr的水溶態(tài)較低,表明Cr主要以非水溶性化合物形式存在;Cd有部分殘余態(tài),但其酸可提取態(tài)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要注意在其在酸性條件下的釋放。綜上所述,貴州省污泥中重金屬的不穩(wěn)定態(tài)所占比例較高,主要是由于生化污泥由微生物絮體構(gòu)成,具有較大比表面積,有利于重金屬離子的表面弱吸附,這些弱吸附態(tài)的金屬離子易于重新釋放到水溶液中,從而導(dǎo)致生化污泥中重金屬的活性高于其他污泥[20]。因此,建議貴州省污泥采用相關(guān)的消化處理以降低污泥中重金屬的生物活性,進(jìn)一步提高污泥土地利用的價(jià)值。
重金屬的生物活性系數(shù)是易利用態(tài)與總量之間的比率,反映不同重金屬被生物利用,進(jìn)而對(duì)環(huán)境構(gòu)成潛在危害的能力[21,22]。由圖1可知,貴州省污泥中5種重金屬生物活性系數(shù)大小依次為Ni>Cu>Mn>Cr>As>Zn>Cd>Pb,表明Cu、Ni在污泥中表現(xiàn)出相對(duì)較高的不穩(wěn)定性和可利用性,而作為兩種毒性較強(qiáng)的重金屬Pb、Cd在污泥中穩(wěn)定性好,生物可利用性低,這是因?yàn)橘F州省污泥經(jīng)厭氧消化后污泥中所含的硫酸鹽等含硫化物可被硫酸鹽還原菌轉(zhuǎn)化成S2-,可促進(jìn)重金屬由不穩(wěn)定態(tài)向硫化物穩(wěn)定態(tài)的形式轉(zhuǎn)化,使污泥中重金屬的穩(wěn)定性提高。此外,Mn和Cr也表現(xiàn)出較高的生物活性,其潛在的遷移性和植物毒性在污泥利用時(shí)應(yīng)給予關(guān)注。
2.4 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重金屬污染程度分析
由表9可知,各污泥對(duì)應(yīng)的內(nèi)梅羅綜合指數(shù)可以看出,貴州省污水廠污泥中重金屬總體上對(duì)環(huán)境存在嚴(yán)重的潛在生態(tài)風(fēng)險(xiǎn),由于內(nèi)梅羅指數(shù)不僅考慮到各種影響參數(shù)的平均污染狀況,而且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污染最嚴(yán)重的因子,同時(shí)在加權(quán)過(guò)程中避免了權(quán)系數(shù)中主觀因素的影響,克服了平均值法各種污染物分擔(dān)的缺陷,能較好反映污泥總體上的潛在生態(tài)風(fēng)險(xiǎn)[2,3,23]。從整個(gè)調(diào)查區(qū)域范圍來(lái)看,重金屬Cr、Ni、As單因子污染系數(shù)均值均小于1,屬于低污染水平;污染系數(shù)均值由大到小依次為Cd>Pb>Cu>Mn>Zn>Cr>Ni>As,由此可知,Cd、Pb和Cu是整個(gè)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中最主要的環(huán)境污染因子;從綜合污染指數(shù)來(lái)看,貴州省各城市污泥均達(dá)到重度污染。

表9 污泥中重金屬污染單因子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
2.5 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重金屬潛在生態(tài)風(fēng)險(xiǎn)評(píng)價(jià)
經(jīng)計(jì)算可知,貴州省污水廠污泥中重金屬的潛在生態(tài)危害指數(shù)(Ei)與復(fù)合生態(tài)危害指數(shù)(RI)如表10所示。由表可知,貴州省各城市污水廠污泥中重金屬危害指數(shù)(Ei)基本表現(xiàn)為:Cd>Pb>As>Ni>Mn>Zn>Cu>Cr,其中毒害性最強(qiáng)的是Cd,其最大危害指數(shù)為135.2(銅仁污水廠污泥),處于重危害范圍(80
2.6 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地累積指數(shù)評(píng)價(jià)
貴州省污水處理廠地累積指數(shù)(Igeo)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見(jiàn)表11,由表可知,貴州省各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泥Cu和Zn污染均較輕,均表現(xiàn)為輕度污染,說(shuō)明貴州省污水處理廠Cu和Zn污染受黏質(zhì)沉積巖中該元素的地球化學(xué)背景值影響較小,主要是人類活動(dòng)造成,而其他重金屬的地累積指數(shù)較高,各城市之間的地累積指數(shù)差異較大,其中以銅仁和貴陽(yáng)重金屬地累積指數(shù)較高,污染程度較高,而其他城市地累積指數(shù)相對(duì)較低。從均值來(lái)看,Cu、Ni、As和Zn屬于輕度污染,Cr和Mn屬于中度污染,Pb和Cd屬于重度污染。因此,從整體的分析來(lái)看,貴州省以銅仁和貴陽(yáng)市污染程度較高,這2個(gè)城市污泥可利用性較低,而其他城市均表現(xiàn)出Pb和Cd的重度污染,對(duì)于污泥的農(nóng)用生產(chǎn)來(lái)說(shuō),仍需要進(jìn)行一定的“脫毒”處理。

表10 污泥中重金屬潛在污染評(píng)價(jià)

表11 污泥中重金屬地累積指數(shù)及分級(jí)
3 結(jié) 語(yǔ)
(1)貴州省污水廠污泥呈現(xiàn)高有機(jī)質(zhì)、高氮的特點(diǎn),具有較好的土地利用價(jià)值。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中8種重金屬元素平均含量的大小順序?yàn)镸n>Cu>Zn>Pb>Cr>Ni>As> Cd,其中Mn和Cu占重金屬總量比例最高,Cd占重金屬總量比例最小。
(2)相關(guān)分析可知,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中pH與重金屬均呈相關(guān),有機(jī)質(zhì)含量與各重金屬含量均呈顯著或極顯著正相關(guān),由此表明有機(jī)質(zhì)含量是決定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重金屬元素分布的主要因素。
(3)貴州省污水廠污泥Cu和Cr主要以酸溶可交換態(tài)形式存在;Pb和Cd主要以水溶態(tài)形式存在,Pb和Cd主要以與污泥中水溶性有機(jī)物結(jié)合形式存在;As和Zn則主要是以可氧化態(tài)和可還原態(tài)存在,表現(xiàn)較高的潛在的移動(dòng)性和生物可利用性,極大地威脅著土壤環(huán)境的生態(tài)安全;Ni較均勻地分布于5種形態(tài)中。貴州省污泥中5種重金屬生物活性系數(shù)大小依次為Ni>Cu>Mn>Cr>As>Zn>Cd>Pb。
(4)內(nèi)梅羅綜合指數(shù)分析表明,貴州省各城市污水廠污泥中重金屬Cr、Ni、As單因子污染系數(shù)平均值均小于1,屬于低污染水平;污染系數(shù)均值由大到小依次為Cd>Pb>Cu>Mn>Zn>Cr>Ni>As,Cd、Pb和Cu是貴州省污水處理廠污泥中最主要的環(huán)境污染因子。
(5)Hakanson生態(tài)風(fēng)險(xiǎn)評(píng)估,貴州省各城市污水廠污泥中重金屬危害指數(shù)(Ei)基本表現(xiàn)為:Cd>Pb>As>Ni>Mn>Zn>Cu>Cr,其中毒害性最強(qiáng)的是Cd,其最大危害指數(shù)為135.2(銅仁污水廠污泥),處于重危害范圍(80
(6)貴州省各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泥Cu和Zn地累積指數(shù)(Igeo)較低,表現(xiàn)為輕度污染,而其他重金屬的地累積指數(shù)較高,各城市之間的地累積指數(shù)差異較大,綜合來(lái)看,以銅仁和貴陽(yáng)重金屬地累積指數(shù)較高,污染程度較高,而其他城市地累積指數(shù)相對(duì)較低。從均值來(lái)看,Cu、Ni、As和Zn屬于輕度污染,Cr和Mn屬于中度污染,Pb和Cd屬于重度污染,對(duì)于污泥的農(nóng)用生產(chǎn)和利用來(lái)說(shuō),仍需要進(jìn)行一定的“脫毒”處理。
□
[1] Wang C, Hu X, Chen M L, et al. Total concentrations and fractions of Cd, Cr, Pb, Cu, Ni and Zn in sewage sludge from municipal and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05,119(1):245-249.
[2] Alvarez E A, Mochón M C, Sánchez J C J, et al. Heavy metal extractable forms in sludge from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J]. Chemosphere, 2002,47(7):765-775.
[3] 楊凌波, 曾思育, 鞠宇平, 等. 我國(guó)城市污水處理廠能耗規(guī)律的統(tǒng)計(jì)分析與定量識(shí)別[J]. 給水排水, 2008,34(10):42-45.
[4] 余 杰, 田寧寧, 王凱軍, 等. 中國(guó)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理, 處置問(wèn)題探討分析[J]. 環(huán)境工程學(xué)報(bào), 2007,1(1):82-86.
[5] 王 琳, 楊魯豫. 我國(guó)城市污水處理的有效措施[J]. 城市環(huán)境與城市生態(tài), 2001,14(1):50-52.
[6] 翟云波, 魏先勛, 曾光明, 等. 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泥資源化利用途徑探討[J]. 工業(yè)水處理, 2004,24(2):8-11.
[7] 鄭翔翔, 崔春紅, 周立祥, 等. 江蘇省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泥重金屬含量與形態(tài)研究[J]. 農(nóng)業(yè)環(huán)境科學(xué)學(xué)報(bào), 2007,26(5):1 982-1 987.
[8] 陳同斌, 黃啟飛, 高 定, 等. 中國(guó)城市污泥的重金屬含量及其變化趨勢(shì)[J]. 環(huán)境科學(xué)學(xué)報(bào), 2003,23(5):561-569.
[9] 姚金玲, 王海燕, 于云江, 等. 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泥重金屬污染狀況及特征[J]. 環(huán)境科學(xué)研究, 2010,23(6):15-22.
[10] 鮑士旦. 土壤農(nóng)化分析[M]. 北京: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出版社, 2000.
[11] 余秀娟, 霍守亮, 昝逢宇, 等. 巢湖表層沉積物中重金屬的分布特征及其污染評(píng)價(jià)[J]. 環(huán)境工程學(xué)報(bào), 2013,7(2):439-450.
[12] 邴海健, 吳艷宏, 劉恩峰, 等. 長(zhǎng)江中下游不同湖泊沉積物中重金屬污染物的累積及其潛在生態(tài)風(fēng)險(xiǎn)評(píng)價(jià)[J]. 湖泊科學(xué), 2010,22(5):675-683.
[13] Arain M B, Kazi T G, Jamali M K, et al. Speci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ediment by conventional, ultrasound and microwave assisted single extraction methods: a comparison with modified sequential extraction procedure[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08,154(1):998-1 006.
[14] 馮素萍, 劉慎坦, 杜 偉, 等. 利用 BCR 改進(jìn)法和 Tessier 修正法提取不同類型土壤中 Cu, Zn, Fe, Mn 的對(duì)比研究[J]. 分析測(cè)試學(xué)報(bào), 2009,28(3):297-300.
[15] Zhang W, Feng H, Chang J, et al.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Yangtze River intertidal zone: an assessment from different indexes[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9,157(5):1 533-1 543.
[16] Hakanson L. An ecological risk index for aquatic pollution control. A sedimentological approach[J]. Water research, 1980,14(8):975-1 001.
[17] 韓春梅, 王林山, 鞏宗強(qiáng), 等. 土壤中重金屬形態(tài)分析及其環(huán)境學(xué)意義[J]. 生態(tài)學(xué)雜志, 2005,24(12):1 499-1 502.
[18] 劉 清, 王子健, 湯鴻霄. 重金屬形態(tài)與生物毒性及生物有效性關(guān)系的研究進(jìn)展[J]. 環(huán)境科學(xué), 1996,17(1):89-92.
[19] 馮慕華, 龍江平, 喻 龍, 等. 遼東灣東部淺水區(qū)沉積物中重金屬潛在生態(tài)評(píng)價(jià)[J]. 海洋科學(xué), 2003,27(3):52-56.
[20] 周立祥, 沈其榮, 陳同斌, 等. 重金屬及養(yǎng)分元素在城市污泥主要組分中的分配及其化學(xué)形態(tài)[J]. 環(huán)境科學(xué)學(xué)報(bào), 2000,20(3):269-274.
[21] 郭觀林, 周啟星. 污染黑土中重金屬的形態(tài)分布與生物活性研究[J]. 環(huán)境化學(xué), 2005,24(4):383-388.
[22] 雷 鳴, 廖柏寒, 秦普豐, 等. 礦區(qū)污染土壤 Pb, Cd, Cu 和 Zn 的形態(tài)分布及其生物活性的研究[J]. 生態(tài)環(huán)境, 2007,16(3):807-811.
[23] 郭 平, 謝忠雷, 李 軍, 等. 長(zhǎng)春市土壤重金屬污染特征及其潛在生態(tài)風(fēng)險(xiǎn)評(píng)價(jià)[J]. 地理科學(xué), 2005,25(1):10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