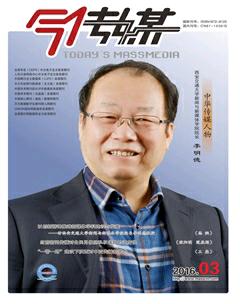戴錦華對當代中國電影女性形象的解讀
郭維易
(山西大學 文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
戴錦華對當代中國電影女性形象的解讀
郭維易
(山西大學 文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在完成了對女性的精神解放、消除了肉體奴役的同時,所謂的“女性”也就成了文化中的一種子虛烏有,這也使得她們作為一個性別的群體亦是悄然失落于文化的視域當中了。對于這樣的現象,戴錦華將其命名為當代女性面臨著的“花木蘭式的境遇”,當她們終于獲得了分享話語權利的時候,卻失去了她們的性別話語身份;在她們真實的參與歷史的同時,她們的女性主體身份卻也不得不消失在一個非性別化的假面之后。
關鍵詞:女性形象;電影批評;跨學科
一、引 言
作為一名在電影批評、女性寫作研究和大眾傳媒文化研究領域均有建樹的學者,戴錦華在國內外一直有著超高的人氣。她還曾是新時期中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的先驅和推動者,有著“中國蘇珊·桑塔格”的美譽。她以自己獨有的智慧與鋒芒成為學界“傳奇”。
雖然在上述三個領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績,但戴錦華始終堅持認為電影才是她“真正”的專業,稱自己只是一個電影研究者。不過事實也的確如此,無論之后的女性主義文學研究還是大眾文化研究,戴錦華始終堅持以電影作為自己研究的窗口,從中探尋著社會文化的發展脈絡與軌跡。1982年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戴錦華被分配到北京電影學院任教,從此開始她的學術生涯。在之后的幾年里,她直接參與組建了中國第一個電影理論專業,填補了中國電影理論的學科空白,并且積極參加西方電影學術培訓班,嘗試翻譯電影理論專著,正是因為這樣的治學態度和學術經歷,使得戴錦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她以開闊的中西文化比較視野,將西方電影理論快速地引入了中國的電影研究領域,極大地拓展了當時中國電影理論狹窄的研究視域[1]。戴錦華如今已出版了多部電影理論專著,包括:《電影理論與批評手冊》《鏡與世俗神話—影片精讀18例》《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等,她將自己極富才情的文字表達,自然流暢地貫注于電影文本,并且還以敏捷靈便的思維在多種文化角度中自如地行走。但是戴錦華對電影批評的研究腳步卻沒有停留在文本細讀的階段,從最初側重于文本解讀,運用經典影片挑戰西方理論,再到之后漸次明晰了的女性主義立場和大眾文化批評的方法,戴錦華始終不斷的開闊、融通自己的研究領域[2]。女性主義是戴錦華在電影批評的過程中逐漸明了并堅持的基本立場和研究方法,她認為電影將“性別角色與男性的欲望結構深刻的內在于影片的敘事機制”[3]。對于電影這個行業,時至今日也不得不承認它依舊是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行業,那么對于這些“攝影機里的女人”,在男權為上的行業規則下,不同時代的導演們究竟會賦予她們哪些不同的特質?戴錦華也在她的電影批評中進行了深刻的論述。
二、第三代:消解于無形之中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推行了一系列婦女解放措施,“女人能頂半邊天”“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一樣能做到”“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這樣的口號深深的根植于一代人的心中。在這樣的潮流之下,當女性作為被解放的群體,不再需要輾轉、緘默于男人為她們制定的規范之下時,男人的規范也就成了當時社會文化中的唯一規范。在完成了對女性的精神解放、消除了肉體奴役的同時,所謂的“女性”也就成了文化中的一種子虛烏有,這也使得她們作為一個性別的群體亦是悄然失落于文化的視域當中了。對于這樣的現象,戴錦華將其命名為當代女性面臨著的“花木蘭式的境遇”,當她們終于獲得了分享話語權利的時候,卻失去了她們的性別話語身份;在她們真實的參與歷史的同時,她們的女性主體身份卻也不得不消失在一個非性別化的假面之后[4]。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登上藝術舞臺的中國第三代導演,正是在這種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差異與對立被取消的文化語境中,將自己電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無形地消解了。在第三代導演的電影中,男性與女性沒有了階級的差異,也沒有了個人化的情感,他們都是在黨的光輝下照耀的兒女,只有親密無間的革命友誼,在這樣的政治象征化的經典革命敘事中,女性在傳統被壓制、受迫害的形象被延續,但是在敘事過程中女性的命運開始被拯救并得到翻身,最終成長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這類女性形象的電影包括水華導演的《白毛女》和謝晉導演的《紅色娘子軍》等,她們在國民黨代表的黑暗社會中受到凌虐,并最終被共產黨代表的光明所拯救,如果說在這之前她們還擁有精神上的“女性性別”,那么來到新時期之后,她們卻被融化在一個巨大的革命隊伍中,成為一個和男性一樣的得到解放和新生活的“人”。
三、第四代:溫情脈脈的控訴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也成為第四代和第五代導演揮之不去的夢魘記憶,但對當時處在不同年齡階段的他們造成的影響卻是不盡相同的,因此戴錦華也對第四代、第五代導演作品中塑造的不同的女性形象進行了批評論述。第四代導演對于中國電影的最大意義在于他們完成了電影政治工具論的藝術突破,他們自覺地打破了高揚革命斗爭精神的電影模式,將自己強烈的情感表達熔鑄于電影作品中,每個人的電影都打上了強烈的個人烙印,但他們只是以哀婉憂怨的情緒低沉地進行控訴與抗議,最終也只是成就了一些大時代的小故事,畢竟他們曾深陷其中,帶著切身的創傷和體驗。在《都市里的村莊》《老井》《湘女蕭蕭》等電影中,女性成為了歷史政治的剝奪與男性心中內在匱乏的泛指,她們是第四代導演心中“斷念式的美好愛情中的那些再也看不到的幻影”,時代的洪流裹挾著第四代導演生命的無可奈何,于是在那些或柏拉圖或烏托邦的愛情故事中,心中的寄寓代替了欲望的味道,女性再度被物化,她們成了愚昧的犧牲品,文明的祭品,而在楊延晉的《小街》中,敘鏡中的女性甚至不曾被指認,戴錦華將之命名為“不可見的女性”。此時此刻“女性”不得不淪落成了第四代導演被政治暴力所阻斷的青春夢旅和心中解不開的死結,她們既是美麗的女神,更是神圣的祭品[5]。總體而言,第四代電影導演的作品帶著一股人道主義的溫情,對人性、理解和良知的低訴,來慰藉或解脫歷史苦難的負重。
四、第五代:暴力反抗下的中西融合
第五代導演則完全不同,他們眼中的父輩早已被時代抹去了英雄的至高無上感,呈現出的只是一副“臣服的姿態”。戴錦華將中國的第五代導演稱作“無父的子一代”,他們不滿足于第四代導演的“憂傷與纖弱”的情感表達,在狂野的反叛與無奈的臣服中填補自己的電影,呈現出了父輩的想象以及對女性的臆想。當第五代導演無奈的發現他們作為天之驕子的時代匆忙墜落,盡管還沒有如同上一輩那樣心甘情愿的臣服,卻也早已不再有壯志滿懷的奮斗之心。正是在這樣的失敗感和挫敗感之下,第五代導演選擇了對現實的逃避,去遺忘那和第四代一樣充滿缺憾的青春,卻張開雙臂接受了外來文化的沖擊,并積極與之碰撞。他們自然的接受了歐美電影中的女性塑造方式,女性在男人的欲望中、視域中再次浮現,他們以女性再次進入電影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禮。在第五代導演的作品中,女性甚至可以成為絕對的主角,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男性在視覺上是缺席的,女人們在逃不出的四方天地中爭風吃醋,妻妾們的斗爭暗喻了中國的權利爭斗,負荷了第五代導演對中國歷史的深沉反思。然而戴錦華同時指出,在第五代導演的作品中,女人即是欲望的表征,更是被操縱的對象。他們出現在男人的眼光中,失去了自身的主體意識,她們的身體和命運都操縱在男人的手中[6]。在《紅高粱》中,“我奶奶”九兒一直價值客體存在,影片從未對九兒的主觀意愿進行渲染和突出,導演對她的正面大特寫鏡頭和局部小特寫鏡頭,在戴錦華的眼中就如同“欲望的目光穩定而貪婪的框定了這張女人的面孔。”此時的女性依舊無法逃離被動的命運,她們是人也非“人”,最終也依舊是成為了歷史的祭品。
然而或許也是因為涉及領域的廣博,使得戴錦華在學界始終存在著“難以界說”的身份認定,甚至被一些人視作“越軌”。因為她的研究內容包括了文學和電影的批評理論、社會學、歷史學,甚至政治學、人文美學等多重領域,但與其將其視作是一種學科的越界或越軌,倒不如說是一種全新的拓展。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戴錦華早已擺脫了社會文化權利機制對其的牽引,她在宏觀的歷史語境與微觀的文本細讀之間不斷探索,尋求全新的結合點,進而對一系列看似復雜無序的文化現象做出合理的、具象的分析與描述。戴錦華正是在這樣宏大的跨學科視野中,專注于對整個社會文化的話語結構分析,甚至從更深的理論層面上說,她在不斷完善著人文學科的社會研究功能[7]。正因如此,戴錦華將自己的學術研究稱之為一間“沒有屋頂的房間”,也正是在這樣一間可以仰望浩瀚宇宙蒼穹的房間之中,她將自己深厚的西方理論素養,精湛的文本細讀功底,以及廣闊的文化史、美學史視野,貫注于對電影批評、女性文化研究和大眾傳媒文化研究領域的深入發掘,在重重鏡像中一次次突圍,勾勒出了一副明顯的且獨屬于戴錦華特色的文化地圖。
參考文獻:
[1]岳秀芳.戴錦華眼中的第五代導演[J].電影文學,2008(5).
[2]賀桂梅.沒有屋頂的房間——讀解戴錦華[J].南方文壇,2000(5).
[3]鄒贊.戴錦華的文藝思想疏略[J].新疆大學學報,2001(2).
[4]戴錦華.不可見的女性——當代中國電影中的女性與女性的電影[J].當代電影,1994(6).
[5]陳林俠.一本書與一種表達方式——評戴錦華《電影理論與批評手冊》[J].文藝研究,2011(1).
[責任編輯:傳馨]
作者簡介:郭維易,女,山西大學文學院藝術學理論專業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藝術理論與文化藝術學研究。
收稿日期:2016-03-07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3-007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