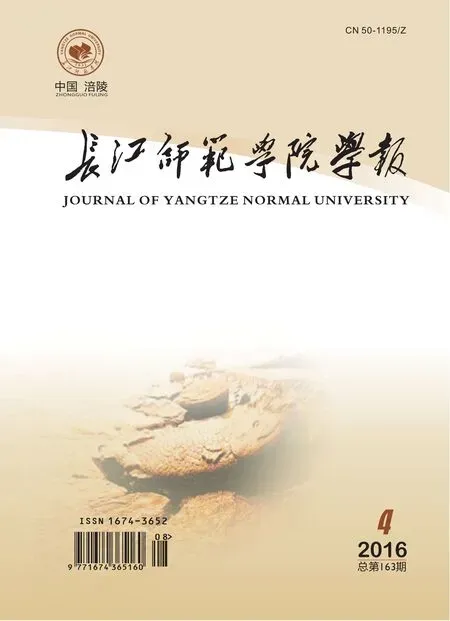散雜居蒙古族研究的拓荒之作
——評王希輝新著《從馬背到牛背:散雜居蒙古族社會與文化變遷》
向瑞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100081)
□品書錄
散雜居蒙古族研究的拓荒之作
——評王希輝新著《從馬背到牛背:散雜居蒙古族社會與文化變遷》
向瑞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100081)
一、序言
在眾多歷史悠久、積淀深厚的老牌學科中,作為西方 “舶來品”的文化人類學,無論在學科 “年齡”上,還是在自身 “體格”上,都是一門既年輕又薄弱的新興學科。這門新興學科根基于田野調查、民族志、理論建構3個方面,它們就像文化人類學的 “三駕馬車”組成的穩固模式,互相掣動,互相支撐,互相促進,缺一不可。要想穩坐馬鞍,在 “三駕馬車”前的駕駛位上縱意神游、舞鞭馳騁,談何容易?除有博聞強記的知識儲備、靈活自如的方法運用、開闊創新的思維視野之外,還應具備非同一般的勇氣與毅力。
王希輝博士的新作 《從馬背到牛背:散雜居蒙古族社會與文化變遷——以重慶彭水向家壩村為考察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以下簡稱 《散雜居蒙古族社會與文化變遷研究》),淋漓盡致地顯示出了作者駕馭文化人類學 “三駕馬車”的實力和魄力。該書既有扎扎實實的田野調查、第一手資料,又有散雜居蒙古族多方位全景式、深入厚重的民族志撰寫,還有基于前兩者之上的,對 “文化固守”理論的初步建構與闡釋。該書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武陵山區散雜居民族的生態適應與文化傳承研究”及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 “散雜居民族的文化變遷與文化固守——重慶蒙古族的個案研究”的成果之一,同時也是湖北省民宗委民族文化研究項目 “武陵山散雜居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與對策研究”的研究成果。
《散雜居蒙古族社會與文化變遷研究》是由作者的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幾經修改而成,正文除導言、結論外,共9章28節,文末附有附錄、后記,洋洋灑灑32萬余字。作者在多次調研、反復思考、總結論證的基礎上完成了這本著作。作者以深入淺出、精雕細琢的筆鋒,展示了在國家權力、社會環境、文化語境影響下,重慶彭水向家壩蒙古族的社會文化變遷與文化固守,對族群認同的內在結構、文化變遷的原因進行深層透視,并以極具探索創新的精神嘗試構建 “文化固守”理論。王希輝以深厚的學術功底、獨特的理論創新視野、詳實的田野調查資料、高超的寫作技巧和語言鑄成了這部散雜居蒙古族研究的拓荒之作。
二、主題拓展:重慶蒙古族文化變遷歷程的勾勒與探索
我國少數民族具有復雜性和獨特性,在學術研究中不能以偏概全、概而論之。高山河流、丘陵平原、草場黃坡,少數民族地理空間和生態環境的殊異性,塑造了經濟文化類型各不相同的采集漁獵型、草原游牧型、農耕型等少數民族特點;歷史上主流民族軍事統治或文教懷柔政策形塑了與主流民族交往密切型、疏離型的少數民族;各少數民族自身獨特的文化性格造就了有語言有文字、有語言無文字、無語言無文字等民族……由于我國少數民族的復雜性與獨特性,從類型學角度對各少數民族進行細致、科學的分類,是尤為必要的。
從民族分布的維度看,我國少數民族的分布總體呈現大雜居、小聚居的格局,少數民族相應分為聚居區和散雜居少數民族兩類。聚居區民族占地面積廣闊、族際交往頻繁、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也易于民族語言和文化的保存。散雜居民族作為 “非主流”民族夾雜在居住地主流民族之間,人口較少、占地面積小、輻射范圍弱、地理位置偏。在學術研究過程中,散雜居民族的研究成果遠遠少于聚居區民族。深度詳解的學術專著,除張海洋的 《散雜居民族調查:現狀與需求》、雷振揚的 《散雜居民族問題研究》、許憲隆的 《散雜居民族概論》外,鮮有其他。而且我國散雜居民族眾多,以自治形態為維度分類,可分為沒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已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但不在自治地方居住的、居住在自治地方又是非自治民族的3種形態;以族別為維度分類,有散雜居回族、苗族、瑤族、彝族、哈薩克族、塔吉克族等;無論從哪個維度看,目前對重慶蒙古族的研究都非常少,只有榮盛 《烏江河畔的蒙古族 (上、下)》、趙開國 《血淚凝詩句,僻壤隱天驕——對彭水蒙古族的調查》幾篇學術論文。甚至,散雜居民族的研究主題多集中于民族格局形成史、族群關系、民族文化保護等方面,以民族志的視角展現散雜居民族社會文化變遷全貌的研究還未有之。因此,該書對居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的散雜居蒙古族——這座 “文化孤島”新探索,可謂是散雜居蒙古族研究的開山拓荒之作。
作者一直致力于散雜居蒙古族的研究,《散雜居蒙古族社會與文化變遷研究》是他多年積累、辛勤耕耘、嘔心瀝血的集成。作為一個 “異鄉人”和 “他者”(作者是湖北恩施的土家族),他以嚴謹的治學精神、果敢的勇氣與態度走進了重慶彭水向家壩的蒙古族社區,以之為樣本,在長期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牢牢緊抓文化變遷和文化固守的主題,全面展示了重慶蒙古族文化的 “變”與 “守”。首先,以 “變”為中心,作者對移入蒙古族從 “馬背”到 “牛背”的 “本土化”質變過程進行了宏觀勾勒。全書主體部分的第二、三、四、五、九章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為時間分界,分別從生計方式與經濟生活、宗族制度與村民自治、婚姻形式與家庭制度、教育與文化傳承、衣食住行之風俗等幾個方面,探究了這些文化事象在時間序列上的變遷歷程,并從文化生態學的角度剖析文化變遷的動力機制、內外原因。其次,圍繞 “守”的主題,探索重慶蒙古族在 “大傳統”和周邊民族文化影響下所激起的認同情感和 “文化自覺”。第六、七、八章著重探究了重慶蒙古族通過宗教信仰、民族歷史傳說、重修族譜、保留碑刻和遺跡以強化民族集體記憶與民族邊界,維系民族認同情感的 “文化固守”行為。最后,結論部分由現象感知上升為理性思考,對 “文化固守”理論進行了更為深入獨到的闡釋。重慶蒙古族社會文化變遷全面而系統的探索,既彌補了散雜居蒙古族研究成果不足的缺憾,促進散雜居民族理論和體系的建構,對烏江流域、武陵山沿線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
三、史志縱橫:多方位全景式的民族志撰寫與細描
民族志既是一種研究手段,也是一種文本寫作形式。“馬林諾夫斯基革命”后,現存的社會文化的田野調查方法被有機地融入到民族志中,因之,民族志不再是傳教士、商人帶回來的檔案、報告、資料,也不再是 “書齋人類學家”充斥著主觀臆斷的、對二手文獻的 “再研究”,而是強調科學性、客觀性、規范性的學術范式。當然,民族志的理論方法決不是獨一無二的,更不是一成不變的。當代解釋人類學派的代表人物格爾茨,提出了民族志的詩意性、解釋性、主觀性。他對研究者的 “價值有涉”毫不在乎,反而認為應該用研究者對生活本質、場景故事的詩意的表達來拓寬文化的解釋空間,民族志的目的在于以 “深描”的研究方法闡釋文化事象的意義。撰寫民族志絕非易事,民族學家還被稱為人文社科學界的“瘋子”和 “搗蛋鬼”[1],早在馬林諾夫斯基的 《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出版時,民族志就不斷受到詰問和質疑,尤其是在主位與客位、宏觀與微觀、描述與解釋、要素與整體、主觀與客觀等多重問題的衡量取舍上。
在被視為經典民族志的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基于文化整體論與結構功能論的觀點提到了 “文化全貌觀”,認為民族志要用一系列的圖表記錄部落組織及其文化構成之全貌概觀,提供特殊敘事、典型說法、風俗項目、巫術模式等說明[2]。后來,有人批判馬林諾夫斯基的民族志范式對歷史避而不談,忽視和消解了研究對象的歷史,他筆下的土著人成為 “沒有歷史的人”[3]。為此,王希輝以其扎實的民族學、歷史學功底,在本書中采取了史志結合、縱橫交錯的呈現方式。既有全景式的民族志細描,又兼顧了縱深感的歷史維記述;既有共時性的橫向展演,又兼顧了歷時性的縱向梳理;既有來自田野的第一手資料,又兼顧了來自前人的文獻史料;既有廣度,又有深度;既有 “今”,又有 “古”,達到了史中有志、志中有史、史志交融的境界。
首先,全面厚重的民族志的記述。縱觀全文,作者以全景式的視野,多方位地選擇了散雜居蒙古族具有典型意義的文化樣態,通過對互相聯系、各自區別的文化要素的細致記述,來構筑整體文化變遷的概貌。以生計方式代表物質文化,以社會組織形式、家庭制度代表制度文化,以教育、宗教、喪葬和風俗習慣代表精神文化,每種文化的下位概念都有與之對應的文化特質。作者剝離了文化的形而上意義,賦予了文化飽滿、充實的內涵與生命。并且,對每種文化特質的描述不是浮光掠影、點到為止,而是由個案、訪談、問卷、圖表、數據、文字資料等編制而成的細致、詳盡而富有深度的闡釋網絡,以深刻展示各種文化特質的變遷。其次,精研苦思的歷史考釋。在變遷內容交互縱橫的呈現序列下,史料和田野調查資料交錯涌現,從彭水縣志、蒙古族社會歷史調查、民族志、蒙古族簡史、族譜、政府報告等文字資料,到村民口述史、墓碑、匾額、遺址、文化遺跡等非文字資料,史料引用數量之多、內容之全、涵蓋面之廣,完整還原與再現了多種文化特質的變遷史。并且作者秉承深度挖掘史料的理念,認為不應忽視 “口述史料”和族譜傳記作為 “主位”建構的歷史書寫行為。在這種理念指導下,他對重慶蒙古族溯本清源,將其族源追溯到蒙元時期蒙古族后裔甚至更遠的奇渥溫家族。憑借深厚的史學功底對鼻塞洞、象鼻塞碑、八角廟、揷 (插)刀洞遺址、《揷 (插)刀洞記》、清代墓碑、碑刻銘文、箭池、馬道子遺址等進行了精密細微地考釋,分析了史料之于社會結構、民族性格、族群關系、民族歷史研究的學術價值,不失為本書的一大特色和亮點。
四、創新視角:“文化固守”理論的初步建構與釋義
《散雜居蒙古族社會與文化變遷研究》既探討了 “文化變遷”這個 “老生常談”的問題,又以開拓創新的視角,另辟蹊徑,首次嘗試建構 “文化固守”理論,為文化人類學做出了理論性的探索。
“正如沒有哪個人會永遠不死一樣,也沒有哪種文化模式會永遠不變。”[4]作為一個涉及多學科的概念和理論,文化變遷是文化人類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研究者尤其關注的是文化變遷的原因、形式、內容、樣態、特質、影響等諸多的問題。任何時代都存在社會文化變遷,文化變遷的形式有傳播、文化喪失、涵化、發明等,究其原因,既有可能來自于族群、文化的外部接觸,也有可能來自于社會內部革新和自我調適[5]。《散雜居蒙古族社會文化變遷研究》從時間節點、內容方式、主要原因等方面分析每種文化特質的變遷情況,并著重探討文化變遷 “是什么”,即文化變遷之內容;和 “為什么”,即文化變遷之原因兩個問題。例如,就經濟生活而言,變遷內容有土地制度、產業結構、職業選擇、收入方式等,制度性因素是引起經濟生活變遷的主要原因,家庭聯產承包制是變遷的歷史分界點;就婚姻制度而言,變遷內容包括婚姻程序簡化、締結方式自主化、通婚范圍擴大化、擇偶觀念轉化、結婚年齡推遲、對離婚和再婚觀念開明化等,變遷的原因主要有自然生態環境的適應,及由經濟、政治、文化綜合作用的社會生態環境的改變。總體而言,散雜居蒙古族社會文化變遷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國家權力、民族交往、自然環境等外部力量。
實際上,文化變遷并不是在外部力量影響下的唯一表現。蘇軾曾言:“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任何事物在發展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變”與 “不變”兩種相生相往的自然狀態,變遷是 “拉力”,守住是 “回力”,兩種力量之間的制約和博弈才使文化具有 “張力”與 “彈性”。當變遷的結果不符合人們的預期需求和價值觀念時,抑或是外來文化的強大喚醒了對本民族文化的崇拜和眷戀時,社會集體意識中的 “固守勢力”便催生民族成員有意無意的保持、維系原有文化的行為。重慶蒙古族重修族譜,保持太陽神、祖先、白馬崇拜等信仰,流傳“八句詩”,對蒙古族保持強烈的認同等,正是社會 “文化固守”勢力的佐證。在對重慶蒙古族的 “文化固守”探究基礎上,作者以深厚的學術積淀和勇于創新精神,嘗試建構 “文化固守”理論。他認為,“文化固守”與 “文化變遷”相互依存,是社會與文化不可逆轉的變遷過程中,作為文化擁有者的民族或者族群成員對它們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傳統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個體作為群體成員所必須的各種基本能力和習慣的堅守與保持[6]。“文化固守”分為主體主動行動的主觀性文化固守和主體被動行動的客觀性文化固守。他根據重慶蒙古族的固守行為總結了4種 “文化固守”的表現形式。八角廟、族譜屬于具象實體的物質層面;祖先崇拜、民族認同屬于意識情感的精神層面;婚俗禁忌屬于規范的制度層面;飲食起居、教育傳說屬于外在表現的行為層面。“文化固守”作為社會真實的存在、“文化變遷”的統一對立面而具有客觀性、動態性、相對性的特征。
“文化固守”理論是社會文化變遷研究領域中一個重要的理論創見,對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民族文化傳承與保護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五、方法多樣:田野調查和多學科方法的綜合與運用
田野調查是文化人類學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是民族志構架的源泉[7],“中國的民族學、人類學具有廣闊的田野資源,這是學術發展的土壤”[8]。沒有田野調查,“民族志”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志,理論建構只會淪為空想、幻想、甚至是妄想。如果文化人類學的 “三駕馬車”能協調行駛,田野調查一定處于 “排頭兵”“領頭羊”的位置,承擔沖鋒陷陣、中流砥柱的責任。同時,文化人類學是一門涵蓋面極寬、涉及面極廣的學科,文化變遷的范疇包括生產生活、社會組織、宗教信仰、法律道德、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僅僅以田野調查作為唯一獲取資料的渠道和方法,略顯單一化和簡單化,且無法從民族歷史、認同心理、比較角度等側面證實所獲資料的真實性、實用性和客觀性。況且,任何一種研究方法并不是 “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應用準則,在它延伸或觸及不到的領域,應汲取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精華予以補充。人類學民族學田野調查的未來走向應是 “吸收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有價值的調查方法,使田野調查更加科學化。”[9]基于此,《散雜居蒙古族社會與文化變遷研究》堅持從事求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本原則,采用了田野調查為主,其他多學科研究方法為輔的多樣、綜合的研究方法體系。
第一,以田野調查法廣泛收集第一手資料。運用參與觀察法、訪談法、座談會法、譜系調查法等具體操作方法對田野點進行多次長期的田野調查。妙用參與觀察法和訪談法厘清向家壩蒙古族生產工具的變遷脈絡,從游牧、“人力牛耕”、挖鋤鐮刀等原始工具到改革開放后機械化農機的購買和使用,以此展現蒙古族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用深入訪談法搜集到蒙古族村民從事農業、狩獵、手工藝的個案,以深入感知蒙古族產業結構調整對村民生產生活的影響;巧用問卷法調查蒙古族的地域認同、民族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來深入分析向家壩蒙古族文化認同體系、認同特征和認同結構;用譜系調查法,對族譜殘譜、“角格兒”墓碑上記載的人物譜系進行追蹤,來探究蒙古族血緣、宗族、聯姻、親屬等制度。田野調查法既是一種研究方法,也是一項艱苦的事業,沒有克服困難的勇氣和堅忍不拔的意志,難以達到科學研究的目的。在該書的字里行間里,無不流露出作者勤勤懇懇的調查態度、兢兢業業的調研工作、嚴嚴謹謹的治學精神。第二,以其他多學科研究方法對資料進行補充、證實、分析和解釋。作為史志結合的著作,史學研究是其亮點和特色,《散雜居蒙古族社會與文化變遷研究》運用了歷史學研究的文獻法、口述史法和遺存考證法。歷史文獻資料的搜集和引用、村民的口述歷史記載、碑刻遺址的考證實例在文中俯拾皆是、不勝枚舉。此外,作者還采用了比較法,對不同地域蒙古族社會文化進行跨時空、跨地域的比較,以總結散雜居蒙古族社會文化特征和變遷規律。
六、結語
一言以蔽之,《散雜居蒙古族社會與文化變遷研究》是一本散雜居蒙古族研究的拓荒之作。它以散雜居蒙古族為研究對象,選擇重慶蒙古族為個案,以重慶蒙古族社會文化變遷為研究主題,拓寬了我國散雜居民族研究的領域及散雜居蒙古族研究的主題。以縱橫結合、史志交融的方式,完成了重慶蒙古族全景式的民族志記述和縱深化的歷史梳理,向我們呈現出了一本全面系統、脈絡清晰的民族志。作者以極具開拓創新的精神,初步建構了 “文化固守”理論,對文化變遷和民族文化的保護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作者綜合運用了田野調查和其他多學科研究方法,收集、分析、解釋資料,提高了研究的科學性、規范性和開放性。
作者未對重慶蒙古族文化變遷在當代社會背景影響下的未來發展路徑進行展望與思考,應該說是一個遺憾。當然,科學研究不是窮盡真理、一步到位的,尋求 “真實”[10]的使命也并非一本著作所能完成的。在這一點上,還有待作者的進一步深入研究。
[1][英]奈吉爾·巴利.天真的人類學家[M].何穎怡,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13.
[2][英]馬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李紹明,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18.
[3][美]古塔·弗格森.人類學定位:田野科學的界限與基礎[M].駱建建,袁同凱,郭立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43.
[4][美]C·恩伯,[美]M·恩伯.文化的變異[M].杜杉杉,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533.
[5]王銘銘.文化變遷與現代性的思考[J].民俗研究,1998(1):1-14.
[6]王希輝.從馬背到牛背:散雜居蒙古族社會與文化變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244.
[7]林耀華.民族學通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150.
[8]郝時遠.“中國田野”中的人類學與民族學[J].民族研究,2009(10):1-12.
[9]何星亮.人類學民族學田野調查的歷史與未來[J].民族研究,2002(5):43-45.
[10][美]艾爾·巴比.社會研究方法[M].邱澤奇,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20.
[責任編輯:慶來]
向瑞,女,湖南湘西人。博士生,主要從事教育人類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