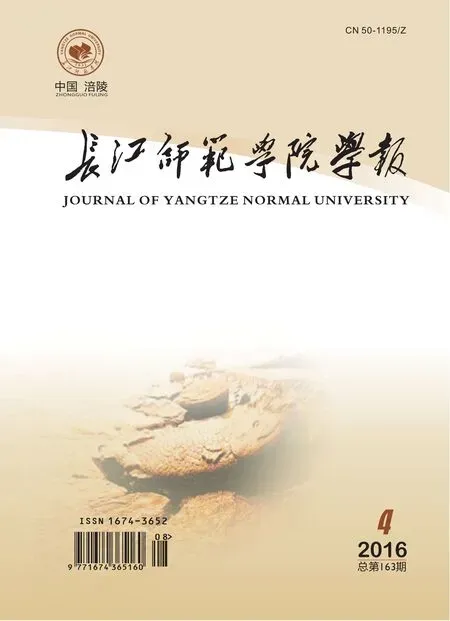文化生態視閾下的土家族民歌研究
熊曉輝
(湖南科技大學 藝術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
□西南民族文化研究
文化生態視閾下的土家族民歌研究
熊曉輝
(湖南科技大學藝術學院,湖南湘潭411201)
文化生態保護與研究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文化生態視閾下的土家族民歌研究主要擬在生態學及相關理論的指導下,結合土家族地區民歌的史實來進行實證研究。其一,圍繞土家族民歌生態生成環境的內容與特征,用文化生態保護的立場和民族志方法來進行個案描述和理論分析,全面探討文化生態視閾下土家族民歌的內容、特征、形式、發展等,研究土家族民歌在發展創新及基于文化生態視域下的發展策略。其二,針對土家族民歌所表達的方式、特點及對音樂文化研究的影響,采取歷時態和共時態相結合的研究思路來組織材料與分析問題,通過時態性的文化把握,考察土家族民歌研究的重要意義。其三,對土家族民歌進行規律性的提煉和理論創新,在認真研究、鑒別現有文獻資料的同時,豐富對土家族民歌的認識。
土家族;文化生態;民歌
一、引言
21世紀初,世界各地的學者們已經開始運用新的技術和方法來研究 “民歌”,于是文化生態保護與“民歌”的聯系等一系列問題就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里,人們試圖透過各種紛繁復雜的 “民歌”現象揭示環境因素的作用,以期做出具有規律性的解釋。人們根據 “民歌”與其文化生態環境的具體形態以及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和地區的運動狀況,來決定 “民歌”研究的對象與范圍。此后,自然、社會環境與 “民歌”的關系逐漸引起學術界普遍關注。在文化生態視閾下,人們研究 “民歌”已經取得了一些豐富成果,同時西方學者在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音樂學等學科領域也奠定了相關的理論基礎和研究范式。一些學者如 (美)蕾切爾·卡森、(英)約翰·布萊金、(法)埃德加·莫蘭、(德)卡爾·雅斯貝斯等,對民歌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在重視非歐洲民歌研究的同時,開始重視對本民族民歌的研究。西方學者提出的各種文化價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較、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使得民歌研究對象有了相對基礎,當論及民歌與生態的關系時,對影響民歌的環境因素展開了具體化的研究,并對可以觀察到的層面給予定值、定型、定序分析,同時也對一般理論意義上的環境因素進行因子分解。西方學者的研究雖然注意了民歌的生態分析,也借助了自然科學量化分析的方法,但其研究卻顯得有些零散,而且還受到一些非學術因素的制約。
國內學者在2000年后才開始關注該問題的研究,并產生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中專著有:田世高的 《土家族民歌論》《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4期),蕭梅的 《田野萍蹤》(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4年),余詠宇的 《土家族哭嫁歌之音樂特征與社會意義》(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年),鄧光華的《貴州土家族宗教文化:儺壇儀式音樂研究》(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等。論文方面,據不完全統計,近10年來約公開發表30余篇。綜而觀之,既有研究的主題主要集中在民歌的發生、流源、類型與嬗變等方面。由于現有的民歌與生態環境研究大多是以民歌本體形態為中心而進行討論的,故而對民歌與其生態生成環境、對民歌與自然和社會環境的關系問題關注不夠,特別是對當前民歌與環境的相互關系、相互作用的社會意義方面更顯不足。所以,土家族民歌研究存在著值得深掘的空間。近年來,盡管土家族民歌研究似乎在相當程度上被介紹與傳播,但它的真正的學術價值不易在整體上被認識,在學術界,倡導這種研究的氣氛并沒有形成。隨著民歌與生態環境等問題研究與應用的展開,土家族民歌的研究范圍在不斷拓寬,對土家族民歌研究及其意義上的肯定只有在經過一番批判性的工作之后才能達到。實際上,對土家族民歌研究,仍然是一種有待于結合當代音樂學、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及各學科種種具體問題,吸取新經驗,從現代方法論水平上重新開展的艱巨的研究工作。
將土家族的民歌文化及其所處的自然與生態類型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揭示其間的內在關聯性,以便將土家族民歌的流失與生態安全的維護納入同一個問題去思考,從而從根本上化解人類社會所面對的民族文化的流失和生態環境的惡化這兩大挑戰。同時,對土家族 “民歌與文化生態保護”的內涵做了前沿性的思考和理解。土家族的 “民歌與文化生態保護”是指該民族成員憑借其特有的民族文化藝術,在世代延續的漫長歷史過程中,一方面加工、改造了該民族所處的自然與生態系統,使之獲得了文化的屬性;另一方面,通過民歌文化適應環境的稟賦,不斷地完善和健全民族文化自身,最終使民族文化與它所處的生態背景之間,結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耦合關系。文化與生態的這種耦合體就是該民族的文化生態。
二、民歌與文化生態環境的屬性與內容
(一)民歌與文化生態環境的自然屬性
民歌與文化生態環境的聯系并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早在19世紀初,從鮑亞士到馬林諾夫斯基都對民族文化及民歌文化的習得性作出了深入的探討,而且還將民族文化定義為一套信息系統,揭示了文化的本質,努力把生態學和文化學共同感興趣的適應問題、種間斗爭、文化沖突、自然選擇與社會選擇問題,都納入了信息系統創新的范疇去加以闡釋。我們研究民歌與其文化生態環境的關系,實際上就是研究民歌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包括民歌產生的地理環境、社會政治、社會思想、政治制度等。民歌是指處于社會底層的民眾在長期的位置生產、精神生活與社會交往過程中口頭即興創作的一種聲樂藝術[1]3。從文化藝術角度來講,民歌文化是社會文化整體中的一個面相,與其他文化類型一樣,它最基本的一個特征便是群體性,而且這種群體性是通過人與文化這兩個方面因素表現出來[2]17。在中國民族音樂的發展過程中,“民歌”一詞自古就有,如 《詩經·國風》《楚辭》《漢樂府》等都大量記錄了中國古代民歌的表現形式、內容與結構,也可從中看出中國民歌充滿了原始的宗教氣氛。明代楊慎的 《古今風謠》和馮夢龍的 《山歌》都是較早研究、搜集與整理中國民歌的論著。縱觀歷史,事實上人類在幾千年以前的漁獵、農牧生活中,就注意到了自然條件和地理條件是如何影響著收獲的,同時也常常運用民歌演唱的形式,表達了狩獵與農作物耕種的技術特點與時令氣節,這些其實就是樸素的民歌與生態環境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觀念。再者,從古代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到我國北魏時期賈思勰所輯的 《齊民要術》,都對人類改造自然環境以及各種生態現象進行了闡述。我們認為,比較系統地觀察與分析自然環境與人類文化關系的應首推美國生態人類學家斯圖爾德 (Jul i an St eward),他于1955年提出了文化生態學概念,強調從文化生態變遷的角度研究人類適應環境的過程,并提倡設立專門學科。早在17世紀,達爾文的 《物種起源》就已經表述了 “自然選擇”理念,探討了生物與自然環境的相互選擇作用,生物進化論探討的也就是生態學問題。直到20世紀80年代,人們才在斯圖爾德觀點的基礎上,對文化與生態的相互關系進行全面深刻地探討,而且把文化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看成為一個相互聯結的整體。自從人類創造音樂起,民歌就占了相當大的比例,我們發現,音樂的歷史,應當是從民歌開始的。音樂學家們認為,民歌起源于遠古人類的生產勞動[3]3。因為伴隨著勞動節奏的呼喊和身體律動,就有了人類最早的音節與舞蹈節奏,民歌也由此產生。可見,民歌一開始就與人類的產生勞動環境分不開。《吳越春秋》一書中曾記錄了一首相傳是黃帝時期的民歌 《彈歌》,其成分說明了民歌與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關系。如 《彈歌》中唱道:“斷竹,續竹;飛土,逐宍。”[4]128歌中生動描繪了早期人類社會人們集體狩獵的情景,反映了勞動使人們獲得了生存所必需的物質。民歌成為了人們民俗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人們集體創作的民歌是一種有目的的行為,對于這種行為,起主導作用的生態因素顯然是社會文化環境與自然環境,但自然環境一般來說只起外因作用,民歌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必須要通過心理機制的作用來體現。
既然我們認為 “文化生態環境”通常關注的是環境影響下的文化生態生存狀況,那么民歌與生態環境就要復雜的多,它是一門研究自然和社會環境與民歌關系的學問,它把民歌作為 “核心物”,探討民歌在創作過程中與天然環境及人造環境的相互關系而形成的藝術文化環境場,著重研究與把握民歌生成與民歌環境的調適及內在聯系。現代科學的發展拓展了我們視野,研究民歌與環境的關系,考察文化生態的形成與方法論,是十分必要的。民歌與環境的關系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復雜問題,需要借助多學科綜合方法進行研究。研究文化生態與民歌的關系,一定要把民族文化與歷史過程、民族交往、民族生存環境納入統一框架內。在此基礎上,認識和了解民歌生態生成特征,加強對民歌保護,做到歷史性、區域性、民族性有機統一,達到對民歌與其文化生態的整體性研究。研究文化生態與民歌的關系必須重視學者們對民歌文化的理解,民歌文化的實質在于它是一種具體的人為信息系統,民歌生態學具有功能性、習得性、共有性、穩定性、整體性和單一歸屬性等。
(二)文化生態視閾下 “民歌”的內容
對民歌與其生態環境的研究,我們還得回到文化生態的定義上去,應該先去探討一下 “生態學”。“生態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由德國生物學家赫格爾于1870年首次提出。由于人類研究生態是從自身的價值取向出發,希望通過生態學的研究來解決切身的經濟利益。于是歷史上生態學曾被理解為有關生物的經濟管理科學[5]279。但是,我們縱觀人類文化藝術的進化與演進,每個民族在早期總是針對特定的自然生態系統去構建民族文化藝術的。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是從純粹的自然生態系統中獲取生命物質和生物能,而是從該民族生境中獲取存在和發展的各種物質和能量。這樣,生態變化如果與人類的活動有關聯,那么它肯定不是發生于原生的自然生態系統之中,而是集中表現在各民族的生態環境之中。民歌作為特定文化的產物,又受到特定文化的干預,其民族生境必然具有該種文化的特性,同時文化的固有屬性在民歌中,會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長期以來,學術界習慣于認定民歌與民族文化的環境與變遷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范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有部分學者提出,當今人類生態環境遭受破壞與全球范圍內的民族文化趨同存在眾多關聯性,但這僅僅是學者們的猜測而言。隨著文化生態學逐步被我國學術界所接受,民歌與生態環境的理論與方法在民族文化和自然與生態系統之間構建了相互銜接的分析模型,使學者們的上述猜測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理論支持,不過進一步的驗證其內容仍屬空白。民歌與生態環境其實就是以民歌發展與創作的生態環境為突破口,取材于生態學、民族學、音樂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已有的研究成果,具體實證當代及歷史上生態環境保護對民歌的影響。
文化生態視閾下民歌研究的主要內容在于,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必須適應于它所處的自然于生態環境,而適應意味著民族文化與環境的相互兼容,但同時會在一定限度內導致所處生態系統的人為性,具體表現為人們價值觀、審美觀的改變和民歌傳承內容的改變。隨著人們對環境認識和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將意味著他們的民族文化也隨著這種改變發生了變遷甚至消亡。據此可知,任何民族文化都具備通過改變生態系統,而改變民歌內容與結構的潛力。所以,這就為我們通過文化手段優化自然生態環境提供了理論依據。民族學家們認為,民族生境內的生物物種構成格局總是以特定文化的需要為轉移,并通過該文化的干預來維持這一構成格局的延續。一旦失去了文化的干預,民族生境內的生物物種構成以及物種間的配置關系,就會與原生的自然生態系統趨于相同[6]45。就在這一層面去理解,民歌的特殊性正在處于它完全是特定文化在生態領域內的再現,并與特定文化的運行相始終。民歌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口頭創作的歌曲,是人們集體智慧的結晶,又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需求最大的資源。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其中必然包含民歌資源的可持續再生,中國民歌資源就已經處于瀕危的邊緣,也是制約我國民族文化發展的首要因素。
三、土家族民歌的本體特質
土家族聚居于高山地帶,這里樹木茂盛,物產豐富,人們一直承襲著古老的宗教信仰。土家族人相信萬物有靈,敬奉土王、祖先,敬獵神、土地神、梅山神、四官神、五谷神等。主持宗教祭祀的叫 “梯瑪”,梯瑪在人們的心目中占有著重要的位置,人們認為梯瑪是人神合一的統一體,他既是神的代言人,又是人的代言人,能為人排憂解難、消災祛病。武陵山地區土家族民歌的數量、種類繁多,主要有山歌、小調、號子、神歌、燈歌、跳喪歌、擺手歌、薅草鑼鼓歌等,土家族民歌中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深厚的歷史積淀、精巧的形態樣式、洗練的表現手法。
(一)文化內涵豐富
土家族民歌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千百年來,民歌成了土家族人相互交流和表達的主要方式,也是他們學習生活生產知識的重要途徑。解放前,土家族的文化經濟比較落后,普通群眾是沒有機會受到正式教育的,他們只有通過歌唱的形式來傳遞感情和學習知識,從而使得民歌成為了土家族人最重要的文化載體。土家族社會,人們唱歌沒有金錢、權利等世俗物質衡量標準,更沒有封建社會門當戶對的要求,唱歌是聰明才智的標志,會唱歌就能得到人們的尊敬。所以,土家族人都形成了以善于歌舞為美的價值觀和審美觀,這種喜愛歌唱的文化模式,在歷史演進中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民族思維習慣。土家族民歌曲調非常優美,并且緊密地與土家族語言相結合,曲調近似于朗誦調,在句末或腔末使用下滑音,形成自己鮮明的特征。土家族民歌大多數是用土家語來演唱,基本音韻的民族化不言而喻。在民歌中,土家族人的機智、憨厚、幽默往往貫穿始終,鑄造出土家族民歌的個性風采。土家族民歌是土家族民族藝術中最具代表意義的形式之一,除了演唱者運用演唱技術外,對于事物的描述與渲染還有著妙不可言的傳遞功能。作為一種在山野勞動生活中產生的歌唱形式,土家族民歌在傳承中不斷創新,歌手表演已經作了再度創作,它極富于表現力和感染力,為了使演唱內容更貼近人們生活、風俗習慣,民歌力求和土家族生活相適應。從土家族民歌獨特風味來看,它不僅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而且已經具有了極富個性的民族地方化特征。如流傳于湘西保靖縣土家族地區的山歌 《盤歌》,歌詞大意是:“什么無骨鉆硬土?什么無骨飄江湖?什么無骨鼎鼎坐?什么無骨有戲出?蛐蟮無骨鉆硬土,螞蝗無骨飄江湖,豆腐無骨鼎鼎坐,雞蛋無骨有戲出。”[7]122土家人人幽默、俏皮,他們用優美的唱腔,用自己的語言,通過詩一般的藝術處理,構成了土家族民歌的濃郁民族特色,蘊藏著豐富的土家族文化內涵。
(二)歷史積淀深厚
土家族民歌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淀,它主要體現在土家族民族文化的遺存上,我們從土家族民歌中都可以看到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土家族人的音樂與民俗生活的蹤影。如鄂西土家族喪葬音樂 《撒爾嗬》至今還演繹著春秋時期 《詩經》散遺的篇章,巴東地區土家族的 《跳喪》仍然演唱楚辭中 《國殤》的原詞。土家族民歌演唱時程式化特征鮮明,這種程式化的民歌尤能表現土家族人的審美情趣,在武陵山土家族地區,幾乎到處都可以聽到節奏自由而綿長的民歌,程式簡單,語言簡潔,旋律優美。從內容和形式上看,土家族民歌與人們生產勞動、日常生活、宗教祭祀等有著直接的聯系,是人們抒發內心情感和傳達思想情意的特殊形式。如土家族 《梯瑪神歌》,其曲調來源于遠古巴人的牛角號,舞蹈則來源于古代巴人的巴渝舞,它記敘了土家族的起源、繁衍、戰爭、遷徙、開疆拓土、安居樂業、生產生活等諸多內容。唐代在巴渝地區盛行的 《竹枝詞》仍然流行于武陵山土家族地區,它對研究古代土家族文學藝術、民俗民風、宗教祭祀等都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節奏鮮明莊重的土家族 《擺手歌》則包含了人類生存、勞動創造等內容,是一部土家族生動的文明史詩。土家族民歌的歷史積淀,還體現在其樣式和表現手法對古代土家族先民,或者說對土家族傳統歌樂的繼承。
(三)形態樣式精巧
土家族民歌在長期的發展與創作過程中,經過加工雕琢、傳播變異,在藝術形式上可以說是十分成熟了,許多種類都有著獨具特色和精致巧妙的形態樣式。土家族民歌的節奏、節拍都比較自由、悠長,這種程式化的樣式特征是許多民族民歌的共同特征。土家族民歌在演唱時,唱腔的節奏有時接近土家族語言的節奏,且能準確、清晰地唱出心里想說的內容。在土家族民歌的襯腔中,為了盡情抒發心中的情緒,歌手自由延長,也許,此時已形成了民歌中有規律的節奏和自由節奏的強烈對比,在我們常常聽到的土家族民歌中,《破頭腔》《沿河腔》等最為明顯。土家族民歌有著非常豐富的題材內容和形態樣式,按歌手的演唱風格與形式來分,有固定唱詞的熱唱和即興創作的冷唱兩種,一般在休閑時,無論在什么地點,都是民歌演唱的場所。按旋律曲調創作手法來分,有五聲調式體系、三音列、四音列、旋宮轉調等等樣式。“三音列”結構是土家族民歌最常見的旋律形態,土家族 “三音列”民歌是由3個音構成,因而句幅短小,在3個音的運動下展開樂思,旋律下行、二度級進的現象比較多[8]7。土家族許多民歌的音樂思維都是建立在土家族 “三音列”民歌的基礎上的,它在發展與創作過程中必然從 “三音列”中借用其固有的手法,并加以改造、發展,從而確定其獨特的個性。由于土家族民歌源于生活,在歌手的再度精心創作中,它已經成為可以表達主觀需要和獲得美的享受的一種手段。在審美的需求中,土家族民歌能揭示特定環境中特定人物的關系和各自的性格,并為民歌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普遍吟唱提供現實依據。
(四)表現手法洗練
土家族的民歌善于運用素材,采用洗練的手法,塑造出一個個鮮明、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在土家族民歌中,有時為了加強情節的氣氛,歌詞內容很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畫,有著濃厚的東方寫意傳神的固定模式。在研究中我們發現,土家族的民歌創作構思是依附于歌詞內容的,人們在勞動中總是把歌詞內容掌握的明白、透切才進行民歌吟唱或創作。比如土家族民歌 《蜜蜂只愛繞花臺》,其歌詞大意為:陣陣春風吹過界,蜜蜂繞繞彩花來,蜜蜂見花雙翅拍,花見蜜蜂朵朵開。從這首民歌中,我們可以看出它的曲調和吟唱風格與人們生活是有直接聯系的,民歌的內容都是人們對平時生活、勞動、愛情的體驗。正因為這樣,歌手在演唱土家族民歌時,覺得心中有數,土家風味入微入妙,既達意又傳神,即便是新創作的民歌,也能在獨特的演唱過程中潛移默化,獨鑄個性風采。
土家族民歌的創作是即興的,是歌手一種心象顯示。因為歌手的心理活動是捉摸不透的,是通過歌手運用唱腔藝術與表演來體現歌曲內容的。在土家族民歌中,用唱腔揭示人物性格特征和內心活動是最具特色的表現手法,也是心象示現最突出的手段之一。民歌,來源于勞動生活,但它又高于勞動生活,它有規律、有固定模式、有美的夸張,與其他民歌一樣,它是通過歷代歌手精心創作的民族音樂藝術。民歌是真實的,因為它從生活出發,經過藝術加工,并且準確地能將人物的情感和性格傳達出來。盡管民歌的演唱形式很多,但敘事的傾向性很強,能在歌中緊緊扣合情節,在演唱中傳達審美情志。我們發現,土家族民歌的表現手法非常豐富和細膩,而且能多側面、多層次地勾畫人物性格,是絕妙的心象示現。比如土家族民歌 《沿河調》,歌詞大意為:正月喜鵲在樹林,口含沉香樹一根,口里有根沉香木,日不曬來雨不淋。民歌借以12種鳥的叫聲,刻畫了富于浪漫氣息的日常生活,明朗樂觀。《沿河調》唱出了土家族人對美的追求、對美的向往,民歌把對鳥兒歌唱的情感美表現得淋漓盡致。
四、土家族民歌形態分析與民歌范疇概念的意義
(一)土家族民歌形態
人們對于土家族民歌的認知首先是通過對其外部形態的直觀感受來獲取,民歌形態有著自身的結構層次,應選取適當的層次來進行分析、研究,但必須注意環境選擇作用的焦點所在。
1.唱詞內容。土家族民歌有山歌、小調、號子、梯瑪神歌、獵歌、漁歌和勞動歌,等等,就其內容來看,民歌與勞動生產及宗教祭祀活動有直接關系。或反映先民們漁獵及農作物收獲后之喜悅;或伴隨勞動過程而吶喊呼喚;或解釋人類來源、萬物始源等現象;或表述驅鬼逐邪、祈求人畜平安的愿望[9]32。比如梯瑪神歌的內容取決于主持活動儀式的性質,即不同宗教活動唱不同內容的神歌。《梯瑪神歌·請神捉鬼》這樣唱道:“懸崖陡,刺叢深;水流激,路難行。尊敬的大神們啊,沒有好路,讓你行啊。”這首歌描述的是梯瑪與大神對話,請大神捉鬼,在描述山區道路崎嶇艱難、乘船注意安全時,卻十分生動,生活氣息較濃。如 《打獵歌》,它是這樣描述土家族先民獵猴的:“背銃就往樹林走,走進樹林去趕猴。拿銃攆猴三天整,猴子跑得屁股冒紅煙。”我們可以從短短的獵歌中看出土家族先民謀取生活資料的艱難,以及他們在獵猴時的耐心與機智。又如 《船工號子》唱道:“里耶上來 (眾唱:嗨嘿)轉個彎 (眾唱:嗨嘿),船兒要過 (眾唱:嗨嘿)螺絲灘 (眾唱:嗨嘿),上了一灘 (眾唱:嗨嘿)又一灘 (眾唱:嗨嘿),五家灘來 (眾唱:嗨嘿)過陡灘 (眾唱:嗨嘿),嘿喲 (眾唱:嗨嘿),吆嗬吆嗬 (眾唱:嗨嘿)。”這首《船工號子》屬 《酉水號子》,多為老船工即興所唱,采用比擬、夸張等手法,生動地再現了酉水一帶當年的地理狀貌、風土人情及船工的艱辛生活。再如土家族的勞動歌,其歌詞內容主要是一些知識性和解釋性的農業歌謠,保留了土家族先民刀耕火種、廣種薄收的原始農耕生產特點。唱詞內容與人們的生產、生活及宗教活動緊密相聯,是土家族民歌的一大特點。
2.音樂結構。土家族民歌的音樂結構是由旋律、調式調性、節奏等組成,因為其民歌的個性化、色彩化,旋律是土家族方言民歌音樂特征中最具代表性的主導要素,獨特的地理環境孕育出獨特的語言音調,可以說武陵山區土家族民歌的旋律就是這種語言的音樂化。但是,它自己有約定俗稱的表述風格與形態。
旋律特征。土家族民歌旋律是以 “級進”或同音交替、同音重復較為普遍,并且旋律都是在 “同音重復”中得到引申。級進和連續級進的旋法在土家族民歌中最為常見,較為獨特的是,土家族民歌旋律在進行中一直保持著級進勢頭,乃至越過一個八度,這可能是由人聲或樂器的音域造成的一種意欲超越極限的結果。在土家族民歌中,二聲音列、三聲音列序進是五聲調式中最基本的運行方式,二聲音列、三聲音列依次向高、依次向低的序進形態,以及回旋形態都較常見。與漢族民歌一樣,土家族民歌一般分為起、承、轉、合4部分,起、承、轉、合是土家族民歌旋律發展的必經程序,也是土家族民歌旋律發展的基本原則。
調式調性。土家族民歌以五聲調式音階為基礎,旋律進行以級進、三度小跳為主,間以四度或四度以上的大跳的旋法為主為多,同時出現同音反復或舒而不展,形成一種平穩、怡然自得的旋律走向[10]31。土家族民歌常用的調式有:徴、宮、羽、商,其中徴、宮、羽使用較多,角調式很少使用。土家族民歌主要以羽、宮調式最為常見,在調的發展方面非常簡單,主要表現在平行調式的交替上,轉調極為少見。
節奏特征。在土家族民歌中,各個不同種類其節奏型是有很大區別的,往往又有相似之處。但是,這些種類的民歌都是產生于人民勞動、生活之中,生活氣息濃厚。經過長期考察,土家族民歌節奏的形成主要有兩個途徑,其一是從語音節律的基礎上逐步提煉而來,土家語音本身的律動美就是土家族民歌旋律形成的基礎。其二是由于受到人們長期的勞動生活的影響而形成的,勞動、祭祀、舞蹈等活動本身的節奏特點形成部分民歌的基本節奏。土家族民歌中不同類型的民歌節奏形態有不同的特點,如號子的節奏與勞動有關,其節奏規整,節奏型的頓逗適合勞動的氣息運用,節奏重音突出。山歌則節奏自由、靈活,以散板居多。
3.演唱形式。土家族民歌在演唱時,有獨唱、對唱、合唱等多種形式。在湘西自治州土家族地區,土家族民歌多是男、女聲獨唱,男、女對唱或兩女對唱。多人合唱時,有女聲合唱和男聲合唱。唱歌時,歌手喜歡用手板托面腮吟唱,聲音高尖。一些祭祀儀式歌曲的演唱形式又有不同,其必須按儀式的程式來進行,比如 《梯瑪神歌》,演唱時梯瑪頭戴鳳冠,身穿八幅羅裙,腳踏馬蹄沙鞋,右手拿著司刀,左手握八寶銅鈴搖晃,配以鑼鼓伴奏,邊跳邊唱。《哭嫁歌》又是土家族民歌的一大特色,出嫁前一天晚上,姑娘和相鄰姐妹十多人圍著火坑同哭,稱 “陪十姐妹”;因此,不少土家族姑娘從小就要跟人學哭嫁,觀摩或參與陪哭。
流行于湖北利川土家族地區的 《燈歌》,其演唱形式獨具特色。《燈歌》表演主要是劃地為臺,載歌載舞。一領眾合,打一遍鑼鼓就唱,打一遍鑼鼓就收。表演者 (演員)一般由一生、三旦、兩丑組成,化妝、表演已具戲劇雛形,所以人們把 《利川燈歌》又叫跳燈、玩燈、燈夾戲等。土家族 《薅草鑼鼓歌》是土家族先民在長期生產勞動中集體創作的一種直接用于農業生產的民歌,一般由兩人演唱,一人按節奏擊鼓,一人應節奏點敲鑼,鑼鼓間歇、歌聲即起、輪流對唱。3人演唱與4人輪唱的形式也有,但很少。
(二)土家族民歌范疇概念的意義與民歌生態分析
1.土家族民歌范疇概念的意義。武陵山區土家族民歌是土家族人在長期產生勞動和民俗生活中集體創作、口傳心授傳承下來的音樂樣式,根據內容、形式的不同,我們把土家族民歌分成為山歌、風俗歌、小調、勞動號子、兒歌等幾大類。民歌文化是社會文化整體中的一個面相,從藝術文化的角度來說,民歌的群體性表現在它是一個協調人們的創作、表演和欣賞方式的文化角色集合體。或者說是人們在進行上述活動時所必須遵循的一種行為規范[11]17。土家族民歌對于演唱者來說,是環境選擇的直觀感受,通過自己的二度創作,達到表意抒情的目的和效果,實現審美價值。如果以抽象的范疇來描述,民歌可以是高亢、優美、細膩、粗狂等詞匯,描述但如果仔細分析到具體的單元上,也許就會失去詞匯描述的作用。鑒于土家族民歌范疇的側重點在于探討民歌背后的民族文化環境與差異性的人文原因,我們認為土家族民歌基本范疇的根本任務就是,以民族歷史為主線,以人物故事為內容,以環境為取材,在直觀上使人可以感受到的具有同一審美表意的歌唱。
很顯然,土家族民歌范疇概念的確立與發展,對于土家族民歌生態學研究的進程具有重要意義。從民歌生態學方法論上觀察,土家族民歌范疇概念的確立是對民歌特質分析的一種哲學思考。人們對方法論的探討,使我們對于土家族民歌中普遍存在的精確性與模糊度的辯證關系逐漸具有了高度自覺的意識。受人類學、民族學、音位學等學科研究成果的啟發,土家族民歌生態學研究引用了自然科學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同時建立了適合藝術特質分析的可操作性概念。這種認識論或思維方式的產生,在土家族民歌生態學研究中會得到長足的發展具有突破性的意義,也會對我們以后的民歌生態學研究產生事半功倍的作用。
2.土家族民歌生態分析。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武陵山脈的高山地帶,人口約800萬。從自然生態條件來看,武陵山地區森林茂密,野果滿山,雨量充沛,河溪交錯,氣候溫和,四季分明,因此可以說是人類生息繁衍的理想場所。遠古時期,武陵山地區就是土家族人生息繁衍的地方,這一點已為越來越多的考古學材料所證明。據土家族民歌 《擺手歌》所述,土家族 “八蠻”①“八蠻”是土家族8個部落的俗稱,因其共有8個部落或8個峒而得名,故又稱“八部大王”。據土家族人世代相傳,遠古時代,土家族共有8個部落,各部落均有各自的首領,8部落的首領分別叫:熬朝河舍、西梯佬、里都、蘇都、那烏米、農比也所耶沖、西河佬、接耶費耶納飛列那。八蠻在武陵山土家族地區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最初是沒有固定的生活場所,遷徙到酉水流域,留下了不少歷史遺跡。湘西龍山縣里耶境內土家族傳說是八蠻早期從事農業生產的地方而得名,“里耶”為土家語,“里”即 “地”之意,“耶”即“開”“辟”“耕”之意,“里耶”即 “辟地”之意。從地名學角度看,土家族先民八蠻遠古時代就活動于武陵山地區的酉水流域一帶。土家族是一個古老且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有著漫長的歷史,相繼經歷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各個朝代,從五代到梁開平四年清代雍正年間,先是羈州后是土司政權的彭氏世襲領地,經歷 “改土歸流”的二百年到全國解放。土家族經歷了漫長的、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創造了可歌可泣的歷史業績和光輝燦爛的民族文化。
由于居住地型的原因,土家族居住的地方多為依山傍水,后面靠山,前有流水,而且多是聚族而居,少雜他姓。有的村寨,山高谷深,村寨相望,雞犬相聞,呼喚可應,但一上一下,相距十多里,有的村寨在高山密林之中,野豬與家豬同眠,家狗與野狗同嬉。甚至有時猴子會進屋翻鼎罐,開碗柜,做偷吃飯菜之事;在武陵山地區的土家族村寨,這樣的事司空見慣。武陵山地區的土家族具有獨特的民族文化和傳統節日,每逢正月到元宵節前,都要舉行擺手活動,唱擺手歌、跳擺手舞,這是土家族大型的祭祀祖先的活動,土家族的宗教文化很深厚,他們信奉祖先信奉神靈,每家堂屋的神龕都有敬供祖先的神位,過年過節都要敬奉祖先,其中正月、七月,從初一到十五,早晚都要焚香敬祖,其余都只在初一、十五兩天,焚香敬祖[12]114。
武陵山區土家族民歌浩如煙海,主要有山歌、小調、情歌、燈歌、兒歌、號子、風俗歌、時政歌、勞動歌、盤歌等,內容豐富,特色鮮明,表現了土家族人的性格,具有鮮明的土家特色。土家族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一萬余年的古人類化石演繹著古代蠻夷人群的生存圖騰。刀耕火種沿襲了數千年,高山峻嶺成了人們生存的障礙。為了追求幸福、自由與征服自然,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高興了對著大山吆喝,憤怒了對著河流呼喊,久而久之吆喝成了美妙的樂章,呼喊成了動聽的旋律,民歌成了土家族人舒心的感情釋放。于是,高亢悠揚的山歌破空而來,委婉柔和的小調穿山而來,激越雄渾的船工號子踏水而來,歡快活潑的燈歌隨舞而飛,昂揚的薅草鑼鼓歌隨風而飄。“一人歌唱萬人和”“村村寨寨都是歌”。唱起這些民歌,人們就會感受到先民們狩獵、生產的艱辛,體驗到人類生活的艱難和團結的可貴。聽著這些歌聲,人們就會被它那古老神圣、變化多段的藝術魅力所陶醉。千百年來,土家族民歌傳遞著土家族人民的喜怒哀樂,表達著土家族人生生不息的愛的理念。走進土家族民歌,如同走進一個茫茫無邊的歌的海洋。在這里大山長的是歌謠,溪澗流淌的是歌謠,村寨傳出的是歌謠,那各種不同的曲調中流動的音符無不顯示出土家族民歌永恒的魅力。
五、自然科學量化分析的方法對土家族民歌研究的作用
民歌研究引進了自然科學 (生態學、物理學)和社會科學 (語言學、音樂學)的方法論,順應民歌研究發展的需要,也符合當代藝術和科學發展的總趨勢。之所以要借助于現代自然科學方法,是因為我們所確立的研究目標,不能靠傳統的經驗總結,更不能靠臆測,而應通過實地考察,進行相對精確的測查、計量,再經綜合分析,探討出科學規律,才能達到[13]32。因此,對土家族民歌研究的探討,既順應了民歌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應順應當代藝術與科學發展的總趨勢。
(一)土家族民歌研究需要自然科學量化分析
土家族民歌研究在實踐中已經證明,在研究民歌具體現象,不論是自然現象還是社會現象,如果孤立地對民歌進行研究分析,然后不假思索地將分析結果簡單融合,希望從中得出整體性的結論,這樣的做法很難達到目的。土家族民歌是一門集體創作的藝術形式,美感是高度綜合的,也是人們喜聞樂見的,它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積淀。所以,我們對土家族民歌的研究、分析、統計、錄音錄像、測查等,決不能簡單化。比如說對于土家族民歌唱腔分析,人們積極引用自然科學量化分析,可以也應該對其進行物理、數學或生理學分析。但需要提醒大家,千萬不能就此把土家族民歌藝術還原為數理化的精確描述,這種分析方法有悖于民歌研究的本質,也不能說其就是 “科學化”“合理化”。土家族民歌研究,重點是研究民歌與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關系,要特別注意在分析事物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中去考察各種文化行為,同時還得注意民歌本身的活性結構。從審美的角度分析與研究,對于民歌欣賞的研究必須與研究其他心理現象一樣,應盡量克服主觀同客觀相割裂開的絕對化傾向。
(二)研究方法應有可操作性
土家族民歌研究在不排除基本邏輯構思和邏輯推斷的情況下,應把研究方法、研究視角放在可操作、可測查的經驗事實上。但結論必須在分析考察之后才能做出,在研究過程中,假設的證實與否決都是非常有意義等。從可操作性考慮,我們研究土家族民歌與環境相互聯系時,都必須仔細研究分析出可能測查到的因子。所謂因子指的是文化結構的組成部分,這些因子或者說是文化元素都應相互獨立,統計出的總和必須能概括研究對象的總體效應。研究方法上應該遵循從局部開始,逐漸向縱深展開。
(三)研究過程中注意共時性與定量、定性的描述原則
研究土家族民歌與其環境的具體關系時,必須弄清民歌與其環境相互作用的結合部、層次與側面,不能將它們含糊混雜地進行比較,不僅要注重對其共時性關系考察,還要注意傳承、變遷、生滅、分合、興衰、演進等歷時性變化,更要研究與分析不同環境因素對文化因子的作用方式、影響程度,比如同步性、積累性等等。對土家族民歌生態學及其一些經驗事實的分析總結,不能采取抽樣的方式泛泛描述,應根據實際操作對象的特點,運用科學方法進行定量、定型、定序地分析與描述,切忌過于簡單化。當然,民歌生態因子的分解與確定還需要在測查研究中進一步證實,有的開始只能是假設性的。有些民歌生態因子與客觀現象不易于直接測度或定型、定序,應該考慮用某種模式將搜集到的資料化為某種數值,類似心理學和生理學上所闡述的 “量化度”,遇到像這樣的現象與模式,可依據研究對象的性質而定。
(四)應對民歌研究結論作精確處理
土家族民歌研究引用與借助了大量文化生態的學術概念,如 “生態災變”“生物制衡”“文化適應”“生態環”等,我們用這些名詞來解釋土家族民歌與環境因素關系的諸多現象。介于土家族民歌與環境關系的復雜性,在具體研究中,要求我們必須注意精確性與模糊度的結合,也就是把 “或然率”與 “因果律”進行交叉認識的思維方式。假設,我們把土家族民歌中的一些模糊現象看著一種絕對的精確性處理,即使理論上可行,但也會失去其蘊含的活力。民歌與環境的關系,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它們往往不是單線條的,而是交錯復雜的網絡,因此應對民歌研究結論作精確處理。考察它們歷時性變化時,不能局限于線性變化關系,不一定會遇到平衡態和單解質。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中,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的興衰與演化,諸如土家族民歌所有導向民俗、祭祀、娛樂、交往、戰爭、禁忌等行為,根據民族文化內部邏輯發展起來的無意識選擇原則轉化為一致的模式。可見,文化模式與民族生境都是一個動態的平衡體系,由民族文化維系和生態環境規約的土家族民歌同樣是一個動態平衡的共同聚合體系。
六、文化生態視閾下土家族民歌研究的價值認識
土家族民歌是中國民族音樂文化中寶貴的元素之一,在土家族社會文化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從文化發生學來說,它的部分內容是中國民族文化的古根;從藝術學來說,它是中國民族音樂的 “活化石”。民歌與生態環境關系研究,以其跨學科的學術視野和開放的理論體系出現,意味著人們認識民歌的觀念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通過對土家族民歌與生態環境關系的研究和探討,尋求一條能夠清晰闡釋民歌意義的路徑,因為民歌意義有不確定性,人們把民歌與人類環境有機地連接上了,這是一個質的探索與嘗試。實際意義上,民歌研究受到其他學科的啟發,在吸收其他學科研究成果的同時,形成了多樣化的、特有的自然環境和文化研究領域,也逐漸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從理論意義上講,我們從土家族研究、民歌研究與生態學研究中開拓自己的獨特領域,這種理論創建有助于推動民族文化與人類生態的協調發展,推進民歌生態學學科建設的完善。我們把土家族民歌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研究,探索它不斷發展和組合的規律,指導民族文化藝術在現代社會的發展方向,對民族文化的繼承和弘揚,服務于人們文化需要,豐富人們文化生活與藝術享受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與理論意義。
[1]周耘.中國傳統民歌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
[2]楊民康.中國民歌與鄉土社會[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17.
[3]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3.
[4][東漢]趙曄,撰;吳慶峰,點校.二十五別史之吳越春秋[M].濟南:齊魯書社,2000:128.
[5]楊庭碩,羅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與生境[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279.
[6]楊庭碩.生態人類學導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5.
[7]熊曉輝.湘西土著音樂叢話[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122.
[8]熊曉輝.土家族三聲音列民歌形態研究[J].吉林藝術學院學報,2011(1):7.
[9]彭繼寬,姚紀彭.土家族文學史[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32.
[10]熊曉輝.湘西土家族民歌旋法探微[J].民族音樂,2009(1):31.
[11]陳銘道.書寫民族音樂文化[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17.
[12]熊曉輝.湘西歷史與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4.
[13]資華筠.舞蹈生態學學科闡釋[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3(3):32.
[14]熊曉輝.武陵山區辰河高腔唱腔及伴腔手法研究[J].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13(1).
[責任編輯:慶來]
J607.73
A
1674-3652(2016)04-0022-09
2016-01-20
熊曉輝,男,湖南鳳凰人。博士,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傳統音樂、音樂人類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