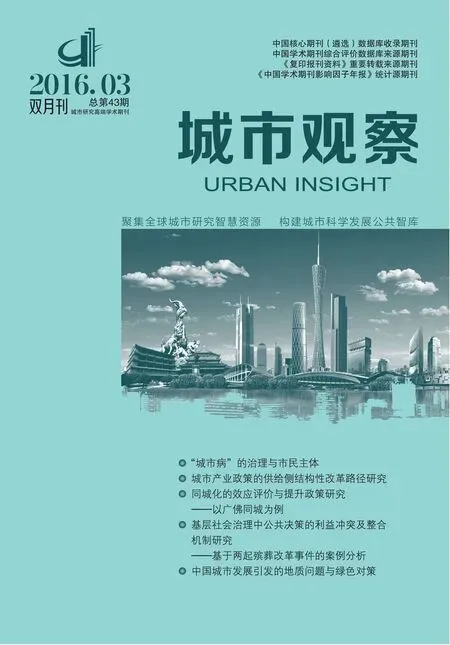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的亮點與問題分析
◎ 黃仲山
?
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的亮點與問題分析
◎ 黃仲山
摘 要:近些年,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工作穩步推進,非遺文化視野擴展、非遺文化觸角延展、非遺文化傳播方式更新形成值得關注的亮點,但仍然存在保護管理部門溝通欠缺、文化品牌建設尚待突破等新老問題,需要在文化傳播實踐中進一步打開思路,與時俱進,形成北京文化發展全局中鮮活的一頁。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 文化傳播 文化視野 文化傳播方式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城市重要的文化資源,也是城市文化軟實力的重要依托,而非遺文化傳播則是展示城市形象、加強與國內外文化聯系重要路徑,正如美國傳播學學者邁克爾·普羅瑟(Michael H. Prosser)所言:“傳播和文化是難分難解的,因此,人的一切社會互動都是與文化聯系在一起的。”[1]
近年來,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傳播工作按既定軌道推進,出現許多新亮點,主要表現在非遺文化視野不斷擴展、非遺文化觸角向社會各角落延伸、文化傳播方式與傳播思路不斷創新。總體上,北京非遺文化傳播出現新舊交織的格局,機遇與挑戰兼有,新亮點與舊積弊并存,成為城市文化發展過程中一道鮮活而頗具張力的風景。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工作的亮點
(一)非遺文化視野的擴展
北京近些年強調自身文化走出去,尤其希望將北京優秀的傳統文化向外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則承擔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在國際合作、國內交流、京津冀區域協同三個方面取得較大進展,開拓自身文化視野,給非遺文化發展帶來新契機。
1.走向世界:非遺文化的“國際范”
北京作為一個國際化都市,越來越注重文化視野的展開,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北京“文化名片”,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塑造歷史韻味十足而又充滿活力的北京城市形象。
北京市文化局等單位每年都會組織北京優秀非遺項目赴國外進行文化交流,比如,2013年4月,在韓國首爾舉辦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展;2014年6月,北方昆曲劇院和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赴法國和馬耳他進行文化交流,進行昆曲演出,展覽北京風箏、京繡、北京剪紙等優秀藝術作品,展示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藝術魅力;2015年9月,選派延慶舞龍、二韃子摔跤、舞獅、旱船、竹馬等非遺項目,遠赴南非參加“南非中國年”活動。此外,北京有意識地邀請國際友人傳播非遺文化,連續幾年舉辦“外國攝影師拍北京”活動,邀請世界各國優秀攝影師,用鏡頭聚焦非物質文化遺產,記錄北京城市歷史,將北京燦爛的文化遺產傳播到世界各地。北京在對外文化交流中頻打非遺牌,提升了北京的文化形象,增加了北京城市文化在國際上的人氣。
2.面向全國:非遺文化的“中國心”
北京向來重視與國內其他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交流,一方面,北京作為全國文化中心,每年都會吸引來自各地的非遺項目匯聚首都。北京積極承擔首都功能,為各地優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亮相舞臺,舉行各種全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展覽和展演活動,帶來富于地方特色的文化盛宴。
另一方面,北京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沒有自設藩籬,而是積極地走出去,在全國各地亮相,展示精湛技藝,傳播北京文化。北京玉雕、牙雕、金絲鑲嵌、景泰藍制作等“燕京八絕”,作為北京非遺文化的代表,在全國各地保持了較高的“曝光率”。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傳統文化一部分,在非遺保護與傳承過程中始終將自身放在中華文明框架下,強調中華文化的歷史源流和譜系,這就將北京非遺文化與全國各地的非遺文化溝通起來,共同詮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中國特色和“中國心”。
3.京津冀聯動:非遺文化的“三地情”
京津冀三地非遺文化傳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許多非遺項目具有相互溝通的元素,能吸引三地觀眾共同欣賞與品味。隨著京津冀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強,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文化尋求通過多種途徑進行合作,非物質文化遺產交流在這種背景下悄然升溫,尋求合適接口和適宜模式進行三地非遺文化的有機結合與靈活交流,從而加深相互之間的文化認同。
近年來,京津冀三地在非遺文化傳播中有意識地加強聯系,首先是以三地共同傳承的非遺項目為突破口,尋求文化上的親近感。如2014年,京津冀河北梆子優秀劇目在京津冀三地巡演,北京市河北梆子劇團、天津河北梆子劇院、河北省石家莊市河北梆子劇團等“三地四團”河北梆子名家組成強大演出陣容,登臺演繹傳統名段,將這一流布于京津冀地區的劇種發揚光大。其次,在京津冀三地文化部門和非遺傳承人的共同努力下,彼此之間的聯系交流明顯增多。北京在自身開展的許多非遺展演展示活動中,自覺加入“京津冀一體化”元素,引入天津、河北的優秀非遺項目同臺演出,共同展示各具特色的非遺文化。再次,京津冀三地非遺文化的整理、建檔與研究工作不再各自為陣,出現了彼此溝通、互通有無的趨勢。三地學者和研究機構正積極將京津冀文化融合納入視野,非遺文化研究出現新的氣象。
(二)非遺文化觸角的延伸
近些年,北京重視將非遺文化向社會深處延伸,進校園、入社區、進市場等,形成文化傳播過程中的亮點,給校園文化教育拓展、社區文化生活豐富和城鄉一體化建設推進提供了新的認識角度和發展契機。
1.非遺進校園
學校是文化和知識傳承的重要場所,利用學校的教學組織方式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可以更集中、更有效地傳輸非遺文化,在下一代心中播下非遺文化的種子。
北京市將非遺文化作為課堂和課下教育的重要內容,京劇、抖空竹、太極拳、踢花鍵、北京童謠等非遺技藝在北京的許多中小學普及開來。北京還加強非遺文化傳播的師資建設,通過培訓教師、課題研討等形式,加強教師非遺文化教育的能力。除此之外,許多學校還邀請非遺技藝傳承人走進校園,傳承技藝,培養非遺文化的土壤。比如,2014年1月,在西城區“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推進活動”中,40名傳承人被區教委和文化委授予“非遺進校園活動校園傳習師”稱號,鼓勵非遺傳承人親身參與校園非遺文化教育。非遺文化進校園活動的開展,推動了相關文化交流,一些學校承擔著非遺文化使者的角色,開展國內、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北京學生近些年在各項涉外交流活動中體現出優秀的人文素養和高超表演技巧,說明非遺文化在這些校園扎下根,并且開花結果,流芳海外。
2.非遺入社區
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來自民間里巷,是老百姓社區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然而由于現代生活方式變遷,以及人員流動等因素,許多非遺項目在過去一段時間失去社區生活的土壤,比如相聲等曲藝、“兔兒爺”、剪紙等工藝品、幡會等群眾游藝,在急劇變化的現代社會環境下與老百姓產生距離和陌生感。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需要一個重新回到百姓生活、回到街巷社區的過程。
非遺入社區首先是讓社區居民有機會觀看和接觸非遺文化,作為文化惠民工程的組成部分,近些年西城區等區縣舉辦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演出季等活動,發放演出票,讓居民欣賞非遺傳統文化精華。非遺入社區的許多活動常包含濃濃的人情味和趣味,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社區的傳播活動拉近街坊們的感情,豐富社區文化生活,成為社區文化建設的重要推進因素。
3.非遺進村落
北京京郊許多村鎮保存有原汁原味的非遺文化,比如門頭溝區千軍臺村幡會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此外,門頭溝爨底下村、大興魏善莊鎮等都是非遺文化非常活躍的村鎮。隨著城鄉一體化建設步伐的加快,北京對郊區村鎮非遺保護與傳播也越來越重視。2014年6月14日是第九個“文化遺產日”,此次文化遺產日活動主題是“非遺保護與城鎮化同行”,重點強調城鎮化進程中如何保護鄉村原有的文化生態,激發傳統鄉村的文化活力。通過一系列活動增進人們對北京郊區村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了解,促進非遺文化在傳統村落的傳承與傳播。
(三)非遺文化傳播活動的新氣象
近幾年,北京非遺文化傳播出現一些新氣象,一方面體現在傳播活動開展得紅紅火火,非遺文化展演、展示活動形成有效的固定模式;另一方面,非遺文化傳播過程進行許多有益的嘗試,通過多種媒介和多種渠道宣傳推廣,傳播方式日益呈現多元化的趨勢。
1.非遺展示活動的集中化和常態化
北京每年都舉辦多場大型非物質文化遺產集中展示(展演)活動,有些已經固定為常規性的文化項目,比如,東城區、西城區等區縣每年都舉辦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果大展,匯聚非遺保護成果進行集中展示;此外,東城區舉辦的非遺集中展示活動還包括每年一度的新春非遺廟會,以非遺為主題,為非遺項目展示提供專門平臺,這些活動已形成常態化、成規模的文化展示體系。
每年一次的“文化遺產日”是非遺集中展示的時間,北京近年來在文化遺產日已形成較為成熟完善的宣傳運作模式,各區縣集中在“文化遺產日”舉辦各種形式的非遺項目展示宣傳活動。廣大群眾在節日和紀念日多姿多彩的展示活動中,近距離與非遺大師接觸,感受非遺文化的獨特魅力。
2.非遺傳播方式的多元化
北京近年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方式上進行許多有益嘗試,體現多角度、多層次、多形式的特點。2014年1月,北京首家專門進行非遺演出的“龍在天非遺小劇場” 在海淀區舉辦掛牌儀式,這種小劇場模式表演方式靈活,開展活動便利,有利于培育市場,為京城非遺項目提供一個很好的發展空間。攝影、視頻、電影等也是非遺重要的傳播途徑,通過影像方式,藝術化地呈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各種面貌。除攝影展之外,非遺文化還借助微電影和紀錄片等形式進行傳播。隨著微電影逐漸流行,許多非遺項目也尋求利用微電影來講述非遺背后的故事,傳遞非遺濃郁的文化氛圍。這些代表老北京文化精髓的非遺項目在片中活色生香,喚起年青一代對中國傳統非遺文化的熱愛,加入到弘揚傳統文化的行列中來。電視臺則通過拍攝紀錄片,講述北京非遺歷史與文化。2014年,北京電視臺名牌欄目《這里是北京》持續關注北京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專集的形式聚焦天橋中幡、六郎莊五虎棍、京西太平鼓、東岳廟廟會等非遺項目,取得極佳的社會傳播效果。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的問題分析
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工作逐年穩步發展,但需要正視一些問題的存在,有些問題屬于歷史存在的體制性痼疾,有些則屬現實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老問題常談常新,其內在矛盾和存在方式年年都有新變化;新問題往往和老問題因果相連,需結合現實找準問題癥結,以尋求合理的解決之道。
(一)非遺文化現代轉換障礙重重
過去我們一直強調保留非遺文化的原汁原味,強調本色、原色和傳統價值,然而非遺文化面向真正的現實社會時,卻難以繞開現代轉換的問題。在現實傳播工作中,一方面強調非遺活態文化特性,另一方面卻不肯承認融入現代元素的必要性,事實上就是走進了死胡同。
北京是傳統與現代交織的都市,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在現代生活中留有一席之地,必須將傳統文化精神與現代生活方式對接,比如傳統花會表演借鑒現代演藝方式;對非遺小吃進行必要的改進,以適應現代人不斷變化的口味;對傳統武術和舞蹈技藝進行簡化,以符合現代人日常健身需要。這種變化雖在有些地方悄然進行,但很多非遺資源仍然處于沉睡和半沉睡狀態,并未真正融入現代都市生活,與時代潮流同步,其中原因一方面是非遺文化改造的意識不強,另一方面是非遺文化現代轉換的辦法不多,使得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面對現代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沖擊時,難以形成相對強勢的文化支撐與掌控能力,從而在都市生活中形成真正有影響力的文化生活方式。
(二)非遺項目管理部門溝通不暢
北京作為全國文化中心,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部門多、層級復雜、條塊分割現象較為嚴重,非遺管理部門包括國家級部門、市級以及區縣級部門,甚至深入到街道社區,不少部門工作人員并沒有理順其中的權責劃分,而且缺乏溝通意識,往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活動開展帶來困擾。分析近年北京重要節慶所舉辦的各項非遺宣傳推廣活動,可以發現各部門各自為陣,互不溝通的現象時時存在,從全局來看則呈現出某種混亂無序的狀態。對于一些傳承人和傳承單位來說,具有不同的體制身份,接受不同層級文化部門的管理,這往往會導致非遺項目保護工作中部門撞車、地區爭搶的現象,而落實到具體的傳播工作時,常出現不同部門劃分地塊、推諉責任的現象,給資金使用、資源利用和文化整合帶來困擾。
(三)非遺資源圈地思維痼疾難消
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人的流傳而不是以物的存留為核心,是一種活態文化,具有很強的地域流動性。然而長期以來對非遺項目的行政劃片管理,將非遺項目的文化傳播范圍按行政區劃強行切割,造成一種排他性的圈地思維,給非遺文化的傳播傳承設置人為障礙。[2]從2014年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來分析,每個入選項目都標明申報地區,客觀上是出于非遺項目實際保護工作的需要,然而不少地方卻將非遺看成是本地獨享獨占的文化資源,守著自家一畝三分地,這就造成不少區縣節慶活動“年年歲歲花相似,同一臺戲唱十年”的情況,非遺項目的文化傳播范圍受到極大限制。
從文化傳播角度來看,非遺文化只有超越行政區劃的狹隘限制,才能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成為最廣大地區人們共同的文化財富。因此各地需要摒棄狹隘的地域意識,消除圈地思維的痼疾,提高文化資源共享意識,加強區域間協同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從現行的文化體制來看,這似乎需要走很長一段路。
(四)非遺文化品牌建設遭遇瓶頸
北京擁有雄厚的非遺文化品牌資源,包括眾多享譽海內外的傳統老字號,京劇、相聲等曲藝則是家喻戶曉。應該說,北京在非遺文化品牌建設上擁有許多先天優勢,而且一直比較重視品牌的管理維護,并且致力于開拓品牌建設的新領域,包括“北京小吃”打包申遺,提出“北京味道”、“北京禮物”等概念,建立專門的推廣渠道進行宣傳,試圖將北京各種非遺資源整合起來,形成具有辨識度和市場價值的文化品牌。
然而,近些年非遺文化品牌建設也屢屢遭遇瓶頸,主要表現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差距較大。對于北京來說,非遺品牌的辨識度并沒有隨著投入力度的加大而產生實質性提升,花費大量資金卻效果不彰,損耗許多精力卻很難找到著力點。許多非遺品牌認知度長期停留在固定水平線上,在市場上不溫不火,除全聚德烤鴨、同仁堂醫藥等原有的老字號品牌,并沒有新的非遺文化強勢品牌和拳頭產品涌現出來。深究其原因,首先是品牌戰略的制訂缺乏足夠的可操作性;其次,非遺文化的傳播過程創意不足;再次,不少非遺項目傳承人缺乏品牌意識,創建品牌的動力不夠;最后,相關部門“抓大放小”的思維使得資源過于集中,有發展潛力的非遺文化品牌得不到更多支持,這些因素涉及品牌建設的各個環節和參與品牌建設的各個群體,造成非遺文化品牌創建過程中的尷尬局面。
三、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的對策分析
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經過多年發展,已初步形成其市場基礎、管理系統和傳播渠道,然而文化傳播工作需要進一步更新觀念、進一步完善機制以及進一步改進傳播方法。聯系近年北京非遺保護與傳承具體情況來看,需要建立縱向的各級部門協調機制,深化橫向的區域聯合交流機制,在常規的非遺文化傳播工作之外,大膽嘗試貼近都市生活的非遺文化傳習方式以及符合當下流行文化的傳播方式。
(一)建立各級保護部門的協調機制
如前所述,北京非遺項目保護和管理部門不同程度地存在溝通渠道不暢的問題,給現實的保護與傳播工作帶來一定阻礙。換個角度來看,非遺保護部門多意味著資源優勢,但如果協調溝通不暢就會將優勢化為劣勢,成為非遺傳播的掣肘因素,因此建立各級部門的協調機制十分必要。首先要分清各級部門權責,在傳播工作中形成清晰的分工思路;其次,打破各級部門的圈地思維,在申遺和宣傳推廣的組織管理方面相互分享資源,共同發力;第三,保證各部門間信息通暢,運用部門網站和微博及時發布信息;第四,努力完善全市統一的非遺活動統籌運作和統一發布機制,比如每年的文化遺產日,北京文物局都要列表公布主要宣傳活動計劃,這種模式可進一步推廣完善,將傳統節日和文化遺產日等重要節慶活動由權威部門統一發布,不僅有利于溝通協調,還可以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第五,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的協調職能。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成立于2010年,為北京非遺保護的專門性部門,除非遺保護的常規工作,其還應該更多地承擔相關的溝通協調工作。
(二)嘗試開發品牌化的非遺綜合性演藝活動
北京歷來重視為演藝性非遺項目搭建多形式、多渠道的演出平臺,每年組織多場大型的非遺項目集中展演活動,還有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的小型演出。然而熱鬧的背后卻隱藏著品牌建設遭遇瓶頸的尷尬,許多非遺項目如天橋中幡等,雖亮相頻繁,但仍屬于零敲碎打,成為節慶文化和廣場文化的的點綴性元素,獨立的品牌效應不強,社會認知度相對較低。
在非遺品牌建設方面,可以借鑒張藝謀團隊的“印象”系列,嘗試類似“北京印象”的品牌性非遺文化商業演出,以北京代表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為骨,以京味文化為魂,以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演藝方式為血脈,將盧溝橋傳說等民間故事串聯起來,形成舞臺演繹的故事主線,糅合京劇、太極拳、抖空竹、京西太平鼓、傳統幻術等曲藝雜藝,整合包裝,加入現代聲光電等創意元素,在前門、南鑼鼓巷等歷史文化街區劃出專門地塊進行常態化的類“北京印象”演出。這種品牌化的大型演出不僅聚集人氣,也可帶動非演藝性非遺項目發展,比如演藝場所附近可以進行傳統飲食和非遺工藝品的展覽和售賣,這樣有利于北京非遺文化整體認知度的提升,從而促進北京旅游業的全面發展。
(三)建立適應現代都市生活的傳習方式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代傳承,需要建立開放的、符合現代社會生活發展變化的傳習方式,尤其是在北京這個現代都市,非遺文化的傳習方式更應該嘗試突破現有模式,面向更廣大的公眾,面向更廣闊的都市生活空間。比如2014年,北京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藝傳習方面出現一些新變化,2014年8月14-29日,西城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首次面向社會招募非遺傳承志愿者,最終從來自全國的400名候選人中選出42人,跟隨北京刻瓷、戲曲盔頭制作等5項非遺項目傳承人進行面對面學習,最終擇優進入正式傳承人序列。這種面向社會的傳承人遴選模式是一種可貴的探索。
然而從整體情況來看,北京非遺項目的傳習活動并沒有真正意義上走向大眾,融入現代生活,開放性和融合度都顯得差強人意。非遺文化保護與傳承不能遵循“文化鴕鳥主義”,關起門來自娛自樂,而是應該融入現代生活,融入大眾文化,體現都市氣派,緊跟時尚潮流,呈現出大眾化、時尚化、青春化的新面貌。
(四)嘗試借用流行文化運作和傳播方式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人們習慣將其與流行文化進行對照,甚至將兩者對立起來,其實站在歷史的角度來看,非遺在特定歷史時期往往也是一種流行文化,只不過隨著時代更替,時尚成為傳統,流行成為經典,其中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將非遺文化與流行文化割裂的思維已不適于當下文化發展的需要,相反,將非遺文化重新輸入流行元素,使其重新成為時尚潮流追捧的寵兒,這樣,非遺“活態”文化才真正地活在社會的機理之中,活在現代人的生活中。
鑒于這種思路,非遺項目的傳承可以嘗試借用當下流行文化的運作方式和傳播方式。[3]在運作方式上,可以借鑒近些年北京文藝演出市場流行的“小團隊+小劇場”模式,比如風靡京城的相聲團隊嘻哈包袱鋪和德云社等。在展示形式上,可以借用當下流行的動漫等形式來吸引人氣,增加傳播效果。“非遺的動漫化,使非遺以動漫影像的形式得到保存與表達……所以我們認為動漫能夠作為非遺的傳承與傳播的有效途徑之一。”[4]這對于非遺傳播具有積極的意義,起碼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輕人關注非遺,進而投身非遺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此外,在受眾人群上,非遺文化傳播需要深耕青年文化市場,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非遺項目傳承人甚至可以走偶像化、明星化路線,展現青春氣質,引領時尚潮流。
(五)充分利用互聯網媒介的傳播優勢
近年來,“互聯網+”概念的持續火熱,互聯網對于非遺文化傳播的重要意義越來越受到關注,有學者說:“(網絡)作為一種全新的公共領域,其提供的話語環境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與發展提供了全新的視角與舞臺。”[5]
在文化傳播領域,互聯網媒介早已是不可或缺的環節。事實上,北京利用互聯網進行非遺文化傳播走在了時代潮頭,文化局、文物局等職能部門都在網上發布大量非遺活動信息,不少熱門的非遺項目、非遺老字號、傳承人開通了微博微信,而且還有數量繁多的民間論壇、網絡自媒體等參與非遺文化的網絡傳播。通過互聯網,非遺文化傳播在線上線下形成互動,非遺文化活動更為活躍。然而,網絡也是一把雙刃劍,網絡信息龐雜萬端,真假難辨,如果缺少必要的監管,則容易導致虛假信息泛濫,傷害非遺文化的整體形象。因此,利用互聯網媒介進行非遺文化傳播,一方面要加強相關的網絡建設,鼓勵非遺項目和傳承人利用網絡進行宣傳,促進“互聯網+”全面落地,另一方面要凈化網絡環境,合理利用網絡媒介,讓網絡真正為文化傳播添上翅膀,助力非遺文化向全社會深度傳播。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工作是一個連續的、流動的過程,應該適應社會發展、因應時代變化、順應文化潮流。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背景下,非遺傳播工作更應該更新思路,積極變革,將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魅力展現在世人面前。
參考文獻:
[1](美)邁克爾·H.普羅瑟(何道寬譯).文化對話——跨文化傳播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4.
[2]黃仲山.反思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圈地思維[J].理論月刊,2015(10):61-65.
[3]黃仲山.“非遺”傳播應對接流行文化[N].光明日報:2015-8-19.
[4]陳少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動漫化傳承與傳播研究[M].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4:75.
[5]趙新艷.新媒介環境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中的媒介角色與傳播特點[J].新聞傳播,2011(8):65-66.
(責任編輯:陳丁力)
【中圖分類號】G1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6.03.015
作者簡介:黃仲山,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首都文化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文學博士,藝術學理論博士后,研究方向為城市文化、城市遺產保護等。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審美趣味變遷與文化權力演變關聯性研究”(14CZX062),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重點項目“文化中心城市發展戰略研究”(2014A2283),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重點項目“北京文化體制改革關鍵問題研究”(2014A1962)階段性成果。
Analysis on the Highlights and Problem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Beijing’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uang Zhongshan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of Beijing’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ve developed steadily. There are many noteworthy highlights including the expansion of vision and reach of culture, and the updating of the mod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many new and old problems such as ineffectiv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departments, constructing cultural brands, and so on. We need to further open our mind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keep up with the times, and open a new chapter for Beijing culture.
Key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vision of culture; the mod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