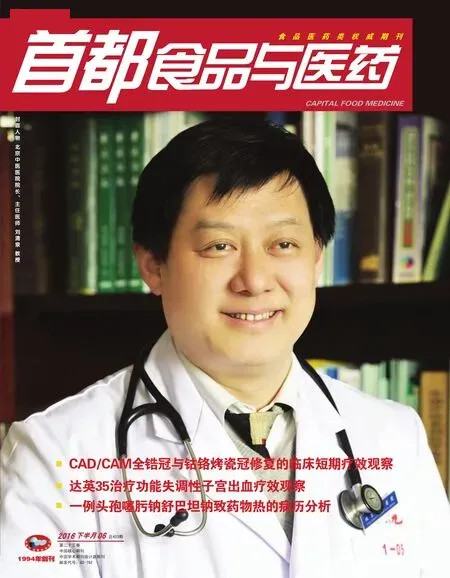一例頭孢噻肟鈉舒巴坦鈉致藥物熱的病歷分析
北京京煤集團(tuán)總醫(yī)院(102300)陶麗源 張麗超 李健 馬輝
頭孢噻肟鈉舒巴坦鈉為三代頭孢聯(lián)合β-內(nèi)酰胺酶抑制劑的復(fù)合制劑,臨床上可用于許多革蘭陽性菌和陰性菌的感染。由于該類藥物具備了廣譜抗菌藥物以及β-內(nèi)酰胺酶抑制劑的雙重特征,在臨床上得到了廣泛的應(yīng)用。藥物熱發(fā)生率最高的藥物是抗菌藥物,下面簡(jiǎn)述并分析討論一例頭孢噻肟鈉舒巴坦鈉致藥物熱的確診病歷,探討藥物熱的診斷要點(diǎn)、臨床特征及處理原則,為臨床醫(yī)師準(zhǔn)確診斷藥物熱,正確處理藥物熱提供參考及注意事項(xiàng)。
1 病歷摘要
1.1 病史資料患者,男,77歲,主因“咳喘加重伴胸痛3天,發(fā)熱1天”于2015年7月25日收入我院。入院查體:體溫:38.6℃,脈搏:82次/分,呼吸:23次/分,血壓:13.30/7.98kPa。雙肺呼吸音粗,可聞及散在干濕性啰音。既往史:“II期煤工塵肺”診斷史20多年;2014年10月診斷右側(cè)支氣管肺癌鱗癌(T2N0MX),無藥物過敏史。診斷:①煤工塵肺合并感染;②右側(cè)支氣管肺癌鱗癌(T2N0Mx)
1.2 治療過程 患者入院后頭孢噻肟鈉舒巴坦鈉皮試陰性,給予該藥抗感染,甲潑尼龍琥珀酸鈉解痙平喘,以及祛痰、抗腫瘤的輔助治療。入院后患者體溫恢復(fù)正常,但訴咳喘癥狀未見減輕,并出現(xiàn)黃痰,7月29日復(fù)查血常規(guī),WBC9.7×109/L↑,N%72.1%,白細(xì)胞偏高,停用頭孢噻肟舒巴坦鈉,換用美羅培南0.5g,q8h加強(qiáng)抗感染治療14天,咳喘減輕,8月11日將美羅培南更換回頭孢噻肟鈉舒巴坦鈉抗感染,換藥當(dāng)天患者又出現(xiàn)發(fā)熱,最高38.5℃,8月13日,即入院第20天行氬氦刀減瘤手術(shù),術(shù)后咳出黑色分泌物并再次出現(xiàn)發(fā)熱,午后為著,最高39℃,伴寒戰(zhàn)。主管醫(yī)師考慮發(fā)熱原因與其手術(shù)對(duì)腫瘤組織的破壞而導(dǎo)致吸收熱有關(guān)。但觀察3天后患者體溫未見明顯下降,復(fù)查胸部CT示“右肺上葉前段占位,內(nèi)部壞死,比較2015年6月29日CT病變?cè)龃蟆保瑥?fù)查血常規(guī):WBC9.1×109/L,N%78.1↑,中性粒細(xì)胞比例偏高,不排除感染加重,于是將頭孢噻肟鈉舒巴坦鈉換為頭孢哌酮鈉舒巴坦,但體溫?zé)o變化,仍每天午后出現(xiàn)發(fā)熱。8月19日和8月20日患者因家中有事出院2天,病人訴出院后體溫恢復(fù)正常。8月21日再次入院,繼續(xù)給予孢噻肟鈉舒巴坦鈉抗感染,體溫又再次升高,后停用,體溫恢復(fù)正常。
2 病歷分析
藥物熱的診斷尚缺乏特異性標(biāo)準(zhǔn),主要依靠排除診斷、回顧性診斷和再激發(fā)試驗(yàn)[1]。因藥物熱最易與感染性發(fā)熱混淆,故排除感染性發(fā)熱是診斷藥物熱的前提;回顧性診斷是對(duì)患者停用可疑藥物后體溫的變化情況進(jìn)行觀察,如體溫下降或恢復(fù)正常,則很可能是藥物熱;再激發(fā)試驗(yàn)是確診藥物熱的依據(jù)。
醫(yī)師考慮該患者發(fā)熱主要是感染性因素,但是血常規(guī)白細(xì)胞和中性粒細(xì)胞百分比升高不明顯,未復(fù)查降鈣素原和C反應(yīng)蛋白等感染性相關(guān)指標(biāo),雖然復(fù)查胸部CT示“右肺上葉前段占位,內(nèi)部壞死,比較2015年6月29日CT病變?cè)龃蟆保⒉荒芘懦悄[瘤的進(jìn)展,故該患者診斷為感染性發(fā)熱證據(jù)并不充分。停用頭孢噻肟鈉舒巴坦換用頭孢哌酮舒巴坦后,因二者藥物有共同的成分——舒巴坦,因此患者體溫?zé)o變化,也可能因?yàn)榛颊咛幱诟呙魻顟B(tài),故接連對(duì)多種靜脈制劑過敏,停用所有靜脈制劑后,患者體溫恢復(fù)正常。此時(shí)應(yīng)考慮患者發(fā)熱很可能是藥物熱。但患者再次入院后繼續(xù)給與頭孢噻肟鈉舒巴坦鈉,結(jié)果再次發(fā)熱,停用后體溫又恢復(fù)正常,故該患者藥物再激發(fā)陽性,因此藥物熱可明確診斷。
3 討論
藥物熱的診斷不易,特別是不伴皮疹、關(guān)節(jié)痛等其他過敏癥狀者尤為困難,常致誤診為原感染未被控制,從而加大用藥劑量、聯(lián)合用藥、長(zhǎng)療程使用多種抗菌藥物,既干擾正確診斷,又延誤病情。該患者即屬于這種情況,只有發(fā)熱癥狀,不伴皮疹、嗜酸細(xì)胞升高等過敏癥狀,因此誤診,將藥物熱與感染性發(fā)熱混淆,延誤了疾病的治療。
對(duì)于抗菌藥物致藥物熱的診斷,劉正印在《藥物熱40例臨床分析》[2]中建議針對(duì)感染性疾病,在應(yīng)用抗菌藥物后,體溫一度下降后又升高,或者體溫不降反升,如果患者的發(fā)熱不能用原有的感染來解釋,且無繼發(fā)感染的證據(jù)時(shí),應(yīng)考慮藥物熱的可能。當(dāng)考慮藥物熱時(shí),應(yīng)停用可疑致熱藥物,在判斷可疑藥物時(shí),需根據(jù)患者發(fā)熱與用藥的時(shí)間相關(guān)性。藥物熱可以發(fā)生在治療過程的任意時(shí)間點(diǎn),不同種類藥物差異較大,中位發(fā)生時(shí)間為用藥后7~10d,如果患者以前用過該藥,當(dāng)再次用藥時(shí)藥物熱可于數(shù)小時(shí)內(nèi)很快發(fā)生。有文獻(xiàn)報(bào)道,抗生素發(fā)生藥物熱中位數(shù)6d,平均7.8d[3]。另外判斷可疑藥物時(shí),還需根據(jù)引起藥物熱的藥物的流行病學(xué),何代洲[4]對(duì)2004~2011年藥物熱的報(bào)道文獻(xiàn)進(jìn)行分析總結(jié),引起藥物熱最常見的藥物是抗菌藥物,其次分別是中藥制劑和神經(jīng)系統(tǒng)用藥,中藥注射劑因受制備工藝(提取方法、提取設(shè)備)的限制,在其提取過程中并不能將一些雜質(zhì)如植物蛋白、多肽等完全去除,他們具有抗原性,易引起藥物過敏[5]。停用可疑藥物后體溫可逐漸下降,并多于1~2天內(nèi)體溫降至正常,半衰期長(zhǎng)的藥物可能需要相應(yīng)長(zhǎng)的時(shí)間退熱,如磺胺異惡唑一般在停藥4~5d方退熱[3]。對(duì)于接受多種藥物治療出現(xiàn)可疑藥物熱的患者,也可每2~3d停用一種藥物,首先停用最易引起藥物熱的藥物,并密切觀察體溫變化與停藥的關(guān)系。對(duì)于嚴(yán)重的高熱患者,如疾病允許,應(yīng)果斷停用所有藥物。停用可疑藥物后,避免應(yīng)用結(jié)構(gòu)近似的藥物,另外如果可能避免停藥后加用任何靜脈制劑,因?yàn)榇藭r(shí)患者可能為高敏狀態(tài),對(duì)多種藥物過敏。本患者在停用頭孢噻肟鈉舒巴坦后應(yīng)用頭孢哌酮舒巴坦,體溫?zé)o明顯變化,可能與頭孢菌素間存在交叉過敏有關(guān),也可能與二者存在共同的成分——舒巴坦,也可能患者處于高敏狀態(tài),對(duì)多種抗生素過敏。關(guān)于藥物熱的再激發(fā)試驗(yàn),該試驗(yàn)本身可引起超高熱,給患者帶來痛苦甚至危及生命,因此,一般不宜采用[2]。但如果對(duì)于接受多種藥物治療出現(xiàn)可疑藥物熱的患者,停用全部藥物待體溫正常后,再對(duì)治療有重要作用的藥物,可以在嚴(yán)密監(jiān)視下,分別試用,對(duì)有的患者再次使用某類藥物后,發(fā)熱更高時(shí),應(yīng)考慮其藥物熱之可能。
回顧該病歷,該患者發(fā)生藥物熱的不良反應(yīng),可能與抗生素應(yīng)用療程過長(zhǎng),不合理應(yīng)用抗菌藥物有關(guān),根據(jù)《抗菌藥物臨床應(yīng)用指導(dǎo)原則2015》,抗菌藥物療程因感染不同而異,一般宜用至體溫正常、癥狀消退后的72~96小時(shí),針對(duì)普通的肺部感染,不宜將肺部陰影完全吸收作為停用抗菌藥物的指征。因此建議臨床醫(yī)生應(yīng)按照《抗菌藥物臨床應(yīng)用指導(dǎo)原則》和相應(yīng)疾病治療指南合理應(yīng)用抗菌藥物,應(yīng)有明確的感染適應(yīng)癥,根據(jù)感染部位,感染嚴(yán)重程度選擇合理的抗生素,采用合理的用法、用量,并根據(jù)疾病制定合理的用藥療程,合理應(yīng)用抗菌藥物從而減少抗菌藥物的不良反應(y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