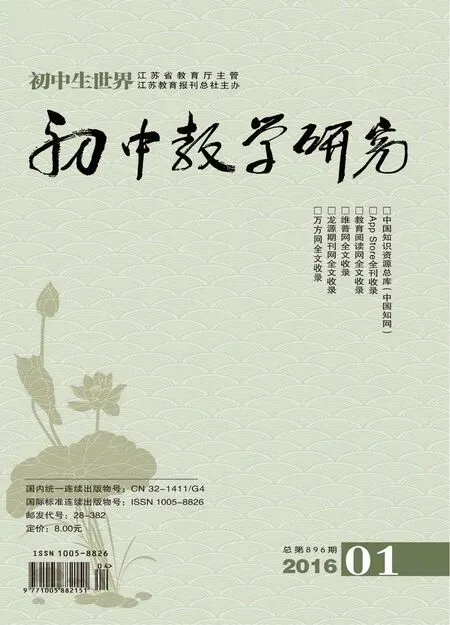淺談文言文教學的“一體四面”——兼評俞永軍、甄方園兩位老師的同題異構課《山市》
■張寧生
?
淺談文言文教學的“一體四面”——兼評俞永軍、甄方園兩位老師的同題異構課《山市》
■張寧生
《山市》是蒲松齡寫的一篇文言文,篇幅短小,文筆優美,思路清晰,構思精巧。聽了俞永軍、甄方園兩位老師的同題異構課后,我深有感觸,對文言文課堂教學有了新的體會。
文言文是以“文言”這種古代書面語寫成的文章,包括先秦時期的作品以及后世歷代文人模仿先秦書面語寫成的作品。
文言文教學是初中語文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和現代文教學相比,文言文教學是“語文教學改革的一個‘死角’”(錢夢龍語)。長期以來,我們的初中文言文教學都處于模式單一、枯燥乏味的狀態,大多數教師在教學時只注重對字詞句章的條分縷析,過多強調“字字落實,句句清楚”式的割裂分析,缺乏古今互動、師生互動,嚴重地扼殺了文言文自身的生命力,不能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自主性與積極性。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對初中階段的文言文教學提出了更高的教學要求和評價要求:“誦讀古代詩詞,閱讀淺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釋和工具書理解基本內容。注重積累、感悟和運用,提高自己的欣賞品位。”“背誦優秀詩文80篇(段)。”“評價學生閱讀古代詩詞和淺易文言文,重點考察學生的記誦積累,考察他們能否憑借注釋和工具書理解詩文大意。詞法、句法等方面的概念不作為考試內容。”因此,我們要以上述標準作為評價文言文教學的指南。
文言文教學教什么?王榮生老師指出,在文言文中,“文言”“文章”“文學”和“文化”一體四面、相輔相成。其中,“文言”層次最淺,“文化”層次最高。但“文言”是基礎,沒有對“言”的理解,就談不上對后面三個內容的把握。
下面,我就從這“四面”談談我對這兩節課的理解。
文言與現代漢語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詞匯和語法方面。
俞老師和甄老師都非常重視對“文言”的教學,在疏通詞句上花了20多分鐘時間。其中,俞老師從字音、字形、詞義等方面進行了細致的強調;甄老師則提綱挈領地從古今異義、通假現象、斷句、譯句4個方面分層次引導學生學習。在字詞教學上,兩位老師都突出了學法指導:俞老師指導學生圈點批注、根據語境推斷讀音、借助注釋和工具書理解句義;甄老師教給了學生“注、順、讀”的方法,并且有創意地將一段文字的標點去掉讓學生斷句,直指文言文教學的精髓。此外,兩位老師均重視利用學生已有的體驗來學習新的詞語,例如講解“惟危樓一座”中的“危”字時,都提到了李白的詩句“危樓高百尺”,以此幫助學生加深對詞語的理解。這樣的文言文教學,可謂“貼在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
文章,即章法結構。《山市》在結構安排上頗具特色,通讀全文可以發現文章有兩條線:一是時間線——“忽→無何→未幾→忽→既而→逾時→倏忽”,寫出了山市由現而滅的過程,表現了其變幻莫測的特點;二是作者的情感線,“忽見(驚喜之情)→相顧驚疑(回扣“忽見”,因為“忽見”,所以不得不驚;但想到“無此禪院”,所以驚奇疑惑)→始悟(恍然大悟后的輕松釋然)→居然(意外之喜)→遂不可見(遺憾惋惜),蒲松齡巧妙地在描寫中引入了自己的主觀感受。在這一點上,俞老師下了功夫,引領學生細致揣摩、品味。
文學,這里指一篇文章的表現形式,教者應引導學生通過斟酌詞句,提高欣賞品位和審美情趣。
蒲松齡筆下的山市是奇美的。
一是“奇”。奇在無中生有,奐山數年不見山市,現在山頭卻忽然出現了孤塔;奇在孤塔不是漸漸隱現,而是突然聳起;奇在孤塔雖是撲朔迷離的虛像,卻看似直指云天的實景;奇在孤塔不孤,在它周圍又豎起數十所宮殿;奇在景中有城,有樓,有人煙、市肆。
二是美。我們可以透過文字想象以下圖景:城內房舍幢幢,有一高樓直接云端;樓外碧空晴天,樓內窗明幾凈,人影綽綽。宋代詩人梅堯臣說:“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寓于言外。”作者如果能夠把不容易捕捉到的景物描繪得形象逼真,讓讀者看了以后仿佛親臨一般,就表明他有著高超的寫景藝術。兩位老師在課堂上雖然都提到了奇美,卻沒能讓學生涵泳吟誦一番,感受這奇美的景象,個人認為,這是兩節課的遺憾。
文化,在文言文中有多層面的體現。
首先,文言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體現,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語言,兩者的同一程度超過了人們的任何想象。
其次,文言和文言文體現了傳統的思維方式。如《魚我所欲也》偏重比喻論證,《鄒忌諷齊王納諫》偏重類比論證,都體現了偏于感性的民族思維方式。
再次,文言文傳達了中國古代仁人賢士的情意與思想,即“言志”“載道”。我認為,文言文教學應從“文化母題”中建構文化。關于“母題”,歌德說它是人類過去不斷重復,今后還會繼續重復的精神現象。還有人認為“母題”實際上就是原型,是一種典型的、反復出現的意象,是有助于整合統一我們文學經驗的象征。我的理解是,最早的文學作品中出現了某種情景、旨趣、事件、人物,以后,這些內容不斷地出現重復,甚至成了后代文學作品中的基本要素,這就是“母題”。可供我們參考的傳統文學母題有:文人登高、名士傷懷、閨婦思親、客子羈愁、親友惜別、官宦感時等。這些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直接體現,也是初中生文言文學習的主要方面。
《山市》這篇文章的文化內涵更多地體現在蒲松齡在文章中所表現出的情意思想上。對此,兩位老師都非常精當地在自己的課堂設計中融入了對作者情意思想的解讀:《聊齋志異》敘述的是非現實的、虛幻的人和事,這與蒲松齡困窘的生活、仕途失意的身世有著密切的關系,他是借幻境之美來表達對黑暗現實的憤懣。兩位老師能夠突出知人論世的教學原則,上升到文化層面解讀文本,看得出他們解讀文本的深厚功底。
總之,兩位老師的課雖是“異構”,但有共通之處,那就是都在課堂教學中努力體現語文教學的至高境界:
廣博——縱橫捭闔,左右逢源,信手拈來,旁征博引,妙趣橫生,給學生帶來一路春風;
獨到——獨具慧眼,對教材有真知灼見,能夠于平凡中見新奇,發人所未發;
深刻——一針見血,入木三分,把教材的編寫意圖看穿、看透,挖掘出教材的精髓、內涵。
(作者為江蘇省特級教師,教授級中學高級教師,現任教于江蘇省淮安外國語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