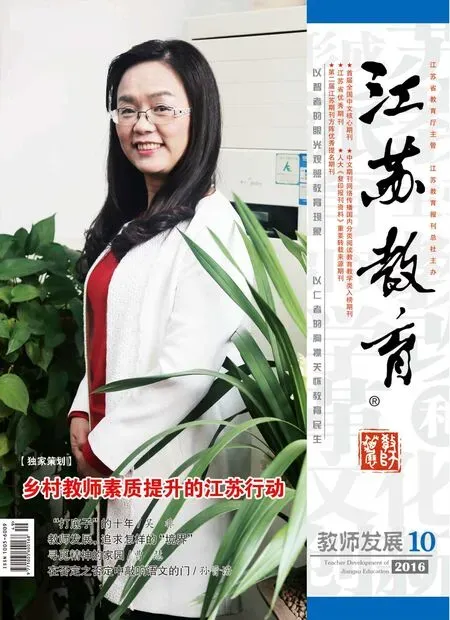做“懶螞蟻”,也為自己出主意
馮衛東
·馮衛東專欄:一線教師如何做教科研·
做“懶螞蟻”,也為自己出主意
馮衛東
“懶螞蟻”喻指群體里出謀劃策的人物,其行為有鮮明而強烈的向他性、利他性。教師也要做做“懶螞蟻”,首先為自己出主意,謀劃教育人生,進而有序、優效地推進個人事業,努力成為“智慧型行者”或“行動型智者”。
“懶螞蟻”;學、思、研、判;智慧型行者;行動型智者
一
我是在原無錫市蠡園中學校長、現就職于溫州翔宇教育研究院的邱華國先生《學校里的“懶螞蟻”在哪里?》一文中第一次讀到“懶螞蟻”這個詞的:日本一家生物研究所發現,在一群螞蟻中,總有少數螞蟻不像其他同伴那樣辛勤地搬運食物,它們東張西望,好像在觀察和研究著什么,而當食物來源或取食通道失去或被堵截時,原先忙碌的螞蟻們無計可施,“懶螞蟻”卻大展才智,把大家導向新食源,并使失控的秩序恢復到井然狀態……后來有機會多次在不同書刊中見到“懶螞蟻”的“芳蹤”。這些“懶螞蟻”無一例外喻指群體里出謀劃策的角色,他們雖然不是直接的生產力因素,卻發揮著許多一般因素所不能產生也無法比擬的巨大效力。在復雜性越來越成為經濟生產、教學生活等領域共同規律、共性傾向的當下,倘若徒有不息奔命的“勞人”,而沒有運籌帷幄的智者,那么,組織效率的低下,生產效益的低迷,教學效果的低劣,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我們理當寬容“懶螞蟻”的存在,尊重其價值,以一種與時俱進的人才觀審視其獨特的生存方式、“行為藝術”,甚或熱情期盼、呼喚與迎接他們的“誕生”與到來。
上述理念是許多開明豁達人士的共識。我也是這樣想的,有時還自詡為南通教育在教師專業發展、隊伍建設方面的一只“懶螞蟻”:雖說不是忙碌于教學一線,雖說不是躬耕于三尺講臺,卻總喜歡抽空去教室里,到師生中,從一種較為專業的視角,以一種較為理性的眼光觀察課堂現象,發現存在問題,然后展開對話、協商,提出改進結構的策略,或優化細節的技巧,使許多教師有所啟迪,獲得進步。“懶螞蟻”就是這樣,是冷靜的旁觀者,也是清醒的發現者;是事實的分析者,也是智慧的貢獻者;是方向的引導者,也是行為的促進者……他們往往以一種看似邊緣的身份和力量而存在,實則參與到了某些教育行為的核心區域,助推它的變革,引發它“靜悄悄的革命”。
由此看來,“懶螞蟻”都有鮮明而強烈的向他性、利他性。然而,作為個體的人,他首先是屬己、利己的,只有在屬己亦利己的基礎上,才能屬于大眾,利于他人。基于此,我既希望廣大教育同仁中涌現出更多智慧滿滿的“懶螞蟻”,更倡導,這些“懶螞蟻”也為自己想心事,拿方略,精心謀劃、反思、斟酌和優化自我行為,不斷提高個人行為的科學水平和智慧程度,實實在在地讓自己先成為一名“智慧型行者”或“行動型智者”。
一言以蔽,做“懶螞蟻”,也為自己出主意。
二
我的理由是——
其一,只有做“懶螞蟻”、為自己出主意的教師,才能是一個有“主腦”的人;而一個缺乏“主腦”的教師,他的行為一定是雜亂無章、高耗低效的。
“主腦”出自清代戲劇理論家李漁筆下,他在《閑情偶記》一書中提出“立主腦”的概念,說“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腦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王夫之也有言:“文以意為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一出戲劇、一篇文章的寫作尚且如此,需要明確的命意、清晰的謀劃,更何況我們一直在從事的工作,一生在開展的事業?我們也許一輩子都是教師隊伍中的普通一員,沒有機會領導別人,卻總要“領導”自己,管理好個人工作或事業中的諸多元素、方方面面。如果沒有一點做“懶螞蟻”的必要耐心、自覺意識和基本能力,那肯定不能“經營”好自己,更遑論“經營”好一個班級的學業質量、一群學生的心智發展。說到底,我們起碼要“做一個有主意的教師”,起碼要做一個能不時用個人較好的“主意”去統領自我行為的“懶螞蟻”,沒有這些,就沒有主心骨,也將失去立足講臺的力量和資格。
其二,“求人不如求己”,不為自己做“懶螞蟻”,卻寄望于別人,這既有悖于專業自立精神,也不能贏得“被求者”的尊重與慷慨。先“求己”再“求人”,乃是處世與處事之道,也是與外界“懶螞蟻”實現互惠共進的一條重要“游戲規則”。
在 “教師即研究者”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的當下,每個教師都必須學會先琢磨好自己的事情。我們可以信賴專家、同道,卻不可以依賴他們。一味依賴智者、匍匐于高人陰影之下的教師,只能亦步亦趨,機械模仿,食而不化,而不能形成、擁有真正的和較為深刻的研究,真正的和較為豐富的經驗。“我的課堂我作主”,其實,這句話、這個理念的背后還有一層意思——“我的思考(研究)我作主”。沒有自我思考的主宰,沒有自我研究的主導,所有的課堂舉止都只能是死守葫蘆的“畫瓢藝術”,抑或受制他人的“玩偶行為”。
“上山打虎易,開口求人難”,在許多事情都要仰仗集體力量、眾人智慧才能開展和完成的今天,我們必須打破這一傳統觀念,善于相機“求人”,樂于適當“借腦”。當然,只有先斬獲一些真正屬己的體驗、經驗和思想,然后才能擁有自信、底氣和勇氣,讓“開口求人”不再難,進而得體有效地“求人”;也才能擁有“分享智慧,收獲更多”的充實與快樂,并不斷提高個人在群體生活和共同事業中的貢獻率。
其三,倘要為他人做“懶螞蟻”,那首先也要為自己做并且力爭做好“懶螞蟻”,一個不屑于或不善于“從我做起”的人,根本不可能具有折服、影響和改變他人內心及行為的能力。要做深孚眾望的“懶螞蟻”,必須以自己的思想和行為為“試驗田”,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實證精神,也是一種自信信人(使人相信)的人格力量。
人們大多有成為他人智囊、高參,讓自己的才智在更多人那里贏得青睞和產生價值的欲望和追求,有做他人的“懶螞蟻”甚或好為人師的心理訴求,這無可厚非,關鍵有兩點:一是不要強把己見當人見,強人所難;一是盡可能審慎考量作為“懶螞蟻”,自己的意見、觀點是否妥當、熨帖,能否有益于他人“為正確而行動”(一位著名教育官員演講的題目)。而要使之妥當、熨帖,進而有助于他人“走向正確”,往往有一個必要前提、先決條件,那就是,在“懶螞蟻”自身加以實施、得以“確證”。一般而言,能在自己身上妥加實施、獲得“確證”的東西也適于他人,反之亦然。由此看來,“懶螞蟻”要有負責精神,這又首先是對自己的負責與盡責。
三
那么,怎樣為自己做“懶螞蟻”,又怎樣才能做好自己的“懶螞蟻”呢?我有幾點建議:
首先,要“眼睛朝外”,加強學習,多去汲取周邊和更廣大范圍內一些專家、智者(特別是有影響力的“懶螞蟻”)的經驗、理論和智慧,“轉益多師為吾師”,進而擁有做好“懶螞蟻”、做“好懶螞蟻”的底氣、底蘊和精神底色。
“懶螞蟻”看似是一個人在那里悄悄地琢磨事兒,不動聲色,而實際上卻要調動很多過往的積累、經驗積淀,調動很多知識資本、智力因素,一個小小的“點子”背后往往是經年累月的學習、實踐、觀察、思考和研究之結晶的有效支持、有力支撐,絕不要期望任何一個靈感、任何一種創意會垂青于沒有準備、空空如也的大腦。“貨真價實”的“懶螞蟻”在貢獻智慧、表現才華的顯性“A面”以外必定有砥礪功力、厚積薄發的隱性“B面”;先把“B面”做好,再來謀劃、實施“A面”的事亦不晚,即便晚了,這“B面”也還是一份不得不交的作業,終究回避不了。
《弟子規》云:“不力行,但學文,長浮華,成何人?但力行,不學文,任己見,昧理真。”“力行”與“學文”都是“懶螞蟻”的必修課。“學文”之途多矣,讀書則為主要途徑,這一點留待下篇專門去說。
其次,要有“教學研一體化”的意識、能力和習慣,使之成為個人樂此不疲、“揮之不去”的一種職業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常態。努力做到,教就在學,教就在研,學促進教,研提升學……努力做到,正式研究或非正式研究的“全息性”和全程化,盡可能保持對“研”的深度浸入和高度卷入,在不斷研究中一點點塑就“懶螞蟻”之“金身”。
“教學研一體化”也可以說由我首倡,通過“百度”搜索,能看到直接有關這五個字的若干網頁、信息,但大都是高校或職業教育的研究人員發表(布)的。基礎教育的施教對象大多是未成年的兒童,兒童心靈是充滿奧秘的黑箱,施教于他們時,尤其要常常學、時時研。在此方面,年輕教師更要及早形成這樣的教學品性與教育品質,不使之占滿心房,就會有另一些消極品性、不利品質長驅直入。學校及年輕教師自己要形成一種“倒逼機制”,力研不輟。我與一所學校合作開展“經歷教育”實踐研究,其中有一個重要專題即是“青年教師的‘經歷教研’”,倡導和要求新教師、年輕人在集體備課之前先行充分自備,原則是“歡迎成功,擁抱失敗(指課堂內容把握不準、教學設計不夠合理等情形),只要努力,就是勝利”。我們認為,對于歷練不多、經驗較少的年輕人,自我鉆研、獨立備課中所遭遇的困頓、錯誤、挫折和教訓本身就是未來教學經驗的磨刀石、后續教育智慧的墊腳石,自有價值,彌足珍貴。相信如此“倒逼”之下,每一個勤勉的年輕人都能夠將外學內化,同時學會 “與自己對話”(日本教育家佐藤學所倡導的四種“對話式學習”方式之首),進而漸漸成為足智多謀的“懶螞蟻”;他今后的教育教學行為也將隨之由過去更多的 “算術級增長”而趨向于 “幾何級增長”,此時的“裂變效應”恰恰是“懶螞蟻”優效思維的效力之所在。
再次,不吝“劃撥”一些時間,讓自己“有閑”去做“懶螞蟻”;甚至無妨“浪費時間”,讓自己發一會兒“呆”。這一定是“得能償失”的,因為它能“以時間換空間”——思維拓展、思想發展的無形而又無限的空間;因為它能讓人從“不會”到“會”,而“忙者不會,會者不忙”……
“懶”意味著悠然與閑散,從來不曾見過任何一個“懶人”行色匆匆,忙忙碌碌。“懶螞蟻”亦如此,他有優裕的時光——經濟學中有“帕累托法則”,也稱“二八定律”,仿此,似乎亦可將20%左右的工作時間用于做“懶螞蟻”,專事拿主意、出計謀及相關的一些活動——有悠閑的節奏,有“慢工出細活”的手法,當然也有“該出手時就出手”的膽識。他們懶中有勤,外懶內勤,形懶實勤,懶亦為了勤,而勤則在思維、思想,在謀篇、布局,在想活化全盤的高招,出優化結構的妙方,在致力于把“精氣神”用到點子上,又在點子上激活“精神氣”,等等。印第安人說,“讓腳步等一等自己的靈魂”;猶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倡導“止步思維”(stop and think),亦即從活動之中抽出身來,在活動之外審視、深思活動本身;我國古人也說,“大智知止”……的確,當我們開始懂得并善于把握“等待藝術”“止步策略”時,就有了點“懶螞蟻”的味道與氣質,此刻的“呆”其實是一種“意義充溢的沉默”(佐藤學語),也是一種別具意味的“呆萌”——發呆,卻讓優質的思維、優秀的思想從腦際萌生。
最后,特別在自己步入“高原”或身陷“迷局”時,要自我提醒,切勿“一往無前”地“低頭拉車”,而要“昂起高貴的頭顱”,為自己做“懶螞蟻”。把現實厘清,把對策想明,把前路照亮,再去行動,“高原”就將成為“高峰”,“迷局”也能化作“勝境”。
以我為例。2004年成為一名專職教科研人員之始,我便立志做一名優秀學者,后來幾年進步確實非常顯著,有了一批科研成果,但隨之而來的是,由于未曾受過專門學術訓練,也沒有機會再到高校或更高級科研機構深造,理論視點與視野都有較大局限,使做一名“書齋學者”的夙愿難圓。一陣郁悶、糾結、彷徨之后,“靜夜思”自身優長與短處,決計走“理論下嫁”“科研普及”的“中間道路”,在理論與實踐之間雙向建構。“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我認真謀劃其后一段時期的“全局”,較為出彩地在幾個課題、若干問題域之間做了一些新事、實事和益事,也使自己收獲了一點點知名度和影響力。倘若沒有那幾晚輾轉反側的“靜夜思”,我則難以取得其后的工作進步、事業起色。與其講,這是一條“自我救贖”之路,毋寧說,是腦子里的那只“懶螞蟻”成了個人教育生活中的“關鍵他人”“生命貴人”……
上面談的是為自己做做“懶螞蟻”的若干方法與要領,未必在同一個邏輯層面上,有的有交集,最終都指向于學、思、研、判,它們既是“懶螞蟻”的工作內容,也是其生存方式,還是他們的生命特質。慣于如此行走的人,他們定然是優秀的“懶螞蟻”,除了自身受益,還將普惠他人。
四
著名作家關仁山談及“農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日頭》時說,主人公金沐灶“仰望星空的姿態,代表時代的良心”。為自己做“懶螞蟻”,也是這樣的一種“姿態”,它也能代表我們的“教育良心”。
G451
B
1005-6009(2016)49-0046-03
馮衛東,江蘇省南通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江蘇南通,226000)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