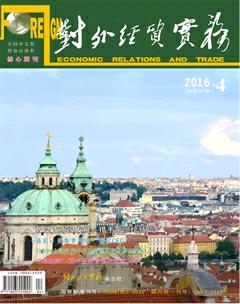加快推進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鉆石10年”的探討
張維 馬敏象 常冬
2013年10月,李克強總理在第10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上提出要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使中國與東盟之間貨物貿易達到1萬億美元,投資達到1500億美元,開啟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的“鉆石10年”。目前,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談判已在第13次中國—東盟經貿部長會議上正式啟動,對中國來說,順應國際國內發展大勢,充分挖掘雙方潛力,選擇適宜的路徑與東盟國家深化經貿合作,不僅有利于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也有利于東盟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實現雙邊合作的互利共贏。
一、中國深化與東盟經貿合作面臨的機遇
(一)中國國家戰略實施開辟了深化合作的新境界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壓力較大,產能相對過剩,支撐中國過去高速發展的土地、能源、水體、礦藏進一步萎縮,環境承載力進一步下降,創新實施跨區域經貿合作,加強國際尤其是與周邊東盟國家的產能合作,在原有貿易基礎上構建新的國際價值鏈、技術鏈和產業鏈分工格局,是實現發展要素的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積極開拓新興市場,推動經濟社會轉型升級成為必然選擇,有助于推動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實現從貨物貿易向深化區域經貿合作的全面提升。東盟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個樞紐,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將有助于發揮地緣政治優勢,推進跨境貿易與產能合作,一方面通過打破國內的限制,使資源要素在更大的范圍自由流動,市場機制在更深的層次發揮作用;另一方面通過構筑綜合立體大通道,根據東盟各國特點優化產業合作布局、推動當地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二)東盟經濟一體化進程拓寬了深化合作空間和領域
近年來東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東盟經濟共同體藍圖》中列出的506項優先措施中,463項已經落實,完成率達到91.5%,東盟內部平均關稅稅率幾乎降至零。東盟的老六國(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已實現99.65%產品零關稅,新四國(越南、柬埔寨、老撾和緬甸)98.86%產品關稅稅率已降至5%以下,域內汽車、紡織、林業等多個產業加速融合,在建立單一市場、統一生產基地等方面取得了切實進步,在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依然遲緩背景下,東盟新興經濟體在市場規模、購買力和勞動力方面的巨大潛力顯得十分突出。同時,東盟奉行“大國均衡”戰略,謀求在國際舞臺更多的話語權,提出了包含中國在內的“10+6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的廣域一體化經貿合作模式,這一模式的實現既可以通過貨物貿易初始出價模式創新擴大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貨物貿易成果,又可以在服務貿易、投資市場準入減讓模式達成一致,擴大中國和東盟的市場準入,有利于深化雙邊的經貿合作。目前,中國與東盟各方正全力推動2016年內盡快結束RCEP協定談判。
(三)中國與東盟戰略關系升級將深化雙邊經貿合作
2013年中國—東盟特別外長會議,就打造中國與東盟戰略關系升級版達成共識,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瀾滄江—湄公河對話機制等經貿關系全面升級,將通過打造“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深化雙方互利合作:一是通過基金設立和新型投融資機制,以“互聯互通”建設推動貿易便利化、結構性和監管改革、交通物流便利化等創新合作;二是啟動對話和磋商機制,探討包括服務業便捷化在內的新的自由化政策,將從宏觀調控層面進行調控,彌補單純降低關稅和市場作用方面的不足;三是通過進一步減少敏感及高度敏感產品清單數量,提高貿易便利化、投資自由化和經貿合作承諾水平,使中國與東盟各國得以充分挖掘市場潛力;四是按“負面清單”和“準入前國民待遇”原則談判開放安排,提升投資和服務領域的開放水平,提升傳統簡單的產業間互補性貨物貿易結構,推動產業內分工,構建跨境區域性產業鏈,增加貿易附加價值。
二、中國深化與東盟經貿合作也存在諸多挑戰
(一)全球財富東移過程中多種力量正競相爭奪東盟市場
首先,美國實施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其先后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參加2011年東盟峰會,高調重返東南亞;通過介入南海和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框架,不斷鞏固與日本、菲律賓的軍事同盟關系,插手南海事務,是挑起南海爭端的幕后推手;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通過全免關稅區框架,將有利于東盟內的少數國家與北美區的貿易和投資,大幅削弱中國對東盟傳統的貿易優勢。
其次,日本繼續把東盟作為對外戰略的重點。其對東南亞展開全方位的外交,一方面積極推進“日本—東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AJCEP)建設,鞏固原產于日本的高附加值產品在東盟加工成終產品等產業內貿易布局;另一方面積極推行所謂“價值觀外交”,積極介入南海事務,拉攏菲律賓、越南等,加大對緬甸滲透的力度,以基礎設施建設、示范計劃、政策咨詢等公共產品提供和發展援助不斷擴大影響力。
再次,印度繼續推動“東向政策”,依托孟印緬斯泰經濟合作組織、湄公河—恒河經濟合作組織等平臺,在基礎設施建設、農業、旅游業及新能源等領域,發展與東盟尤其是越南、緬甸等國的關系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印度—東盟自由貿易協議(CEPA)從 2010年開始逐步取消80%的關稅稅目,同時允許印度和東盟國家根據本國實際,將部分敏感產品排除在關稅減讓或取消清單之外,雙邊貿易總額在2022年將達到2000億美元。
(二)來自內部的不利因素增加阻礙了雙邊經貿合作的深化
其一是中國與東盟各國部分產業結構相似,存在同質競爭,比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在機電裝備等資本密集型制造業領域,越南、柬埔寨等在紡織鞋襪等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領域,都與中國對東盟傳統互補型貿易存在同質競爭。再加上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建設20年多年來,東盟內部貿易年均增長10.5%,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5%,東盟內部貿易增速已超東盟國家與域外國家間貿易,隨著東盟共同體的建成,預計到2020年內部貿易占東盟貿易總額的比重將至30%,將會削弱與中國的貿易總量。
其二是東盟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容易產生利益分歧。貿易保護主義在一定范圍依然存在,部分東盟國家為保護本國重要和敏感產業,在關稅壁壘不斷降低的同時設置了非關稅壁壘。比如,印度尼西亞、泰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對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員國的進口商品設置了諸如技術標準壁壘和綠色壁壘,提升了中國向東盟出口商品的技術附加值。
其三是部分東盟國家內政更迭,產生社會動蕩,引起經貿合作的變數。比如,中泰大宗商品貿易(蔬菜換石油)和中泰鐵路建設等受泰國政壇紛爭的嚴重影響;緬甸政權更迭和地方武裝沖突對中緬重大經濟合作項目、中國在緬北的替代種植計劃、邊境口岸和跨境公路運輸正常運轉等都產生負面影響。加上南海爭議存在升級可能,將直接導致其對華政策不友好,影響雙方深化經貿往來。
三、深化與東盟經貿合作的國別路徑選擇
(一)對新加坡的合作路徑
對發展程度高于中國的新加坡,宜采用雙向交互滲透策略,歡迎新加坡推廣蘇州工業園、天津生態城建設成功經驗,在中國的中西部尤其是臨海產業園和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發面開展政府間項目合作;依托新加坡海外第二大人民幣離岸中心和航運貿易等國際化平臺,鼓勵更多中國企業在新加坡融資上市、設立區域總部、開展跨國并購,并通過新加坡向東盟其他國家擴展;充分發揮中國資金和工程建設經驗和新加坡在建設環境友好型項目享有的聲譽,組成聯合競標體到東盟第三國承攬項目和進行產業園開發。
(二)對文萊、馬來西亞、泰國的合作路徑
對于處于轉型階段的文萊、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宜采取開發策略,充分發揮企業市場開拓能力,在文萊的鐵路和電廠建設、鋼鐵、建筑、日用化工品、農業優質高產等領域,在馬來西亞的基礎設施、石化、農副產品深加工及食品制造、生物技術、人力資源引進與培養等領域,在泰國的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石化、機床制造、水電燃油、日用品制造等領域形成需求發現,依托華商等市場進入渠道,形成新辦市場的合作路徑。
(三)對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的合作路徑
對于處于成長階段的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宜采取延伸策略,引導有條件的企業把總部留在國內,在印尼、菲按生產要素配置和優化布局生產線,通過跨國公司、戰略和技術聯盟、特許經營等方式,延長成熟技術的生命周期,帶動設備、原材料進出口,并規避貿易壁壘;支持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選址以商建園,建設中國—東盟經濟開發區、科技產業園、農業示范園等,開展兩頭在外的全產業鏈建設。
(四)對越南、柬埔寨、緬甸、老撾的合作路徑
對于處于起步階段的越南、柬埔寨、緬甸、老撾等國家,宜采取多元化策略,發揮中國在資金密集型的電力和建筑行業總包的強項,針對上述國家電站電廠、高速公路、港口碼頭等亟待建設的情況,鼓勵有條件的企業承包大型工程,促進企業到東盟國家開展服務貿易和投資,形成中國管理輸出、資金輸出和品牌擴展的創新合作路徑;利用與部分新四國接壤的條件,加快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探索創新應用“PPP”新模式,充分發揮“境內關外”的優勢,規避貿易反傾銷;同時加大對上述國家在應對自然災害和氣候變化、改善發展環境、人員培訓和教育等民生領域提供援助、貸款和能力建設幫助。
四、深化與東盟經貿合作的對策建議
(一)體現大國風范,充分尊重和幫助東盟
在東盟已將對話機制向全球鋪開的情況下,積極開展多邊務實外交,增多與美、日、印、韓、澳、新(西蘭)等就東盟經貿關系上交流溝通頻次,尊重東盟主導東盟事務,倡導亞洲人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合作的進程。同時,中國要以包容的大國心態淡化與東盟的分歧,在應對南海問題上政經分開,在經濟上加大與南海諸國的往來,實現經貿多邊化、多樣化和區域化。另外,大力推進軟實力經貿合作,多為周邊東盟國家提供務實的安全和公共產品,在打擊跨國犯罪、聯合緝毒、保護航道安全以及應對氣候變化、能源短缺、環境惡化、防災減災、非傳統安全領域加強合作,增進與東盟諸國的親緣和友善。
(二)順應后零關稅發展趨勢,積極推進服務升級版建設
主要包括:一要提升通關便利化服務,強化國內“區區”聯動大通關協作,加快推動對東盟業務經認證的經營者(AEO)地位和跨境“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互認制度,加快與東盟開展原產地證書聯網管理協作,擴大綠色通道、無紙化報檢、直通放行實施范圍,在對東盟國家陸路邊境貿易中推動“一口岸、多通道”模式創新。二要強化跨境現代流通體系建設,充分發揮與東盟國家陸水聯通的優勢,積極推進公路網、航空網、能源網、水網、互聯網等五大互聯互通基礎網絡建設,加快推進中泰高鐵、泛亞鐵路、安全湄公河水道等建設,培育對東盟貿易綜合化的快捷物流體系。三要在對東盟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基礎上加快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建設,借鑒新加坡淡馬錫和日本ADB對東盟業務經驗,首先關注于東盟新四國基礎和公共設施融資項目,然后拓展到產業項目,利用信貸、證券、信托等手段,開展多種形式的跨境金融模式探索。
(三)優化對東盟貿易結構,擴大基礎設施的投資
我國企業要通過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進一步優化對東盟貿易的產品結構,避免同質競爭;要從過去由單純追求數量擴張向注重質量轉變,由附加值低為主商品向附加值高為主商品轉變,由貨物貿易為主向服務貿易和投資相結合拉動貨物貿易的方向轉變。尤其是對欠發達東盟國家,要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加大對其基礎設施的投資;包括高速公路、鐵路、港口以及水利、電力等項目;同時,對發達東盟國家也要注重服務貿易和投資合作推動產業升級和技術改造。以加快推動東盟一體化建設。東盟的一體化以及東盟經濟的迅速發展,是中國與東盟深化經貿合作的基礎,也是加快推進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磚石10年的重要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