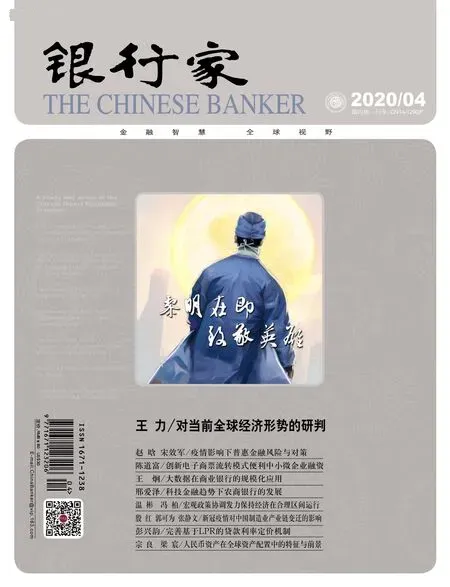供給側結構改革的著眼點
王松奇
在世界歷史上,許多偉大事業往往是由偶然因素決定的,少年時自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時,就常常被偶然和必然的關系攪得頭暈腦脹,現在年紀大了,對到底是偶然之中有必然,還是必然之中有偶然越發想不清楚。就拿現今最流行的詞匯“供給側改革”來說,它的誕生與成長軌跡就讓人感到不問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據報道,中國于2012年冒出了一個“中國式新供給經濟學派”,學派的主要成員是: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深圳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李萬壽,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副司長姚余棟,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黃劍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培林,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副研究員李宏瑾。他們的“立派宣言”是一篇名為《中國式新供給經濟學》(以下簡稱《賈文》)的文章,該文曾刊載于2012年第34期《財經》雜志上,該文篇幅不長,線索清晰,主要分三部分:1.傳統供給管理學派的沿革;2.需求管理政策效用減弱;3.改革需要新的理論基礎,其政策主張表述為“雙創雙化雙減”。雙創:創新與創業;雙化:城鎮化與產業優化;雙減:減稅與減少行政審批。該課題組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如何能得到決策層的注意呢?據本人了解,中國民生銀行董事長洪崎在使中國式供給學派的研究成果“上達天聽”方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是他通過一定管道將該課題組文章送達王滬寧和寧吉手里,這兩位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智囊總管在將一個課題組的理論建議轉化為這樣直接推行的重大決策方面起到了催化作用。于是便有了克強總理在2014年年初冬季達沃斯論壇上那個著名的雙引擎構想演講,便有了2015年11月10日上午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講的“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有了2016年1月27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首次寫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此,幾位有才華的經濟學家的一個課題成果終于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擬在十三五計劃時期系統推行的改革政策。這其中,到底有多少偶然因素在起作用,故事的發生又有多少必然成分,我們實在說不清楚。
《財經》2012年第34期刊登的那篇文章,我猜一定是該課題組成果的刪節版,因為其內容過于粗略,無論從理論、實踐還是政策建議方面都有許多待討論的話題。
例如:
1.從經濟思想史角度,《賈文》關于傳統供給管理學派沿革的概括性敘述似乎頗有漏洞。
2.需求管理政策效用減弱這一事實人所共知,但對世界上任何體制類型的市場經濟體來說都是一樣——需求永遠是經濟增長的引擎。
3.政策建議應當講清實施前提和具體實施路徑,例如“減稅”一條,美國供給學派理念被里根接受以后,在其競選綱領中都十分明確地提出減哪些稅,減稅幅度有多大,這樣的減稅幅度對聯邦政府的預算收入影響幾何,等等。
總之,如果僅以《財經》2012年第34期刊登的《賈文》為分析藍本,我們的確可以看出許多有欠周全之處,但話說回來,一群中青年學者的一個課題成果,能對中央決策層的理論用語、政策舉措以及官方語境產生如此之大的影響力,這在中國這么多年的經濟學研究成果的實踐作用中也堪稱奇跡。
最近一年來,決策層在接受了中國式新供給學派的政策建議后又將政策主張總結為“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在落實過程中,我們看到,已在各個方面碰到了一些新的問題。以去產能為例,去產能是為解決中國許多產業如鋼鐵、煤炭、造船、電解鋁等重化工業產能嚴重過剩的問題,要讓一些僵尸企業不再耗費經濟資源,這似乎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但人們發現,僵尸企業大多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因為缺少政府的“父愛”其死亡與否都無關宏旨,沒有人會在對其救助上不計成本地進行資源傾斜,所以本質上,民企在市場經濟中的進入退出生生死死是一種自動決定機制,只有國有企業才會讓政府瞻前顧后地從就業、社會穩定等方方面面考慮去做銀行的工作對其不斷輸血打氣,維持其死而不僵的狀態。從這一經濟現實出發,我們就可以深入思考一個問題,即供給側結構改革的著眼點究竟應該在哪里?
如果有人說將國企改革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這算得上是讓討論進入到正確方向,如果進一步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任務就是要實施國退民進重新構建中國的微觀經濟基礎,我認為,這樣答案才算充實完滿。就像我們在討論降耗降污節能減排問題上直接用發展服務業用發揮國內消費需求的引擎作用實際上就是用產業結構調整來達到目的一樣,對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用大無畏的精神進行重新構造就像上個世紀90年代朱镕基大刀闊斧對國企進行關停并轉的做法一樣,實際上是用最簡單的措施解決了去過剩產能、滅僵尸企業的問題。
問題如此簡單,邏輯如此清晰,我們那些聰明絕頂的大內高手們會想不到嗎?我猜想,將重構中國微觀經濟基礎嵌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框架內不會有技術障礙,阻力可能在觀念上。例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改革60條》里對公有經濟國有經濟的表述以及那個看起來不偏不倚天衣無縫的“兩個毫不動搖”的結論性表態,肯定會讓人不敢再重提國退民進這種近乎不識時務的老話題。
其實,只要對國企和民企進行一下資金使用效益比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的主攻方向應當是什么。中國加入WTO后世界上一些重要經濟體尚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中國的決策層包括經濟理論界的許多人都認為中國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這件事我們實際上可以當成個中性事件不摻雜任何意識形態色彩地認真傾聽一下外部聲音即它們為什么認為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國家。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國有經濟比重、國企享受的傾斜性政策資源等問題。如果我們自己也能有一個豁達開放的心態,思想無教條禁區,而將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進行改革改造甚至出售,國家財政包袱就會小許多。同樣的事,國有企業能干,民營企業也能干而且干得更好,那就莫不如誰干得好就讓誰干。很多很多年以前,“四人幫”曾鼓吹,“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樣的話讓現在的年輕人聽起來頗具腦殘風格,但在那個左傾橫行左棍跋扈的動亂歲月,這樣的左傾口號就是大有市場。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50周年,我覺得思想理論工作者都應該認真對那場浩劫進行一些教訓總結,對我們國家左右傾特別是行之有年的左傾思潮的危害進行重新思考。我們面前碰到的許多問題有時候就是一層一捅就破的窗戶紙,捅破了說開了,我們就會豁然開朗,我覺得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眼點這個問題上情形也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