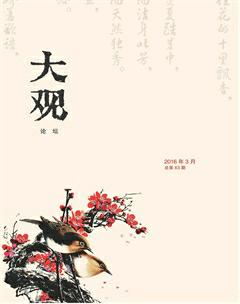封閉社會下的階層固化
摘要:本文通過對《不平等的日本——告別全民中產(chǎn)社會》一書的評析,揭示當(dāng)今日本的社會結(jié)構(gòu)。近些年來,日本的社會階層流動不夠順暢。在職業(yè)領(lǐng)域,代際繼承性日益增強,正逐漸形成 “努力了也沒用”的社會,即“封閉”的社會。基于這一社會形態(tài),本文將進一步探討日本社會未來的出路與走向。
關(guān)鍵詞:封閉社會;階層固化;不平等
在戰(zhàn)前日本社會,“只要努力就有辦法”是理想,“努力了也沒用”是現(xiàn)實。隨著戰(zhàn)后經(jīng)濟的高速增長,“只要努力就有辦法”迅速成為現(xiàn)實。國民中有七成人都回答自己的社會地位是“中中”,形成了一個全民中產(chǎn)社會,這是戰(zhàn)后對日本社會的常識性看法。但是本書對全民中產(chǎn)社會的觀點提出了質(zhì)疑,認為戰(zhàn)后日本社會的具有雙重基礎(chǔ),即 “只要努力就有辦法”和“努力了也沒用”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高速增長期,日本與戰(zhàn)前相比確實成了“只要努力就有辦法”的社會,即“開放”的社會。但近些年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這種開放性卻在急劇喪失。父母與子女間的地位繼承性日益增強,正逐漸形成比戰(zhàn)前尤甚的“努力了也沒用”的社會,即“封閉”的社會。
一、“學(xué)歷社會”下的階層固化與階級再生產(chǎn)
當(dāng)今的日本人希望越努力的人得到的應(yīng)該越多,而現(xiàn)實是業(yè)績越多的人得到的越多。但是業(yè)績往往不等于個人努力,而取決于論資排輩的企業(yè)人力資源制度和文化資本的代際繼承。由于日本企業(yè)人事制度中幾乎沒有降等的說法,雖然常有人遭降級或靠邊站,可很少會從管理層或?qū)I(yè)型工作降到事務(wù)型或藍領(lǐng)工作。也就是說上層白領(lǐng)這一地位本身十分穩(wěn)固,其業(yè)績或收入也會隨著年齡的底線在不斷提高。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種“論資排輩”的現(xiàn)象。另外,業(yè)績主義者的父親學(xué)歷往往比較高,他們的高學(xué)歷是與父親的高學(xué)歷一脈相承的。也就是說,信奉業(yè)績主義的人是否果真只靠自己的力量奮斗成功?他們是否果真生活在“只要努力就有辦法”的世界。答案是否定的,這其實是代際繼承或傳承的結(jié)果。“只要努力就有辦法”是當(dāng)今日本人的愿望,但是業(yè)績主義思想是當(dāng)今日本的現(xiàn)實,但是這種業(yè)績主義下的地位獲得不是真正的取決于業(yè)績,而是由許多既定因素決定的,但又披著業(yè)績主義的外衣。因此,許多下層民眾還是讓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參加學(xué)校和公司的選拔,結(jié)果只能是失敗,疑慮和無形的屏障。
從代際流動角度看社會,社會可以分為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假若一個社會里子女都和父母從事同樣的工作,那至少從就業(yè)路徑這一點來說,就是一個“努力了有沒用”的封閉社會。不管父母從事什么職業(yè),都不影響本人的職業(yè)狀況,那么這個社會的階層流動是順暢的,屬于開放社會。而日本每十年舉行的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全國官方調(diào)查顯示“日本社會正逐步走向開放”,也就是說日本逐漸變成“只要努力就有辦法”的社會。另外在1970年總理府“關(guān)于國民生活輿論調(diào)查”中,回答屬于“中等”的比例已經(jīng)超過了總?cè)藬?shù)的九成。自此,所謂1億人“全民中產(chǎn)”的社會開始固化為日本代表的社會形象。上述結(jié)論實質(zhì)是數(shù)據(jù)陷阱和新中間大眾論的錯覺。因為日本戰(zhàn)后的高學(xué)歷化發(fā)展迅速,越是年輕人,學(xué)歷越高。但是作為年輕人,他們履歷很短,不能進入管理層,因此收入并不高,職業(yè)聲望也不高。戰(zhàn)后出生的白領(lǐng)階層開放性也已經(jīng)開始失去,又回到了戰(zhàn)前相仿的“努力了也沒用”的社會形態(tài)。上層白領(lǐng)的代際再生產(chǎn)的高速增長期也并未消失。“學(xué)歷社會”,一般的理解是重視學(xué)歷的社會,這似乎很自然,但日本社會的“學(xué)歷”還具有更深刻的意義。上層白領(lǐng)的再生產(chǎn)不論是學(xué)歷水平也好,職業(yè)地位提升也好,都必定會通過本人努力這一途徑。但是,日本上層白領(lǐng)的“本人努力”絕不僅僅取決于本人自身的努力,而是受父母職業(yè)、學(xué)歷和家庭社會地位的影響。上層白領(lǐng)為了將父母的學(xué)歷和職業(yè)之類的資產(chǎn)從名義上洗掉,他們刻意的傾向于業(yè)績主義,希望借此顯示自己的地位乃源于自己的實力。從而使自己的地位依靠業(yè)績主義得以正當(dāng)化,并且使得努力主義看起來好像是“失敗者的強詞奪理”。
二、從開放社會到封閉社會的轉(zhuǎn)化路徑
二戰(zhàn)后至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之前,日本可以說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和中產(chǎn)會,這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第一,二戰(zhàn)前階層再生產(chǎn)現(xiàn)象比較顯現(xiàn),只要你擁有高學(xué)歷,父母屬于上層白領(lǐng)階層,會比較容易得從事專業(yè)型和管理型工作。而在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以后,則是需要在圍繞學(xué)歷競爭和提升競爭力的過程中經(jīng)歷漫長時間之后才逐漸被再生產(chǎn)出來,上層白領(lǐng)的再生產(chǎn)逐漸變得模糊不清了。第二,在這一階段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xiàn)象:下層藍領(lǐng)即半熟練和非熟練藍領(lǐng)出身者跨越了白領(lǐng)與藍領(lǐng)之間的界限,到40歲時藍領(lǐng)也有機會可以從事上層白領(lǐng)的職業(yè)。第三,學(xué)歷—升遷的路徑開放了,戰(zhàn)后生活水平的提高拓寬了躋身上層白領(lǐng)層的主要道路。另外,戰(zhàn)后另一種從上層藍領(lǐng)或下層藍領(lǐng)職業(yè)走向自雇職業(yè)上升路徑也被打通了。總之,上層白領(lǐng)再生產(chǎn)的隱形化、白領(lǐng)/藍領(lǐng)界限的破除、以及從藍領(lǐng)雇傭職業(yè)上升至自雇傭職業(yè)這三點,構(gòu)成了戰(zhàn)后的階層化社會即所謂“戰(zhàn)后階層化”日本的特征,也可以稱為“戰(zhàn)后型階層—流動模式”。
從20世界80年代中期以后,“作為可能性的中產(chǎn)”開始走向消亡了。各種各樣的問題顯露出來。通過選拔實現(xiàn)的上層白領(lǐng)的再生產(chǎn)日益明顯,除此之外的上升機會大幅度縮減。不僅如此,另一條從上層藍領(lǐng)職業(yè)流動向自雇職業(yè)的上升路徑也被阻塞,在升任上層白領(lǐng)這一主要路徑的內(nèi)部失去了開放性的同時,不做上層白領(lǐng)也能晉升這種路徑形式自身的開放性也在逐漸喪失。特別是父母地位與本人地位的結(jié)合強度急劇增加。自80年代下半期開始,上層白領(lǐng)處于一種封閉化的狀態(tài),甚至稱為“知識階級”也不為過。這樣就會使得上層白領(lǐng)的代際再生產(chǎn)有擴大收入及資產(chǎn)差距的效果,上層白領(lǐng)的繼承性又幾乎回到了戰(zhàn)前的水平,再考慮到父親的地位再生產(chǎn)對資產(chǎn)的影響,可以說總體的經(jīng)濟差距反而在加倍擴大。
上述兩種不同的結(jié)果基于兩種社會動力機制。一是開放的動力機制,成為開放動力的是戰(zhàn)后經(jīng)濟發(fā)展所帶來的絕對生活水平的提高,及貧困程度的降低。絕對富裕程度增長,教育費用的負擔(dān)相對減輕,因缺錢而失去上學(xué)機會的孩子與戰(zhàn)前相比有所減少,那些以往無法加入競爭行列的人們也得參與進來。結(jié)果,從外部流入上層白領(lǐng)職業(yè)的人數(shù)增多,從而提高了上層白領(lǐng)職業(yè)領(lǐng)域的開放性。二是封閉的動力機制,成為封閉力量的是上層白領(lǐng)這一職業(yè)自身強大的再生產(chǎn)能力,也就是所謂的“龍生龍,鳳生鳳”。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期,由于經(jīng)濟高速增長期結(jié)束,管理層的崗位減少,選拔制度趨于飽和,封閉的動力開始出現(xiàn)。endprint
從歷史社會學(xué)的角度考察,“團塊代”成為了受日本社會轉(zhuǎn)型影響的重要一代,他們是指二戰(zhàn)后日本第一次“生育高峰期”當(dāng)中出現(xiàn)的人,此處結(jié)合研究需要,指代日本1936-1955年出生的人口。這一代還是學(xué)生時,是否是白領(lǐng)出身所造成的差距的確縮小了,可當(dāng)他們進入就業(yè)領(lǐng)域獲得相應(yīng)職業(yè)地位時候,確發(fā)生了上層白領(lǐng)層的封閉化。與這一代緊密相連的則是選拔制度的變化,選拔與其說是屏障,不如說是更接近一種游戲,因為他們不是考慮沖破障礙后要去做什么,而是跨越本身成為目的。也就是說為了選拔而選拔,為了考試而考試。日本的選拔考試分為筆試和面試或小論文,筆試相對公平,小論文和面試注重個性,只有那些與評判者個性、特點相近的人可以得高分,而這些人往往是大城市尤其是東京周圍高學(xué)歷家庭的孩子。筆試對上層白領(lǐng)的階級化傾向具有牽制作用,重視個性的面試和小論文反而加速了上層白領(lǐng)層的階級化。那些父母是高學(xué)歷的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或管理者,通過將自己文化存量向其下一代的轉(zhuǎn)移,使其子女獲得了高于其他階層子女的文化資本,在考試特別是面試或主觀考試中,具有較大優(yōu)勢。
對于“團塊代”群體來說,上升路徑縮減成單一的“學(xué)歷—升遷”型,非上層白領(lǐng)出身者的社會提升機會大幅度減少。即使本人已經(jīng)成為上層白領(lǐng),也會因為父親是否為上層白領(lǐng)而出現(xiàn)相當(dāng)大的差距。“昭和初代”,上層白領(lǐng)出身者的平均收入為60萬日元,“戰(zhàn)中代”以前的三代也同樣如此。“團塊代”,上層白領(lǐng)出身者的平均年收入為1000萬日元,而非上層白領(lǐng)出身者為812萬日元,差別非常大。“戰(zhàn)后式階層—流動模式”塑造的和緩的連續(xù)體逐步出現(xiàn)斷裂。階層分化如果按這種形勢發(fā)展下去,上層白領(lǐng)之外的人,甚至上層白領(lǐng)本身也會喪失對社會建制的信任。總之,日本正在經(jīng)歷從“只要努力就有辦法”的社會到“努力了也沒用”的社會,最終再到“沒有努力意愿”的社會。當(dāng)然,在上層藍領(lǐng)階層還是看到了新希望,盡管上層藍領(lǐng)從事自雇傭職業(yè)的路徑被堵塞。但是上層藍領(lǐng)流入上層白領(lǐng)職業(yè)中的專業(yè)型工作的很多。上層藍領(lǐng)出身者向?qū)I(yè)技術(shù)人員的轉(zhuǎn)變意味深長,對于創(chuàng)造出“戰(zhàn)后階層化”社會的同質(zhì)性與異質(zhì)性的組合,它具有大幅度改組的可能性。
三、重建日本社會的未來出路與走向
面對經(jīng)濟停滯,既往社會架構(gòu)分崩離析,許多人主張日本向美國式的產(chǎn)業(yè)社會和市場社會轉(zhuǎn)變。其實,日本社會與美國社會不同,美國擁有特殊的勞動力市場,一方面從全球網(wǎng)絡(luò)了優(yōu)秀的高智能型人才;另一方面又通過非法移民的形式輸入及其廉價的勞動力。日本如果轉(zhuǎn)向美國式的市場社會,還應(yīng)該明確指出勞動力流動屏障問題。即使解除移民問題,只要日本未變成比美國更有吸引力的移民去處,就只能增加“沒去成美國,所以才到日本”的人數(shù)而已。要實現(xiàn)美國式的市場社會,首先就有必要把日本的公用語變成英語,而且增加移民之后,對于圍繞民族問題發(fā)生激烈糾紛還要做好充分準備,另外廣泛的貧困層形成之后,犯罪也會頻繁發(fā)生。日本中產(chǎn)階級社會的再生處方只有從日本式產(chǎn)業(yè)社會當(dāng)中尋找,不要美國化和西歐化,哪怕冒未知的風(fēng)險,還是尋找出自己獨特的路徑更自在。循著這種思路,若要打破選拔型社會和產(chǎn)業(yè)社會的僵局,作為今后應(yīng)該著手開展的課題和對策。
首先,讓藍領(lǐng)出身者跨越白領(lǐng)——藍領(lǐng)界限,成為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一方面只選有能力的人承擔(dān)專業(yè)型工作,哪怕少也無妨;另一方面,讓公司或組織外面的人任職時,要有奏效機制。其次,導(dǎo)入了績效工資,個人提供自己的技能,企業(yè)提供品牌這種信任機制,再通過兩者結(jié)合所產(chǎn)生的效益加倍提高附加值。使公司和個人分享報酬,共擔(dān)風(fēng)險,模仿藍領(lǐng)系統(tǒng)機制來創(chuàng)造白領(lǐng)系統(tǒng)機制,也是一種有效的辦法。其次,需要重組“公司人”。過去,上層管理型白領(lǐng)只了解公司內(nèi)部世界的人,對公司沒有歸屬感,沒有責(zé)任感,做決定瞻前顧后、不搶最先、不落最后,慎重?zé)o比的模仿別人,形成了“封閉的”公司人。現(xiàn)在需要積極提供機會讓他們暫時離開公司,去參加志愿者等社會活動,或者在大學(xué)等機構(gòu)接受繼續(xù)教育,吸收了新的專業(yè)知識之后,可以轉(zhuǎn)做專業(yè)型工作,這也是恰當(dāng)?shù)娜肆Y源配置方式。再次,增加階層流動的路徑,一方面是社會總體增加目標,即增加上升路徑的種類與數(shù)量;另一方面是增加以個人為單位參與選拔挑戰(zhàn)的機會。將專業(yè)型工作與管理型工作分開,創(chuàng)造出一種可以更好地發(fā)揮各自特長的機制。決定選拔功能的大致框架的,理所當(dāng)然是教育同社會的關(guān)系。引起精英空洞化現(xiàn)象的原因是學(xué)校外部的選拔路徑日趨消亡,這個問題并非在教育改革內(nèi)部就能解決。即使教育進行改革,現(xiàn)有的選拔制度存在,仍然會產(chǎn)生大量的失敗者。要消除這種負面影響,只有停止選拔或再創(chuàng)造其他選拔路徑
四、結(jié)語
個人的底線是公平,市場的底線是效率,在現(xiàn)實生活中,某些情況下寧可犧牲效率也要保證公平,某些條件下哪怕犧牲公平也要堅持效率。但是至少不能忘記其中到底犧牲了什么。近年來,“實力本為”常常被人掛在嘴邊,結(jié)果卻常常止于空洞的口號。現(xiàn)實中學(xué)歷就是實力的代理指標,許多人認為學(xué)歷不能代表實力,但是難以找出比學(xué)歷更好的代理指標,即使找到,它仍然是代理指標,難以代表真正的實力,因為實力的復(fù)雜性決定了,實力很難被真正的測量。不實際調(diào)查每個人的背景差異,就不清楚是否已經(jīng)維護。而且,調(diào)查也是在人們通過選拔、競爭等各自得到財產(chǎn)和地位之后,也即社會資源的分配結(jié)束之后的事。另外,機會平等也無法直接、及時的被看到。機會不平等具有不確定性,因此一個建立在機會平等基礎(chǔ)上的社會,至少需要有監(jiān)督機會不平等的機制,以及一旦確認不公平就可以對收入進行再分配機制。在同一代人里,當(dāng)財產(chǎn)、地位分配之后發(fā)現(xiàn)不平等的情況下,安全網(wǎng)可以成為一種補償。在連續(xù)幾代人都造成機會不平等的時候,安全網(wǎng)也就失去了意義,因為這種長期的機會不平等糾正起來成本過高,代價過大。總之,希望在一個社會里,任何人只要取得成果堪稱成功,就都能挺起胸膛說“這是我自己的業(yè)績”。出身差異如果影響到每個人的業(yè)績,那就是不正當(dāng)競爭,只不過是場表演賽罷了。真正的“業(yè)績社會”,準確地說,就是感覺上更為公平的競爭社會,以及能夠?qū)ふ业竭x擇意義的選拔制度。
【參考文獻】
[1]佐藤俊樹.不平等的日本——告別全民中產(chǎn)社會[M].王奕紅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
[2]三浦展.階層是會遺傳的[M].蕭云菁譯.北京:現(xiàn)代出版社,2008.
作者簡介:徐京波(1983.09-),男,漢族,山東平度,鄭州市輕工業(yè)學(xué)院政法學(xué)院講師,校聘三級教授、社會學(xué)博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