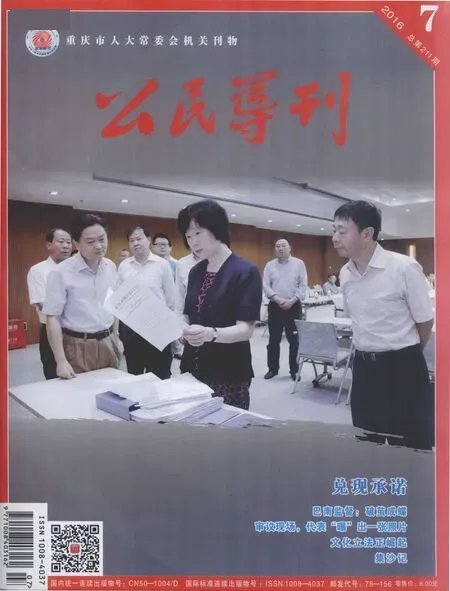家暴實(shí)質(zhì)是“一個公民對另一個公民施暴”
張育仁
家庭暴力怎么就屬于“私權(quán)自治”的范疇?不管什么樣的暴力,與文明社會的“私權(quán)自治”扯得上關(guān)系嗎?如果家暴可以用“私權(quán)自治”為由排斥公權(quán)干預(yù),那么,反家庭暴力法到底有多大的施展空間?
家庭暴力在幾乎所有國家都普遍存在,但是以怎樣的法律措施應(yīng)對和處置,比較而言我國在這方面還有一定的差距。
正是著眼于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于2015年12月27日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2016年3月1日起施行。媒體在報(bào)道時掩不住內(nèi)心的激動寫道:“這部法律將從整體上構(gòu)建起我國反家暴的組織架構(gòu)、預(yù)防機(jī)制和處置措施。”
在中國,家庭暴力案件近年來呈多發(fā)態(tài)勢,并且不斷惡化升級,嚴(yán)重破壞了家庭與社會的和諧。
打開網(wǎng)頁,有關(guān)家庭暴力的文字記錄紛至沓來,讓人喘不過氣。奇怪的是,在是否采用采取法律手段治理家暴時,上上下下又感到“非常棘手”。甚至有權(quán)威人士為之大吐苦水:“與其他暴力犯罪相比,家庭暴力犯罪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復(fù)雜性。”
可以說,在針對家暴問題時,無論是在專家的思維層面,還是公眾意識的層面,所存在的顧慮相當(dāng)明顯。我們的顧慮主要在于“清官難斷家務(wù)事”的親情思維上,處理起來有投鼠忌器之嫌。
十多年前,有一部電影《刮痧》,講述華人爺爺在孫子生病的時候,采用中國傳統(tǒng)的刮痧治療方式,將其孫子的背上刮得“傷痕累累”,因涉嫌家暴被鄰居報(bào)警,警察將爺爺抓捕到局子里。
這部電影讓中國觀眾大開眼界的同時,也普遍表示“不適”,認(rèn)為外國的法律實(shí)在是“小題大做、稀奇古怪”。
由此可見,我們在對家庭暴力的認(rèn)識方面確實(shí)是將自己搞得過分的“特殊”和“復(fù)雜”了,足見我們在此問題上法理意識之落后與混亂。
盡管社會各界一致贊同對家庭暴力進(jìn)行法律處置,可是,像發(fā)達(dá)國家那樣,把對妻子施暴的丈夫、對丈夫施暴的妻子,或者對兒女進(jìn)行暴力管教的父母抓起來,甚至投入牢獄,許多人還是覺得不太合適,強(qiáng)調(diào)“國情有別”。
如果是鄰居或者路人舉報(bào)家庭暴力,導(dǎo)致施暴者鋃鐺入獄,普遍反應(yīng)是,這些人在“多管閑事”。甚至有專家也居然認(rèn)為“這些案件涉及到公權(quán)干預(yù)與私權(quán)自治的界限把握。”
家庭暴力怎么就屬于“私權(quán)自治”的范疇?不管什么樣的暴力,與文明社會的“私權(quán)自治”扯得上關(guān)系嗎?如果家暴可以用“私權(quán)自治”為由排斥公權(quán)干預(yù),那么,我們期待的反家庭暴力法到底有多大的施展空間?
其實(shí),我們的困擾主要是來自上上下下對家庭暴力的實(shí)質(zhì)認(rèn)識不清,對為什么要從國家層面制定反家庭暴力法認(rèn)識不清。包括許多執(zhí)法者在內(nèi),更多是停留在所謂親情的狹隘層面。直白地說:在現(xiàn)代文明體系中,國家面對的是一個個具體的公民。
不管這個施暴者的家庭身份是什么,只要是施暴,從國家法律的視角來看,其實(shí)質(zhì)都是“一個公民對另一個公民施暴!”惟有全社會將認(rèn)識提升到這種文明的層面,所謂的“特殊性”和“復(fù)雜性”就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