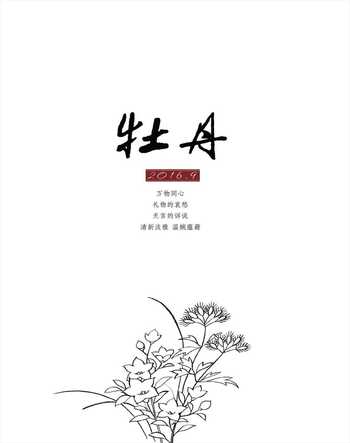淺談儒家詩教觀
高會燕
儒家“詩教觀”由來已久,從孔子到后來的儒家學者,都推崇其“詩教觀”。儒家詩教觀對后世的社會生活產生重大影響,其本身也具有獨特的文藝學意義。
一、先秦儒家之“詩教”觀
“詩教觀”由來已久,最初只包含在樂教之中,自春秋戰國禮樂崩壞之時,詩教的地位才比樂教的地位高些。詩教雖是一個歷史概念,但歷來人們對它的認識不一。在讀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等著作時,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及“詩教”。基于此,筆者就儒家“詩教觀”展開論述。
“詩教”一詞最早出現于《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這一段話提到,詩教為六藝之首,其基本精神為“溫柔敦厚”。而對詩教的定義,則指的是詩的教化作用和社會功能,是儒家學者通過總結《詩經》的內容、性質和社會作用而提出的一種重要的文學主張。這在孔子的經典著作《論語》中大量提到。《詩》成為孔子教導學生的重要教材。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可見孔子認為《詩》的思想主旨純正無邪,是人們通向學者的必由之路。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在孔子教導學生的過程中,也多引用《詩經》里的原話。孔子十分看重《詩》,甚至把《詩》作為自己的一個信仰。孔子曾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詩》是基本,所有的事情都需從詩開始,只有立好根基,才能長成參天大樹。孔子這樣談論《詩》的功能:“《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因此,“興觀群怨”之說為各家引用。《詩》可以抒發人的思想感情,可以觀察風俗民情政治得失,可以交往朋友,可以諷刺評論不平的事情。而且近則可以用來侍養父母,遠則可以用來侍奉君主,并且可以認識許多鳥獸草木的名稱。孔子也曾對其兒子孔鯉說過:“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如果不學習《詩經·國風》里的《周南》《召南》兩部分,就像是面對著墻壁站著無法前進。
在《孟子》《荀子》等書籍中,大多情況下是把《詩》當作解釋說明的工具。《孟子》《荀子》中引用詩的共同點在于大部分是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且涉及國家政治及個人道德修養。在《孟子·梁惠王下》中提到:“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荀子·天論》中曾提到:“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在孟子所引的《詩》中,大多是贊美西周統治者的美好,歌頌偉大業績和突出“圣王”的地位及功能。孟子也積極向統治者論證“仁政”的重要性,希望統治者能夠實行仁政。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學說是孟子的政治綱領,而其王道思想是他的政治理想。在此,孟子提出“保民”“養民”“教民”的具體實施綱領。只有與民眾同樂,才能真心得到人民的擁護。
而荀子與孟子不同,荀子更多地引用《詩》來表達“禮”的權威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為此,荀子提出“隆禮”的觀點,對禮在維護社會安定的作用方面給予了高度評價。荀子認為,禮是道德之本,“人道之極”,“天下從之則治,不從則亂;從之者安,不從之者危;從之者存,不從之者亡”,甚至認為“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可見荀子認為“禮”極其重要,禮的存在甚至關乎國家的存亡。《荀子·修身》篇中提及:“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宜于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焰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是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此類的言語在《荀子》一書中比比皆是。荀子用“詩”來傳達自己關于“禮”的言論觀點。不管是國君治國還是君子修養自身,都要以禮為最高標準。
二、詩教觀之影響
孔子在《論語》中提到了著名的“詩、觀、群、怨”說。重視詩的社會政治作用是儒家詩論的核心。而教化主要是統治者對臣民的教化。統治者利用詩歌,按照本階級的政治要求和倫理道德規范對臣民進行正面教育,以使被統治者和被教化者恪守所謂的倫理綱常、禮儀制度,維護、鞏固自己的封建統治。鮮明的例子就是“黨八股”這種選舉考試。不可否認,這種考試也讓很多真材實學者實現了自己的仕途理想,但更多的是人們為了考取功名利祿,束縛于這種制度之下,沒有自己的思想甚至人格,典型的人物事件就是“范進中舉”。在這種封建統治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深入人心。詩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產物,其意識形態性鮮明,那就是為封建時代的政治統治服務。而這種意識形態影響深遠,直到現在依然存在。
所以說,詩學觀是工具型的、道德化的、社會化的。而儒家需要詩歌,就個人而言,是為了修身養性,增長知識和鍛煉才干;就社會而言,則是為了“補察時政”“泄導人情”。主張“言志”,其主要目的則是治理和組織社會,尋求一種能深入人心的勸善懲惡的教化工具。儒家的詩學公式是“詩歌—人心—治理”。詩歌可以塑造人善良的心靈,而善良的心靈可以使社會的風俗習慣變得純潔。中國文學正視現實人生,通過文學的感化作用來安撫民心,以增強民族凝聚力,保持社會秩序安定團結,促進社會的長期進步與發展。
“詩教觀”是一把雙刃劍。“詩教觀”讓文學與政治聯系在一起,一方面體現了中國的人文精神,有利于文明的發展,另一方面限制了文學的自由發展,進而束縛了人的思想,不利于文學的優質發展,削弱了文學的生命力和活力。
三、“詩教觀”的文藝學意義
《論語》載:“《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些初步顯示了詩歌具有“言志”的功能。而漢代的《毛詩序》則對言志說做了經典性的表述,認為詩歌是情志的抒發。荀子之后,言志說大體形成。此后,司馬遷認為詩為發憤而作,陸機又提到“詩緣情而綺靡”,韓愈提出詩為不平則鳴,朱熹提出“志者詩之本”,嚴羽提出“詩者,吟詠性情也”,等等,言志說不斷發展,而其理論的源泉則是孔子的“興觀群怨”之說。
讀孔子的著作,可以了解到,孔子十分重視“詩無邪”。孔子在《論語》中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極為強調詩的“興觀群怨”以及“事君”“事父”。由此可以推出,孔子論《詩》,把詩或者偽文學的真實性原則放在次要位置,而把“善”作為衡量文學的首要標準。所以,很長一段時期,作家創作出很多“善”的文學,與這有很大的關系。
在儒家文藝思想內,“言志觀”“詩緣情以綺靡”與詩的“溫柔敦厚”有機結合在一起。儒家重視“善”這一思想,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發展,也對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聯系做出了重要貢獻。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