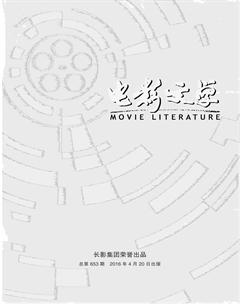中國第六代導演的行為藝術與文化姿態
朱姍 向懷林
[摘要]在20世紀90年代的“放逐”文化姿態中,中國電影出現了放棄“社會代言體”性質的情緒化思潮。這種思潮是一種個體凸顯個性的行為,它的形成與特殊時代限定有關,與張揚青春的文化思維有關,與對功利的追尋熱潮有關,這種思潮逐漸成為中國第六代導演具有時代特色的“行為藝術”與文化姿態。這種情緒化思潮于第六代導演的作品之中,體現在去戲劇化的表演方法、即興表演、非職業表演和日常化語言等方面,并形成了紀實性和虛幻性的兩種“行為藝術”。
[關鍵詞]第六代導演;“行為藝術”;文化姿態
第六代導演以“邊緣”為武器,“放逐”地進入國產電影的歷史場域。區別于第五代導演的分散化敘事與殘缺性構圖,中國第六代導演在作品中大量使用情緒化敘事手法,情緒化成為第六代電影及其表演的關鍵詞。
一、“情緒化”的文化身份
中國第六代導演的“行為藝術”并不是特例,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先鋒文藝人跨越各個文化領域,構成一個特定的群體,他們呈現出與之前的文藝工作者截然不同的行為征候。他們認為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堅持的個性,也有一代人要履行的職責,他們不會跟在前輩的身后人云亦云,而是要用自己的聲音說話,表達一種前無古人的獨特聲音。這聲音凝聚著青春的壓抑、成長的矛盾和抗爭的力量,這一代文藝工作者篤定自己要親手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第六代導演在電影創作上,呈現出與早期導演作品不一樣的姿態。第六代導演的作品放棄了傳統的戲劇美學思維,融入“殘酷青春物語”獨有的審美態度,影片充斥著情緒化色彩,帶有明顯的叛逆思想甚至黑色暴力元素。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第六代導演的創作方向受到青春族群情緒化特征的影響。
中國第五代導演是一撥經過特殊時代背景鍛造的人群,他們大多在經歷了基層工作生活經驗積累后才開始接受高等教育,這一代電影人有豐富和扎實的人生閱歷。而第六代導演按正常的升學路線升入大學,當他們走出校園開始從事電影創作時,并沒有積累足夠的生活閱歷和文化積淀。他們無法處理或不能更好地處理電影這一文化產品與社會的關聯。他們在藝術領域掀起一陣反動思潮,甚至崇尚情緒暴力。由于經驗不足,他們的執行手法并不成熟,他們的專業積累不足以支持他們的美學反動。于是,中國第六代導演另辟蹊徑,他們使用本色出演的手段,用表演來詮釋自己內心堅持的真實,他們將自己的“現實主義”肆意張揚,用崇尚本真的表演來表達自我的個性。這種風格的表演與其說是一種表演,倒更像一種演繹自我的行為藝術,表演與生活沒有完全清晰的界限。電影藝術與其說是在傳達藝術思想,不如說是在張揚創作者的個人情緒。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經歷了從經濟開放到文化開放的漫長過程,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才開始與外界完成文化上的接軌。這一時期,大量西方文化涌入并獲得青年一代的追捧,使得當時涌現出一股模仿西方文化的潮流。當時的中國雖然試圖與世界接軌,但從社會發展的各個角度來看,都與發達國家存在一定的差距。西方文化中的各種迷茫與悲觀情緒是基于其社會發展狀況而產生的,當時的中國文化人所面臨的思想問題,與西方國家不盡相同。第六代電影人卻盲目地基于對西方文化的情緒化進行模仿,反而呈現出一種無病呻吟的窘境。
由于第六代電影人的閱歷不夠深厚,又急于效仿西方文化的情緒思潮,稍有感悟便急于表達在電影作品之中,使得這一時期的電影作品過多地體現出社會的灰暗面。這種情形是由第六代電影人的成長經歷和審美取向造成的,同時也受到了對西方文化消極浪潮的誤讀的影響。
二、“文化標志”及精神“姿態”
細數中國新時期的一代又一代電影人,我們不難發現,第六代電影人在大眾的認知中始終欠于清晰,他們的作品量也并不豐富。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化遇到西方文化涌入的強流,呈現一種模糊不清的態勢,這是第六代電影人成長的宏觀環境。20世紀90年代,第六代電影人用強大的聲音宣告自身的獨立,他們直接批判上一代電影人,認為他們一直沉淪在不清醒之中。他們號稱自己是清醒的一代,要用清醒的目光審視世界,并自詡為全新電影作品的創造者。第六代電影人的文化姿態表現在兩方面:其一,他們一改之前電影對社會現象進行映射和啟示的目的,而將電影單純看作一件藝術作品。他們不主張通過電影來呼吁,不主張擴大電影的社會作用。他們認為電影只需要承擔創作者的內心觀點和審美訴求,電影在他們的手中,由社會性的作品轉為個人藝術品,呈現“個人現實主義”。其二,第六代電影人對藝術和美的評判和對真實世界的認知都有其獨到的見解,雖然他們的思想由于時空限制而并不完整和客觀,但這種思想卻匯成了一股新時代的思潮。第六代電影人對于“個人現實主義”的推崇,使得這些電影人將更多精力用在以電影來表達個人思想上。電影開始演變成他們的“自傳”,他們不再重視甚至直接無視電影的市場效應,也無視輿論的評價與關注,他們只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抒發自己的胸臆。
通過分析第六代電影的眾多代表作品,我們將第六代電影的特點歸納為以下幾點:第一,第六代電影選取的題材和人物都傾向于非主流。由于第六代電影的創作環境一般都在體制以外,沒有大量的運作資金來支撐宏大的場景和視角,他們沒有條件像第五代電影一樣保持“專業的角度和制作標準”,只能也甘愿在繁華都市的邊緣地帶游走,挖掘邊緣故事和邊緣人物。而事實上,第六代電影人本身也是一類邊緣群體,他們普遍沒有正規單位編制,沒有中國人信奉的“鐵飯碗”,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生活狀態,他們是早期“北漂”人群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注社會邊緣群體也就等同于在關注他們自身,這種行為是一定程度的自我認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第五代電影已經在電影行業樹立了標桿,第六代電影人在前輩建造的格局面前,若要進行改變或超越十分困難,他們只好另辟蹊徑,從主流電影人不關注的邊緣文化來入手。第二,第六代電影普遍呈現出主題不鮮明的特征。第六代電影并不像第五代一樣有明確的主題和社會目的,它們只是一種散漫的情緒,體現了創作者的個人思想狀態,是思想層面的自傳體,是第六代電影人在成長過程中經歷的矛盾與迷惘的直接表現。第三,第六代電影摒除了傳統的敘事方式。第六代電影中大多沒有明確的情節架構和故事主線,而是用一種意識流的模式將片段接續在一起,這與傳統的戲劇美學相悖。第四,第六代電影擅長使用局部構圖,它們能夠利用特寫或近景畫面來詮釋人物的心理世界,利用局部場景的構造來表達人物的內心。第五,第六代電影拋卻了第五代電影中常有的靜止畫面,而是大量運用運動的鏡頭和多媒體畫面,在畫面的拼接和跳轉中講述人物的凌亂與迷茫。
第六代電影的所有特點都和表演存在共通的關聯,甚至有合二為一的傾向。由于第六代電影大多以邊緣人群為主體,這類人群并不被主流意識所認可,他們長期處于一種頹喪和茫然的意識狀態,要塑造這樣的形象,勢必要求演員要更加付出努力,走進邊緣人群的內心世界。第六代電影用迷惘的內心世界、復雜的感情關系、零碎分散的細節和接地氣的語言模式來表現都市邊緣人群的生存狀況,演員的表演是這種思想情緒表現的最主要媒介,而在這類電影中,表演則體現為在悲觀和迷惘中掙扎的情緒化表現。由于第六代電影大多主題不鮮明,缺少了主題的限制,導演和演員都有了很大空間進行即興創作,表演更加呈現自我情緒化的趨勢,使得電影創作演變成自我思想的表達。散碎的敘事架構、窺探角色內心的局部鏡頭、體現迷茫和混亂的多媒體鏡頭接續,這些元素都是為了輔助情緒化創作,第六代電影中的表演成為一個極具標示性的獨特姿態。
三、“行為藝術”
第六代電影中的表演與第五代電影有顯著區別,不僅如此,其本身也表現為兩個相反的趨勢。這種兩極分化的表演特征與第六代電影人本身有關,這類人群極其講究個性,他們本身的個性有很大差別,他們的情緒化堅守讓他們堅持著各自不同的認知,自然在創作過程中也表現出不同的方式。第六代電影人的情緒和文化認知呈現出“理性”與“熱忱”兩個相反的方面,這兩方面導致了第六代電影在敘事結構和表演方式上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理性”的一面要求影片客觀地去揭示真理,這更像是一個旁觀者,但這樣的視覺角度太過冷酷。于是,第六代電影人必須在“理性”之外,給影片中的人物或情節加入熱忱,這更像一種表白與申訴,因為在電影中他們不可能真的成為旁觀者。
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兩種不同的思想方面從兩個方向出發,最終在情緒化表演中交會,呈現出一種獨屬于第六代電影的美學效果,同時反映出情緒化表演的文化內涵和深刻意義。為了更貼切地旁觀現實,第六代電影創作者不顧一切地融入現場、觀察現場,甚至創造現場。我們發現,第六代電影大多或明或暗地能看到創作者的成長經歷和思維模式,也正因為紀實能夠更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文化情緒,第六代電影導演十分認可這種紀實性的表達模式。
第六代導演中的代表人物賈樟柯的很多作品就是紀實性表達模式的范本。賈樟柯的電影中大量運用即興創作、非專業群眾出演、現場收聲、自然光線等手段,使得影片畫面更加貼近真實生活,貼近最原始的情緒化表演,這樣的畫面沒有劇本設計中的主線脈絡,而只是類似真實的片段截取。
賈樟柯的作品《小武》講述了小縣城的小偷梁小武的故事,至于梁小武為什么會變成小偷,他的偷竊生涯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梁小武的未來又會如何,影片沒有清晰的表示,也沒有任何隱喻和暗示。影片中只是講述了梁小武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方式,以及一場沒有結果的愛情,這些都只是沒有前因后果的片段。影片想要傳達的只是一種寂寥和茫然的情緒。紀實性表演又分為思想自傳類型和熱點關注類型。很多第六代電影以社會熱點為主題,而社會熱點的重新創作本身就具有邊緣色彩,它既具有寫實的紀錄風格,又具有劇情片的美學元素,在這種前提下,情緒化創作模式成為必然的結果。
由于第六代電影人必須在“理性”之外,給影片中的人物或情節加入熱忱,所以在第六代電影中,虛幻性表演被廣泛采用,在幻夢中身處多個角度的多元主體成為當時主要的表演模式。第六代電影導演李欣的作品《花眼》就是一個用幻夢來詮釋的故事。《花眼》利用了與之前普通電影不同的敘事方法,營造了一個超現實中白日幻夢的語言環境,強烈地表達了個體的思想和認知。大量的臺詞和畫外音使得影片顯得淡漠與沉郁,這些語言好似脫離于故事之外,但去除之后又顯得少了什么,這種虛幻的表演形式散發著一種情緒宣泄的意志。同樣,第六代導演婁燁的作品《蘇州河》也采取了這種表現手法,《蘇州河》塑造了虛構的美人魚的故事,展現了導演婁燁內心真正的想法和對“蘇州河”的期望。整個構架的虛構使得影片的創作充滿情緒化,影片的視覺語言在冷漠中透露著茫然和隨性,這使得該影片成為虛幻性表演模式的范例。
從某種角度來看,中國的第六代電影呈現出的文化內涵并不正統。第六代導演的作品放棄了傳統的戲劇美學思維,融入“殘酷青春物語”獨有的審美態度,影片充斥著情緒化色彩,帶有明顯的叛逆思想甚至黑色暴力元素。第六代導演獨特的“行為藝術”和文化姿態使這一時期的作品極富個體性和紀實性。然而,因第六代電影人的經歷和思想,這一代中國電影過多地體現出社會的灰暗面,其社會現實意義與主流美學價值并不突出。
[參考文獻]
[1] 賈磊磊.時代影像的歷史地平線——關于中國“第六代”電影導演歷史演進的主體報告[J].當代電影,2006(05).
[2] 史鴻文.論“第六代導演”的電影美學風格[J].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4).
[3] 黃國華,孫淑娟.從邊緣出發——簡論第六代導演的敘事手法[J].南昌工程學院學報,2006(04).
[4] 陳旭光.“影像的中國”:第五代、第六代導演比較論[J].文藝研究,2006(12).
[5] 田永剛,賈新剛.第六代導演的生存與前路[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04).
[作者簡介] 朱姍(1982—),女,重慶人,重慶工商職業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文化與文學。向懷林(1953—),男,重慶人,重慶工商職業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與文藝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