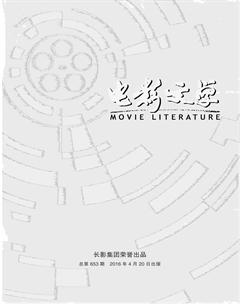馬修?沃恩電影的商業(yè)美學(xué)概論
[摘要]在電影的不均衡發(fā)展過程中,歐洲電影常常以其藝術(shù)性來對(duì)抗好萊塢的商業(yè)大片形成的霸權(quán)。事實(shí)上,一部分歐洲導(dǎo)演也著眼于其電影在商業(yè)美學(xué)上的優(yōu)化,立足于本土進(jìn)行創(chuàng)作。這些導(dǎo)演的成功之路既不能單純以好萊塢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比照,又在操作模式上與歐洲文藝片截然不同,英國新銳導(dǎo)演馬修·沃恩便是其中一個(gè)典型的代表。文章在厘清商業(yè)美學(xué)概念的基礎(chǔ)上,從主題與類型選擇、視聽效果營造兩方面,分析馬修·沃恩電影的商業(yè)美學(xué)。
[關(guān)鍵詞]馬修·沃恩;電影;商業(yè)美學(xué)理論
就藝術(shù)表現(xiàn)方式的豐富性以及市場影響力、信息和價(jià)值傳遞的強(qiáng)大程度而言,電影算得上是目前首屈一指的藝術(shù)形式。在電影產(chǎn)業(yè)進(jìn)入高速發(fā)展軌道的今天,商業(yè)美學(xué)的概念應(yīng)運(yùn)而生,并且已經(jīng)得到了電影市場的供給方和消費(fèi)者的共同認(rèn)可。綜觀有關(guān)商業(yè)美學(xué)的研究,人們往往將注意力放在早已做大做強(qiáng)的好萊塢電影上,而與之形成對(duì)比的則是歐洲電影往往被認(rèn)為是不能完全以商業(yè)美學(xué)衡量的文藝片的重鎮(zhèn)。而事實(shí)上,一部分歐洲導(dǎo)演則著眼于其電影在商業(yè)美學(xué)上的優(yōu)化,立足于本土進(jìn)行創(chuàng)作,再將作品投放于包括好萊塢在內(nèi)的國際市場,獲取巨大的商業(yè)利潤。這些導(dǎo)演的成功之路既不能單純以好萊塢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比照,又在操作模式上與歐洲文藝片截然不同,他們有著屬于個(gè)人的商業(yè)美學(xué)實(shí)踐。英國新銳導(dǎo)演馬修·沃恩(Matthew Vaughn,1971—)便是其中一個(gè)典型的代表。無論是由他和蓋·里奇共同打造的《兩桿大煙槍》(Lock,Stock and Two Smoking Barrels,1998),還是沃恩本人單獨(dú)執(zhí)導(dǎo)的《海扁王》(KickAss,2010)、《王牌特工:特工學(xué)院》(Kingsman:The Secret Service,2014)等均獲得了觀眾的熱議以及電影批評(píng)界的關(guān)注,滿足了人們?cè)谖幕瘜徝郎系钠谂巍?/p>
一、馬修·沃恩與商業(yè)美學(xué)理論
商業(yè)美學(xué)(Commercial Aesthetics)的概念是由學(xué)者理查德·麥特白在《好萊塢電影》中首次提出的,其研究對(duì)象也以好萊塢電影為主。[1]莫爾特比認(rèn)為:“好萊塢是電影商業(yè)美學(xué)運(yùn)作的典范。其核心是電影的制作中尊重市場和觀眾的要求,有機(jī)配置電影的創(chuàng)意資源(類型、故事、視聽語言、明星、預(yù)算成本等)和營銷資源(檔期、廣告、評(píng)論等),尋找藝術(shù)與商業(yè)的結(jié)合點(diǎn),確立自己的美學(xué)慣例,并根據(jù)市場和觀眾的變化不斷推出新的慣例。”[2]其對(duì)好萊塢電影的商業(yè)性特點(diǎn)的總結(jié)無疑是到位的,但商業(yè)美學(xué)作為某種電影進(jìn)行拍攝的慣例實(shí)際上存在的范圍與時(shí)間,都是要遠(yuǎn)遠(yuǎn)超出形成成熟運(yùn)作體系之后的好萊塢的。這是電影的雙重屬性決定的,電影藝術(shù)的存在離不開其商品性,而電影的商業(yè)價(jià)值要得到充分的實(shí)現(xiàn)也離不開其內(nèi)在的藝術(shù)性。當(dāng)前的電影也正是根據(jù)在兩種屬性上的偏重程度分為商業(yè)電影和藝術(shù)電影。在商業(yè)電影中,觀眾所需要的便是刺激、快樂和消遣,通過觀看電影來進(jìn)入某種滿足的心理狀態(tài)之中,電影中文化理想和教化語言所占的比重較少。在電視、網(wǎng)絡(luò)等不斷對(duì)電影進(jìn)行沖擊的當(dāng)代,這類商業(yè)電影更是體現(xiàn)出了它的重要性和靈活性。除卻少數(shù)電影只作為意識(shí)形態(tài)宣傳工具的地方,絕大多數(shù)國家與地區(qū)的電影都是工業(yè)與資本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產(chǎn)物,是文化商品的一種,只不過最具有代表性的莫過于進(jìn)入到消費(fèi)時(shí)代以后創(chuàng)造電影神話最多,大片云集的程度最為引人注目的美國好萊塢。
沃恩是一位頗為特殊的兼具英美氣質(zhì)的電影人。他深諳電影必須由商業(yè)利益進(jìn)行驅(qū)動(dòng),也了解觀眾喜歡在觀影過程之中獲得怎樣的享受,觀眾的需求直接關(guān)系到票房,因而必然是投資方以及電影主創(chuàng)人員最為關(guān)心的。然而,從沃恩離開好萊塢返回英國又不難發(fā)現(xiàn),沃恩最終并不全盤認(rèn)可好萊塢電影的美學(xué)傾向,英國與美國之間在政治制度、社會(huì)氛圍與文化市場上面有著一定差異,而沃恩顯然覺得祖國能提供給自己更為如魚得水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在創(chuàng)作電影的同時(shí),沃恩也并不排斥美國電影的經(jīng)濟(jì)規(guī)律,也始終將好萊塢乃至全世界觀眾作為自己潛在的票房來源。而從沃恩所取得的成就來看,他也確實(shí)拍攝出了一批在商業(yè)利益上能與誕生于美國本土的商業(yè)電影相抗衡的作品,如他的《海扁王》盡管是一部R級(jí)(即帶有限制內(nèi)容)電影,卻一經(jīng)上映就在北美票房上稱霸一時(shí),同時(shí)這些作品又能給人以較為深刻的印象,不同于人們已經(jīng)產(chǎn)生審美疲勞的好萊塢“流水線”之作。可以說,在沃恩身上,他在盡量取得電影商業(yè)經(jīng)濟(jì)與美學(xué)精神之間的平衡點(diǎn)的同時(shí),又在尋找著英國商業(yè)電影與美國商業(yè)電影兩種美學(xué)氣質(zhì)的平衡。
二、馬修·沃恩電影的主題與類型選擇
類型片的誕生是電影開拓營銷渠道,樹立目標(biāo)觀眾的產(chǎn)物,電影在主題與類型上的確定有助于電影基調(diào)的定位以及輿論宣傳的先行,如好萊塢的喜劇、歌舞、西部、愛情等便是擁有了一批穩(wěn)定觀眾的類型片。馬修·沃恩也深諳選擇適當(dāng)?shù)摹⒐逃械碾娪爸黝}與類型有助于電影制作各要素的組合以及對(duì)觀眾的吸引,并且沃恩明白如復(fù)仇主題、打斗主題、間諜類型、警匪類型等在商業(yè)美學(xué)中的意義,但是沃恩卻在這些電影中表現(xiàn)出了自己反諷或戲仿的態(tài)度,從而使其電影對(duì)于類型片有著取乎其中、超乎其上的藝術(shù)價(jià)值。
以《海扁王》為例,電影改編自英國著名的漫畫編劇馬克·米勒的同名漫畫。電影的情節(jié)較為簡單,即講述一個(gè)一心想成為超級(jí)英雄的小男孩戴夫·萊澤斯基因?yàn)榫W(wǎng)購了一套神奇的裝備而將自己打造成了一個(gè)未成年的小英雄的故事。然而整部電影卻是一個(gè)“反英雄”的故事,好萊塢超級(jí)英雄電影中主人公在成為超級(jí)英雄之后遇到的種種奇遇,在電影中反而成為主人公的噩夢(mèng)。在電影的結(jié)尾,戴夫和“超殺女”都放棄了自己所謂的英雄身份,回歸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并且在他們看來,遠(yuǎn)離血腥和殺戮,過著平凡的、屬于孩子的健康生活才是幸福的。電影實(shí)際上并不是在講述英雄的成長,而更像是在揭露“逞英雄”會(huì)帶來的風(fēng)險(xiǎn)。
這部電影盡管在藝術(shù)上并非完美的佳作,但是卻可以視作沃恩在選材上最具代表性的電影。從主題上來說,該片借用了一直在世界影壇上風(fēng)生水起的超級(jí)英雄電影模式。原本毫無任何超級(jí)能力,但是堅(jiān)持著個(gè)人英雄主義的戴夫突然間成為一名風(fēng)云人物,與好萊塢套路相契合的除了他的奇遇之外,還有他也如超級(jí)英雄一般收獲了“愛情”。從風(fēng)格上來說,該片帶有鮮明的日本邪典(cult)電影的氣質(zhì),女主人公“超殺女”身穿黑皮衣,頭戴黑眼罩,小小年紀(jì)就被父親“大老爹”訓(xùn)練為一個(gè)殺人不眨眼的打手,大老爹為了訓(xùn)練她的實(shí)戰(zhàn)經(jīng)驗(yàn)甚至不惜讓她穿上防彈衣然后對(duì)她射擊,還令她熟悉各類槍械刀刃等,但是《海扁王》又與純粹的邪典電影存在鮮明的區(qū)別。邪典電影是劍走偏鋒的,它主題上的詭異之處是為了體現(xiàn)出導(dǎo)演本人強(qiáng)烈的、個(gè)性化的觀點(diǎn)。[3]因此電影在制作之初就考慮到難以有足夠的票房回報(bào)而采用小成本制作模式。而《海扁王》則是以市場為主導(dǎo)的。電影中雖然也有個(gè)人的、帶有一定爭議性的觀點(diǎn),如認(rèn)為所謂的超級(jí)英雄實(shí)際上得到的只不過是表面風(fēng)光而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馬克·米勒本人就是一位堅(jiān)定不移的“反英雄”編劇,米勒與沃恩旨在通過這部電影來迎合觀眾對(duì)超級(jí)英雄電影和好萊塢復(fù)仇套路的反感情緒。如電影的一開始,一個(gè)假“海扁王”就因?yàn)樽约旱难b腔作勢而丟了性命,而后來成為海扁王的戴夫也差點(diǎn)死掉,并且也間接地害死了“超殺女”唯一的親人大老爹。這樣不落俗套的敘事主題反而更能吸引見慣《蜘蛛俠》《蝙蝠俠》等電影的觀眾,從而為沃恩的后續(xù)電影打下牢固的票房基礎(chǔ)。
從沃恩的其他幾部電影中也完全可以看到這種在電影主題和類型上的大膽顛覆。如《兩桿大煙槍》《夾心蛋糕》(Layer Cake,2011)等在選用了警匪片類型的同時(shí)又對(duì)傳統(tǒng)警匪片做出了突破。在《兩桿大煙槍》中,無論是幾乎未出面的執(zhí)法一方,還是作為匪的毒販、賭場老板、偷槍的小混混和“黑吃黑”的主人公都沒有成為勝利者;又如選用了間諜片類型和復(fù)仇、“平民英雄拯救世界”套路的《王牌特工:特工學(xué)院》更是對(duì)好萊塢的《碟中諜》等間諜電影進(jìn)行了辛辣的諷刺。
三、馬修·沃恩電影的視聽效果營造
在商業(yè)美學(xué)中,電影需要具有奇觀化的畫面和聽覺效果,要在視聽兩方面給觀眾強(qiáng)烈的沖擊和享受。在娛樂工業(yè)語境中,觀眾之所以走進(jìn)電影院,正是希冀電影能夠提供給自己一個(gè)暫時(shí)逃避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光影世界或曰夢(mèng)境,而電影導(dǎo)演便是這個(gè)夢(mèng)境的造夢(mèng)者。[4]夢(mèng)境越是夸張、奇幻、光怪陸離,與現(xiàn)實(shí)的差距越大,觀眾越會(huì)覺得票有所值。而隨著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以及高投資的進(jìn)入,電影人在視聽效果營造上的難度也在逐漸下降,創(chuàng)造出絢麗、流暢、動(dòng)人心魄且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聲畫效果幾乎成為所有商業(yè)電影保證觀眾不至于流失,市場不至于萎縮的重要法寶。在電影主題上的叛逆并不意味著馬修·沃恩電影帶有強(qiáng)烈的擺脫好萊塢商業(yè)電影痕跡的特色,從視聽語言的運(yùn)用方面,沃恩可以說是效仿了好萊塢電影商業(yè)美學(xué)的一貫制作套路的。
例如,在《星塵》(Stardust,2007)中,沃恩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gè)名為“圍墻村”的平行世界,這里風(fēng)景宜人,且充滿了各種超自然的生物,也正是在這樣美輪美奐的環(huán)境中才能誕生主人公——雜貨店的窮小子特里斯坦·索恩對(duì)維多利亞純潔的愛情。電影不光擁有細(xì)膩唯美的風(fēng)光,還有恢宏的場面,陰險(xiǎn)冷酷的王子們?yōu)榱送跷欢ハ鄽⒙荆瑫?huì)施魔法的女巫們則依靠吞食星星來維持青春等。在同樣改編自漫畫作品的《王牌特工:特工學(xué)院》中,沃恩更是將令人耳目一新的視聽語言發(fā)揮到了極致。電影中不僅延續(xù)了《海扁王》中花樣百出的打斗場面,更是一改《海扁王》中令人瞠目結(jié)舌的血肉橫飛,而以正反雙方矯捷的身手和高科技對(duì)決作為賣點(diǎn)。如反派億萬富翁瓦倫丁的女助手兩只腳為金屬假肢,然而女助手卻絲毫沒有殘障人士的不便,相反卻比一般人的動(dòng)作更為靈活犀利,在影片一開始就用假肢將之前讓觀眾為之驚艷的,同樣武功高強(qiáng)的特工蘭斯洛特一劈兩半,她的打斗動(dòng)作暴力卻又不失優(yōu)雅,在速度與力度方面幾乎完全脫離現(xiàn)實(shí);又如在影片的結(jié)局中,主人公艾格西等金士曼特工破壞了瓦倫丁的陰謀,操縱瓦倫丁的設(shè)備讓他所挑選出來的所謂社會(huì)精英們腦內(nèi)的芯片發(fā)生爆炸,但是畫面也完全沒有血腥和令人作嘔之感,觀眾所看到的只是一個(gè)個(gè)腦袋突然迸發(fā)出五顏六色的煙花,既無頭骨的崩裂,也無腦漿的流淌,只有伴隨著交響樂此起彼伏的美麗煙花,可謂奇妙之極。
同時(shí)值得一提的是,當(dāng)代電影中對(duì)數(shù)字技術(shù)的大規(guī)模運(yùn)用也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電影主創(chuàng)與接受者兩方面主體性的萎縮,觀眾的注意力很容易為導(dǎo)演所提供的新奇畫面所吸引,而不需要再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的想象,而這些奇妙的畫面本身也可以不承載導(dǎo)演的思想,無論是導(dǎo)演抑或觀眾都停止了應(yīng)有的思考,使電影的審美價(jià)值大打折扣。但由于沃恩本人的節(jié)制,這一問題卻并沒有出現(xiàn)在他的電影中。
毋庸置疑的是,商業(yè)電影憑借著巨大的利潤空間以及利潤之下的生產(chǎn)動(dòng)力,如今已然成為世界電影市場中的主力軍。單純追求所謂的藝術(shù)性,不從商業(yè)利益出發(fā)的電影勢必在實(shí)踐中遭受挫折。從馬修·沃恩電影的商業(yè)美學(xué)體系中,不難看出他超乎尋常的藝術(shù)與商業(yè)天賦,他既善于根據(jù)觀眾已經(jīng)被好萊塢培養(yǎng)出來的觀影口味使自己電影出現(xiàn)明顯的類型化,讓電影包含類型片中固有的多種元素,同時(shí)又有意另辟蹊徑,以對(duì)原類型片中常有的主題進(jìn)行解構(gòu)或顛覆,這實(shí)際上擴(kuò)寬了電影類型片的表現(xiàn)空間,同時(shí)也創(chuàng)立了屬于沃恩自己的電影特色;另一方面,沃恩在電影的形式即視聽語言的運(yùn)用上,充分發(fā)揮著電影的娛樂本性,讓觀眾能從中充分地宣泄自己的欲望,這也正是沃恩電影一直能符合電影發(fā)展主流,不斷制造票房經(jīng)典的原因。
[參考文獻(xiàn)]
[1] 李淼.“電影商業(yè)美學(xué)”還是“商業(yè)電影美學(xué)”?——對(duì)“電影商業(yè)美學(xué)”的質(zhì)疑[J].當(dāng)代電影,2009(08).
[2] [英]理查德·麥特白.好萊塢電影——1891年以來的美國電影工業(yè)發(fā)展史[M].吳菁,何建平,劉輝,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5.
[3] 杜春艷.暗夜的邪典精靈[D].濟(jì)南:山東師范大學(xué),2009.
[4] 臧娜.當(dāng)代文藝娛樂化問題研究[D].沈陽:遼寧大學(xué),2012.
[作者簡介] 吳玲(1980—),女,河南鄭州人,碩士,河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外國文學(xué)、外語教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