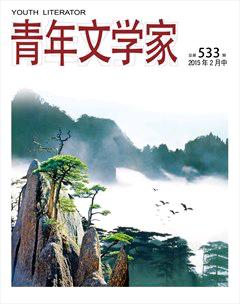試析《憤怒的葡萄》中的母親形象
摘 ?要:斯坦培克的小說《憤怒的葡萄》中母親形象的塑造往往被認為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然而從女性主義的角度觀察,小說中的“約德媽”這一形象卻是較為保守的。本文通過細致的文本分析,發現小說中的母親對家庭內部的性別歧視缺乏意識,自覺認同,并在某種程度上充當著父權制代言人的角色,維護和延續著父權制的運作。斯坦培克通過強調女性傳統美德,美化女性作為母親/哺育者的形象,事實上再現了父權制的觀念,參與了保守意識形態的宣傳,削弱了作品的進步作用。
關鍵詞:《憤怒的葡萄》;母親形象;女性主義;父權制
作者簡介:羅靜(1980-),湖北武漢人,北京大學外語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05-0-02
《憤怒的葡萄》是美國文學史上的一部名作。該書于1939年3月出版,立刻引起轟動,到五月就以每周一萬本的銷量躍升至暢銷書榜首。該小說也使作者獲得1962年諾貝爾文學獎,從而奠定了它在美國文學史上的經典地位。這部小說真實可信地描寫了經濟大蕭條中美國農民艱難的生活狀態,得到讀者的廣泛共鳴。盡管有人批評這部小說冗長,或宣傳口號的色彩太重,但總的來說,它受到普遍贊譽。小說中的母親形象塑造也被認為是十分成功的。不少評論者認為小說中最著名的女性形象“約德媽”堅強、勇敢、無私,是一個有別于傳統女性的進步形象。然而,以女性主義的觀點詳細考察這部小說,會發現其中母親形象的塑造具有相當的保守性。“約德媽”這一人物對于家庭內部的性別壓迫并無意識,是一個嚴格遵守自身性別角色和維護父權制家庭的形象,而作者也刻意美化“約德媽”作為哺育者和男性附屬品的形象。以下筆者將著重就其保守性展開論證。
在小說開篇處,作者就對俄州農民進行了一個群像描寫,從中可以看到,在這些農村家庭里,男女性別角色和分工涇渭分明。男性負責農活,是家庭收入的來源,也是家庭重大事件的決策者,而女性只是其附屬品。當干旱和沙塵暴威脅著土地的收成和家庭的命運,男人們觀察著受災的玉米地,“他們沉默著,不大動彈。婦女們從家里出來,站在自己的男人身邊—悄悄窺測他們這回是否會完全泄了氣。婦女們偷偷地打量著男人們的臉色,只要他們不氣餒,玉米沒有收成也不要緊。”而當她們看到男人臉上的勇敢和決心之后,“婦女們知道問題已經解決了……婦女和孩子們都深深地知道,只要家里的男人挺得住,他們就再沒有忍受不住的災難了。” 于是婦女們繼續進屋去干活,而“男人們靜靜地坐在那里——想著——算著。” “悄悄窺測”和“偷偷地打量”等描述表現了女性的膽怯和在家庭中低下的地位。男人是家庭的大腦,負責“想”和“算”,女人則只負責不動腦地“干活”。
小說的主人公約德一家和群像式描寫中的俄州農民家庭一樣,男女性別角色明確,家庭等級嚴格,家庭中的重大決定都是由男性商議得出的。每次家庭會議,由是男性圍成一個小圈,“這就是全家的核心”,而女人“在蹲著的男人們背后就位,”發言的順序也是從最年長的男性開始。“爺爺還是名義上的家長,但是不再管事了。他的地位只是習俗上的掛名地位罷了。但是他雖然昏庸老朽,卻還是保持著首先發言的權利。”爺爺發言之后就輪到“爸”,然后是兒子湯姆。家里較為年長的女性如“媽”在少數情況下也參與自己的意見,但她們主要的角色是從屬性質的,只負責家務、照顧家庭成員和哺育后代。
“媽”對父權制的家庭等級和分工是完全認同的。她認為“女人全靠她的一雙手過活,男人全靠他的腦子過活。”她毫無怨言地接受了自己在家庭中作為“一雙手”的角色,而這意味著她所承擔的工作大多是繁重枯燥的家務勞動。然而有趣的是,作者對“約德媽”在家中地位的描述卻使她看起來不像一個沒有地位的普通主婦,反而在家里占據著特殊的重要位置:
她似乎知道自己是全家的堡壘,是一個攻不破的堅強陣地;她似乎是承認了自己這種地位,還表示歡迎。除非她承認遭到了憂患,老湯姆和孩子們是不知道憂患的,因此她就把自己鍛煉得很堅強,根本就不把憂患放在心上。每次發生了什么快樂的事情,大家就首先看看她是否有快樂的事情,于是她就養成了一種習慣,遇到無足輕重的喜事,也大笑一場。但是比快活更大的特色,是她的鎮定。她經常都保持著泰然自若的神色。由于她在這個家庭里處著這么一個偉大而又平凡的地位,她就有了她的尊嚴和純潔的、嫻靜的美。在她給別人醫治精神創傷的時候,她是很有把握,冷靜而沉著的;在評判是非的時候,她的見解是大公無私的,象女神那么公正。她似乎是知道,如果她動搖了,全家就會動搖,如果她居然大大地動搖或是絕望,全家就會完蛋,全家的意志就會不起作用了。(89,90)
這段描述中“媽”的地位頗高,似乎與小說之前表現的男尊女卑狀況相矛盾,但仔細考察之下會發現并非如此。之所以在一個男性主導的家庭中,家庭主婦是“全家的堡壘”,并且只有當她“承認遭到了憂患”,丈夫和孩子們才會感受到憂患,是因為父權制所規定的忍耐和自我犧牲精神等女性/母親的美德使得她們在家庭遭遇困難時選擇犧牲自己的利益來保證丈夫和孩子們的舒適溫飽,因此連她們都感受到憂患時,才代表家庭真正的憂患和困難到來了。“約德媽”將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家庭,卻極少顧及到自己。為了不給家人增添麻煩和造成心理負擔,她“把自己鍛煉得很堅強”。當牧師說她看起來“實在比平常更累……真是累得厲害……簡直累壞了”的時候,“媽”也許是想到作為“全家的堡壘”,自己必須堅強,于是“她那張松弛的臉慢慢緊張起來……她的眼神銳利起來,肩膀也挺直了。”這種忍耐和犧牲精神最極致的表現是在小說的第18章。為了保證一家人順利地通過沙漠,“媽”向家人隱瞞了奶奶去世的消息,獨自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和煎熬,徹夜守著奶奶的尸體,直到全家安全到達平原地區。當一家人都對她“有那么大的魄力”而感到“有點畏懼”時,媽“凄然地”說“一家人要過沙漠呀。”因此,“全家的堡壘”、“堅強陣地”的地位對女性實際上是一種精神上的枷鎖,使她們必須毫無怨言地克己奉獻,自我犧牲。作者斯坦培克對于這種家庭中不平等的男女分工和權力關系不作任何批判,反而通過歌頌女性美德來肯定父權制關系,表現了他在性別觀念的保守性。
“約德媽”這一形象的保守性最突出地表現在小說的第26章。約德一家在青草鎮收容所里因為生活無法維持而必須離開,當“爸”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媽”堅決地表示“我們一早就動身”。“爸”于是諷刺地說“從前是男人家出主意。現在好像要女人家出主意了。我看這樣下去,非把棍子拿出來不行了。”對于“爸”的威脅,媽進行了如下的回應:
從前有東西吃,有房子住,你也許可以用你的棍子擺擺威風。可是你現在并沒有干活,想也不想,干也不干。要是你在干活,那你盡可以用你的棍子,把女人家收拾得服服帖帖,只敢哼哼鼻子,不敢說話。你現在拿根棍子來試試看,包管你不敢動手打女人;看我跟你對打,因為我也預備了一根棍子呢。
“爸”雖然只是口頭上威脅,最終也默認了“媽”的意見,但讀者從中可以察覺家庭暴力在當時的農村家庭文化中并不陌生。約德家女性的意見是不受男性尊重的,當她對家務以外的事情發表見解時會被視為對男性權威的挑戰,甚至有可能遭受家庭暴力。盡管“媽”和“爸”針鋒相對,似乎頗有反抗精神,事實上這種反抗十分有限。“媽”對男性在家庭中的權威還是認同和服從的,暗示只要男性承擔養家的責任,就有權力在女性挑戰其權威之時對她進行暴力制服。而且,“媽”對“爸”的挑戰不是真的要推翻他的權威,恰恰是因為“爸”在生活的折磨之下變得越來越頹喪,不能肩負起一家之長的責任,“媽”需要通過刺激他來激起他的男子氣概。在這場小沖突結束之后,媽“得意地”對兒子湯姆說自己其實是故意惹“爸”生氣。她說,“一個人老是愁來愁去,不久就要愁壞心肝,躺倒下來死掉的。你要是招他生氣,他反而就好了。爸,他本來不說話,可是現在人可氣壞了。現在他會對我發脾氣的。他好了。”因此,男性家長的權威建立的條件是女性的馴服順從,以及男性對女性的主導和支配,甚至暴力,而“媽”主動地參與到男性權威的建立過程中去。
在維護現有家庭秩序的同時,“媽”也通過對子女的教育將他們培養成能夠適應各自角色并擔當起相應責任的接班人。當“媽”發現“爸”已經不再適合擔當男性家長的時候,就將希望寄托在了新的父權掌管人,兒子湯姆身上。她對湯姆說,“你是有腦筋的,湯姆。我用不著招你生氣。我還得依靠你呢。”以老約德為代表的老一代男性農民喪失了男子氣概和在家庭中的威嚴,那么代替他成為家庭核心的兒子小湯姆·約德就代表了充滿陽剛之氣的新一代農民,而這種陽剛之氣是建立在父權意識之上的。“媽”作為父權制的自覺維護者,將這種觀念也灌輸給她的子女。與對湯姆的教育不同,她將女兒羅撒香規訓成一個和自己一樣任勞任怨的合格的家庭婦女。在全家前往加州的旅途中,當女兒覺得旅途辛苦,自己無人照顧,抱怨丈夫康尼不該離開她時,“媽”說,“只怕他會打你耳光呢。你成天唉聲嘆氣,要不就是胡思亂想地哄自己,挨打也活該。他要是真把你打得懂事一點兒,我還要祝福他呢。”在“媽”的教育下羅撒香逐漸不再抱怨懷孕的辛苦,不再要求特殊照顧,除了力所能及地勞動之外,還盡可能照顧更多的人。小說結尾處那個著名的哺乳場景頗有象征意味。羅撒香為一名受傷的陌生男子哺乳,象征著她接替“媽”成為新一代的妻子/母親。
《憤怒的葡萄》是一部偉大的社會現實主義小說,傳達著豐富的進步思想,然而這其中并不包括女性從男性壓迫中的解放,因而是具有保守性的。通過“約德媽”這一形象的塑造,小說強調女性傳統美德對于男性主導的家庭的凝聚作用,美化女性作為母親和哺育者的形象,事實上再現了父權制的性別觀,參與了保守的意識形態的宣傳,與作者總體的社會進步主張相矛盾,從而削弱了作品批判力度。
參考文獻:
[1] Fadiman, Clifton. Books [J]. New Yorker, 1939, 15: 81-83.
[2]Gladstein, Mimi Reisel. The Indestructible Women: Ma Joad and Rose of Sharon [A]. In Harold Bloom, ed. John Steinbecks The Grapes of Wrath [C].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8. 115-128.
[3] Motley,Warren. From Patriarchy to Matriarchy: Ma Joads Role in The Grapes of Wrath [J]. ?American Literature, 1982, 54(3): 397-412.
[4]斯坦培克.《憤怒的葡萄》[M]. 胡仲持譯. 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