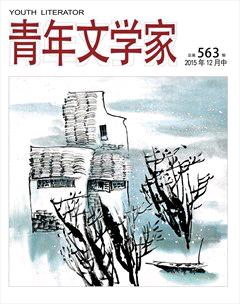無法掙脫的藩籬
梁向榮
摘 要:王安憶的小說“三戀”,在20世紀80年代被文壇稱為是首次沖破“性”禁區的作品。在《荒山之戀》中她以一種冷靜而旁觀的態度進行了性愛的寫作,書寫了一對已婚男女苦苦追求戀愛卻以悲劇告終的愛情故事。他們既受到傳統男權文化的制約,又被各自生存的狹小環境所束縛。
關鍵詞:悲劇;文化傳統;生存環境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5-0-01
《荒山之戀》講述一個有婦之夫,大提琴手與一個有夫之婦,金谷巷女孩在愛情意識覺醒之后演繹的一段大膽、熱烈的婚外戀情。他們的婚外戀雖然幸福,但同時有著不可抗拒的悲劇性,他們的戀情不被小城閉塞、落后的風俗文化傳統所容納,最終兩人服藥殉情于荒山。
《荒山之戀》中的大提琴手怯懦、自尊而又自卑,從小有一種強烈的依賴感,在家依賴母親,在外依賴大哥。性格上固有的弱點,以至于他把這種依賴感轉移到他的妻子的身上。“他需要的是那種強大的女人,能夠幫助他克服羞怯,足以使他依靠的,不僅要有溫暖柔軟的胸懷,還要有強有力的臂膀,那才是他的休棲地,才能叫他安心。”[1]而他的妻子在一定意義上充當了他的母親的角色,他的妻子是那種表面文靜內心十分強大的女人,在她的體內有一種母性的博愛,因而“她愿意被他依賴,他的依賴給她一種愉快的驕傲的重負,有了這重負,她的愛情和人生才充實。他的依賴也使她身后的柔情和愛心有了出路”[2]就這樣他們心與心之間的距離拉近了,在朦朧中慢慢地靠攏,此時劇團風傳他們戀愛了,輿論的力量總是難以抵擋的,加速了她與他的關系,促使他們走進婚姻的殿堂。
“大提琴手與他妻子的結合或許被一般人認為是幸福的結合,然而這種結合模式卻不是男女平等的,沒有人格上的真正平等,也沒有精神上的真正平等,他是她精神上的兒子,而她則是他精神上的母親。”[3]他們雖然是夫妻,過著夫妻間應有的一切生活,但是他們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性意識的覺醒,只是彼此之間的性格上的一種需求,一種心靈的互相慰藉,一種外來力的推動。
大提琴手的性格弱點讓他開始了一段沒有愛的婚姻,同時也為他婚姻的出軌埋下伏筆。人的性格的形成塑造總是受到一定社會歷史和生存環境的影響。大提琴手從小生長在那所高大而陰森的宅子,堂屋正中永遠端坐著他的祖父。“高大而陰森的宅子”象征著封建而不可觸及的社會法則,而“堂屋中永遠端坐的祖父”則是那種社會法則的擁護者與執行者。從小在那種無形的社會法則下循規蹈矩的做人做事,向來不敢,也不曾逾越那種規則。
與之性格迥異的金谷巷女孩:活潑、叛逆、熱情、不受社會世俗的限制。同時她的性格的形成也決定于她所生存的環境。金谷巷女孩從小受到母親的影響,看到母親與諸多叔叔的交往,讓她覺得男人不過是用來消遣的,對待男人不必付出自己的真心,男人只是奴才。她相好無數,不過是乏味生活的調味劑,她覺得最好玩兒的就是用盡各種手段與男人周旋,她深知男人的本性,甚至是男人自己不知道的地方,通過征服男人來尋找快樂和顯示自己的魅力。雖然她過早的嘗試到了被愛的滋味,但是從未真正感受到愛別人是什么樣子的,直到棋逢情感游戲對手。
“愛情其實是一場戰爭,那戰爭真是持久而激烈。”[4]這場戰爭沒有因為婚姻而結束。金谷巷女孩和丈夫之間的婚姻是一種游戲的結果,彼此之間更多的是一種戰勝的欲望,征服的欲望,由于棋逢對手讓他們彼此有了戰勝對方的欲望,這種征服欲戰勝了情欲,戰勝了愛情,他們之間沒有愛的基礎。金谷巷女孩風流,爭強好勝,最真實最強烈的內心欲望沒有因為婚姻而得到真正的釋放,尤其是婚后丈夫對她的私下監視,婚后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刺激與興奮,一個本性不甘心寂寞的女人注定要掙脫婚姻的束縛。
兩個家庭的婚姻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在他們的婚姻生活中沒有真正的性意識,沒有真正的愛的基礎,兩個婚姻都是失敗的。這正是傳統文化對人的性意識的禁止所造成的。
大提琴手與金谷巷女孩相遇于文化宮。金谷巷女孩長期以來被壓抑的情感被激發了,她對大提琴手進行挑逗,逢場作戲,然而卻弄假成真,不由自主的動了真情甚至連她自己都害怕了,那種沉睡于靈魂深處的性意識覺醒了;此時的大提琴手已經在妻子“母性”的培養下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男的在婚前是大半個孩子,他的妻子實際上是他的母親,她培養他長成一個男人,這場婚姻給他造成錯覺,他自己以為很行了,便想再找一個舞臺,擺脫使他自卑的妻子”[5]于是他們的婚外情順理成章,他們走出婚姻的圍城,在本能欲望的驅使下沖破禁區,獲得內心的歡愉。
他們幽會,不顧羞恥,沖破世俗的約束,甚至在被妻子發現,被單位處分,被女方丈夫毆打都不知悔改,反而激起了他的反抗。她甚至可以與丈夫離婚,但是面對一個既舍棄不了她,又難以斬斷與妻女關系的男人,她的愛情理想破滅了。人類婚姻和家庭的締結本是復雜文化引誘的結果,一旦打上社會的印記,就要在法律、道德等的認可中受到限制和干預。這種強大的文化力量在閉塞的小城中近乎于一種天命。他們這種試圖破除文化藩籬的行為無法在閉塞的小城中得到超越,在社會輿論的壓迫下,他們無法逃脫罪惡感與羞恥感,他們無力與社會環境相抗衡,最終選擇死來結束他們不被認可的愛戀,從而獲得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實現自己的價值。
參考文獻:
[1][2][4]王安憶.荒山之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98,98,123.
[3]陳墨、朱霞.愛的悲劇與人的命運——評王安憶小說三戀[J].當代文壇.1987(6).
[5]王安憶、斯特亞凡、秦立德.從現實人生的體驗到敘述策略的轉型——一份關于王安憶十年小說創作的訪談錄[J].當代作家評論.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