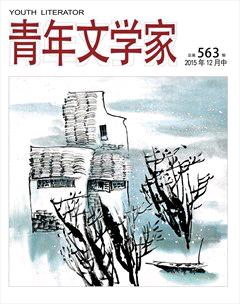復仇與人生
摘 要:《伍子胥》作為詩人馮至寫的,一部歷史新編復仇小說,既有詩意浪漫的語言,又有一種直面現實的精神。本文旨在結合馮至的背景,探討《伍子胥》里個人與社會理想追求的矛盾關系,思考理想之委婉和現實之殘酷,從而啟發人對現代社會的思考。
關鍵詞:伍子胥;理想;復仇;人生;困境
作者簡介:陶然(1994-),女,漢族,河南鄭州人,河南大學文學院2013級本科生,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師范專業。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5-0-02
《伍子胥》是著名詩人馮至在1943春年完成的一部現代歷史小說。在這部歷史小說中,經過兩千多年流傳、豐富、傳奇化的伍子胥的人生并未被全部演繹。被魯迅評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的馮至,以其詩人式清麗幽婉的語言和充滿奧妙的哲思,為我們講述了伍子胥“為復仇的流亡”片段式經歷。《伍子胥》“在現實生活與歷史生活的錯綜之中,升華出一個存在主義的人生命題:在關于怎樣取舍的決定中,使人感受到生命的意義。”[1]本文意在探究這種艱難抉擇產生的原因,以及體現。
一、馮至的特殊經歷
馮至最先以詩歌聞名,作為重要的抒情詩人,他的作品特色處處表現出“藝術的節制”,馮至的抒情詩首先具有“沉思”的調子,并在后來有像“哲理抒情化”的發展跡象。而當馮至留學德國后,更受到里爾克、歌德、艾略特、雅斯貝爾斯等人的影響,徜徉在充滿哲思和存在主義的思辨當中。他“堪稱獨步”的敘事長詩,不僅受到德國歌謠的啟發,亦融入了中國傳統民間神話的思索。凡此種種,都為后來創作散文詩般的《伍子胥》打下基礎。
在馮至1946年發表的《伍子胥》后記中,我們可以更細致地觀察到他創作該作品的脈絡。早在十六年前接觸到里爾克《旗手》的時候,他已感到“色調的絢爛,音調的和諧”,他形容《旗手》“像一陣深山中的驟雨,又像一片秋夜里的鐵馬風聲”。但經過了十六年的動蕩與變遷,伍子胥于馮至而言,除卻浪漫主義的想象,更“成為一個在現實中真實地被磨煉著的人”。于是在1942年讀到卞之琳重新改訂的《旗手》后,馮至再次想到伍子胥,手中筆墨因興而出,“二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變成一個含有現代色彩的‘奧德賽了”。
“我早有把他們的故事寫成敘事詩或小說的愿望,但是總沒有下筆。后來能以放開筆,不受歷史傳說的約束,給故事添了許多新的內容,是受到魯迅《故事新編》的啟發。它是跟我抗日戰爭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耳聞目睹以及個人的生活分不開的。其中有國民黨軍隊里的黑暗,視士兵如草芥,有奸商的投機倒把和囤積居奇,有特務的陰謀陷害,有知識分子的窮困和美國兵的趾高氣揚,還有國民黨御用教授從重慶飛到昆明,耍嘴皮子亂談歷史,騙取聽眾的錢財……等等,這都不是春秋時代,而是眼前的現實。”[2]可見在相隔十六年后,寫出的《伍子胥》已遠非“昭關的夜色、江上的黃昏、溧水的陽光”那般簡單。
二、語言的幽婉與境遇的殘酷
唐湜曾在《馮至的<伍子胥>》中說到:“在中國的古老傳說里,伍子胥的故事原就有過一些絢爛的浪漫色彩,經詩人馮至的手,加上了現代主義的詩情,尤其是意識流或內心情緒的渲染,就成了一個完整而透明的詩的果子。一句話,這是詩,抒情的詩,卻不是;它應該是嚴格意義上的小說。”[3]
馮至節奏舒緩、音韻柔美的語言風格使得這部本該殘酷的復仇逃亡故事,掩蓋了其中驚心動魄、激烈洶涌的元素。
在《城父》一章中,伍子胥與哥哥伍尚被“邀請”前往郢城,那里囚系著被饞人費無忌污詬的父親伍奢。伍尚說:“我的面前是一個死,但是穿過這個死以后,我也有一個遼遠的路程,重大的責任:將來你走入荒山,走入大澤,走入人煙稠密的城市,一旦感到空虛,感到生命的煙一般縹緲,羽毛一般輕的時刻,我的死就是一個大的重量。一個沉的負擔,在你身上,使你感到真實,感到生命的分量,——你還要一步步地前進。”馮至連用三個“走入”,強調伍尚內心的沉淀。用羽毛的輕渺反襯死亡之凝重,正是馮至的詩意,一種柔和而奔放的浪漫情懷。兄弟二人“一個要回到生他的地方去,一個要走到遠方;一個去尋找死,一個去求生……誰的身內都有死,誰的身內也有生;好像弟弟將要把哥哥的一部分帶走,哥哥也要把弟弟的一部分帶回。”通過在兄弟身上視角的變換、闡釋,使得讀者在對比中得到關懷的感動而削弱了實際上無比沉重的抉擇意義。當面對生死的分離,一切激烈的掙扎都在內心默默生發,生命艱辛的抉擇卻在此刻被染上了神圣、肅穆的顏色,馮至以其詩化整飭的語言,讓其產生優美的旋律,使血腥的殘酷現實得到更委婉的凈化。
《溧水》整章則如同詩般輕盈、夢幻。子胥與女子相遇,“她過去的二十年也是一個長夜,有如吳國五六百年的歷史;但喚醒她的人卻是一個從遠方來的,不知名的行人。”把愛情比喻成一種喚醒,喚醒前就是漫長的睡眠。“她不知道除了‘我以外還有一個‘你。”自發的生命狀態,只有當遠方的人來喚醒,才能轉為自覺。
“——水流得有多么柔和。
——這人一定走過長的途程,多么疲倦。她繼續想。
——這里的楊柳還沒有衰老。
——這人的頭發真像是一堆蓬草。
……一個人在洗衣,一個人佇立在水邊,誰也不知道誰的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他們所想的,又好像穿梭似地彼此感到了。”
散文詩式的反復以及意識流動構成的潛在對話,構思十分精巧。伍子胥夜行晝伏,奔走過程里饑腸轆轆,生活的匆忙與復仇使命,本不應使他有出格的幻想,他精神渙散,身體疲乏,在異國的流浪里,突然出現這么一個攜帶簞筥的女子,“她把飯放在那生疏的行人的手里,兩方面都感到,這是一個沉重的饋贈。她在這中間驟然明了,什么是‘取,什么是‘與,在取與之間,‘你和‘我也劃然分開了。”二者的人生在給予和被施舍中得以交融,只可惜,他別無選擇,憂愁錯過,文本浸在一種哀傷凝持的氛圍里。但分明不同于相遇之前的空白,二者的人生已被彼此開拓出更豐饒的一面。
三、“小我”的吸引被“大我”壓倒
從子胥拿起弓箭并決定走到更遠地方的那一刻,他已背負了來自家族父兄的復仇重擔。他開始流亡,荒野之外,遇到眾人。他見到了林澤中與妻過平靜生活的楚狂,見到久違的小時玩伴申包旭,也見到抱著極大希望去覲見卻只能令自己失望的太子建。當行到鄭國,他對賢德卻已逝的明君子產感到敬慕;走到宛丘,也遭到過小人司巫的暗算。他看到士兵并不悲壯而極其渺小的死亡,他得到漁夫友善而質樸的幫助。在這之中,他在行進中不斷拾起自己的仇恨,也不斷思索自己異于常人的命運。
他始終對有高貴美好心靈的賢人季禮懷有崇敬,可現實卻縛住了他的手腳。“他雖然還有向著高處的,向著純潔的紙鳶似的心,但是許多沉重的事物把他拖住了。”正如馮至在后記中寫的“在停留中有堅持,在隕落中有克服。”為了國仇家恨,伍子胥不得不放棄自己本心所追尋的美好,但人生本來就是在抉擇和可能的往復中行進,當一個民族面臨極大的威脅,個體往往不能適情任性,而必須去承受其中的苦痛。
四十年代戰爭時期,馮至在與夫人姚可昆合譯《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的譯本序中曾提到德國的修養小說,“在社會里偶然與必然、命運與規律織成錯綜的網,個人在這里邊有時把握住自己生活的計劃,運轉自如,有時卻完全變成被動的,失去自主。經過無數不能避免的奮斗、反抗、誘惑、服從、迷途……最后回顧過去的生命,有的是完成了,有的卻只是無數破裂的片段。”[4]顯而易見,《伍子胥》這部偏重人物內心思索的詩化小說,深受德國修養小說的影響。而伍子胥歷險式的逃亡經歷,雖受到誘惑、走入迷途,但最終并無妥協地卷入了復仇計劃的部分。
在馮至這里,伍子胥最終拋棄了對于形而上的自我追尋,反諸于形而下的真實痛苦,他走到吳市當中,作為面貌黧黑的畸人,吹起飽含深情的曲子,人們涌向他,而一個偉大的復仇計劃便從此開始。
注釋:
[1]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391頁.
[2]馮至.《馮至全集:二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192頁.
[3]唐湜.《馮至的<伍子胥>》[J].文藝復興(第2卷),1947,(1).
[4]歌德著 馮至、姚可昆譯:《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8.第二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