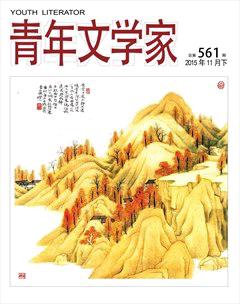小說《桃之夭夭》的女性主義思想淺析
摘 ?要:王安憶創作的《桃之夭夭》可以說是一部表現女性主義思想的小說。故事女主人公郁曉秋從小到大面臨的艱難處境,有著深刻的文化和歷史原因;同時,作家對小說中女性的形象塑造,也反映了女性的堅韌與偉大,彰顯了女性獨特的生命體驗和價值。
關鍵詞:女性主義批評;處境;文化批判;女性形象
作者簡介:呂蓮(1989-),女,漢族,湖北仙桃人,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3-0-02
女性主義批評起源于西方,它與當時的婦女解放運動是聯系在一起的。婦女們通過兩次女權運動爭取平等與自由,由此女性主義批評催生出來,并在后來為女權政治運動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女性主義批評是一種以女性為中心的批評模式,它關注的是女性形象、女性作家及其創作,女性話語等方面的內容。通過對隱含在作品背后的政治、經濟、性、種族等因素的深刻分析,企圖對男性中心話語進行重新的解構,在爭取男女平等的同時,真正尋求女性的獨特價值。女性主義理論在20世紀八十年代傳入中國,引起了軒然大波,從此女性批評、女性作家創作風起云涌。王安憶作為新時期女性作家中的一員,她以女性特有的筆觸和獨特的思想深度給我們創作了一部部優秀的作品。小說《桃之夭夭》是其中的一部,它講述的是上海市井間的一位普通女子郁曉秋的半生歷程。女主人公遭遇的冷漠親情、友情和負心愛情以及周圍人對她的種種流言蜚語,都使她處在艱難的境地中。然而,這樣一個如桃花般美麗的女子,卻有著單純善良而又積極向上的旺盛生命力,讓她“灼灼其華”。
小說中的郁曉秋因為是個私生女,從小就遭到弄堂巷里人們的各種非議。她的母親和同母異父的哥哥姐姐也對她很冷漠,仿佛她是個多余的人。她的青春美麗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都成了她被打壓的理由。她十幾歲的時候,因為過早發育的身體曲線,便被母親罵為騷貨。“她走路有一種挺胸收腹的姿態,后臀微微翹起,腳尖著力,步態輕盈。”[1]這本是少女發育的正常體態,但是她的這種變化卻滿足了男人們的性幻想。不知不覺,她有了“S”、“貓眼”、“工廠女西施”這樣的稱謂。“自從男權中心秩序被確立以來,女性就作為男性欲望的對象存在著,女性是男性的財富,供男性享樂。女性的身體是男性欲望的載體。”[2]所以她成為眾多男人側目的對象。在學校練習腰鼓的時候,她的“特殊”引發了工宣隊領導的“關注”。他們把這個只有十五歲的女孩稱為“女人”,她的舉手投足成了焦點。在那個革命文化的背景下,禁欲傳統時時刻刻壓抑著人們。而她的身體一方面使男人的性壓抑得到暫時的想象發泄,而另一方面她卻成了人品不正、淫蕩的代表。關于這點,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闡釋。首先,在男權社會里,女人便被認為是“禍水”。女性在這里不僅是男性發泄性欲的工具,同時又承擔了可怕的罪責。小說中工宣隊的領導因此不讓郁曉秋出現在游行方隊中,理由是有不良行為記錄,作風有失檢點。當母親笑明明去詢問原因時,給出的卻是“教育她艱苦樸素”。這其實是男權社會對女性特別的壓制與詆毀。這與她在下鄉的時候,被當地人認為是“大地方人真是知曉人事晚”,認為她在性方面單純率真,形成了多么強烈的反差。其次,這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革命的政治已經由于畸形的發展而演變成新的專制體系,這是一種嚴酷的異化。這種專制體系是對個體生命內涵的全面封鎖。”[3]革命時期,個人作風問題被提上日程,保持低調樸素一致,是時代的大的趨勢。郁曉秋注定是被時代所排擠的。
女性除了要面對男性社會的規約,還要遭受來自同性的無聲打擊和詆毀。郁曉秋的媽媽笑明明因為生下了她,便被保姆排擠。在保姆看來,這家的男主人郁子涵雖然出軌在先,但是是正常的,仿佛已經在心底默認就應該是這樣。但是笑明明的出軌卻是不容原諒的。關于這點,法國著名女性主義批評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說:“一個女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沒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經濟上的定命,能決斷女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而是人類文化整體,產生出這居間于男性與無性中的所謂‘女性,女人是男人用以確定自己存在的參照物,是一種補償性事物,是男人的理想和神話,而唯一不是的便是她們自己。”[4]“女人”是由后天“形成”的,在男性社會她們成為“他者”,成為“第二性”。同樣還有郁曉秋的那些女同學,她們用犀利的目光和意味深長的笑容開始檢視她,“你晚上穿的和白天不一樣!這一突然的指出似是沒頭沒腦,但女生們的神情卻很可玩味,懷著一股故意的嫌惡,有心要揭露和刺傷什么的。”[5]市井間流傳的流言蜚語,它們可以肆意詆毀一個人,甚至可以阻擋一個人的幸福。郁曉秋和初戀何民偉情投意合,卻因為姐姐何民華聽信外界的讒言,便也認為郁曉秋是放蕩不潔的女人,從此就拼命阻止戀情直至最終拆散了他倆。是想,同樣身為女人,她們為什么會對這樣一個內心善良的女孩子進行打擊呢?不排除的一點是內心深處的妒忌與艷羨。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她們受到男權社會根深蒂固地影響。在她們的觀念里,女人應該是男性眼中的那種女人,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文化所倡導的“三從四德”、“三綱五常”下的貞潔女子。在古代,如果一個女人不是貞潔的,那是要被處死的。而在郁曉秋的時代,她被惡意地認為是個不潔的女人,這在人們心中是不能接受的。這些女人們受著根深蒂固的男權思想的禁錮而不自知,反而成為男權社會的幫兇,去傷害她們的一位同胞。這是集體無意識下的群體悲哀,廣大女性深受其害的同時又去傷害其他同胞,實在是可悲的。女主人公郁曉秋深知作為女性的辛酸與不易,所以在后來她結婚產下一名女嬰后,“她的心里疼痛了一下”。她是女人在這個社會已經受到各種折磨與刁難,而一想到自己的女兒也許將來也要面臨作為女性的種種痛苦而不能改變,她自己是難受的。
雖然經受了命運的各種不公與折磨,但是小說里的女主人公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精力與生命力。在命運面前,郁曉秋展現出來的狀態是平靜的,順其自然的,野性的,堅韌的。她沒有刻意地去叛離去回避,反而在面對一次次命運的打擊時去接受與面對,在殘酷的生活面前,帶給人的是真實善良的努力向上的女性形象。親情雖然淡漠,但是她依然對他們不離不棄。母親忙于戲劇,她從小便獨自承擔起家務活。雖然從小與姐姐不親,但是姐姐生病住院,她省吃儉用,補貼家用的同時又想方設法地弄錢給姐姐買營養品;姐姐因為生孩子而死亡,留下的一個小生命,她每次都去悉心照顧。“當她接近嬰兒時,嬰兒竟像遇到熟人似地,朝她懷里一頂。郁曉秋心頭一熱,看著懷里的肉團,眉眼已可見出幾道線,分明也是個人,有知覺的,不由摟了摟。”[6]在這個世態炎涼的社會里,她有一顆始終善良真摯的心。姐姐的婆婆是個十分嚴厲的寧波老太太,而她的一系列舉動卻令這個老太太心里動容,孩子和老太太十分喜歡她。而姐夫最后能與她結婚相守,也證明了這樣一個女孩子的人格魅力。在面對愛情時,她似乎是遺傳母親的心性的。在小說第一章便介紹了她的母親笑明明。笑明明是個個性爽朗,敢作敢為的女子。這與她的丈夫郁子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郁子涵出場給人的印象是衰落門第下孱弱的書生形象。“可這少年,穿了洗白的毛藍布長衫,藏在梨樹的花影里,真像一個秀美的姑娘。”[7]他見到笑明明時是羞怯的,緊張不安的,從此以后笑明明便記住了這個清秀的男子。她心疼他,用她的母性包容他,支持他。郁子涵跟著她跑到劇團里,她養活他;送他去重慶讀會計學校以便將來在上海有好的工作,她給他學費與生活接濟;他把錢拿去與友人吃喝玩樂,讀書不成,窮酸可憐地回來找她,她卻放棄大好的結婚人選去與他結合。與笑明明高尚的無私的母性形象相比,作為男人的郁子涵是脆弱的、自私的,不負責任的。他甘于活在笑明明的保護傘之下,受盡呵護與疼愛,像個長不大的孩子。以至于后來在單位出軌女同事,惹上財務危機,最后還要笑明明來收拾爛攤子。而郁曉秋作為她的女兒,在愛情里對男人也是無私付出的。她與何民偉相戀,為了他一直在上海等待著他回來,然而他們倆的戀情卻遭到了來自以何民華的家庭成員的反對。正當他們為了在一起而努力時,這個男人卻經受不起外界的考驗,沒有堅持下來,最后怯弱自私地放棄了她而與別的女孩結婚。而郁曉秋雖然把自己的身體給了他,可是,她并沒有像別的女人那樣去拿性去糾纏,這是她意識中的覺醒,也是心底里的善良。這兩個男人的形象在兩個女人的映襯下是矮小的,脆弱的,自私無用的。他們需要女人照顧,又經不起外界的風雨。劉慧英在《走出男性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一書中曾經說過,在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里,人們對女性的形象要求就是應該是無私奉獻的,不求回報的,她們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母性關懷,時刻照耀著男人,這樣才是完美的,也就是傳統道德標榜的“賢妻良母”。而這樣的“賢妻良母”往往成為了男人最終拋棄的對象。當然,在這里也并不是主張女人變成“與男人一樣的人”。女性應該要擁有自己獨特的特性,但是也要追求兩性關系的一種和諧。女性對男性,不論是從身體靈魂來說,都不應該是從屬或者屈服,而應該如學者李小江所說,“在兩性和諧共處的基礎上爭取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
回顧王安憶的一些小說,我們可以看到她塑造的男性形象有些是孱弱而矮小的。例如《長恨歌》里面與王琦瑤接觸的一些男子,《荒山之戀》里面與兩名女性有愛恨糾葛的那個“他”,本文所討論的《桃之夭夭》里面的郁子涵和何民偉。相比之下,作家創作出來的女性卻是獨特而唯一的。她們都在自己的人生經歷中去感悟作為女人的獨特體驗,或是經歷時代變遷繁華落盡,或是處于兩性的復雜情感糾結,或是面對平凡的生活中的流言蜚語,等等。這不僅僅是作者為了展現兩性優劣而刻畫的兩性人物形象,更是作為一個女性作家,她以自己的女性視角去感受筆下的女性獨特的生命體驗。《桃之夭夭》中,作家始終是以冷靜而不飽含情緒色彩的心態去敘述,仿佛是讓女主人公郁曉秋自己去經歷她人生的悲歡離合。
小說《桃之夭夭》不僅表現了在男權社會的控制下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和所承受的重負,也向人們刻畫了女性獨特的生命意識,體現了女性的堅韌與偉大之處。正如小說結尾所描寫的,在經歷了如桃花般的年紀之后,女主人公那特別活躍的外在生命力逐漸向內延伸。“就像花,盡力綻放后,花瓣落下,結成果子。外部平息了燦爛的景象,流于平常,內部則在充滿,充滿,充滿,再以一種另外的,肉眼不可見的形式,向外散布,惠及她的周圍。”[8]這就是女性隨著年齡增長的獨特價值與魅力吧。
參考文獻:
[1][5][6][7][8]王安憶.桃之夭夭[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2]李清霞.女性:如何從肉體回歸身體—兼論<桃之夭夭><青狐>女性的描述[J].小說評論,2004,(6).
[3]劉新征.<桃之夭夭>的文化批判探析[J].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7,(4).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