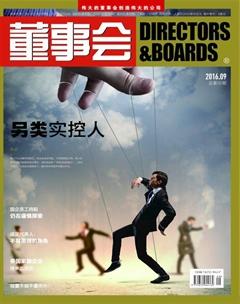阿里合伙可以,萬科為何偏不行?
劉鳳委
萬科與阿里在推進合伙人制中存在本質不同,后者在上市初定規則時就已經得到了大股東的支持并公開按照此事先約定的規則融資,是規則改變在先,絕大部分已有的科技型企業也都是按照這個邏輯,不涉及控制權的組織變革也往往是股東在推動
在近期如火如荼的萬科事件中,“內部人控制”一詞被股東反復提及。上世紀80年代,日本學者青木昌彥使用內部人控制來特指轉軌時期由于國有股權缺位所形成的內部人接管和控制公司并最終損害國有股東利益的行為。也是在兩年前,萬科總裁郁亮提出了“職業經理人已死,事業合伙人時代誕生”的口號,合伙人的概念日益引發關注。管理層是侵害股東利益的內部人,還是重塑公司價值的合伙人?隱藏在萬科控制權斗爭背后,除了利益和情懷之外,是否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所應有的經濟規律,值得深思。
誰最終決定控制權歸屬?不是法律
在現代企業治理中探索股東與管理層關系時,我們常提到的一句話就是遵守現有游戲規則。當我們用游戲規則來框定事件當事人行為時,或許需要檢討規則本身是否正在遭受時代的挑戰。
科斯在利用交易成本理論從契約觀視角解釋公司存在的理由時,并未確定公司控制權的歸屬標準,即誰控制公司更有效。決定公司控制權歸屬的最終原則,其實不是法律,而是市場競爭。即使法律嚴格規定某一生產要素獲得控制權,當環境改變時,效率和企業生死存亡的壓力必然會衍生制度變革,使得順應市場競爭環境的商業模式、組織管理與文化制度脫穎而出,為企業迎接新的生存發展邏輯提供注腳。法和經濟學的關系表明,法律的頒布與實施同樣遵從嚴格的經濟規律,現有治理規則框架本身就蘊含著效率標準,即資本所有者控制公司是相對合理的一種安排,資本雇傭勞動本身蘊含的契約和權力架構更有助于公司形成及發展。但當我們熟悉并普遍采用這套規則,以及按照這套規則去作為是否對錯判斷的準繩時,往往已經忽略規則制定本身的邏輯所在。
當前,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治理準則,就是資本所有者掌控公司,經理人管理公司;前者是委托人,后者是代理人;委托人會通過監督、評價與控制等一系列治理手段降低代理成本,甚至可以罷免不聽話的代理人。按此標準,一旦委托人和代理人出現矛盾時,社會都會爆發對管理層的譴責;而不會去思考時代變革背后所賦予的公司使命,是否需要去重新認識,更不會關心游戲規則是否合理。從社會發展角度來說,對于已經形成的契約和規則的遵守是社會正常運轉的基石;但從實踐發展和社會變革的角度看,則必須承認最終決定成敗的關鍵不是規則賦予誰權力,而是要靠市場競爭的結果判定誰擁有控制權更能夠讓企業保持可持續發展。歸根結底,公司價值創造的源泉是客戶與市場,只有適應市場發展并積極參與競爭勇于革新的公司才能夠為公司利益相關者創造價值,保持公司存在的歷史使命。傳統的公司治理規則過于強調價值分配和效率,突出由此導致的利益沖突如何控制與防范;知識經濟時代則更強調價值創造和可持續發展,重視公司如何在高度不確定的適應競爭環境下生存與發展。
時代變了,知識資本共享組織權力
公司合伙人制度的到來不是偶然,背后的宏觀背景是方興未艾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驅動邏輯是生產技術的進步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方式改變了企業的組織形態。
回顧歷史,人類社會共經歷了三次影響深遠的技術革命,每一次技術變革都伴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和企業組織形式的更迭。毫無疑問,我們當下正處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重大變革之中,隨著互聯網徹底改變了人們的消費和生活習慣,企業的組織與生產方式也正在實施轉型。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看,第四次工業革命對人才的依賴更強,而資本的稀缺程度下降,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重新博弈,成為企業組織轉型的重要背景。博弈的結果是資本所有者要讓出部分所有權、決策權、分紅權與人力資本共享,改變資本雇用勞動的局面,實現物質資本和知識資本的共同治理。對那些迫切依賴于知識資本并因此陷入成長困境的企業而言,只有這樣才能留住人才、發揮人才的積極性,實現組織的基業長青;而對某些行業或企業而言甚至可以更進一步,引發公司控制權革命,知識資本獲得控制權,充分確保公司價值觀與文化的傳承,實現公司法人主體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基于股東價值最大化的治理邏輯容易忽視公司的社會屬性,尤其是上市公司常常被短期利益或業績壓力所左右,缺乏為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堅守;合伙人制度下公司是一種組織、制度,也是人們生產生活存在的一種重要載體和方式,其和諧發展的可持續性更強。
合伙人制成為公司組織模式變革的一個重要方向。目前,這種制度變革趨勢已經不是預測,而是真實地發生在已有的各類企業實踐當中。谷歌、臉譜、京東、阿里等大量互聯網公司所出現的公司治理變革,說明知識資本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現象,其已經開始對傳統的治理規則形成挑戰。港交所迫于現有規則拒絕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既可以稱之為對規則的遵守與承諾;也可以視作對現有企業制度創新的挑戰應對不足。目前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包括海爾和華為,正在不斷實施組織再造以適應社會環境的巨變。美的、碧桂園、綠地集團、龍湖地產、越秀地產、首創置業等傳統制造業和地產業,也都開始逐步摸索合伙人制度,試圖破解企業成長發展困境,克服現有組織發展的瓶頸。目前合伙人制在各公司的實踐雖方法不盡相同,有的涉及治理層面的控制權變革,有的涉及管理層面的組織創新變革,但制度設計的出發點類似,就是要通過與知識型人才合伙,發揮人才的創造力,形成公司的持續創新能力,以迅速響應客戶需求,提升公司運營效率。
合伙人制,并非每一個公司都適用
但毫無疑問,并非所有公司都適合這種模式。
首先,公司必須是知識型人才或文化驅動的公司,這是前提和基礎。其次,由于涉及控制權問題,合伙人制度實施時必須要注意實施的先后順序,包括實施的方式與方法,需要得到股東的理解和支持,否則將產生激勵的利益沖突和斗爭。此外,合伙人制本身也可能會產生新的問題,如合伙人內部團隊的治理是否順暢、合伙人是否會以追求公司長期利益和價值觀名義損害股東、員工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等。
譬如,萬科與阿里在推進合伙人制中就存在本質不同,后者在上市初定規則時就已經得到了大股東的支持并公開按照此事先約定的規則融資,是規則改變在先,絕大部分已有的科技型企業也都是按照這個邏輯,不涉及控制權的組織變革也往往是股東在推動。
萬科事件之所以引發爭議,是在于公司上市時已經接受了現有治理規則安排,是事后的規則變革。現有萬科合伙人制度包括持股計劃和項目跟投制度,將從某種程度上深刻改變利益分配方式、發展方式和管理模式,因此其管理層必須在現有規則下得到股東的理解支持,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要進行充分的協商與溝通。否則就是嚴重違背現有規則,甚至存在侵占股東利益獲取非法收益的可能性,內部人控制的說法也就由此出現。畢竟,承認規則的前提下再挑戰規則,并不是單方面的努力就可以實現。因此,本次萬科事件所折射出的公司治理問題值得深刻反思。
總之,在技術變革與智力資本崛起的時代環境下,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將會在更廣泛的利益面前重新思考彼此的關系與定位,企業組織的發展邏輯與評價方式或將在人力資本控制時代獲得根本性的轉變,這將對企業長期價值觀的確立、傳承與可持續發展帶來重要影響,對未來人類社會關系也將帶來革新。
作者系上海國家會計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