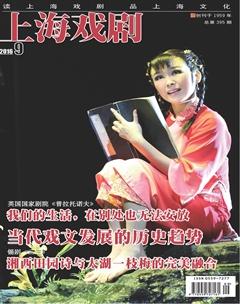永不消失的溫暖
史濟華
談起我和畢老師,不得不說幾件至今記憶猶新的細瑣之事。然則,細瑣的點點滴滴于我個人和越劇卻都存有著永不消失的溫暖。
1958年,我剛從戲校畢業進入越劇院,參加越劇折子戲青年匯演,記得是在瑞金劇場,當時這里是靜安越劇團戚雅仙和畢春芳老師常駐劇場。二位老師因為晚上自己要演出,因此特地提前來看戲。演出結束后,老師們來到后臺,畢老師高興地對我說:“小史,儂男演員扮相好,嗓子好,唱得好,基本功也扎實,是我們越劇難得的人才呀!”我一個剛畢業的毛頭小伙,當時聽了畢老師的話不知有多少激動,心里頓時閃爍著無盡的喜悅。90年代,靜安越劇團借我去演一出歌頌當代英雄的現代戲。劇本趕創出來,日夜馬不停蹄地排練,畢老師和戚老師經常來排練場探班,時刻關心排戲的情況和演員的狀態。畢老師總對大家說:“小史聰明來賽,自己作唱腔,塑造人物有辦法,出戲也快!”對我說:“辛苦你了,來幫阿拉靜安團的忙!”這些溫暖的話語和鼓勵,我都一直銘記于心。畢老師始終抱持著對青年演員濃厚的關心和支持,同時對越劇男女合演的支持也為我們的發展增添了無盡的動力。而當時許多人對越劇男演員上臺演出的態度依舊處在不習慣,甚至反感的階段。觀眾不習慣,認同少,支持少,可以說當時越劇男女合演充滿著難以言表的艱辛與滄桑。前路流溢著黑暗與光明,陽光終會來臨,而就是有了像畢老師這樣一批支持者溫暖的關心與鼓勵,我們的越劇男女合演才能更有足夠的勇氣和信心,步伐才能走得更加堅定。
1979年,文化廣場舉辦尹派專場,我在去的路上正好巧遇了畢老師,和老師一路暢聊。當時我冒昧地問畢老師,我說:“畢老師,感覺您的流派中有很多尹派和范派的元素,是么?”畢老師笑了笑,坦率地回答:“是呀!我學習吸收了尹(桂芳)派和范(瑞娟)派,結合自介條件,瞎唱唱出來的!”當時心想:哇!老師那么謙遜、好學,已成大家依舊是如此謙虛,心中油生敬佩之情。是呀,所謂的戲曲“流派”藝術是演員個人學習繼承中沉淀出的較為穩定且特有的表演風格。戲曲流派在戲曲藝術發展繁榮時必然會出現,這不是偶然。從戲曲藝術規律而言,唱腔、表演需要演員自己不斷探索、刻苦實踐,與此同時需集眾家之長,融匯貫通,傳承中不斷地突破創新,這才能締造出真正的有風格特色的流派藝術。畢老師懂得博采眾長,去粗取精,學習尹派和范派時,不是盲目地依樣模仿或炒雜燴,而是結合自己的條件注意吸收創新,提煉創造出了風格相異自己的流派。可以說老師的藝術實踐點滴都印證著戲曲藝術創作的規律,這對我啟發太大了,應一直銘記和學習。
藝術的創造是在生活里體悟與融合,在生命中點亮的。80年代,我給畢派高足阮建絨創作一段曲。我二人一同去老師家請教,畢老師看了看唱詞,五分鐘后便哼出了一段動人的曲子,唱腔感情抒發到位,既符合人物性格和規定情境,同時風格上也是地道有味的畢派特色。我迅速將譜記下,當時冒失地問:“畢老師,儂識簡譜么?”畢老師說“不識的。”我不禁大聲稱贊道:“天才!”經過不斷地舞臺實踐,老師音樂組織能力極強,對音樂節奏和色彩的把握上,她從人物感情出發,結合劇情幻化出劇中人生命的唱腔。這是老藝術家們長期舞臺鍛練實踐的結果,也是流派形成的必要條件。且在藝術創作中,老師使得自己的流派特征統一于整體,符合劇本的主題、情節結構和人物性格與情感。這些點滴都是我們后輩所要學習的地方。
談起畢老師,大家一定會想到她那招牌表情,舞臺上神情幽默風趣,生活中聲音笑貌那樣的祥和溫暖。我永遠記得畢老師的招牌表情,那一抹祥和溫暖的笑容!
時間流逝的何其之快,悄無聲息。于今參加完畢老師追悼會路上追憶起過往歲月中我與畢老師的點滴,傷逝的悲情中蘊藏著無盡的溫暖與感動。“人生一世,春芳百代。”祝畢老師一路走好,愿越劇畢派藝術常青! (執筆:上海大學 吳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