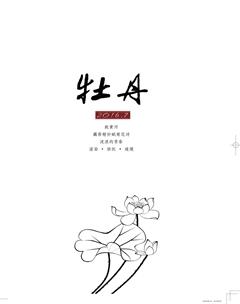《北戴河故事》中處境兩難的異鄉人
王丹妮
哈奈·米納是一位久負盛名的敘利亞作家,他以多產、求新的特點成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阿拉伯作家之一。在其眾多作品中,《北戴河故事》尤為特別,它是一部以中國為背景的敘事小說,小說以獨特的視角描述了主人公祖貝德20世紀70年代在中國的生活經歷,小說的內容反映了當時外國專家這一特殊群體在中國的生存現狀,并由此反映了當時的外國專家,即異鄉人兩難的生存處境。
“異鄉人”這一概念是置于社會學“空間關系與人際關系”的背景下產生的,齊美爾在其作品《異鄉人》中這樣定義這一特殊群體:“異鄉人是潛在的流浪者,他被固定在一個特定空間群體內,或者在一個它的界限與空間大致相近的群體內。”小說中的“異鄉人”主要是指以祖貝德為主的這些來中國支援社會主義建設的外國專家們,他們中有些人是從西方而來的白人,有些則是從其他國家漂泊而來的亞洲人,流亡是他們共同的生存狀態。
小說中作為異鄉人的外國專家們小心翼翼地生活著,他們的生存空間十分狹小。主人公祖貝德非常想問最早來到中國的外國人:他們真的了解中國嗎?他得到的答案是:“到現在我們都沒有真正地了解中國,因為我們住在友誼賓館這一特殊居住區,像是被隔離在外一般,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接觸到中國人,我們也不能進入中國人的家里,我想我們永遠也進入不了吧,至少在目前這一時期。”是的,他們仿佛被這個社會隔絕在外,在這里他們不能完全地做自己,走出家門便開始偽裝自己,背井離鄉的他們無法找回自己的身份。
在這種被隔離的狀態下,“異鄉人”漂泊無依、寄人籬下的孤獨與無奈油然而生。在描述祖貝德的生存現狀時,小說寫道:“這種前所未有的孤獨使他非常痛苦。這種痛苦與過去、將來都沒有關系,在這種情況下,他無法擁有夢想,即使有了夢想,這個夢想又何去何從呢?他又該在哪里去實現他的夢想呢?是的,在這里他有固定的工作,體面的收入,健康的身體,豐富的娛樂活動,可是他依然感到孤獨,他該怎樣才能擺脫這種困境?回家嗎?他回不去了,最后他對自己說還是選擇忘卻吧。”小說中的主人公祖貝德經常思考自己孤獨的原因,有一日他似乎找到了答案:“第一是因為他無法回國,第二則是因為他與這里的人在思想、原則上都不同。兩個國家的差異是無法逾越的鴻溝。他們回不去自己的國家,也無法安然地生活在這里,他們的歸宿在哪里?他們的根又在哪里?”他們無法抵抗現實,他們在流浪的途中始終沒有忘記對自己身份的追尋與認同。
小說主人公祖貝德在面對自己身份的追尋與認同過程中進行了空間實踐,這尤其體現在他與女人的關系上。他不斷尋找不同的女人相處,并與這些女人保持長期的情人關系,其中有來自英國的單身女性瑪麗,還有有夫之婦布里奇女士及音樂家妮露薩女士等。潛意識里,他認為與這些女人的親密接觸能彌補他在身份認同過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防止他被模糊不清的身份吞沒的危險。“祖貝德難以入睡,他感到空虛、不安,而這些女人只能暫時填補他的空虛。”“前一秒他身邊還有一個女人陪伴,可是這一秒,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那些空虛迎面而至,盛滿他的胸懷,他多么希望那短暫的安全感能一直存在啊。”但是事實上,在身份認同的空間實踐中,祖貝德并不能從女人身上得到希望。“祖貝德渴望愛情,渴望真正有一個女人能走進他的心,治愈他心靈的傷口,可是他發現身邊這些女人都無法真正治愈他的傷口,只是給予他短暫的慰藉。”
此外,在身份認同的空間實踐中,異鄉人祖貝德希冀發現自己同他人的差異,并通過彰顯這種差異性來確定自我的身份。霍爾在《多重小我》中指出“差異”在身份認同建構中的作用,在他看來,“所有的身份都是建構在差異之上,而且與差異政治并存”。祖貝德是一個熱愛冒險、特立獨行的人,他皮膚有嚴重的外傷,可他偏偏不去醫院,反而坐在陽光下暴曬,他認為自己是在拿命運賭博,聽天由命。從祖貝德的婚姻觀中,我們也能看出他極力彰顯差異性,他認為婚姻是監獄,是枷鎖,會束縛他的自由。因此,雖然現實情況允許他向其他外國專家一樣建立一個家庭,但他并不想這樣做。他自己也用家鄉“叛逆”的河(阿綏河)類比自己叛逆的個性。可他意識到這是一種冒險,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填補自己內心的空虛與寂寞。“他承認自己是個有心理疾病的病人,不是心理醫生的俄羅斯醫生已經看出了他內心的孤苦,并希望他通過建立一個家庭得到解脫,可是他自己不想承認自己愛無能,他發現來自外界的建議也并不能治療他的心病。”最后他追問自己,為什么要這樣做?“原來他的一切行為——冒險、借酒消愁、與不同的女人發生關系,都不能填補他的空虛,而他做這些事情就是想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但是至今未想通。”
實際上,在身份認同的過程中,祖貝德在與自己同胞的交往過程中也看到了自己的生存困境。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霍頓·庫利在《社會組織》一書中提出“鏡中我”的理論,他認為,人的各種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自我觀念,而這種自我觀念多是在與他人的社會交往中形成的,他人對自己形成的態度、評價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鏡子”。小說中祖貝德獨特的行為經常引來大家的討論,“意大利人穆里認為他所有的行為都是故意為之”。他的情人瑪麗認為他是個飄忽不定、令人捉摸不透的人,布里奇女士及餐廳經理一致認為祖貝德是個叛逆的人,并多次囑咐祖貝德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妮露薩女士則建議祖貝德去看心理醫生。通過小說中其他人對祖貝德的評價,使祖貝德對自我性格及其境遇有了一定的認知。
無論身處異鄉與家鄉,異鄉人都已是“他者”。故鄉與異鄉一樣,都成了永遠也無法進入的“城堡”。這種漂泊的精神處境讓他們不屬于任何一個世界,只能生存在二者的縫隙之間,即“無家可歸”的人。在追求身份認同的一系列空間實踐中,異鄉人的生存困境顯露無遺。“祖貝德覺得只有在與阿拉伯兄弟們的相處中才感覺到輕松自在,因為在這里他不會感覺到自己與他人的差異,大家都有相同的膚色、相同的手、相同的語言,大家都是一家人。”祖貝德無時無刻不在思考自己的歸宿,他不止一次在內心問道:“究竟他們的歸宿在哪里呢?自己在家鄉被驅逐,在這里也會被驅逐?”“憑借著對平等社會的美好信念,他離開了自己的祖國,現在他就身處于這個平等社會,但卻也有著被放逐的威脅,那么他究竟去向何方呢?”“也許最終他的狀態是走向死亡。”
(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