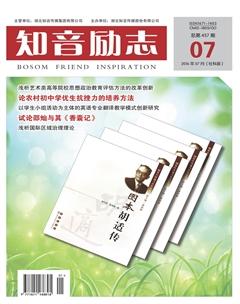“三吏”“三別”歷史場景的寫作藝術
邊婷婷
摘 要
本文將“三吏三別”作為研究對象,分別從作家敘事的形態、宏觀和微觀角度并行、場景書寫的語言藝術三方面著手,分析“三吏三別”組詩中歷史場景的寫作藝術。
【關鍵詞】“三吏三別”;歷史場景;對話和代言;宏觀與微觀;語言藝術
“三吏三別”組詩是杜甫有感于自己從洛陽返華州路上的所見所聞而書寫的詩篇。在詩中,他既描繪了戰亂國衰中的民生苦難的場景,也描寫了民眾眾志成城舍小我保國家的歷史場景,在此基礎上他在傳達了自己復雜矛盾的情感-------在同情憐惜廣大勞動人民的同時又鼓勵百姓獻身國事。在這深切的矛盾中,杜甫展現了自己的寫作藝術,并從這個角度理解元稹對杜甫的以“三吏三別”為代表的新題樂府詩的 “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至高評價。
1 巧用代言和對話
在“三吏”中的書寫便是采用第一種方式-------描寫對話:在《石壕吏》中,敘事者因為借宿在石壕村,所以親耳聽聞石壕吏與老婦的對話;在《潼關吏》和《新安吏》中,敘述者同是與官吏進行對話的對象。敘事者以事件發生的親歷者的身份展開自己的敘事,為讀詩的人營造了一種現場報道的真實感。 “修關還備胡?”等都是敘事者先對吏官進行的發問,在這場“采訪”中,作家通過敘事者的對話,分別向我們展現了防守堅固的潼關和守城的將士自信滿滿的場景和新安征次男、“肥男與瘦男”無奈告別家鄉的場景,進而作者做出自己的評價。這種直接以“我”的敘述視角的進行描寫對話的方式展現歷史場景的方法,是作者有意為之的敘事策略,使讀者認為這是第一人稱親身參與的實錄。
在“三別”中,杜甫采用了一個全新的敘述者,這三個敘述者分別是新嫁娘、無家士兵、老者,作者假托他們的視角展開全景式的心理自白的描摹,進而達到一種符合人物本色的真實。比如在《無家別》中的士兵,他通過自陳說明了自己因為鄴城兵敗歸家,目睹了“園廬但蒿藜”、“世亂各東西”、“日瘦氣慘凄”等的場景,有了“久行見空巷”、“但對狐與貍,豎毛怒我啼”、“方春獨荷鋤”等的生活經歷,進而自白而真誠地訴說了自己痛失家鄉、征役不可躲藏、無法侍奉老母的種種痛處,批判了這個戰亂的時代。杜甫正是通過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說典型人物該說的話,達到了一種主觀化的真實,并通過個體展現當時的歷史場景。
2 宏觀與微觀歷史場景的共同展現
宏觀歷史場景的再現首先就體現在對戰爭慘狀和戰后場景的描摹上,這樣闊大的書寫深化了災難。“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這是典型的宏觀場景的直接描寫,“盡、披”兩字寫到了戰事波及的地區很廣;堆積的尸體可以將一草一木都染腥,血流成河以至于染紅山川平原。悲慘通過文字直逼入讀者的眼睛,這樣宏觀的慘狀觸目驚心、過目難忘。類似大場面在《潼關吏》《垂老別》中也有涉及。總之,闊大的場面書寫是更能突出場景的慘烈的。
僅書寫大的悲慘的場面是缺少說服力的,于是,從微觀的、個人的生活中截取的畫面書寫又做了及時的補充。“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出入無完裙”、“棄絕棚室居”是寫戰亂中百姓生活的凄苦;“二男新戰死”、“子孫陣亡盡”等是寫戰爭中死傷嚴重,人口銳減的實況。從微觀的角度書寫,以一個家的角度書寫死亡,進而展現國事對家庭的破壞,人民連自己的家庭都保全不了,何談安居樂業呢?這樣的書寫也是有力量的,是歷史場面再現的一種有力的補充。
3 歷史場面書寫的語言運用藝術
“三吏三別”的敘事藝術還體現在詩歌本身的遣詞造句之中。
首先,在寫景上,作者做到了融情于景。“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這里寫到了日夜奔流的河水和留著哭聲的青山,以擬人化的修辭,寫到物我一體,人景齊悲。類似的就是《無家別》中的“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凄。但對狐與貍,豎毛怒我啼。”這里作者同樣運用了擬人的手法,通過寫日的“瘦”、氣的“慘凄”襯托當時家鄉的空曠,與之前的“久行見空巷”相呼應,進而寫到了狐貍的猖狂,以此來襯托出家鄉長久無人的大場景。這句話中的“瘦”字就是作者煉字的體現,用得精確巧妙。以上情和景的關系是正相關的,是以哀景寫哀情的體現,還有一類景,是作者以樂景襯哀情的體現。“仰視白鳥飛,大小必雙翔。”這里作者以雙鳥雙飛的喜悅反襯了新嫁娘形單影只的孤獨寂寞,將新嫁娘那份渴望與無奈顯露出來。
杜甫語言運用藝術還體現在裁取得當,挑選精準,在平易之中可以深究出款曲來。這一點在《石壕吏》中表現明顯,作者一筆帶過自己投宿、老翁逃走、官吏的大呼小叫,詳細地寫了老婦的言語,通過老婦以這個家庭為例展現了兵役的沉重,之后直接寫了“獨與老翁別”的告別之景,這樣的省略給人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放棄直白訴說結果的方式,進而引人深思。這正如陸時雍所說的,“其事何長,其言何簡,吏呼二語,便當數十言,文章家所云要會,以去形而得情,去情而得神故也。”此外,“三吏三別”的高妙之處還在于他所選取的描寫對象,年邁的老婦、自信滿滿的前線官吏、成群的次男、新嫁娘、年邁老者、剛剛因為戰敗歸家又再次被征兵的散兵游勇,這些形象都具有典型性,是在戰爭的典型環境下的典型人物,他們可以以自身的特性來突出詩歌的主題。
除此以外,“三吏三別”中的個別字眼也蘊含著值得深究的意義。正如韓成武在他的《杜詩藝壇》中所寫到的一樣,《石壕吏》“以淺字敘事寫人”,他分別分析了“投”、“夜”、“逾”、“看門”等字中的深意。以此廣二推之,《新安吏》中,作者寫道:“縣小更無丁”,一個“更”字,寫出了目擊者對于抓丁這件事的驚訝------難道因為縣小壯丁已經抓完了嗎?這一疑問將抓丁的慘狀突出出來。這首詩中,“青山猶哭聲”一句中的“猶”字也獨具韻味,它的聲音與字義將哭聲在空間中拉長,深化了抓丁的悲哀書寫。
“三吏三別”的中的歷史場景是通過多角度、多維度、巧妙地語言展現出來的,因而場景被賦予了真實的特點,這也就展現了詩史的魅力,也正如元稹所贊譽的那樣,是“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詩。
參考文獻
[1]元稹.《樂府古題序》,《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三.
[2]金啟華,胡問濤.杜詩評傳[M].西安: 陜西人民出版社 1984(10).
[3]韓成武.杜詩藝譚[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09).
[4]杜甫著,仇占鰲撰.杜詩詳注 [M].北京:中華書局,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