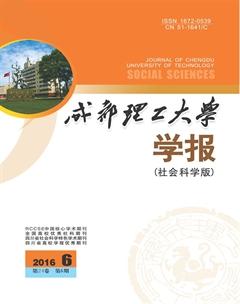論我國古代的商事法律制度お
龐翔宇 高勁軒
摘要:在我國有一部分學者不認同我國古代存在獨立的商事法律制度。本文以兩個部分,分別闡述了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以及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的獨立性及其淵源,以期澄清現代社會對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的誤解。
關鍵詞: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社會歷史條件;獨立性;淵源
中圖分類號: D920.0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6)06002805
我國學界有相當一部分學者不認同我國古代有獨立的商事法律制度,但通過考察我國的商業史和我國古代的法律文獻,筆者發現,我國古代不僅有能使商事法律制度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同時也發現我國古代的商事法律制度有其獨立淵源,我國古代的商事法律制度在實體與程序上獨立于其它法律制度尤其是刑事法律制度之外。
一、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
(一)客觀條件
我們應當承認的是,我國古代商業的發展并不充分。從文明之屬性上,中華古文明屬于農業文明,農業文明的屬性就決定了我國古代社會自然經濟的主體性與商品經濟的不發達性。從國家政策層面,封建君主向來推行“重農抑商”之國策,正如雍正帝所言“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1),國家政策的導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我國古代商品經濟之發育。從民間習慣上,從古至今,我國民眾向來“重儲備,輕流通”,這樣的習慣顯然不利于商品市場與社會化大生產的形成。但不可忽視的是,我國古代商業雖發展不充分,但其并非停滯不前,隨著我國古代生產力的發展,我國古代商業也不斷進步。我國古代的商業活動可追溯至遠古,遠古的中國人以海貝為媒介,進行貿易活動。所謂“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2)。到了周代,尤其是東周,各諸侯國通過改革使“鐵犁牛耕”成為社會生產的主流,通過“鐵犁牛耕”各諸侯國生產力空前提高,在這一背景下,我國古代社會的手工業和商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在東周,不僅出現了如臨淄這樣的商業中心,也出現了像呂不韋這樣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名商大賈,“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3)正表明了當時商業發展的情況。到了西漢,以官營手工業為代表的商業活動開始成為主流,官營手工業開始以長安為中心建立了輻射全國的龐大商業網。在這一時期,我國古代的手工業不僅產生了冶鐵業、鑄錢業、煮鹽業等具體分工,還開辟了一系列商路,連接東西方貿易的絲綢之路即形成于這一時期。隋唐時期,社會的安定與生產力的發展更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在商路上,隋代大運河的開鑿使水路貿易空前繁榮,形成于西漢的絲綢之路貿易量也大幅提升。據《舊唐書》載:“元宵燈會,長安第一,敦煌第二,揚州第三”(4)。可見在唐代由于商路的繁榮,形成了一系列依靠商路發展起來的繁榮城市,地處西北邊陲的敦煌與遠離帝國中心的揚州竟然可與長安一較高下,唐代商路之繁榮著實令人難以想象。從交易的地點來看,到了唐代末期,商業活動漸漸突破了坊市制的界限,甚至還形成了“草市”(5),史籍載“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6),可見唐代商業活動地點之多樣。從商業門類上,隋唐時期的商業門類越發細化,商戶所從事的商業活動越來越專業化。從國際貿易上,隋唐時期幾乎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國的商人,也許我們現在很難看到當時各民族商人交易的場景,但根據歷史學者的研究,今日之回族就是當年來華阿拉伯商人之后代。宋元明清時期,我國古代社會的商品經濟已經發展到了新的高度。在宋代,坊市制已被完全廢除,商業活動蓬勃發展,從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千年前商業之繁榮。通過考察北宋的稅收我們也能了解到當年商業之繁榮。北宋商業稅收一年可達一千余萬貫,以稅率推算,北宋國內貿易額至少為一億六千萬貫,平均到每個北宋居民頭上,北宋人均貿易額可達兩貫之多,合米四到五石(7)。明清時期,我國南方地區產生了以雇傭勞動為特征的資本主義萌芽,形成了為數不少的工商業城市,各地商人也形成了一系列大小商幫,中國商人的階層也從此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
通過考察我國古代商業的發展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我國古代文明雖然是一個不同于西方商業文明的農業文明,但我們不能否認我國古代確實存在著繁榮的商業。我國古代繁榮的商業就是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形成的客觀條件,固然我國古代商業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封建自然經濟的運轉,但我國古代商業的這種存在形式只關乎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獨立存在的形式與特征,而不關乎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是否獨立存在。
(二)主觀條件
在筆者看來,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形成的主觀條件就是我國古代商人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中國商人精神。誠如前文所言,在我國古代存在著繁榮的商業,我國古代的商人在一系列的商事活動中不可能不形成這個群體獨有的精神文化,這種精神文化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國商人精神。中國商人精神作為一種精神文化,自然應被歸入文化的范疇,又因其來源于中國古代商事活動的實踐,根植于中國傳統文明的沃土,因此中國商人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鏈條上的一環。談到中國傳統文化我們就不得不提到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正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之支柱。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鏈條上一環的中國商人精神必然會受到儒家學說的影響,作為古代“四民”中的一員,我國古代商人同樣在儒家學說的影響下形成了較為崇高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在我國古代商人中,素來有愛國重鄉的傳統,上至先秦,有管仲、范蠡等巨富助國君富國強兵,下至清末,有胡雪巖輔佐左宗棠為國效力、張謇辦紗廠力拒洋商。不可否認,作為商人,我國古代商人也存有西方商人一樣的逐利思想,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8),但特殊的是,我國古代商人在逐利的同時也深受儒學義利觀的影響。這里所說的影響并不是說我國古代商人做到了圣人般的道德情操,而是說我國古代的商人群體形成了與儒學義利觀相適應的職業倫理,這個職業倫理一是誠信經營,二是童叟不欺,三是勤儉節約。說到誠信經營與童叟無欺,公沙穆賣豬(9)、趙柔賣犁(10)等故事不勝枚舉,正所謂“吝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11)。可見在中國古代,正直的商人并不會為“利”而賣“義”,徽商以“貨真價實”為核心的商業道德與晉商“以義制利”的商業倫理就是誠信經營的集中體現。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們似乎樹立了中國傳統商人的守財奴形象,但從這個負面形象的另外一面考察,我們就會得出中國傳統商人勤儉節約的一面。自古山西山多川少,晉商之所以成功所依賴的大抵還是在艱苦自然環境里鍛煉出的勤儉精神。當然,在筆者看來,能夠鍛煉我國古代商人群體品格的不只是自然環境,同樣還有社會環境。同樣是受儒家學說的影響,我國古代社會逐漸形成了“重農抑商”的社會傳統和“無商不奸”的社會偏見,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商人們始終排在古代“四民”之末,沒能形成自己獨立的社會力量與政治力量。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我國形成了獨有的“商幫”文化,形成了晉商、徽商、行商等商人群體,商人們抱團取暖,殖產興業,不僅在中華大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商業帝國,也將中華商業文明的種子撒到了海外諸國。可見,以抱團取暖為特征的“商幫”文化也影響了中國的商人精神,或者說它本身就是中國商人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難發現,中國的商人精神實際上是與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相契合的,它為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思想上和道義上的基礎,是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形成的主觀條件。
二、我國古代相對獨立的商事法律制度
(一)我國部分學者對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觀點
國內部分學者對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觀點就是,我國古代并不存在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商事法律制度。關于我國古代法律“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看法由來已久,這個觀點在國內始見于1907年5月清政府民政部的一篇奏文,該奏文云“中國律例, 民刑不分, ……歷代律文戶婚諸條, 實近民法”(12),這一觀點之所以形成大抵是受了日本法學界的影響,近代的日本法學家將梅因(13)有關“中國古代只有刑法,沒有民商法”(14)的觀點奉為至理名言,而近代中國的法學學者由于受到日本的影響,也逐漸形成了我國古代法律“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偏見(15)。這一形成于近代的觀點,時至今日也在我國學界有著重要影響。對這一錯誤觀點,有些學者已有批判,例如,20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法制史學者陳顧遠先生先后發表了《天道觀念與中國固有法系之關系》、《儒家思想與中國固有法系之關系》、《家族制度與中國固有法系之關系》等論文。他在《中國過去無“民法法典”之內在原因》[1]一文中, 分別從程序法和實體法的角度, 對我國古代法律“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說法提出質疑。到了20世紀60年代,陳顧遠先生又在其專著《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2]中再次提出了對我國古代法律“諸法合體,民刑不分”這一觀點的懷疑。一般來講,民法是一般法而商法則是特別法,國內部分學者所持“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觀點不僅否認了我國古代存在獨立的民事法律制度,同時也否認了我國古代存在獨立的商事法律制度。
(二)我國古代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商事法律制度
本文認為,我國古代存在相對獨立的商事法律制度。在筆者看來,之所以會存在“諸法合體,民刑不分”這一觀點,是部分學者對我國古代法律考察不充分所致。這一部分學者將我國古代頒布的“綜合法典”等同于了我國古代法律規范的全部,錯誤地將“綜合法典”里有關商事活動的零星法律規定當作了有關商事活動的全部法律規定。通過考察我國古代所頒布的“綜合法典”我們就會發現:我國古代頒布的“綜合法典”從調整的社會關系來看,它雖然也調整一部分民商事法律關系、行政法律關系以及訴訟法律關系,但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主要還是刑事法律關系;從內容上看,它雖有民商法、行政法以及訴訟法的內容,但其所涉的主要內容還是有關犯罪與刑罰的問題。一言以蔽之,我國古代所頒布的“綜合法典”實際上是律典(16),它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有關全部社會生活的綜合法典。通過對我國古代法律規范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在實體上,我國古代的“綜合法典”雖然能夠調整一部分商事活動,但在國家制定法層面我國古代對商事活動的調整主要依靠的是單行法。例如,《秦律十八種》中《田律》、《金布律》、《關市律》、《均工律》、《徭律》均是有關商事活動的單行法律規范,又如漢初頒布的《田律》、《田令》和《田租稅律》等法律也是有關商事活動的單行法律規范,再如宋代復雜的編敕、編例中也有不少涉及商事活動的規范(17)。總之,在實體上,我國古代調整商事活動的單行法律規范不一而足,如果說我國古代不存在獨立的商事法律制度那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同時,我們也應當注意到,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不只是實體上的獨立,同時也是程序上的獨立。有些學者否認訟獄之劃分,在筆者看來這是個錯誤觀點,實際上在我國古代,主要涉及婚姻田土民商事案件多稱“訟”,而涉及賊盜等刑事案件的則稱“獄”[3]。在我國古代上,民商事案件的審級也與刑事案件的審級有所不同。例如在漢代,雖然刑事審與民商事審在審級上均為四級審,但民商事審最后審為州刺史,而刑事審的最后審是廷尉[3]。總而言之,在筆者看來,我國古代的商事法律制度在實體上和程序上都是獨立的。
(三)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的淵源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發現,我國古代有商事法律制度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我國古代商法的淵源有三:一是國家制定法;二是習慣法;三是國家商業貿易政策。
1.國家制定法
無論是我國還是外國,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無論是商法還是其他法律部門,國家制定法必然居于最高地位并擁有最高效力。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商法的形成經歷了由商事習慣法到國內制定法、再到國際貿易法的不同階段。反觀我國,國家制定法始終居于商事法律的主導地位,這點與西方不同。通過考察我國古代法律,我們可以發現,我國古代的有關商事活動的法律規定主要包括以下兩個部分:一是存在于正式典章中的商事法律制度,這里的正式典章既包括單行的商事法律規范,也包括前文提到的“綜合法典”。單行的商事法律規范,例如秦代《金布律》中規定,除了價值較低的物品外,市場所售物品必須系上標簽明碼標價(18);《關市律》中規定,無論是官府所售之物品還是民間手工業者所售之物品,賣方必須當著買方將錢投入一種特制的器皿,這種器皿只能進而不能出,否則就會被“貲一甲”(19)。又如,宋代的“敕”和“例”以及以“市舶條法”為代表的“海商法”,南宋刊印的《名公書判清明集》就記載了一系列的商事文書與商事判例(20)。再如,明清時期,根據皇帝上諭而形成的“事例”也成為重要的單行商事法律規范。說到前文提到的“綜合法典”,我們也能發現為數不少的商事法律規范隱藏其中。例如,根據《唐律疏議》與《宋刑統》,唐代和宋代由“市司”對市場上商品的價格進行評議,如果評議不公正,“計所加減之價,坐贓論”,若由此從中貪污“得財入己者,以盜論”(21)。再如《唐律疏議》中同樣規定了商事活動中的某些禁止性事項,如嚴禁人口買賣(22)、嚴禁官員貪污受賄以權謀私(23)。二是通過正式典章中的規定形成的某些具有強制性的商事制度。這一系列商事制度既包括商事主體制度,也有包括擔保在內的有關物權的制度,還包括有關債權的制度、訴訟制度以及各種商業管理的制度。例如,在吐魯番出土的《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賬》中記載的“正月一日,曹迦缽買銀二斤,與何卑尸屈,二人邊得錢二文”(24)就是隋唐時期商稅的體現。再如,在唐代,在市場上出售的物品必須合乎質量標準,如果不能合乎質量標準就得按所得利潤以盜竊罪論處(25)。為了能夠落實有關商事活動的法律規定,唐代朝廷設置了一系列市場官吏,可見我國古代為了落實商事法律規定構建了一定的市場管理制度。
2.習慣法
大體上來說,我國古代是個“禮”治社會。我國古代的習慣法就是所謂的“禮”,不僅國家法律要“一準乎禮”,司法審判也需合乎“禮”的要求。例如“春秋決獄”(26)就是這方面要求的體現。與其說我國古代商業活動要遵循習慣法的要求,倒不如說我國古代商業活動要遵循“禮”的要求。在筆者看來,“禮”實際上來源于天地正道,這就決定了其正當性,其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和諧向善,具體到商事活動中,就是使商事糾紛消解于無形。質言之,在中國古代,作為道德教化手段的“禮”實際上是充當了商事習慣法的角色,由于“禮”的存在,商人們循禮而行,通過對圣人道德的實踐,達到商事活動和諧的目的。實際上我國古代多數商事糾紛都是通過“禮”來解決的,通過“禮”來解決的商事糾紛的方式就是調解。調解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官府調解;二是官批民調;三是民間調解。此外,具體到商事調解,清代還發展出了中人調解(27)。無論是何種調解,其依據都是“禮”這一民間習慣法。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國學界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我國古代法律是“禮法不分”的,民商法則是“頗具于禮”。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習慣法的“禮”在我國古代也有一定的法典化傾向。例如唐代的《顯慶禮》、《大唐開元禮》等在一定意義上都是有關“禮”的法典;但是,“禮”作為習慣法深入民間調整商事活動這點是不可否認的。“禮”就是調整我國古代商事活動的習慣法。
3.國家商業貿易政策
通過本文第一部分,我們可以得知,我國古代社會有關經濟發展的總體政策就是“重農抑商”,在這個政策導向下,我國古代統治者對于商業的發展以及商人階層參與社會生活做出種種限制,以致到明清,封建君主最終炮制出了閉關鎖國的國策,我國商業活動從此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我國“事本禁末”的主張始于商鞅變法,變法第一篇法令《墾令》就將商業及商人群體置于危害國家的位置之上,自此之后我國古代國家商業貿易政策的主線就是限制商業發展與限制商人群體參與社會生活。具體來說,我國古代國家商業貿易政策有三個核心:一是鹽鐵官營;二是國家嚴格控制貨幣流通;三是國家嚴格控制兩市貿易(28)。當然,我們同時也應當注意到,我國古代國家商業貿易政策是動態發展的過程,歷朝歷代也有某些政策體現了國家對商業監管的松動。例如,西漢曾有儒生斥責商鞅鹽鐵官營之政策是亡國之道(29),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北宋也出現了批駁“厚本抑末”和頌揚商品貨幣經濟的理論(30),明清時期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曙光的同時,國家也采取一定的保護政策。總而言之,我國古代的國家商業貿易政策還是與商品經濟發展反向而行的。歷史實踐表明,我國古代的國家商業政策嚴重阻礙了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造成了我國近代商品經濟與商事法律制度的落后。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某些歷史時期國家對商業發展的寬容政策也使得我國古代商業取得一定的進步,表現出一定的積極作用。
三、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的形成有其社會歷史條件,在這個社會歷史條件當中形成的我國古代的商事法律制度并非是刑事法律制度的附庸,它獨立存在于刑事法律制度及其它法律制度之外。我國古代的商事法律制度以國家制定法為其主干,習慣法為其補充,國家商業貿易政策為其導向,發揮著調整我國古代商事活動的作用。當然,由于本文篇幅所限,難以就我國古代的商事法律制度進行深入探討,但筆者相信,隨著社會的進步,學界也會越來越重視對我國古代商事法律制度的探討,筆者也必將進一步對我國古代的商事法律制度展開研究,以期還原其本來面目。
注釋:
(1)參見《清世宗實錄》卷五。
(2)參見《尚書·盤庚中》。
(3)參見《管子·輕重甲》。
(4)參見《舊唐書·地理志》。
(5)草市原來是鄉村定期集市﹐各地又有俗稱,兩廣、福建等地稱墟,川黔等地稱場,江西等地稱扵,北方稱集。起源很早,東晉時建康(南京)城外就有草市,大都位于水陸交通要道或津渡及驛站所在地。其命名用意,或說因市場房舍用草蓋成,或說因初系買賣草料市集。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到唐代﹐其中一部分發展成為居民點﹐個別的上升為縣﹑鎮﹔而緊臨州縣城郭的草市﹐則發展成為新的商業市區。
(6)參見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7)參見束世徽:《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第五冊,第15頁。
(8)參見《史記·貨殖列傳》。
(9)參見《后漢書·公沙穆傳》。
(10)參見《魏書·趙柔傳》。
(11)參見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12)參見《光緒朝東華錄》三十三年五月辛丑。
(13)即亨利·詹姆斯·薩姆那·梅因,歷史法學派在英國的代表人物。
(14)參見王瑞:《民商法在中國古代法中的地位和發展歷程》,《河北法學》2012年第六期,第99頁。
(15)李祖蔭為介紹《古代法》一書所做的《小引》云:日本有的法學家把《古代法》作者梅因的“大凡半開化的國家, 民法少而刑法多” 的觀點, 奉為至理名言, “據此對我國大肆誣蔑, 說中國古代只有刑法而沒有民法, 是一個半開化的、文化低落的國家。就在中國, 也有一些資產階級法學家像鸚鵡學舌一樣, 把自己的祖先辱罵一頓。事實上, 古代法律大抵都是諸法合體, 并沒有什么民法、刑法的分別, 中國古代是這樣, 外國古代也是這樣。”
(16)商鞅“改法為律”后“律”實際上已經成為了我國古代刑事法典的專有名稱,在這個意義上,律典即刑法典。
(17)宋代編敕主要包括《建隆編敕》、《太平興國編敕》、《淳化編敕》、《咸平編敕》、《大中祥符編敕》、《天圣編敕》、《慶歷編敕》、《嘉祐編敕》、《熙寧編敕》等等,幾乎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不少關于商事活動的規定。編例中秦檜上《鹽法續降指揮》達130 卷,《茶法續降指揮》共88 卷也是有關商事活動的規定。
(18)參見《金布律》。
(19)參見《關市律》。
(20)總共有245件之多。
(21)參見《唐律疏議·雜律》及《宋刑統》。
(22)參見《唐律疏議·賊盜律》。
(23)參見《唐律疏議·職制律》。
(24)參見《通鑒》卷180《大業三年條》。
(25)參見《唐律疏議?雜律》。
(26)春秋決獄又稱“經義決獄”,是西漢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來的,是一種審判案件的推理判斷方式,主要用孔子的思想來對犯罪事實進行分析、定性。
(27)清代經濟雖然仍為小農經濟,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清代民間產生了大量有關交易的糾紛。為了便利地解決這些糾紛,清代民間自然產生了中人調解這種解決糾紛的形式。中人調解可以說是清代民間調解的一大特色,同時中人調解也是清代民間調解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清代的土地買賣,土地租賃,借貸等契約場合下一般都會有中人的出現,在沒有產生糾紛的場合下中人提供的一般是信息提供者或者擔保者的角色,而在產生糾紛的場合下中人擔當的一般就是調解者的角色了。因此在清代的各類契約中,一般都會加入“憑中理出”,“憑中處理”,“仰原中查處”等字樣。中人依據長久以來形成的交易習慣解決交易糾紛,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清代,中人調解無疑成為了維持交易正常進行的穩定器。
(28)參見《管子》。
(29)參見《鹽鐵論》。
(30)例如王陽明提出“新四民”論與“義利并重”論。
參考文獻:
[1]陳顧遠.陳顧遠法律文集[M].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424-429.
[2]陳顧遠.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M].臺北:三民書局,1969.
[3]楊一凡.中華法系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誤區——“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質疑[J].中國社會科學,2002,(6):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