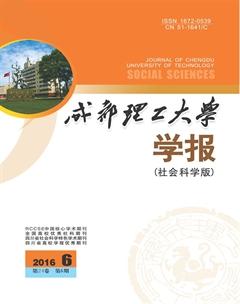英美刑事訴訟未成年人證人資格比較及其啟示お
吳靜
摘要:在英美兩國刑事訴訟中,未成年人在一定條件下具有證人資格,且資格的裁決需要遵循法定程序。與之相比,我國相關立法較為粗糙簡單。未成年人證人資格認定之標準不盡合理,并未對裁決程序做出具體規定,以致在司法實踐中產生操作困難。基于此,我國刑訴立法應當修改目前未成年人證人資格之標準,規定未成年人具備感知、記憶和表達能力即可作證,并且對未成年人證人資格的審查程序做出具體規定。
關鍵詞:刑事訴訟;未成年人;證人資格;英美比較
中圖分類號: D915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6)06003305
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華爾茲教授給出的定義,證人資格(competency of witness)是指證人作證的能力。[1]目前,我國理論界對證人資格的指稱頗為混亂,諸如“證人能力”、“證人范圍”、“證人條件”等,雖不盡確切,但意思大致相同,即訴訟中證人所需具備的要求和條件[2]。誠如貝卡利亞所言,“一切有理智的人,也就是說,自己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連貫性,其感覺同其他人相一致的人,都可以作為證人。衡量這種人可信程度的真正尺度,僅僅在于說真話或者不說真話同他的利益關系。”[3]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及地區的立法表明,一切人被推定享有證人資格。至于證人證言的可信度,則與其他條件有關。然而,未成年人這一群體較為特殊,其是否當然具備合格的證人資格,該問題產生了較大的爭議。三大訴訟均涉及到未成年人證人資格問題,鑒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在刑事訴訟視野下探討該問題。
未成年人證人資格問題最早可追溯到早期英美證據法關于證人適格性之規定。歷史上,英美法認為,未成年人在作證方面劣于成人,其證言的準確性及可靠性未受足夠的關注[4]。十六七世紀,英美普通法曾對證人資格作了極為苛刻的限制,“舉凡有色人種、當事人親屬、破產人、利害關系人、犯罪人、精神障礙人、兒童、無宗教信仰人,均排除其為證人。”[5]直至19世紀早期,未成年人因未達法定年齡,仍被排除在證人之列。端在立法者考慮到未成年人心智尚未發育成熟,其認知、記憶和表達的能力有所欠缺。加之當時由陪審團裁定證人資格,容易受到誤導,故而立法上對此做出嚴格的限制。然此舉也不可避免地產生排除掉可能是唯一了解案件事實證人的后果,影響法官對案件事實的查明。經過權衡利弊之后,立法者發現通過謹慎的指示,讓此類證據得以進入法庭,實現其證明價值,可謂更佳的選擇[6]。故當代普通法革除早期嚴格的證人資格規則,允許未成年人在符合一定標準的前提下作證,并且在立法中詳細明確了未成年人證人資格裁決程序。
我國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第60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與英美兩國相較而言,我國刑事訴訟中關于未成年人證人資格問題的規定僅為寥寥數語,其認定標準不夠具體合理,對未成年人證人資格裁決程序上存在立法闕如,在司法實踐中時常面臨難以操作的困難。因此,本文擬以英美兩國為考察對象,對未成年人證人資格認定標準和裁決程序進行梳理。然后檢討我國刑事訴訟相關規定之不足。最后,在借鑒英美先進立法經驗基礎之上,提出我國刑事訴訟關于未成年人證人資格立法所應遵循的路徑。
二、英美未成年人證人資格立法之考察
(一)未成年人證人資格之認定標準
在英美法系國家,“未成年人證人”被“兒童證人”的概念所取代,即未滿14周歲的證人。在英國,兒童證人資格主要受《1999年青少年審判與刑事證據法》所調整,第53條規定了證人資格的標準:“(1)在刑事訴訟的每個階段,所有的人(不管其年齡)都有資格給出證據。(2)第(1)款遵從第(3)、(4)項發生效力。(3)一個人無資格在刑事訴訟中給出證據,如果法庭查明他不能夠:(a)理解向他提出的問題,并且(b)做出能被人理解的回答……”[7]據此可知,在英國的刑事訴訟中,任何人均被推定有資格作證。并且,立法還著重突出了證人的年齡不再是阻礙其成為合格證人的因素。可以說,未成年人的證人資格問題在無形中被淡化了。根據2006年的R. v. Macpherson一案的判決,英國法官不能僅因兒童的年齡問題而否認其具有作證資格[8]。
但這不意味著所有兒童均可出庭作證,第一款的生效需在滿足第三款和第四款的前提下。第三款明確提出了兒童證人的認定標準,即 “看兒童是否能夠理解向他或她提出的問題、交流和對他或她提供證據證明的事情做出前后一致的、可理解的解釋。”[9]在兒童作證前,法庭一般會通過一定的檢驗程序,判斷兒童是否滿足了前款所規定的標準。法庭一旦查明兒童不能夠理解向他提出的問題,并且所做出的回答無法被人所理解,那么其就沒有資格在刑事訴訟中提供證據。
與之類似,美國《聯邦證據規則》601第一款規定:“每個人都有作為證人的能力,除非本證據規則另有規定。”該規定屬于一般性推定的條款,推定每個人都有能力作為證人[10]。只要此人不具有該規則所規定的排除情形,即具有合格的證人資格。隨后的條文對排除作證資格進行了列舉說明,例如缺乏親身知情的普通證人,不得就該事項作證等。這也意味著,年齡、智力等條件不再是排除證人資格的決定性因素。聯邦最高法院咨詢委員會認為這些標準,“已被證實在實際運用時是難以令人捉摸的……很難設想,某個證人會完全沒有能力。因此,這個問題特別適合交給陪審團解決。他們可以作為證據的證明力和可靠性的問題,在有關評判證據是否足夠的司法權力的約束下進行處理。”[11]美國大部分州的立法亦對證人的作證資格作了寬松的規定。譬如,1967年《加州證據法典》第700條規定,除非成文法另有規定,每個人,不管他的年齡,都有資格作證人。沒有人被剝奪了對問題作證的資格[12]。
《聯邦證據規則》雖未明文規定兒童證人的認定標準,但通過各州的立法例及判例可推斷出,合格的證人應具備三項能力,即感知(Perceiving events)、記憶(Retaining information in memory)和表達(Retrieving information from memory)能力。上述三項能力的降低,只是導致其證言可信度的下降,而不會使其失去證人資格。《馬薩諸塞州證據規則指南》第601條第二款規定:“任何人如果具備了如下條件就具有作證能力:(1)具備基本的觀察、記憶和表達他(她)的所見所聞或經歷的事情的能力;(2)有足夠的理解能力來理解真實與虛假之間的區別,理解虛假的惡性并理解(證人)講真話的義務,并且能大致認識到沒有履行如實相告的義務將要受到懲罰。”[13]而《加州證據法典》則是從反面規定了證人在哪些情況下被剝奪了證人資格:“(1)不能就問題表達自己的意見,以至于不能被他人理解,這種理解或是直接為他人所知,或是通過明白他的人的翻譯;或者(2)不能理解證人說真話的義務。”法律修訂委員會對此解釋道:根據現行法,一個人充當證人的能力是應由法庭裁決的問題并且取決于他理解起誓的能力和感知、回憶和交談他要敘述的事務的能力。1957年的people v. Mc Canghan判例指出:“證人是否正確感知、回憶并且準確真實地交談,是一個事實裁定者解決的可靠性問題。”[12]988此外,肯塔基州上訴法院1947年的一個判例也充分表明:“沒有按年齡衡量證人適格性的一成不變的規則,法院應當確定未成年人是否有足夠的觀察、回憶與敘述事實的智力以及說真情的義務感。如果他具備這些條件,就應該允許他作證。法院一旦裁定他是個合格的證人,應由陪審團確定應給予他的證言多大的分量。”[14]
(二)未成年人證人資格之裁決程序
英國《1999年青少年審判與刑事證據法》第54條專門規定了證人資格的裁決程序:“(1)刑事訴訟的證人是否有資格在訴訟中給出證據,這個問題不論:(a)由訴訟當事人一方提起,還是(b)由法庭主動提起,應當由法庭遵照本條進行裁決。(2)應由傳喚證人的一方說服法庭,基于蓋然性的平衡,證人有資格在訴訟中提供證據……(4)任何為裁決該問題而進行的程序,陪審團不應參加(如果有陪審團的話)。(5)專家證據可以被接受。(6)任何對證人的提問(如果法庭認為有必要)應由法庭在當事人面前進行。”[7]134在未成年人證人資格產生爭議時,任何一方均可提出此項質疑,法庭也可主動發起動議,并依照法定程序做出裁定。傳喚證人的一方對未成年人有資格作證的證明達到蓋然性優勢即可。兒童證人資格的判斷一般作為預審事項,在陪審團不在場的情況下由法官自主裁判,且關于該問題的專家證據可以被采納。在審查時,法官應觀看對兒童的采訪錄像,或者向兒童提出合適的問題[8]。一旦法院裁定兒童具有作證資格,此后對兒童證言的任何質疑均屬證言的可信性問題,而不涉及兒童的作證能力問題[15]。
在美國,證人資格問題是由初審法官裁定的,其可根據特定條件和證人的理解能力自由裁量證人的作證資格[13]102。由于兒童證人的年齡過小,這一特殊群體可能在感知、記憶和表達能力這三個方面比不上普通證人的水平,甚至無法完全理解證人宣誓的意義。因此,為了確保合格的兒童證人證言能夠在刑事訴訟中被采納,兒童證人的作證能力將由法官在聽證后裁決。在聽證中,法庭會提出旨在判斷孩子是否有作證資格的問題,也包括是否認識到講真話義務的問題。當然,這是針對兒童提供證言時對作證能力所進行的測試,而非針對案件事實發生的時刻[1]418。只要法官裁決該兒童具有作證資格,則任何年齡段的兒童均可作證[11]179。
1947年俄亥俄州上訴法院審理的希爾訴基斯拉(Hill v·Skinner)一案,能更好地說明法院是如何進行判斷的。原告是一名4歲的幼童,在路過被告斯基拉家門口時,被其狗咬傷。原告因此要求被告承擔賠償責任。一審中法庭采納了原告的證言,判決被告賠償原告500美元,被告斯基拉以4歲的幼童不具有證人資格為由提起了上訴。二審法院柯南道爾大法官認為,《美利堅合眾國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第11493條規定:“任何人都有作為證人的資格,除了那些心智不全的人和十歲以下的不能就被詢問的內容正確地感知事實和行為的兒童。”經查,初審法院對該幼童的證人資格進行了檢驗。幼童在檢驗中被問道不說真話會有什么后果。該兒童答道:“上帝不會愛我。”即清楚地明白說真話的義務。從法官、律師與該幼童進一步的問答中,該幼童表現出了記憶、觀察、再現和交談的能力。庭審中除了一些答非所問以外,幼童清楚地描述了事發時的情況。遵循州訴維德曼一案的先例所產生的規則:“一個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的作證資格由初審法官自由裁量,只要沒有濫用裁量權,復審法院不得變更判決。”在本案中,上訴法院沒有發現濫用裁量權的情況,故維持一審判決[16]。通過以上判例可以得出,在未成年人證人資格的裁定程序中,法院通過詢問兒童一系列問題,根據回答來判斷其是否具有作證所要求具備的感知、記憶和表達能力及理解說真話的義務。
綜上所述,在英美兩國的刑事訴訟中,未成年人在具備最低限度的感知、記憶和表達能力,理解如實作證的義務之時,通過法律規定的程序審查之后,即具有合格的證人資格。
三、我國未成年人證人資格立法之評析
(一)認定標準之不合理
反觀我國刑事訴訟相關立法,不如英美兩國規范之明確具體。前文提到,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60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即表明,一般而言,只要了解案件事實的人,無論是成年人或未成年人,均可作證。但鑒于未成年人年幼,心智發育尚不健全,一概允許其作證,將會導致未能反映客觀事實的證人證言進入法庭,從而誤導法院對事實的正確認定。因此,立法在此基礎上規定了例外情形,強調年幼的人僅在滿足“辨別是非”及“正確表達”的條件下才能作證人。但經仔細推敲后,這一認定標準確有不合理之處。
其一,“辨別是非”這一要求忽視了證據法的基礎理論。辨別是非,是指能夠分清正確與錯誤,是非曲直。要求未成年人對待證事實具有辨別是非的能力,相當于要求證人能夠對該事實做出評價。然而,這明顯與證人證言應受意見規則規制的證據理論相違背。證人僅需就其所感知的事實提供證言即可,而不能對此加以推斷或發表意見,否則將會給證言的證明力和相關性帶來更多的懷疑[17]。譬如,未成年人甲親眼見到乙將丙殺害,甲只要具有感知、記憶和表達乙殺丙事實的能力,就應認定其具有證人資格,而無需了解乙殺丙的行為是違法的,即不需辨別是非。由此可見,“辨別是非”與證據理論相悖,也為未成年人成為合格證人方面設置了過高的不合理門檻,在實踐中排除了大量本應采納的未成年人證言。
其二,“正確表達”這一要件在司法實踐中難以判斷。首先,“正確表達”是指未成年人僅具備描述其所知事實的能力即可,還是要準確無誤地闡明案件真相?其對事實的描述需達到何種程度才算正確?我國刑事訴訟立法對此語焉不詳。再者,從條文似乎可揣測出,立法要求未成年人只有在表達與客觀真相一致的事實時才具有證人能力。那么,法官在掌握諸多證據的情況下,都無法保證自己所認定的事實能完全符合事實真相,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又如何能夠保證表達是絕對正確的?這不僅在實踐中難以判斷,在客觀上也是不可能達到的要求。“正確”二字僅與證人證言的證明力有關,而不應該作為限制未成年人為證人之條件。換言之,“能夠表達”才是未成年人證人資格判斷標準的應有之義。
(二)裁決程序之不完善
在明確未成年人證人資格的標準后,其裁決應遵循什么樣的程序?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此付之闕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7條僅做了粗略規定:“對于證人能否辨別是非,能否正確表達,必要時可以進行審查或者鑒定。”這一“原則性”條款過于抽象,不僅不具有可操作性,反而還帶來了更多問題:誰有權開啟審查或鑒定的程序?誰負責對未成年人具有或不具有證人資格進行舉證?舉證方所提供的證據應達到何種程度?審查的具體流程如何?與此類似的相應問題在立法上均未得到進一步的解釋與規定。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裁決程序不一,法官在進行裁決時的主觀隨意性較大,得出結論差異較大,不利于法律的統一適用。故而立法上應參照英美法系之規定,對未成年人證人資格裁決程序加以詳細說明。
四、英美未成年人證人資格立法對我國之啟示
基于前面的論述可知,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雖然承認了未成年人在滿足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可以作證,但由于其未能正確認識到證人作證所應具備的最基本能力,加之立法過于簡陋而遺漏審查程序之規定,這無疑影響到未成年人在刑事訴訟中作證的實踐效果。因此,在借鑒英美兩國相關立法經驗之后,完善我國未成年人證人資格立法可遵循以下基本思路:
第一,修改我國刑事訴訟中未成年人證人資格的認定標準,規定未成年人在具備感知、記憶和表達能力時即可作證。如前所述,“辨別是非”要求未成年人能對事實做出評價,“正確表達”則要求其提供與案件客觀的事實一致的證言。這兩項標準對身心尚未完全發育的未成年人提出了過于苛刻的要求,忽略了證人本身所應具有的最低限度能力。在美國,當證人是否具備作證資格成為爭議問題時,最根本的判斷標準是:一個通情達理的陪審員是否應當相信該證人已失去了感知、回憶和表達能力,以至于不值得花費時間聽取其證詞[6]136。通常而言,在案發之時,未成年人能夠通過看、聞、嗅、觸等感知這一事件的存在,記憶并且能夠表達出來,便實現證人證言在證明案件事實上的功能。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宜將第60條修改為:“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具有一定感知、記憶和表達能力的人,不能作證人。”
第二,完善我國刑事訴訟中未成年人證人資格的裁決程序,規范法院的裁決權。由于我國缺乏未成年人證人資格認定之具體流程,不僅在司法實踐中造成了較多的混亂,而且在法官濫用權力的情況下極容易產生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現象。因此,我國立法有必要借鑒英美法系國家較為完善的程序設置,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例如,就未成年人證人資格的審查程序的啟動,可以規定任何一方均有權提出對未成年人是否具備證人資格進行審查,法院也可以主動進行審查;審查中,提出未成年人證人的一方當事人應當對該未成年人具有證人資格進行舉證,其舉證只須達到蓋然性優勢即可;必要時,法官可通過詢問或其他方式測試未成年人的感知、記憶和表達能力。此外,當事人的訴訟代理人在法官允許的情況下,可以向未成年人詢問,但僅限于與其作證資格相關問題;在審查程序中,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或其他適格成年人應當到場;法院經過審查后,發現未成年人符合作證標準的,當場決定其具有證人資格,允許出庭作證。否則,將做出其不具有作證資格的決定。
五、結論
在英美刑事訴訟中,未成年人在具備感知、記憶和表達能力,并理解說真話的義務前提下,具備證人資格。而對這一資格的判斷,通常由法官按照法定的程序進行裁決。我國相關立法也表明,未成年人并不必然被剝奪作證資格。但目前的標準不符合證據法理論及實踐需求,裁決程序也存在缺失。這在實踐中造成大量合格的未成年人證人證言被排除的后果,不利于法院對案件真相的查明。麥考密克曾經評論道,“證據法的明顯命運就是,逐步減少阻礙事實真相發現的障礙。”[6]146因此,我國應修改刑事訴訟中未成年人證人資格的認定標準,完善未成年人證人資格的裁決程序規定。
參考文獻:
[1][美]喬恩·R·華爾茲.刑事證據大全[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415.
[2]何家弘.證人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60.
[3][意]切薩雷·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M].黃風,譯.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29.
[4]See Ray Bull.Children and the law[M].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11:180.
[5]陳樸生.比較刑事證據法各論[M].臺北:漢林出版社,1984:163.
[6][美]約翰·W·斯特龍.麥考密克論證據[M].湯維建,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134.
[7]何家弘,張衛平.外國證據法選譯(上卷)[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99.
[8]齊樹潔.英國證據法[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147.
[9][英]詹尼·麥克埃文.現代證據法與對抗式程序[M].蔡巍,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01.
[10]王進喜.美國《聯邦證據規則》(2011年重塑版)條解[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152.
[11]何家弘.外國證據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75.
[12]何家弘,張衛平.外國證據法選譯(下卷)[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987.
[13]馬薩諸塞州證據規則指南[M].廖永安,等,譯.陳子豪,校.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2:101.
[14]沈達明.英美證據法[M].北京:中信出版社,1996:246.
[15]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特別程序研究——基于實證和比較的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48.
[16]劉曉丹.美國證據規則[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234-237.
[17]See Simon Cooper. Cases and materials on evidence[M]. 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2003:.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