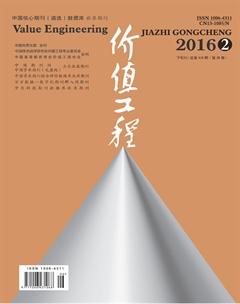學習型城市大系統協調發展模型研究
鄭飛 張竹英



摘要:從學習型城市相關因素的協調關系問題入手,綜合運用動態大系統的理論與方法,探討了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的大系統控制途徑,建立了相應的數學模型。通過在學習型城市建設中運用這些模型,可對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的現狀及未來進行定量評估、預測與控制,有利于學習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為構建和完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學習型城市服務。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relevant factors of the learning cities, and by comprehensively applying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large-scale systems, the control channels of large-scale systems for the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the learning cities are discussed, and a series of relevant mathematical models are set up. These models can be applied to estimate, forecast and control quantitatively for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conditions of the coordinat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cities,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earning cities and serve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arning cities.
關鍵詞: 學習型城市;大系統;協調發展;協調控制
Key words: learning city;large-scale system;coordinate development;coordinate control
中圖分類號:F299.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06-0245-03
0 引言
在“互聯網+”時代,隨著科技進步與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可能將人的一生簡單劃分為學習期和工作期。早在1965年,法國教育學家保羅·朗格朗就提出了“終身教育”的思想;之后,1968年哈欽斯提出了學習型社會的思想;1990年美國管理學家彼得·圣吉提出了學習型組織的理論。受國際終身教育、學習化社會思潮的影響,我國適時提出了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的戰略目標。2001年,江澤民提出要“構筑終身教育體系,創建學習型社會”;從黨的十六大開始到十八大的歷次報告以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都重點強調了構建和完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學習型社會。
作為一種城市發展模式,學習型城市是城市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與重視外在的、物化的商業化、工業化城市發展模式不同,學習型城市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內在的、精神層面的范疇。因此,構建學習型城市是一項龐大復雜的社會經濟系統工程。學習型城市除了具有規模龐大、結構復雜、功能綜合以及因素眾多等典型大系統的一般特點外,還有其自身的特點,如受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雙重制約;在“互聯網+”時代,毫無疑問,學習型城市的構建具有網絡開放性,等。因此,為了更好地促進學習型城市的協調發展,本文從大系統的角度,探討了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的大系統控制途徑,建立一系列數學模型,通過對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進行定量評價、預測與控制,找出不協調因素,為政府進行學習型城市建設進行宏觀調控和科學決策提供參考。
1 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的大系統遞階結構
根據大系統的多級遞階結構思想,學習型城市的大系統多級遞階結構,如圖1所示。
其中,最低級(第一級)為學習型城市綜合服務應用系統局部控制模型。主要功能是為學習型城市綜合服務應用系統的各子系統(人口素質子系統、學習資源子系統、教育培訓子系統、城市競爭力子系統、科技創新子系統)提供局部控制,直接為學習型城市綜合服務應用系統上的學習者提供配套的綜合服務,使城市居民的文化、文明素質得到改進,學習資源得到有效利用,同時建立與健全合適的教育培訓體系,增強科技創新能力,從而提高城市競爭力。
中間級(第二級)為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控制模型。主要功能是為學習型城市進行遞階協調發展控制。根據大系統的協調預測、協調控制思想,對各子系統之間的聯系進行協調分析,同時運用最優化手段,向下對各子系統進行協調控制,向上將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的最優策略方案及綜合數據信息提供給最高級(即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綜合評價控制模型)。
最高級(第三級)為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綜合評價控制模型。主要功能是為學習型城市進行綜合評價控制。根據遞階結構和協調發展指數模型,建立相應的綜合評價指標與實施方案,實現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的總目標。
通過定性分析,為學習型城市建立相應的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提出一套實用的評價方法,并通過定量模型,實現最優控制。
限于篇幅,最低級的綜合服務應用系統局部模型和協調發展指標體系等在此不做討論,本文只研究學習型城市大系統遞階結構中的最高級和中間級的三類模型。
2 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指數模型
在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時,為了力求全面、綜合反映社會經濟的總體發展或某些方面的的基本特征,國內外許多機構和專家根據多目標決策的歸化原理,設計了HDI、ISP、MEW、EPI、SEDI等綜合評價指標,通過對若干統計指標的綜合計算形成一定的標志數值,從而進行整體評價。從總體上考察,這些指標一般只適合排序,無法做深層次的分析,更不能反映協調發展的真實水平。
因此,為了直接或間接反映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的總體性能,在已有工作的基礎上,運用大系統理論,有必要研究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協調發展指數,并建立起相應的定量模型。根據協調發展指數模型的基本原則,該指數模型不僅要能反映學習型城市各子系統之間的協調程度(即協調度),而且要能體現學習型城市的發展水平(即發展量)。
根據已有歷史數據,采用適當的參數預估方法(如參數估計的推廣梯度算法),對學習型城市狀態指標進行自適應預測與控制,進而對學習型城市大系統進行自適應協調控制。
5 結論
本文根據學習型城市相關因素的協調關系,研究了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的規律與趨勢,從而建立了學習型城市的大系統協調發展模型。由于所建立的一系列模型充分考慮了構建學習型城市大系統的動態時變特性,將大系統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模型結構與具體算法較規范,理論依據充分,而且操作方便,因此應用前景廣闊。目前正結合佛山市的具體情況,開展有關項目的研究;通過實際項目的深入研究,對模型進行改進與完善,力圖形成一套較完整的實用模型體系,為實現學習型城市協調發展戰略、政府的宏觀調控與科學決策服務。
參考文獻:
[1]Tim Campbell. Learning cities: knowledge, capacity competitiveness[J]. Habitat International,2009(33):195-201.
[2]孫玫璐,等.可持續發展:學習型城市建設造就社會發展的光明未來[J].高等繼續教育學報,2014,27(1):13-16.
[3]樊小偉.可持續學習型城市的內涵及啟示[J].成人教育,2014(7):12-14.
[4]陳友華.學習型城市建設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南京社會科學,2004(9):81-86.
[5]鄭飛.學習型城市模糊綜合評價模型研究[J].價值工程,2015,34(5):241-243.
[6]席裕庚.動態大系統方法導論[M].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88.
[7]湯兵勇.市場經濟控制論[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
[8]席裕庚.大系統控制論與復雜網絡——探索與思考[J].自動化學報,2013,39(11):1758-1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