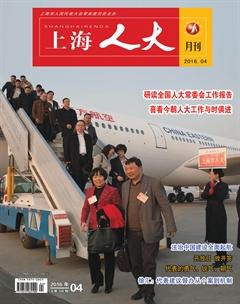關于產業需求驅動下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建議
王戰
“中國制造2025”是未來十年我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的行動綱領,需要職業教育大力培養復合型的各類技術技能人才。但是,長期的獨生子女政策強化了父母“望子成龍”的高期望,不愿子女選擇職業教育;“學而優則仕”的文化傳統和白領導向的就業觀,削弱了年輕人從事職業技術工作的意愿。同時,兩億農民工缺乏職業教育和培訓,進入城市后成為低端勞動力,達不到產業轉型升級的要求。當前,關鍵在于深化校企合作模式,真正實現職業教育服務于產業發展和個體職業生涯發展需求。
一、傳統校企合作方式下職業教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缺乏保障:法律法規和實施細則缺位。傳統校企合作是淺層次的、基于人脈關系的合作,是非制度性的,不穩定、不可持續。其原因在于:一是我國尚未建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規體系。雖然寧波等城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規,但由于上位法缺失,無法形成較大的影響力和約束力。二是對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缺乏具體的、實質性的激勵辦法,配套的實施細則不完善。
2、缺乏協調:缺乏協調職業教育和產業需求的機構。職業教育應該以企業需求為主體,但傳統的校企合作由教育部主導,以職業學校為主體開展,而教育部門實際上無法掌控崗位供給和解決就業需求,使得學生培養與企業需求出現了割裂。因此,校企合作改革需要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建立能夠對職業教育和產業需求進行全國性地設計、統籌、管理和監督的專門機構。
3、缺乏標準:統一的職業資格認證體系尚未建立。近年來,學歷文憑和職業資格證書“雙證融通”零對接的探索實踐,并未給中高職畢業生增加更多含金量。由于職業標準體系不完整、認證體系缺乏專業標準和課程標準、職業資格鑒定過程不嚴格、頒證部門既當教練又當裁判等各種問題,即使畢業生獲得“雙證”,企業也不認可其職業技能符合需求,“雙證融通”形同虛設。
4、缺乏預測:人才需求預測和發布平臺尚未搭建。美國、歐盟都有人才需求預測,提供人才供給和匹配信息,引導現有人才自由流動與補給,但我國缺乏具有公信力的人才需求預測和發布平臺。教育部門在確定招生計劃和專業設置時缺乏依據,開設專業和課程是否對應產業需求無法考證,職業教育發展由于短視而陷入招生困境,畢業生的對口就業率低。
5、缺乏貫通:職業教育隔離于義務教育之外。德國11歲開始教育分流,只有22%的青年成為大學生。瑞士70%以上學生進入職業教育學習。而我國中職教育與普通高中比例大致為4.5:5.5,職教占比偏低,在義務教育階段基本被隔離。尤其是廣大農村學生,在義務教育階段從未接受過職業技術技能學習,只能從事最低端的體力工作,不能適應經濟社會轉型需要。
6、缺乏提升:缺少職業綜合素質的培養。我國職業教育存在功利化導向,將職業發展需求片面理解為“找工作”,缺乏對學生職業綜合素質的培養和提升。除了職業技術技能以外,企業看重的學習能力、敬業愛崗精神、職業道德養成、安全生產意識、對行業的理解和職業文化認同等,恰恰是當前的職業教育所欠缺的,導致畢業生能力單一、后勁不足、可替代性高。
7、缺乏認同:沒有形成職業教育價值的社會氛圍。我國傳統文化觀念中一直存在重普通教育、輕職業教育的導向,并且有進一步加劇的勢頭。其原因:一是職業技術從業者無論是收入、職業環境,還是社會地位都處于劣勢,影響了公眾對職業教育的認同。二是職業教育走出學校、服務社區的意識不強,公眾對職業教育了解少、參與度低。三是對青少年的職業生涯指導滲透不夠。
二、完善產業需求驅動下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的建議
1、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激勵機制。一是盡快修訂《職業教育法》,完善促進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規,明確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主體作用、功能定位,以及權利、義務和責任。二是制定促進校企合作的實施細則和具體政策,設立國家與各級政府校企合作項目專項資金,對切實提供職業教育機會的企業進行經費補貼,包括國家層面的培訓補貼金、地區層面培訓貸款和行業部門補貼。三是要求地方對支柱性產業以及技能型人才短缺行業,必須主動與學校簽訂合作協議,形成長效合作機制。
2、建立協調職業教育發展和產業需求的專門機構。一是各級政府建立以教育、產業和人社部門為核心,財政等多部門共同協作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指導委員會,從國家層面制定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整體戰略,全面設計規劃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平衡政府、企業、學校和學生的不同利益。二是建立職業教育與行業協會的協作機制,各類行業協會與職業教育部門和職業學校建立經常性的對話協商機制。
3、建立國家職業資格證書框架。一是建立基于崗位的職業標準,開發對應的專業培訓包。二是由注冊的具有資質的培訓機構進行職業資格培訓,政府履行監管職能。三是建立國家職業資格框架,實現不同的學業證書之間的對應和轉換。四是培訓機構、考試機構和發證機構互相獨立,避免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不正常狀況。
4、建立技術技能人才需求預測與發布制度。完善教育、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相關部委辦局和行業協會對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需求的信息采集和共享機制。尤其針對重點產業、特色產業與新興產業的若干領域,及時發布技術技能人才需求信息,為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提供重要支撐。建成覆蓋主要行業的技術技能人才需求預測與發布制度,每年出版《崗位需求手冊》。
5、順應互聯網+的發展趨勢,開展職業生涯指導。一是建立國家先進制造業職業生涯路徑引擎網站,幫助個人評估教育技能水平和理想職業要求之間的差距,以便找到合適的教育或培訓項目。二是職業生涯啟蒙教育前移,貫穿幼兒至成人的整個過程。三是在中學設置專職的職業生涯指導和咨詢工作者,工作者必須獲得資格認定,具備相應的知識結構。四是在大學設立就業市場學院,專門負責培訓學生專業知識以外的求職能力和提供職業生涯規劃。
6、營造職業教育的文化認同。一是面向所有教育階段的學生、教師、家長及公共部門發起提升制造業公眾形象的活動,提升制造業職業教育吸引力。二是設立“國家制造日”,鼓勵企業、學校、社區、家庭聯動參與制造業公眾形象提升運動。三是推進“職業體驗日”制度化,依托職業院校,探索建立面向中小學生的職業體驗中心,提高職業教育吸引力。四是面向中小學開放職業院校實訓場所、課程、師資等教育教學資源,要求企業開設面向區域中小學的職業體驗活動或選修課程。
7、推動職業教育建設成服務區域多元化需求的平臺。職業教育突破學校定位,履行服務區域多元化需求的平臺功能,尤其是發揮服務社區的功能。各類職業院校定期舉辦各種形式短期職業教育、繼續教育和文化生活類課程,在設備利用、維修、護理、家政、早教、環境衛生等方面向市民傳授相關專業技術知識和信息。每年開設社區課程10門以上。
8、加強農村學生的“職業預備教育”,發揮職業教育在農民市民化過程中的導向作用。一是九年義務教育初中階段,實行“2+1”或“3+1”模式。“2+1”指初中最后1年為農村學生增加職業培訓課程;“3+1”指3年普通初中教育加1年職業教育,在義務教育框架內增加學歷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選擇機會。二是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延長至12年,增加3年免費義務職業教育。三是新生代農民工從事制造業工作,參加職業學校培訓是準入門檻,培訓經費由政府承擔。四是將參加職業教育和培訓列為農民工落戶城鎮的條件。采用“學分銀行”的方式,累計職業教育和培訓學時學分,對應相應的落戶積分。五是新增高等職業學校主要向中小城市布局,推動縣區職業教育中心(中等職業學校)成為區域學歷教育、技術推廣、扶貧開發、勞動力轉移培訓和社會生活教育的開放平臺,將服務網絡延伸到社區、村莊、合作社、農場、企業。
9、提高職業教育國際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擴大需要大力發展專業的合作辦學。目前已有來自24個國家和我國港澳臺地區的235個機構與我國25個省市自治區的296所高職院校進行了合作辦學,但合作國家主要是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美國,合作機構主要在江浙滬,合作項目聚集在財經、電子專業大類。為此建議:一要推動國際職業教育交流與合作項目向內地及農村地區發展,各省應確立示范性國際合作中等和高等職業學校各1所。二要加強與職業教育發展強國的合作辦學,借鑒德國的“雙元制”、日本的“產學合作”,瑞士“三元制”、新加坡“教學工廠”等先進制度,形成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辦學模式。三要加強在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環保、氣象與安全、資源開發與測繪等專業方向的國際合作辦學,滿足我國需要大力開發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需求。
(作者系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