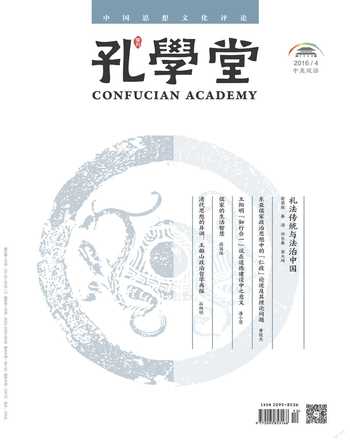律令體系還是禮法體系?
摘要:“律令說”由日本學者提出,并不斷發展完善,得到中國學者的廣泛認可。“律令說”雖然以中國古代法律語詞為外衣,但其背后體現的仍然是日本人效仿大陸法系的歷史過程所產生的“法典情結”;“律令說”的有效時段是魏晉到唐宋,這種對中國法律史掐頭去尾,難以囊括中華法系的法歷史;“律令說”只能用于表述中國古代刑事、行政方面的成文法,不能表述大經大法、祖宗之法、天下之法,難以涵蓋中華法系的法體系;中華法系是禮法體系,從體系上看,包括禮典、律典、習慣法三個子系統,從歷史上看,包括原型期、重組期、成熟期、衰落期四個階段。
關鍵詞:律令說 律令體系 禮法體系 中華法系
作者秦濤,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教師、法學博士(重慶 401120)。
20世紀50年代,日本學者提出“律令說”,并以之來認識中國古代法的整體。20世紀90年代,“律令說”引介到中國,并在學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本文考察“律令說”從產生于日本到傳入中國的來龍去脈,探討了“律令說”的本質,并對之提出商榷,認為中華法系不是律令體系,而是禮法體系。
一、“律令說”的由來和盛行 [見英文版第30頁,下同]
最早用“律令說”來研究中國古代法的整體,乃至整個中華法系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學者。
要想了解日本學者為什么會使用“律令說”來研究中國,我們先要知道“律令制”在日本的情況。日本歷史上有兩次重大的轉折。第一次,叫“大化改新”。隋唐時代,中國國力強盛,聲威遠播海外,日本人慕名而來,派出了大量的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先進的制度和文化。他們發現唐朝有一部《唐律》,律之下還有令、格、式等法律形式。整個官僚系統就在律、令的框架之內有效運作,行政效率很高,他們就把這套“律令”制度引進了日本。公元645年,日本的孝德天皇效仿中國使用年號紀年法,定年號為“大化”,第二年就頒布詔書開始改革,這就是歷史上的“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以后,日本就從以前大貴族壟斷政權的局面,一躍成為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國家。律令制度是完成這一轉變的重要制度建設,所以日本人對律令制是很有感情的。他們將大化改新以后的以律令制度作為基礎制度的國家形態,叫“律令國家”。20世紀日本歷史學家竹內理三主編了一本《日本史小辭典》,專門設有“律令國家”的條目,說:“大化革新時建立,一直延續到平安時代的日本古代國家,以律令為基本法典,故稱律令國家。”日本比較早期的歷史學家,比如桑原騭藏,也把日本的律令和唐朝的律令作一些對比研究。但是他們只是說中國古代有“律”和“令”兩種法律形式,還沒有提出具有理論內涵的“律令制”概念。
但是,明治維新以來,這一現象發生了改變。19世紀,西洋人仗著堅船利炮,打破了很多東方國家原本封閉的格局。日本發現,原先“大化革新”時學習的那套中國的制度和文化此時已經落后了。日本以巨大的魄力和行動力學習西方的科技、制度、文化,完成了近代化的轉型。
在法律制度方面,西方有兩個大的法系:一個是英美法系,一個是大陸法系。日本學習的是大陸法系。大陸法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看重“法典”的編纂,所以又叫“法典法系”。法典是把整個法律體系分成若干法律部門,比如憲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然后把每個法律部門的所有法律文件都整理、審定一遍,去掉其中矛盾、重復的部分,系統編纂成一部基于共同原則、內容協調一致、有機聯系的統一法律。日本人認為,法典是一種先進的法律編纂形式,是法律進化的產物,所以當時很多日本法學學者推崇法典。
但是,日本人在學習西方的時候,也不免于傷到自尊心。他們認為,西方有先進的法典,日本歷史上有沒有類似法典的東西呢?他們找到了律、令,想要構建一個概念,在古代的律令制和近代的法典之間,建起一座橋梁。這個概念就是“律令說”。
1904年,日本學者淺井虎夫完成了一部名作——《中國法典編纂沿革史》,這是早期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名作。這本書把中國古代的法律統統分裝在“律”和“令”兩個籮筐里面,說:“中國法典體裁上之特色,在其略有一定。養(原文如此,疑誤——引者按)中國法典,得大別之為刑法典及行政法典二者。刑法典,則律是也。行政法典,則令及會典(包含《六典》在內)是也。”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淺井虎夫雖然還沒有提出“律令說”之名,但是已經有“律令說”之實了。
最早明確提出“律令說”的,應該是日本著名的法律史學家中田薰。1933年,中田薰在為仁井田陞《唐令拾遺》作序時,寫道:“大概依據可否屬于刑罰法規,而把國家根本法分成律和令兩部分,這是中國法特有的體系。”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中田薰陸續發表了三篇有關中國律令體系沿革的文章,系統闡發了“律令說”。他認為:“所謂律令法系,是指由律和令兩種法典形式組成之國家統治的基本法的支那獨特的法律體系。”那么,中田薰的這些“律令說”,是基于中國什么時段的法律制度提出來的呢?他的后繼者大庭脩說,“律令法”的概念是“中田博士在其晚年著作《關于中國律令法系的發展》一文中,根據唐代法律提出來的”。池田溫則進一步探索這個概念的起源,認為中田薰“早在比較日本國固有法時,就將此作為概念使用”,而在戰后又將之移作中國法律史的研究,“也就是說,在20世紀初,由日本法制史學之父中田薰氏創造出了‘律令法這一名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它作為法制史術語廣為普及”。
中田薰提出“律令說”的概念,是開辟工作,來不及對一些問題進行仔細的論證和推敲。比如:用一個日本法制史的術語,來研究中國法制史,用一個隋唐斷代法制史的術語,來描繪“上起漢代,下迄清王朝”的法制通史,是否有效呢?是否準確呢?有沒有局限性呢?這些問題,中田薰都沒有進行細致的論證。不過,這并不影響“律令法”的概念對此后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者們產生的巨大吸引力。
滋賀秀三很快接過了中田薰的接力棒。他的《關于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1955)結尾部分根據唐代律令的情況明確提出,人們去判斷一個法系是不是“律令法體系”,在中國歷史上“律令法體系”是什么時候成立的,關鍵要看兩個標準:第一,法律要分成刑法和非刑法,刑法就是律,非刑法就是令;第二,律只有一部,那就是律典,令也只有一部,那就是令典。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古代不是說有了律和令,就算是律令制度。比如秦朝、漢朝,雖然既有律又有令,但是不符合兩個標準,不算律令制度,只算律令制度的前身。在中國古代,律令制度是在曹魏、西晉的時候成立的。在中田薰提出“律令法”概念短短幾年后,滋賀氏就進行了這樣精致的考證,并且對中田薰的概念進行了修正和響應,這就讓學界來不及對“律令法”概念本身進行反思,就直接開始了更加具體的細部考證。
隨后的60年代,西嶋定生提出了“東亞世界”的概念。他認為:在古代,有一個共同的文化圈,叫“東亞世界”。哪些國家或地區是這個文化圈的成員呢?那要看它是否符合四個條件:第一,使用漢字,有漢字文化;第二,遵奉儒教;第三,國家實行律令制;第四,有比較昌盛的佛教文化。其中,“律令制,是以皇帝為至高無上的支配體制,通過完備的法制加以實施,是在中國出現的政治體制。此一體制,亦被朝鮮、日本、越南等采用”。西嶋定生的論說,使得草創未久、尚應爭議的“律令制”概念跨出了法制史的研究圈子,超越了國界,具有了更廣泛的文化與文明意義。
在此之后,堀敏一、大庭脩、富谷至等學者也對中國的“律令制”進一步精耕細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今,“律令制”已經成為日本學界研究中國法制史乃至中國史的基礎性概念與前提,研究者要是研究中國法制史而不知道、不認可律令制,那就是不入流的表現。2014年,大陸翻譯出版了一套日本學者編寫的“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系列叢書,其中《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分冊就說:“所謂‘律,是指刑罰法規,‘令則是指有關行政、官僚組織、稅制等與刑罰無關的法令”,“以律、令作為兩個基軸來宣示權力的普遍性及統治的正統性,這樣的時代就被稱為律令制時代”。
雖然“律令說”在日本擁有很大的市場份額,但也有一小部分學者對此持有保留意見,展開了冷靜反思。最早進行反思的是京都史學派的著名史學家宮崎市定。他在1977年寫的一本普及讀物《中國史》里說,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就是要研究事實。如果對事實加以提煉、歸納,抽象出一些抽象的概念或者理論,那就要格外警惕。因為概念和理論一旦離開事實,可能就會“獨立行走”。比如說,日本模仿中國制定律令,有了“律令國家”“律令制度”這些詞語,但是我們不能以日本的情況來推測中國。就算都有“律令”這個名稱,在自發產生的地方(中國)和將之引進的地方(日本),律令的存在基礎和存在形態都是不一樣的。宮崎市定的這段論述非常深刻,發人深省。
再比如,1985年日本出版了一部《大百科事典》,也就是“百科全書”。這部百科全書里收錄了“律令格式”“律令制”“律令法”三個詞條。其中,“律令格式”詞條說了中國、日本、朝鮮的情況,但是“律令制”和“律令法”兩個詞條,卻只說了日本,沒有寫到中國和朝鮮。由此可以看出,《大百科事典》的編寫者認為中國、日本、朝鮮都有“律令格式”四種法律形式,這是事實;但是“律令制”“律令法”這樣富含特定理論內涵的概念,可能只是日本的特產,未必適用于中國。
1992年,池田溫先生主編出版了一部論文集,題目是《中國禮法與日本律令制》,以“中國禮法”與“日本律令制”相提并論,透露出對中、日兩國古代法加以區別的認知。
不過,以上這些反思和謹慎的態度,在日本法制史學界是非主流。而主流的“律令說”很快就流傳到中國來了。
中國的法律史學起步于清末。沈家本寫《歷代刑法考》,其中有“律令”九卷,分別考證律、令、科、法等法律形式的名稱及自上古至明代的法律。民國時期,程樹德繼承了沈家本的法律史研究傳統,寫了《九朝律考》(1925),對已經亡佚的漢律至隋律進行輯佚考證。這兩種著作,代表了擅長于輯佚考證的“漢學”傳統和古代律學的傳統方法研究趨向。它們對“律”或“律令”之名的選擇,都不過是列舉式的,并不帶有建構理論的企圖。
清末民初法制史研究的新潮流,是以現代法理學概念“整理國故”。其中開創之作,當屬梁啟超《論中國成文法編制之沿革得失》(1904);而后續踵武的代表作,則有梁啟超的弟子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以及陳顧遠《中國法制史》等。在這些著作里,律、令都只是作為一種法律形式的名稱出現,不成為一個學術概念,和日本學者的“律令說”是有區別的。
日本學界興盛“律令說”,是在20世紀50年代。當時正逢共和國鼎革之初,中國大陸的法律史學研究也烙上了“革命法學”與階級分析法的深深印記。由于顯而易見的歷史和政治原因,日本的“律令說”不可能流傳到中國大陸,更不可能對中國大陸的法制史研究產生影響。
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日本法史著作被譯介到中國大陸,“律令說”也隨之映入了研究者的眼簾,引起了學界的青睞。1998年,張建國先生發表《中國律令法體系概論》,正式將“律令法體系”的概念引入中國學界。張建國先生在這篇文章里沒有過多介紹日本學者對“律令說”的論述,而是對其進行了符合中國國情的修正。文中寫道:“律令法體系是指以律令為主體、包括眾多的法形式和內容的法律體系”,“以律令法體系作為自戰國(部分諸侯國)至唐代的中國法律體系的一種代稱,還是比較確當的,同時也是有較高學術意義的”。值得注意的是,張先生在對自己論文修訂后收入其《帝制時代的中國法》一書時,增加了一段“夫子自道”,坦陳引入這一概念的兩大意義:第一,引入“律令說”可以避免“翻來覆去總是以某某為綱,靠某些定性語句構成的簡單生硬的研究套路”;第二,引入“律令說”“有利于展開國際間的學術交流,特別是和具有認真、嚴謹、扎實的學風的日本學者之間的交流”。
“律令說”一經引入,便迅速在國內學界占領了巨大的市場。具有較高學術權威性的《北京大學法學百科全書》的“法律史卷”也收錄了“律令制”的詞條:“律令制,以律、令為法的基本淵源的制度。以這種法律制度為基礎的國家體制為律令制國家。律令制起源于中國漢晉,并為周邊國家所模仿。”有趣的是,該詞條除上引寥寥兩句涉及中國外,剩下的主要篇幅都在講日本的律令制。
其他以“律令說”為基本概念的論著也層出不窮。從戰國秦漢,到隋唐宋,再到明清,幾乎每個朝代的“律令制”都有學者在研究。粗略看來,這些研究有兩個特點:第一,將“律令說”的適用范圍自秦漢延至明清,貫穿整個中國帝制時代;第二,對“律令說”中諸如“律令制”“律令法制”“律令法系”等等概念多屬拿來就用,頂多略加介紹,很少對概念本身的內涵和外延進行詮釋或研討。
再進一步而言,還有很多研究以“律令說”為前提,提出了更多的推論:既然中國古代只有刑法典(律)和行政法典(令),可見中國古代沒有“民法”,重刑輕民、民刑不分;既然中國古代的律令都約束不到皇帝,可見中國古代是一種獨裁、專制、黑暗的人治;既然律令是中國古代的成文法,而中國古代還經常引用一些律令之外的法源作為判案、行政的依據,可見中國古代是罪刑非法定主義,是任情破法……正如宮崎市定所擔心的那樣,“律令說”的概念脫離歷史事實以后,開始“獨立行走”“結婚生子”了。
那么,“律令說”到底符不符合中國古代法的全貌呢?以“律令說”為前提的這些推論,到底能不能站住腳呢?這就需要我們對“律令說”進行一番正本清源的辨析。
二、中華法系不是律令體系 [34]
我認為,“律令說”不能涵蓋中華法系的全貌,中華法系不是律令體系。要證明這個觀點,就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考察。
首先,“律令說”不能囊括中華法系的法歷史。[34]
中國古代法萌芽于上古三代,解體于清末,有長達四千年的法歷史。“律令說”能不能用來認識中國古代法如此漫長的法歷史呢?恐怕是不行的。我們先來看日本學者使用“律令說”這個概念的時候,通常是指哪一段歷史時段。
先看“律令說”的鼻祖中田薰的說法。中田薰說:“上述律令法系,如果從時間上說,上起漢代,下訖清王朝,存續了約二千余年。”在持“律令說”的日本學者里面,中田薰所斷的時限是最長的,但也只不過是把時間的上限定在漢代。其實呢,按照日本學者的觀點,漢代的律和令都還分不太清楚,從內容上來講,律和令也不是刑法典和行政法典的關系,而是含混不清的。所以,滋賀秀三在考證曹魏律的篇目后,認為:“在魏《新律》編纂以后,歷史上其實并不存在單行律。”所以他明確提出:魏晉律令“創造律令體系的最初形態”。滋賀秀三的研究很有說服力,從此以后,日本學者基本認同“律令體系”的時間上限是魏晉。
“律令說”引進中國以后,發生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學者們普遍忽視日本學界對時間上限的討論,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時間下限。作為“律令說”的引入者,張建國先生利用出土文獻把“律令說”的時間上限上推到戰國(部分諸侯國),而把下限限縮至唐代。他發現,“此后(指隋唐以后——引者按)律令法系嬗變的結果,與早期中國律的地位已有所不同,而令更是逐漸消失了。”所以在結論部分,他寫道:“至少可以說,以律令法體系作為自戰國(部分諸侯國)至唐代的中國法律體系的一種代稱,還是比較確當的。”另外,高明士先生贊同日本學者的時間上限,而將比較嚴格的下限定至唐代:“拙稿所謂律令法,指令典成為完整性的法典而與律典成為相對關系的法典體系,……就律令法的實施而言,較具體可談,輒為西晉及隋唐而已。”
為什么他們都說“律令說”的下限是在隋唐,而不是宋朝和宋朝以后呢?
因為自從宋代開始,“律”的地位明顯下降。而“令”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大明令》以后,就被廢除了,朱元璋以后的中國歷史上就沒有“令”這么一種法律形式了。所以,名副其實的“律令說”時間下限只能到唐代,而形式上的“律令說”也止于明初。
“律令說”是指的中國歷史上哪一段歷史時期呢?有長、短兩種說法。短的說法認為,“律令說”的有效時段是魏晉到隋唐,只有600多年的時間;長的說法認為,“律令說”的有效時段是戰國到明初,約1800年的時間。不管是持短之說還是持長之說,都有掐頭去尾之嫌。
從“掐頭”來看: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早在三代就已經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治之經,禮與刑”的“禮刑體系”。就出土文物而言,“禮刑體系”至少在殷商已經初具規模,到周公制禮作樂、呂侯制刑,典章文物燦然大備,成為中國法制史上的禮法制度的早期典型。顯然,“律令說”難以容納這一段歷史。
從“去尾”來看:宋代詔敕凌駕律令,律令的地位明顯下降。元代沒有律典。明初《大明令》之后就沒有令典。所以,無論從實質來看,還是就形式而言,“律令說”都難以容納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兩代的法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宋元以降的法制就沒有特色與進步。日本學者就提倡“唐宋變革論”,認為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端;中國學者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從宋代開始,中國古代法律體系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而這個階段恰恰是“律令說”難以囊括的。
用“律令說”這個概念來認識中國古代法的歷史,不僅有“掐頭去尾”之弊,而且存在曲解之嫌。“律令說”的背后,其實隱藏著一種思維方式:唐朝的律令是“東方法制史樞軸”(仁井田陞語),而唐代律令制的模式形成于魏晉時期,所以魏晉以前的法制史只不過是律令制的形成史,隋唐以后的法制史只不過是律令制的衰亡史。這種思維方式,不僅容易在“律令說”光輝的掩蓋下,忽視不同時段法制的自身特色,而且帶有歷史目的論的嫌疑,從而恰如一葉障目,遮蔽了古代中國博雜而自洽的法體制整體。所以我們說:“律令說”不能囊括中華法系的法歷史。
其次,“律令說”難以涵蓋中華法系的法體系。[36]
古代中國的法體系博大龐雜,以前學界往往用部門法體系來表述,比如中國古代的民法、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等;也有的用法律形式體系來表述,比如律、令、格、式、科、比等等。但是卻很少有從中國古代法自身規律出發來歸納的。“律令說”雖然用的是傳統法制的用語來命名,但是卻只見局部、不見整體,很難涵蓋中國古代法體系的全部。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律令說”所謂的法體系,從產生渠道來講,是國家制定法;從表現形式來看,是成文法;從內容來看,是刑事法(律)和行政法(令)。這不僅是“律令說”的視野,近代中國法制史學科剛剛成立的時候,對于自己的研究對象,也就是歷史上的“法制”,也是這樣看待的。
梁啟超在中國法制史的開山之作《論中國成文法編制之沿革得失》(1904)中說:“成文法之定義,謂國家主權者所制定而公布之法律也。”所以在梁啟超看來,“慣習法”“君主之詔敕”“法庭之判決例”都不屬于成文法,不在論述范圍之內。為什么會這樣呢?我們如果查閱梁啟超這篇文章的參考書目,就可以知道:他的參考書目里,除了中國的古籍以外,全是日本學者的著作,比如穗積陳重的《法典論》等等。而且梁啟超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他本人也正在日本避難。所以,梁啟超的視角受日本學者的影響是很深的。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學者就產生了一個深深的“法典”情結,這個“法典”情結直接來自于“法典法系”,也就是歐陸的大陸法系。所以,從這一層淵源來講,“律令說”只不過是為“成文法”或者“法典”這種視角,加上了中國式語詞的外衣而已。為什么日本學者把“律令說”移治中國法制史的時候,會格外關注其時間的上限而忽視其下限呢?因為一直到魏晉時期,“法典”的編纂形式才告成立,而明清時“法典”的存在已經毋庸置疑,也就不必再管“律令”的有無了。
在這樣一種“法典”的視野下,“律令說”難以看到古代中國法豐富多彩的法律樣態。
首先,“律令說”難以容納中國古代的鄉規民約、家法族規——底層的“活法”。[36]
持“律令說”“法典論”者,常常說中國古代缺少私法。其實中國古代不是沒有私法。中國古代的私法并不以律令、法典的形態呈現,而是大量存在于鄉規民約、家法族規以及習俗之中,是一種民間的、底層的“活法”。在古老久遠的禮法社會中,它們無處不在、無時不有,還無人不曉,是真正的“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的“無法之法”。
以家法族規為例,費成康在撰寫《中國的家法族規》的時候,僅僅過目的家法族規就有“上萬種”之多,該書附錄里收了55種家法族規,各具特色,可以窺其一豹。再以契約為例,據學者“保守的估計”,截至20世紀80年代為止,僅“中外學術機關搜集入藏的明清契約文書的總和”,“也當在1000萬件以上”。如此龐大數量的契約文書,如果說其背后沒有一種“私法”在起作用,是不可想象的。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習慣法還有宗族、村落、行會、行業、宗教寺院、秘密社會、民族習慣法等。清末至民國時期,為了制定民商法典,民國政府在全國范圍進行民商事習慣調查運動,先后編纂成《民事習慣大全》《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里面收錄的那些“習慣”,全都是活在社會中的規則體系。日本學者滋賀秀三在撰寫《中國家族法原理》的時候,也對已往的方法論進行反思。他說:“舊中國的私法那樣的研究對象本身,我認為帶有不能接受法實證主義的方法論的那樣的特性。”而這種“法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正是“律令說”與“法典論”的基本立場。所以,處在中國古代法體系底層的豐富多彩的“活法”,難以進入“律令說”的法眼。
其次,“律令說”難以容納中國古代的大經大法、祖宗之法、天下之法。[37]
日本史學家西嶋定生的說法:“律令制,是以皇帝為至高無上的支配體制。”其實在中國傳統法理中,皇帝并不是最高,律令更不是。比皇帝和律令更高的“高級法”“法上法”“理想法”還有天道天理、“先王之法”和“天下之法”、“經義”和禮制、祖制和祖訓,等等。
天道天理是帝制統治和立憲定制的根本法源,所以有“奉天承運”“口含天憲”之說。
“先王之法”和“天下之法”是上古的圣王,比如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代一代傳下來的,作為評價當時政治法制的標準。比如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用先王之法、天下之法來批判秦漢以后帝制中國的法制,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經義、禮制,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圣賢創法立制的成果,在中國傳統語境中,一般被尊為“大經大法”。祖制和祖訓統稱“祖宗之法”,是本朝列祖列宗創法立制的成果,在中國傳統語境中又可以表述為“先祖法度”“祖宗故事”“祖宗家法”“祖宗典制”等。在律令之外,大經大法、祖宗之法也都是司法、行政的重要依據,甚至會成為終極依據。
以經義為例。經義是議政議法的重要依據,也是司法、行政中高于律令的直接依據,最為典型的表現,就是“春秋決獄”。“春秋決獄”,又稱為“經義決獄”,是西漢董仲舒首先倡導的。史書記載:“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兩漢時代,從事“經義決獄”的代表人物除了董仲舒以外,還有公孫弘、兒寬、應劭等。
到了晉朝,當時人提出來一種制度設計:基層“法官”要嚴格遵守法律條文,不允許搞例外;但是對于少數“事無正據,名例不及”的疑案,允許朝廷大臣來“論當”,也就是通過討論的方式,來尋找一個恰當的判決。大臣依據什么來“論當”呢?東晉主簿熊遠在奏議中說:“凡為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大臣們要么引用律令這些成文法,要不然就必須符合經傳、以前的判例。到了北魏,“經義決獄”進一步制度化:“詔諸有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由此可見,在“律令體制”成形以后,“經義決獄”的遺風尚存。法史學界有一種比較通行的看法,“春秋決獄”到唐朝以后就式微了。作為一種定讞依據,這種看法不無道理,但是如果從議刑議法的理論依據上看,經義仍然發揮著權威依據的作用。以唐代翻來覆去爭議的是否允許復仇為例,韓愈的《復仇狀》、柳宗元的《駁復仇議》,無不征引經義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性。比如康買得復仇案,最后宣判“減死一等”,而依據就是“《春秋》之義,原心論罪”。
禮制在中華法系的法體系中也具有很高的地位。憲法學者張千帆先生對“禮”進行考察后認為:“總的來說,憲法是對‘禮的最合適定性。”來自部門法學者的眼光,對我們反思中華法系不無啟迪。
再看“祖宗之法”。祖宗之法,主要是開國君主制定,用來約束包括后代君主在內的最高統治者的“家法”。比如說,漢高祖劉邦曾經殺白馬為盟:“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不是姓劉的,就不能稱王;沒有立功,就不能封侯。如果有誰不遵守此約定,天下人一起討伐他!“白馬之盟”曾經被大臣們引來反對呂氏封王,反對封王氏外戚侯,反對封匈奴降者侯等,在兩漢歷史上起到了強有力的規范作用。再比如,宋代有一個“不殺士大夫”的祖宗家法:“藝祖有約,藏于太廟,誓不誅大臣、用宦官,違者不祥。”宋太祖有一個約定,刻在碑上,藏在太廟里面,說:我朝絕不殺大臣,絕不任用宦官,違反者不祥。又比如,清朝的順治皇帝曾經“命工部立內十三衙門鐵牌”,也就是讓工部在宦官辦公的衙門口樹了一塊鐵牌,上面寫著:嚴禁宦官干政,否則凌遲處死、決不寬貸。類似于這樣的祖訓、祖宗之法,史不絕書。這些祖宗之法的效力位階要比一般律令來得高,后世的君主非但不能違背,而且輕易不得修改,否則會遭到巨大的輿論壓力。
另外,中國在對外關系上也有一套規則體系,不是“律令說”所能夠容納的,有學者稱之為“天下法”。從宋《冊府元龜·外臣部》體例來看,其內容包括封冊、朝貢、助國討伐、和親、盟誓、納質、責讓、入覲,等等。“天下法”以政、刑、禮、德為基本要素,由此而展開結合、統治、親疏、德化諸原理的運作,從而建立天下體系。違反“天下法”的制裁手段,就是“大刑用甲兵”的刑。
綜上所述,來自日本、流行于中國的“律令說”,難以囊括中國古代法的法歷史,難以涵蓋中國古代法的法體系,以“律令說”認識中國古代法,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局限。我們指出這些,并不是要棄“律令說”而不用,而是試圖對其適用范圍加以限制,從而更好發揮其功用;同時探索出一套更加符合中國法律史實際的概念體系,為中華法系正名。
三、中華法系是禮法體系 [39]
中國古代法不僅僅有“律令法”“律令體制”,還有“大經大法”“祖宗之法”“天下之法”,以及規范普羅百姓民事生活時空的大量民間“活法”。中國古代法不能歸結為“律令法”“律令體制”“律令體系”“律令法系”,而是“禮法”。“律令”生于“禮法”,合于“禮法”,“禮法”統攝“律令”,包含“律令”。借用“律令說”的話語方式,它是一種“禮法”法,是“禮法體制”“禮法體系”。
“禮法”不是“禮”和“法”,或“禮”加“法”,也不是指“納禮入法”,或“禮法融合”。“禮法”是一個雙音節詞匯,一個名詞,一個法律學上的法概念,一個法哲學上的范疇,也是古代“禮樂政刑”治國方式的統稱。質言之,“禮法”即法。確切地說:“禮法”是古代中國的法。
前面我們說過,“律令說”難以囊括中華法系的法歷史,難以涵蓋中華法系的法體系。那么,禮法能不能做到這兩點呢?
首先,禮法能夠涵蓋中華法系的法體系。[39]
成熟狀態的禮法體系包括三個子系統,分別是禮典子系統、律典子系統、習慣法子系統。
禮典子系統,包括國家頒行的成文禮典,還包括各種典章制度、儀文節注,以及在長期行政過程中形成的行政慣例和禮儀慣例。禮典子系統,不是某個皇帝心血來潮編撰的結果,恰恰相反,皇帝要受到禮儀的制約。歷史學者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截取明代的一個普通年份,來展現整個帝制中國時代的運作常態。書里說,對于一個皇帝而言,一生中要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參與、主持各種各樣的禮儀活動。從每天的早朝、經筵,到每年的籍田禮、祭禮,到自己的冠禮、婚禮,不一而足。對禮儀稍有違反,就會遭到大臣的進諫和糾正,比如明代的“大禮議”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那么,這些禮如果不是皇帝制定的,是哪里來的呢?禮的來源,一般有兩大部分:一是歷代相傳的禮制。這些制度,可能來自古老的夏、商、西周,也可能經過歷朝歷代乃至本朝的損益增刪。二是圣賢的經典。三代的禮儀、禮制、禮義,在先秦“軸心時代”經過圣賢的整理和提升,制定成了經典。這些經典,是考正本朝禮制的理論標準。每當遇到現實的制度問題難以解決的時候,大臣們總是習慣于回到經典中去,汲取圣賢的智慧,再活用到現實中去。每一代的士大夫,都閱讀著同樣的經典成長起來,形成了具有類似價值觀的共同體,他們結合本朝的現實問題,以經義為理論標準,改造歷代相傳的禮制,就制定出了本朝的禮制。經過皇帝的認可和頒布,就是本朝的禮典。禮典本身只是正面的規范,不帶有負面的罰則。罰則主要通過律典子系統和習慣法子系統來規定。
律典子系統,包括國家頒行的成文律典,還包括令、格、式等成文法律,以及獄訟判例。中國古代的禮和律,并不是并用的兩種手段,而是有先后之分、本末之別,禮先律后,禮本律末。先用禮來預防、引導、規范,可以使得絕大多數的行為都納入常軌。還有極少數難以為禮所化的行為,再動用律的強制力加以制裁。如果單獨動用律,那就是儒家所反對的“不教而誅”,是陷害老百姓的表現。而最好的治理狀態,就是禮能夠預防幾乎全部的犯罪行為,使得律典、刑罰不起作用,這叫“刑措”。措,就是放在一邊的意思,刑罰放在一邊不用了,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清平盛世才能達到的理想境界。
武王滅商以后,殷商遺老箕子曾經傳授給武王一篇統治心法,叫《洪范》。《洪范》把一個國家的制度分為八類,叫“八政”,排列順序是: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其中,內政是前六項,也就是先要讓老百姓有飯吃(食),有錢花(貨),有精神生活(祀),有房子住(司空),受教育(司徒),如果還有人鋌而走險犯罪的,再加以刑事制裁(司寇);外交方面,也是先禮(賓)后兵(師)。唐朝有一部政書叫《通典》,一共包括九個分典,分別是: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排列順序也是:先讓百姓有吃有用(食貨),再通過推舉考試的方式(選舉),組成政府(職官),以禮、樂進行教化,用軍隊保障安全(兵),如果還有人鋌而走險,那么用“刑”來制裁。這是律典子系統在禮法體系中的位置。脫離了禮法體系的律典系統,就會變成專任刑法的暴政;禮法系統統攝下的律典系統,才是天鵝絨手套中的鐵拳,“以生道殺人”,使老百姓“雖死不恨”。
習慣法子系統,包括禮法社會底層的各種形式的“活法”。這些“活法”主要是民間自發形成的“俗”,經過士大夫的改造和上層文化的熏陶,“約之以禮”,逐漸形成的合于禮法的“活法”。中國自古以來,中央政府就是一個有限政府,講究“皇權不下縣”。政治權力不能一竿子捅到底,不能用行政手段、政治權力去干預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社會底層形成了一種“自治”的秩序。一家有家法,一族有族規,一鄉有鄉約。這些“活法”,有很強的地域性,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這些“活法”,又有很強的共同性,都不能違反國法,都要合于禮義。這些“活法”,未必形成書面的白紙黑字,但即便是文盲也能夠輕易了解,自覺遵守,日用而不知、從心所欲而不逾矩。
其次,禮法能夠囊括中華法系的法歷史。[41]
從原始習俗到禮儀、禮制的初成,再到“禮法”的提出和“禮法體系”的成熟,又最終走向衰微,曲折跌宕,貫穿整部中國法律史,從大體上來講,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原型期(夏、商、西周)
夏、商、西周,史稱“三代”,這一階段的禮法體系表現為“禮-刑”結構,“禮”就是夏禮、殷禮、周禮;“刑”就是夏朝的禹刑、商朝的湯刑、周朝的九刑。“禮-刑”結構的運作模式是“違禮即違法,出禮則入刑”——你違反了禮,就等于違反了法,那就要受到刑的制裁。這是禮法的原型期。特點是:禮刑一體、禮外無法、法在禮中、出禮入刑。當時還沒有發展出后世精密的禮典、律典系統,禮法的法體系還處于萌生階段。
第二階段:重組期(春秋—秦漢)
通常的說法是,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這是以儒家為視角、從負面進行的評價。如果從整個禮法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來看,這一階段是舊的“禮-刑”結構的禮法形式的崩壞,而律典系統則開始生長壯大,從而催生著新的禮法結構和帝制時代的“禮法體制”。
漢代開始尊崇儒術,陸續重拾禮儀。由于春秋戰國到秦代的律典系統規模初現,一時成為法律思維定式,以至于弄得其復興之禮典卻無處安放,只好統統稱之為“律”。比如叔孫通制定的“禮儀”稱為《傍章律》,趙禹制定的“禮儀”叫作《朝律》。正如章太炎所說:“漢律之所包絡,國典官令無所不具,非獨刑法而已也。……漢世乃一切著之于律。”與禮、律在形式上相混同的同時,是禮、律在精神上的分離。“引禮入法”只能通過司法領域的“春秋決獄”、律家的律章句等方式從側面切入,個案地進行,而無力制定一部真正的禮典和滲透禮義精神的律典。所以兩漢時代雖然已經獨尊儒術,但是仍然只能稱之為禮法的重組期。
第三階段:成熟期(魏晉—明清)
“儒家有系統之修改法律則自曹魏始。”曹魏《新律》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編纂的律典,也是第一部儒家化的律典。曹魏后期司馬氏執政,開始制定《新禮》,到西晉第二任皇帝晉惠帝的時候頒行天下。西晉《新禮》是“中國第一部依據儒家學說體系編撰,而且是由國家所正式頒行之禮典”。從西晉的《新禮》和《泰始律》開始,此后的王朝在開國之初,大多都要同時并舉禮典與律典兩項大規模的立法活動,而有雄心壯志的帝王也大多都要重修前代的禮典、律典,比如南梁《普通禮》與《天監律》,隋朝《開皇禮》與《開皇律》、《仁壽禮》與《大業律》,唐朝《貞觀禮》與《貞觀律》、《顯慶禮》與《永徽律》、《開元禮》與《開元律》,宋朝《開寶通禮》與《宋刑統》,明朝《大明集禮》與《大明律》,清代《大清通禮》與《大清律》等。總之,這些王朝無不以“制禮作律”為功成治定的標志。這就是帝制中國“禮-律”結構的禮法體系。所以,從魏晉到明清,是禮法法系的成熟期。
第四階段:衰落期(清末以來)
窮變通久,久則不免于僵化。自明清以來,專制集權加強,君主自毀禮法之精神,墨守禮法之形式,致使“制禮作樂”淪為粉飾太平的道具。西方法系強勢入侵,保守派卻不知變通而固守成規,錯失了變法良機。在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下,中華法系走向解體,禮法也就此湮沒不彰。
近現代中國,列強欺凌,戰亂頻仍,內憂外患,民不聊生。其所遭受的“禮崩樂壞”遠甚于孔子時代。中華文化數千年之道統毀損,法統斷裂。為護持華夏國權國域祖產和民族血統文脈,從“師夷長技”到洋務運動,從君主立憲到共和立憲,從開明專制到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方略,從實業救國到主義救國,從維新改良到共和革命,從三民主義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從師法歐美到“以俄為師”……志士仁人不避血雨腥風,不懈探索,從未停滯推進民主、科學、憲政、法治的步伐。
剝極必復,貞下起元。我們終于等來了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宣告。它意味著法制和法學領域迎來了根本性的轉型:從過去崇尚以維護階級專政為目標的革命工具型法制,轉向構建“良法善治”的治理型法制;從過去著重于移植歐美或蘇俄的移植型法制,轉向與人類民主法治文明相向而行又富有中國范兒的特色型法制。實現這兩個方面轉型需要上上下下的齊心協力。道統紹續,法統維新,政統重建,時不我待。就其學術層面而言,認識中國法律史的自我,破解中國古代法的遺傳密碼。非此,無從有效吸納傳統法文化“良法善治”之智慧,而特色型法制如果不能得到中華五千年傳統法文化的支撐,也無疑會成為一句空話。
(責任編輯:張發賢 責任校對:陳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