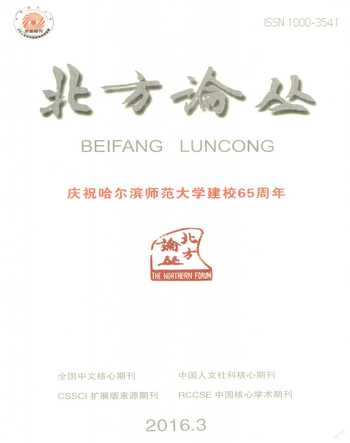認知語用視域下轉喻的修辭功能
江曉紅
[摘 要]傳統修辭學將轉喻約簡為詞匯間的替代,對轉喻修辭功能的討論比較簡單;認知語言學把轉喻看作一種普遍的認知方式,忽略了轉喻在日常語言,特別是在文學語言中修辭效力的體現。轉喻既是一種認知機制,也是一種廣泛使用的語用現象,二者不可或缺。
[關鍵詞]轉喻;修辭;認知;認知語用
[中圖分類號]H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6)03-0067-05
轉喻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最早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傳統修辭學把轉喻看成是一種修辭手段,相當于漢語修辭格中的“借代”。隨著認知語言學的興起,人們認識到轉喻不僅是一種修辭手段,還是一種思維方式,是普遍存在于人們日常思考和談話過程中的一種認知現象。然而,轉喻的認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轉喻的修辭功能,非但沒有加深對轉喻修辭功能的進一步了解, 反而對轉喻傳統的修辭功能闡釋質疑。目前,學界對轉喻的認知研究展開了反思,探討如何利用認知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加深對轉喻修辭功能的理解。同時,轉喻作為一種語用現象逐漸引起語用學家的重視,自21世紀初以來,關聯理論在詞匯語用學的研究中已開始思考和探究轉喻,旨在深化對這一語用現象的認識。認知語言學揭示了轉喻的思維本質,但轉喻作為一種修辭手段的功能并未消失。因而本文嘗試從認知語用的角度進一步探討轉喻的修辭功能,讓古老的修辭話題重新煥發生機。
一、轉喻的傳統修辭學研究
在早期的傳統修辭學研究中,轉喻通常出現在對隱喻的討論中。亞里士多德在《修辭學》中將隱喻分為四種類型,現在人們經常討論的名詞性轉喻可歸為其中的一類。由于亞里士多德的隱喻定義奠定了西方修辭學隱喻研究的基礎,傳統轉喻研究總是在隱喻研究中進行。直到20世紀50年代,Jakobson從結構主義語言學角度提出了轉喻和隱喻兩種模式,對語言的詩學功能進行了闡釋。
轉喻一詞來自拉丁語,意為“換名”。古希臘修辭學家通常都是把轉喻作為一種替換過程來處理,轉喻的替代觀在各種詞典對轉喻的定義中多有體現。例如,《韋氏大詞典》將轉喻定義為使用一種事物的名稱表示另一種與之密切聯系的事物的修辭格。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中也將轉喻定義為相關事物名稱之間的替代,即不直接說出某人或某物的名稱,而是使用一個與之相關的名稱去替代[1(p.65),如用“春秋”代替四季/年,“娥眉”代替女性等。轉喻是人們在言語交際中經常使用的一種表達手段,例如:
(1)我最記得北京雙十節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門吩咐道,“掛旗!”“是!掛旗!”各家大半懶洋洋地踱出一個國民來,撅起一塊斑駁陸離的洋布。(魯迅《吶喊的故事》)
(2)庭院的盆栽,又長出一片新綠。(劉澎萌《雨夜》)
以上兩個例句都運用了轉喻表達,例(1)用“洋布”轉指“旗子”,是因為洋布是做旗子的材料;例(2)用“新綠”借代“樹葉”,是由于綠色是樹葉的顏色。在傳統修辭學中,轉喻通常被視為用某事物的名稱替換相關事物名稱的一種修辭手段。
與其他修辭格一樣,轉喻往往具有偏離語言常規、不同于普通語言表達的特點,以使語言表達更為生動有力,進而增強語言的表達效果。轉喻的修辭功能主要體現在言辭簡潔、表達生動兩個方面。前者主要是指語言形式,后者主要是指內容。結合Jakobson關于轉喻來源于連貫話語(特別是詞組)緊縮的觀點,文學評論家Lodge指出,根據話語的連續性表述原則,轉喻實際上可看作為語言符號不合邏輯地進行刪除和壓縮,從而使轉喻話語具有自身的藝術獨特性[2]。例如:
(3)母親勸我學醫,一向馴順的我,沒有一絲猶豫便反對:不,我去新聞系。我要當作家,我要當丁玲。 (王曼曼《下雪了,我去看丁玲》)
例(3)中的“丁玲”并不是用于指其本人,而是另有所指,聯系前文的“母親勸我學醫”,可以推知“丁玲”實際上指的是“(丁玲那樣的)女作家”。但如果將上述信息都明確地表述出來,便會顯得冗余累贅。
轉喻的另一個重要修辭功能是表達形象生動,通過突顯事物的特征、屬性,使人獲得鮮明、深切的感受。例如:
(4)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李清照《如夢令》)
例(4)中“綠肥紅瘦”一語,堪稱全詞的精絕之筆,歷來為世人所稱道。“綠”指葉,“紅”指花,均以事物特征轉指事物。詞中的“肥”和“瘦”則隱喻綠葉的繁茂與紅花的稀少,描摹風雨過后海棠花葉的不同形貌,葉子豐茂而花朵凋零,生動地反映出作者對春天將逝的惋惜之情。“綠肥紅瘦”一語含而不露,凄婉動人。正是通過事物的顯著特征來指稱該事物,轉喻表達常常具有簡潔、生動的修辭效果。
二、轉喻的認知解讀
傳統修辭學把轉喻的本質約簡為詞匯間的替代,對轉喻的認識還停留在簡單的列舉和分類上,難以揭示轉喻所涉及的深層認知機理,對轉喻修辭功能的討論也比較簡單。認知語言學建立在我們對世界的經驗以及感知和概念化世界的方式的基礎上,指出轉喻和隱喻都是人們認識事物的工具。有關轉喻的運作機制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一是轉喻激活/突顯說把轉喻看作認知域矩陣中某個認知域的突顯;二是轉喻映射理論認為轉喻是在同一個認知域中的兩個概念實體之間的映射;三是轉喻心理通道說將轉喻視為在同一理想化認知模型中,某個概念實體為另一概念實體提供心理通道。轉喻所涉及的認知域,雖然被冠以不同的名稱,如理想的認知模型、框架、百科知識網絡等,但實際上都是指一種特定的認知結構。以上三種模式從不同側面解釋了轉喻的運作機制,轉喻作為一種從參照點到達目標概念的認知操作過程,為概念之間的通達創造了可及性。
認知轉喻在分析語言現象方面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因而涌現出許多從轉喻視角展開的研究,涉及詞匯、語法、語用、語篇等不同層面,拓展了語言研究的新途徑。陸儉明從轉喻的角度,解釋了漢語中的程度副詞“很+名詞”現象[3],如很中國、很香港、很紳士、很陽光等。他把這類語法現象看作一個由此及彼的認知過程,即由某一具體事物激活該事物所具有的性質或特性。因此,轉喻不一定都是“從具體到抽象”,也可以“從抽象到具體”。此外,古漢語中的許多詞性活用現象,從認知轉喻的視角來看,其實就是相鄰概念之間的轉換,這就使古漢語在缺乏嚴格語法秩序的同時,保證了其認知上的合理性。例如,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形容詞“綠”就運用了使動用法,生動形象地刻畫了春回大地、萬物復蘇的景象。
在話語層面上,人們可以通過提及事件的某一部分而傳達某種“會話含義”,從而達到以此代彼、旁敲側擊的效果。例如:
(5)那天晚上你送我去宿舍,當我們邁上那斜斜的山坡,你忽然住足說:“我在地毯的那一端等你!我等著你;曉鳳,直到你對我完全滿意。”(張曉鳳《地毯的那一端》)
例(5)不直接說“婚禮的殿堂”,而只說與此相關的事物,由聽話人根據常識推測說話人的真實意圖,這是人們通常使用的語言技巧。Gibbs強調轉喻是一種思維方式,由于相鄰概念之間的連通,人們能夠自動地將與腳本相關的沒有明示的部分推導出來[4],因此,轉喻在篇章建構和含義推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
(6)老太太發誓說, 她偏不死, 先要媳婦直著出去,她才肯橫著出來。(張愛玲《五四遺事》)
根據“言語行為轉喻”理論,人們可以通過提及言語行為的一個部分來實施該言語行為[5]。例(6)中“直著出去”和“橫著出來”雖然只是陳述了可能的事效, 但通過“事態效力指代事態結果”的轉喻模式,說話人實際上意指這兩個事態的結果,即“離婚”和“死去”。讀者依據特定的言語行為轉喻模式,就能解讀出預期的結果。
認知語言學揭示了轉喻認知的普遍性,拓展了轉喻研究的視野和范圍。然而,轉喻的認知研究相對忽視了轉喻在日常語言中的交際功能,特別是在文學語言中修辭效力的體現。有鑒于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利用認知語言學和語用學研究的新發現,深入挖掘轉喻的修辭功能,揭示其深層的認知和語用動因及其影響因素。
三、轉喻修辭功能的認知語用學闡釋
(一)轉喻修辭功能產生的認知語用動因
在已有研究中,轉喻常被視為一種縮略表達,轉喻修辭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表達上的簡潔。Jakobson認為,轉喻是有組合關系的兩符號的壓縮或精簡[6](pp.76-82),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就是以“四海之內”代“四海之內的人”。Warren指出名詞性指稱轉喻是由一個隱性的“修飾語+中心詞”短語構成。其中,明示成分是修飾語,隱含成分為中心詞,是偏正結構中的以偏代正。指稱轉喻建構的出現是因為說話者將注意力集中在事物的某一屬性上,而不是事物本身[7](pp.113-132)。很多時候,說話人將某些較長的詞組或者短語進行壓縮,被抽取的詞語作為認知參照點,往往是事物突顯的、易辨識的部分,因而具有提示作用,引導聽話人辨認指稱對象。
語言交際受相互競爭的經濟最大化和信息最大化原則支配[8]。根據經濟最大化原則說話人傾向于使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形式;而信息最大化原則要求說話人盡可能準確地傳遞最多的信息。換言之,在言語交際過程中,說話人的表達既要求盡量簡短,又要讓聽者能夠理解。當具備實現成功交際的條件時,指稱表述越簡潔,就越會被選擇。例如:
(7)天安門廣場沸騰了。
(8)她和錢結了婚。
(9)他把那瓶也喝了。
轉喻運作涵蓋了顯性和隱性兩個方面,充當參照點的轉喻詞語在認知上一般都具有“易懂或易感知”的特點[9](p.77),指引聽話人理解隱性的目標概念。在言語交際中,人們常常運用轉喻巧妙地協調和兼顧信息最大化原則和經濟最大化原則。
在言語交際中,使用轉喻實現指稱轉移只是說話人意義的一部分,喻體作為一個不同于本體的概念,它激活的信息就不只是本體,而且還有它所激活的聯想意義,從而增強轉喻指稱的表達效果。在文學類話語中,由于追求語言表達形象生動的效果,使用轉喻的情形十分常見。例如:
(10) 在船上,他們接近的機會很多,可是柳原既然能抗拒淺水灣的月色,就能抗拒甲板上的月色。(張愛玲《傾城之戀》)
轉喻之所以能具有較強的修辭性,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人們的聯想認知。例(10)中的“月色”跟“求婚”似乎沒有關系,但事物之間的鄰近關系有時需要人們去發掘和認識,而這常常依賴于人們的聯想認知,通過聯系上下文,建立喻體和本體之間的聯系。小說中的主人公范柳原和白流蘇正在談戀愛,但范柳原并不愿意結婚。在乘船回上海之前,他們在香港淺水灣經常趁著月色散步、聊天。當聯想到這樣的認知背景,就容易明白月色所指代的本意,達到避免生硬直說的效果。可見,人們理解和鑒賞文學作品的能力依賴于轉喻思維,轉喻表達激起人們的聯想越豐富,獲得的修辭效力也越強。作者正是借助轉喻描述來突顯某一事件的典型特征,創造一種新穎脫俗的表述方式。
(二)影響轉喻修辭效力的認知語用因素
在實際言語交際中,轉喻是涉及跨語義和語用界面的現象。一些轉喻,如“白領”“藍領”“五角大樓”等已成為一種常規性的表達方法,而在“城市多喝一杯奶,農村致富一家人”中,用“城市”轉指“城里人”,就是一種在特定語境下的特定所指。新穎形象的轉喻往往具有較強修飾色彩,一些規約化的轉喻修辭功能卻逐漸弱化。不同類型轉喻的修辭效力存在較大的差異,但影響轉喻修辭效力的因素還有待進一步詮釋。
1.轉喻類型
Panther & Thornburg認為,轉喻有原型轉喻和邊緣轉喻之分,原型轉喻突顯的概念是目標域,而邊緣轉喻突顯的是源域[10]。例如:
(11)那個薩克斯管今天感冒了。
(12)尼克松轟炸河內,殺害了無數平民。
例(11)中的主要對象顯然是人(目標域)而非薩克斯管(源域);但在例(12)中,“美國飛行員”(目標域)的概念認知地位遠不及“尼克松”(源域),造成轉喻概念突顯。出現差異的根本原因是說話人的主觀意圖,因為說話人強調的是轟炸的責任者而非執行者。
根據語義沖突的大小,最能體現轉喻修辭效力的是能夠突顯目標域的原型轉喻,即Panther & Thornburg所說的好的轉喻。因為這種情況下源域與目標域,即形式與內容的沖突最為顯著。新穎轉喻因偏離一般的語言使用規范,通常具有較大的認知效果。在例(11)中,謂語“感冒”的語義選擇要求其主語必須是人,而“薩克斯管”是樂器,主謂之間存在較強的語義沖突。而沖突比和諧在修辭上往往更具表現力,更能引人注目。王希杰認為,轉喻其實是一種偏離現象,從積極的方面說,是因為求美求異,尋求鮮活生動、委婉含蓄的表達形式;從消極方面說,其實是一種避諱行為,不得已才偏離的。相對而言,突顯源域的邊緣轉喻也并不總是不具有修辭效力,以一個經典轉喻“尼克松轟炸河內”為例,就源域與目標域的關系來看,雖然實際轟炸河內的人并非“尼克松”本人而是“美國飛行員”,但二者所指的都是人,語義沖突并不強烈。后續語句保持以源域“尼克松”為話語主題進一步表明目標域的認知顯著性被削弱,轉喻的修辭效力也受到一定的抑制。
在日常言語交際中,一些轉喻由于長期反復使用,已經從原來的新穎用法逐漸演變為一種規約性的使用,而且似乎比原有的表達更為簡潔自然。例如,“壺燒干了”“來一瓶青島”等,這些轉喻關系也趨固化,相當于“死轉喻”。隨著轉喻使用頻率的提高,轉喻逐漸固化或規約化。由于所需激活加工程度小,不再誘發人們的相關聯想, 轉喻的修辭效力也就會日益減退,最終趨于零度偏離。
2.概念激活方式
傳統修辭學關于轉喻的替代觀過于簡單,未能揭示轉喻的概念結構和認知過程。認知語言學致力于解釋概念之間的激活連通過程,認知轉喻共現觀認為轉喻表達式不但經由顯性概念的激活而實現隱性概念的激活,而且顯性概念和隱性概念一起共同構成一個指稱整體。例如,“我喜歡讀三毛”,其中,“三毛”并非泛指“文學作品”,而是指“(三毛創作的)文學作品”。轉喻體現的關系是X加Y,而不是X替代Y。
在轉喻理解過程中,作為一種參照點現象,轉喻表達式首先被激活,是一個經由源域通達目標概念的認知過程。“激活”是認知語言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陸儉明詳細地闡述了轉喻的激活方式[3]。由于客觀事物原本就是相互聯系的,構成人們認知結構的概念相互連接成一個網絡體系,從而促使不同的認知域之間可以相互激活。轉喻激活涉及一個認知域激活與之密切關聯的另一個認知域。根據激活出現的頻率,可分為單一激活和疊加激活。單一激活就是一個源域直接激活一個目標域;疊加激活是指不止一次激活。例如:
(13) 可這些不說,鄔橋總是個歇腳和安慰那烏篷船每年都要載來多少斷腸和傷心,船下流的都是傷心淚。(王安憶《長恨歌》)
(14)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劉禹錫《竹枝詞》)
例(13)的言說本體是“每年坐著烏篷船來的人”,作者通過同一認知域中的源概念“斷腸”和“傷心”激活目標概念“(斷腸/傷心的)人”;例(14) 字面說的是陰晴的“晴”,字里說的卻是情意的“情”,二者同屬一個語音聚合中的兩個同音詞,由源概念“晴”激活了目標概念“情”,讀者結合相關認知體驗可推斷其修辭意義。
概念在激活過程中往往伴隨著擴散,認知心理學上稱之為擴散激活模型。在由概念組成的認知網絡結構中,任何一個節點的激活都可影響到與它關聯緊密的節點。轉喻有時涉及不止一次的激活,從而形成轉喻鏈。例如:
(15)楊意不逢,撫凌云而自惜;鐘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 (王勃《滕王閣序》)
例(15)中的“楊意”、“凌云”、“ 鐘期”和“ 流水”都包含多個轉喻,其中,“凌云”指代《滕王閣序》作者王勃自己的作品,王勃是通過一個復雜的轉喻鏈實現用“凌云”指代自己的作品的,即凌云→有凌云之志→司馬相如賦→優秀的詩文→王勃作品。概念之間由于彼此鄰近而構成轉喻關系,理解詩中的轉喻需進行多次聯想激活,因而具有較強的修辭效力。
隱喻和轉喻是兩種不同的認知機制,然而有時卻難以將它們截然分開。隱喻和轉喻互動可相得益彰,增強語言的修辭效力和審美意趣。單一聯想所帶來的修辭效力有限,轉喻解讀涉及的聯想內容越豐富,修辭效力越強。例如:
(16)清瑟怨遙夜,繞弦風雨哀。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臺。( 韋莊《章臺夜思》)
詩人用“孤燈”“楚角”“殘月”“章臺”等常見意象加以層層渲染,通過概念之間的發散式聯想,描寫了困守寓所,孤燈獨坐,又聽到蒼涼悲切的“楚角”聲,突出“夜思”之苦。“燈”雖然是無生命的物體,詩人卻以此借物抒情,以烘托內心之憂怨、哀傷。詩中的“孤燈”一方面可比喻成“人”;另一方面,夜深人靜、孤燈難眠,“孤燈”又可轉喻“黑夜”與“無眠”。“燈”與“人”合二為一,意境清幽,哀感動人,強烈地表現了秋夜思鄉的凄苦。
3.認知語境
孤立的詞語不能成為轉喻,轉喻表達與語境密切相關,語境影響甚至消除轉喻修辭功能的實現。例如:
(17)各級領導來到菜園子。
(18)各級領導要狠抓菜園子。
同樣是“菜園子”,在例(17)中直指種菜所在地,而在例(18)中,卻由具體的事物“菜園子”聯想到與之相關的活動“副食品生產”。雖然兩句只有一詞之差,不同的上下文語境卻制約著轉喻的生成和理解。
修辭情境是Bitzer提出的一個修辭學概念,具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修辭情境主要指修辭行為所發生的語境;廣義修辭情境就是一種包羅社會萬象的社會環境或象征系統。二者皆屬于一種既定的、靜態的語境觀。關聯理論認為語境是動態的,而非外在因素的簡單組合。客觀環境或文化所規定的某些固有知識只有在轉化為人們的認識后,才能在言語交際中發揮作用。認知語境是一種心理建構體,是動態推理過程中構成聽話人認知環境的一系列假設。這些語境假設主要有三個來源: 話語的上下文、認知背景和現時情景[11]。例如:
(19)張大千:梅先生,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張大千/梅蘭芳趣事一則)
要理解句中的“君子”和“小人”意義,就需進行一系列假設:這是發生在一次招待酒會上的趣談(情景語境);張大千是著名畫家,梅蘭芳是京劇表演藝術家,畫家工作用手,而京劇表演用口(背景知識);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句諺語“君子動口,小人動手”(文化語境)。正是通過以上相似與相關性的聯想,突顯“君子”和“小人”的相關特征,才能了解其真正所指。轉喻表達不僅使話語顯得幽默風趣,還能傳遞一系列弱隱含。
在解讀轉喻時,人們根據顯性的語言表達構建語境假設,推測隱性的轉喻成分,對轉喻的理解取決于建立與參照點的關聯。例如:
(20)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
長大后,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 (余光中《鄉愁》)
鄉愁是人們普遍體驗卻難以捕捉的情緒,詩人從廣遠的時空中提煉出“郵票”“船票”等意象,意境幽遠深邃,內容豐富含蓄,能誘發讀者多方面的聯想。詩行中“鄉愁”經由“是”被定義為郵票、船票,因而一般會把這些東西當作“鄉愁”的隱喻。然而,讀者根據背景知識和上下文構建語境假設,進而推知“郵票”實際上指詩人幼年求學,母子分離,借書信以慰別情;“船票”則指詩人成年后告別新婚妻子,離鄉背井,天各一方。“郵票”“船票”作為書信往來和乘船離家的顯著標志,因此,又可視為轉喻。年少時的一枚郵票,青年時的一張船票,都寄寓了游子綿長的思鄉之情。讀者通過聯想認知建立概念之間的聯系,并獲得一系列體現其詩學效果的弱隱含,從而增強轉喻表達的修辭效果。
傳統修辭學對轉喻的認識主要停留在語言表達的形式層面上,忽視了轉喻的認知和語用維度,轉喻替代觀并未真實反映出轉喻涉及的認知過程和認知機制。認知語言學致力于探討語言顯性的形式與語義的深層認知機理,試圖闡明概念語義之間的激活與通達過程。然而,轉喻作為溝通修辭與語言認知研究的一座橋梁,不應只是把傳統修辭學中的轉喻視作認知研究的起點,還應該把轉喻修辭作為一個研究的目標和方向。本研究表明,認知語言學與語用學存在互補性,利用最新的認知語用學研究成果,有利于深入探討轉喻的修辭功能,揭示轉喻修辭效力產生的認知語用動因、理解機制和影響因素,為傳統修辭格的進一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參 考 文 獻]
[1]陳望道.修辭學發凡[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2]Lodge, D.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79.
[3]陸儉明.隱喻、轉喻散議[J].外國語,2009(1).
[4]Gibbs, R. W,The Poetics of Mind: Figurative Thought,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M]. Cambridge: CUP, 1994.
[5]Thornburg, L. & Panther, K-U. Speech act metonymy[C]//In Liebert, W. A. et al. (eds.), Discourse and Perspectiv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amins, 1997.
[6]Jakobson, R,The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Poles[C]//In R. Jakobson& M. Halle (eds.).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 The Hague: Mouton Press,1956.
[7]Warren, B,An alternative account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ferential metonymy and metaphor[C]//In Dirven, R. &Prings, R.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Gruyter, 2002.
[8]Langacker, R,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M]. Berlin/New York: Moulton de Gruyter, 1999.
[9]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0]Panther, K-U & L. Thornburg.The role of conceptual metonymy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J].Metaphorik.De, 2004(6).
[11]Sperber, D. &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lackwell, 1995.
(作者系肇慶學院教授,語言學博士)
[責任編輯 陳 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