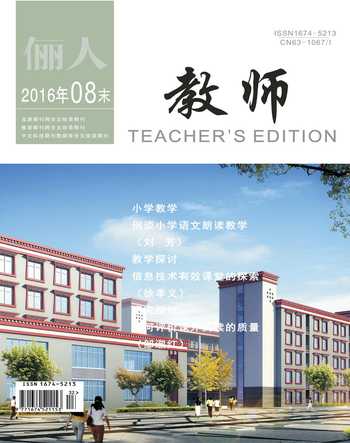論《野草》語言的曲折美
曾書婷
【摘要】作為魯迅的唯一一本曲折幽晦的散文詩集,《野草》的語言中蘊藏著引人入勝的曲折美。魯迅在創作中運用含蓄委婉的措辭構建出散文詩集《野草》曲折深沉,而又洋溢著動人詩情美的語言。這一種曲折筆致,服從于魯迅的抒情需要的同時,也是散文詩這種體裁自身所具備的特性。
【關鍵詞】《野草》 曲折美 含蓄委婉
一、前言
《野草》作為魯迅唯一一部散文詩集,以曲折幽晦的象征表達了魯迅內心世界的苦悶與對現實社會的抗爭。這部散文詩集中,有著含蓄委婉的措辭,矛盾對立的悖論以及反復運用連詞“然而”造成的曲折效果。因此讀《野草》這一部散文詩集,讀者往往會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這一部詩集的語言很美。這種語言的美感就是曲折之美。
誠然,曲折的筆致使得《野草》獲得了“藝術的高度優美性”,但魯迅創作《野草》,其目標的閱讀受眾是群眾,而曲折的筆致往往會加大其散文詩中思想內容傳達的難度,那為何他仍選擇用這樣曲折內斂的語言進行表達呢?筆者認為原因有三,一是魯迅本身創作偏向、二是他在特殊時期抒發感情的需要,三是《野草》作為散文詩集這種體裁的要求。
魯迅曾批評過清末譴責小說的語言,認為這些作品的語言最大的毛病就是“辭氣浮露,筆無藏鋒”,即是指這些作品的語言都過于直白而缺少含蓄曲折的筆致。魯迅不僅在文學批評中表達自己的這一觀點,他在給李霽野的一封信里,也表露過自己對作品語言曲折含蓄的偏向。魯迅在信中曾指出《生活!》一篇小說的結尾一句話這喊聲里似乎有著雙關的意義不夠含蓄。魯迅是這樣解釋的:“我以為這‘雙關二字,將全文的意義說得太清楚了,所有蘊蓄,有被其打破之慮。我想將它改為‘含著別樣或‘含著幾樣。”魯迅在這里指出的是小說,然而根據詩的特性,其語言也許更應要做到曲折含蓄。因此,在《野草》創作中,魯迅力避“辭氣浮露”的弊病,力求在含蓄曲折的語言中包含更深的詩意。正是這種要求,使得《野草》這部散文詩集的筆致曲折而含蓄。
委婉的措辭在《野草》中可以說是隨處可見,如《題辭》中對“充實與含蓄”的表達,又如《秋夜》中對兩棵棗樹的描繪。魯迅,正是采用這種不直陳本義,而用委婉之詞烘托或暗示以使人細細揣摩的措辭,達到《野草》曲折筆致的構建。
魯迅在《二心集?〈野草〉英文譯本序》中說:“因為那時難于直說, 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為什么難以直說呢?不直說,魯迅又采取了何種方式去說呢?
魯迅的難以直說,實際上是因為他在《野草》中所蘊含的自身哲學的不易說,因為無言以對,言不能盡意,“思到深處是孤獨”的語言困境,讓魯迅在創作野草時不得不使用曲折含蓄的語言。然而,魯迅并沒有選擇放棄表達自己“哲學”思想與抒發情感的創作。“這樣一位認真的藝術家是不會像當時的青年作家那樣直抒自己受挫折的感情的,他必須找到能夠包容他哲學沉思的適當形式,必須構建其適合這一目的的語言。”認真的魯迅,在創作《野草》的過程中,選擇了曲折的措辭,構建出達到能夠包容他哲學沉思與思想情感的語言。
《野草》中散文詩,有許多迂回措辭的存在。在魯迅開始創作《野草》第一篇散文詩《秋夜》時,就使用了曲折的語言表達: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愿意驚動睡著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著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秋夜》中的“我”,在后園中看到了棗樹勝利地戰勝了夜空:天空不安得仿佛想離開人間,月亮也窘得發白地暗暗躲避,連那夜游的惡鳥也飛走了。面對棗樹的勝利,“我”給予快慰的笑聲:“我忽然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笑聲明明是由“我”發出的,然而這笑聲在魯迅的筆下卻被描寫成是從別處發出的。接著,魯迅并沒有選擇進行解釋這“吃吃地”笑聲是從我嘴里發出的,反而是轉寫笑聲之輕與周圍之靜,然后才為讀者揭示這笑聲的來處:“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里。”在迂回地描寫了笑聲以后,魯迅并沒有選擇為讀者揭示笑聲來源,反而是寫這笑聲引起了四周的應和,這樣的描寫,以動襯靜地表現出周圍環境的沉寂,同時又委婉地表達出魯迅孤軍奮戰的心跡。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曲折的筆致,一方面增強了文章詩意抒情的氣氛,取得了比直接描寫“我”發出笑聲所不可能達到的藝術效果;另一方面,也滿足了魯迅抒發自己孤軍奮戰心情、以及對“棗樹”所象征的革命戰士不屈戰斗精神的頌贊的情感抒發需要。
《野草》中如《希望》一文的絕望與希望之間的相互徘徊而最終表達希望之意,《題辭》中的空虛與充實的不斷轉換蘊含作者深沉情懷……都是魯迅曲折筆致的體現。有人將這種曲折的詩的表現方法看作是惡趣味的敗筆,然而這一看法,是對這種曲折委婉的語言藝術產生隔閡。實際上,魯迅采用委婉的措辭,更多是為了滿足抒情的需要。這種委婉的措辭,使《野草》的語言達到了韻致含蓄,筆有藏鋒的效果。迂回曲折的作品語言讓讀者不自覺地停留下來,用更多的時間進行思考品讀這些語句,達到了與作者一同完成詩歌形象與內涵的創造,從而體味到深藏這曲折語言背后的無盡情懷。
《野草》這一部散文詩集,曾被馮雪峰評價是具有“藝術的高度優美性”的,而構成它“藝術的高度優美性”這一特性的一個重要表現就為語言美中的曲折筆致。具有中國古典詩歌特性的曲折筆致為《野草》帶來了委婉而詩情的語言美。象征手法的運用,帶來了寓情于景的藝術效果,隱喻而含蓄意象背后傳達出作者的背后的思想蘊含。這樣的一種含蓄曲折的語言,一方面能夠滿足詩歌體裁所要求的韻致含蓄,達到與平鋪直敘所不同的“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同時也是服從于作者抒情的需要,使讀者閱讀過程中感受到魯迅生命哲學與思想情感的弦外音、言外意。
【參考文獻】
[1]馮雪峰.《回憶魯迅》[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
[2]魯迅.《魯迅書信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
[3]孫玉石.《<野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4]張夢陽:《中國魯迅學通史(下卷)》[M].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
[5]何紹基:《與汪菊士論詩》,《東洲草堂文鈔》卷五[M].臺灣:文海出版社,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