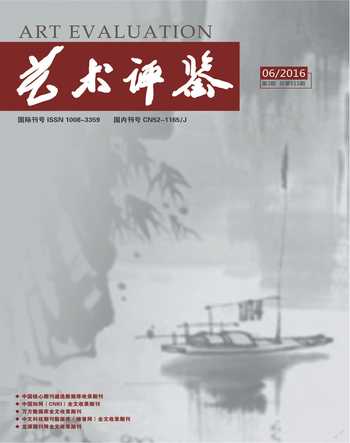論鋼琴語言的民族化
韓冬
摘要:如果說民族語言的鋼琴化是由內而外的融合過程;那么,鋼琴語言的民族化,則是一個由外而內的融合過程,是在業已存在的歐洲鋼琴語言的基礎上,在與中華民族傳統的音樂語言與技法、音樂風格與審美、音樂文化與歷史等各方面,由初始階段的水土不服,到入鄉隨俗融合發展的局面,既體現了中華文化博大的包容性,也體現了鋼琴語言廣泛的適應性。因而,鋼琴語言的民族化成為本文的課題。
關鍵詞:鋼琴語言 民族化
鋼琴被譽為“樂器之王”,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廣泛和普遍的發展。鋼琴自傳入中國的百年間,同樣伴隨文化的興衰而幾度沉浮。如果說民族語言的鋼琴化是由內而外的融合過程;那么,鋼琴語言的民族化,則是一個由外而內的融合過程,鋼琴是在業已存在的歐洲鋼琴語言的基礎上,在與中華民族傳統的音樂語言與技法、音樂風格與審美、音樂文化與歷史等各方面,由初始階段的水土不服,到入鄉隨俗融合發展的局面,既體現了中華文化博大的包容性,也體現了鋼琴語言廣泛的適應性。因而,鋼琴語言的民族化成為本文的課題。
一、鋼琴語言
鋼琴語言是通過鋼琴來陳述和表達音樂的特有語言體系,其中既有一般的、互通的共性語言,更有只能用于鋼琴演奏,而在其他樂器上無法演奏的個性語言,甚至包括挑戰鋼琴極限的極端個性化語言。
(一)鋼琴語言的內涵
鋼琴語言就是鋼琴的表達方式,其中包括思維方式和不同時代、風格、流派、共性、個性的呈現方式。鋼琴音樂的創作,就是以這些語言為基礎和起點的延伸和發展。
1.器樂思維的共性:鋼琴語言中,包括器樂思維與寫作的共性材料與方法。如,主題材料、結構布局、和聲調性組織、復調技術與應用等技術儲備,以及音樂素材的獲取,構思寫作的方式等,與其他器樂作品寫作相同的,均需要在寫作之前就具備的共性部分。
2.鋼琴語言的個性:是對鋼琴性能應用和潛能開發的個性化呈現。在鋼琴織體語言的掌握、積累與創造性運用過程中,需針對某一首作品或某一類作品專門設計和應用。從世界鋼琴音樂的創作觀察發現,身兼鋼琴家與作曲家的肖邦、李斯特、拉赫瑪尼諾夫等,在鋼琴音樂創作中對鋼琴語言個性化方面的貢獻尤為突出。中國鋼琴作品中鋼琴語言民族化、個性化,就屬于這一內容,同樣呼喚著這類人才的涌現。
3.風格流派的特性:在世界鋼琴音樂中,不同國家、地區、作曲家等,均有著明顯的風格流派特征。這正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由音樂創作所主導的必然產物。無論從歐洲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至巴洛克時期、古典時期、浪漫時期、近現代時期的鋼琴音樂風格,以及爵士鋼琴的興起與風靡,在使鋼琴不斷煥發出活力與生命力的同時,風格更疊,交相輝映,異彩分呈。中國鋼琴同樣基于中國特有的文化進行發展,因而終將成為影響世界的風格與流派之一。
4.渾然天成的靈性:是指創作過程中將智慧與情感,技術與藝術,偶然與必然在特定時機相碰撞和巧遇所產生的可遇不可求的,非程式化套路化的輕車熟路所獲得的成果,是任何人都無法復制的珍品。正是這種獨一無二,才能造就鋼琴音樂的獨特和永恒。中國鋼琴音樂在歷經模仿、改編、移植后,必將通過超越前人的非凡創造,實現自身的發展。
(二)鋼琴語言的類型
由于鋼琴的構造與性能與鋼琴演奏的技術規范,使鋼琴的語言類型、織體類型,經過前輩大師創造性的開發而趨于定型。成為現行的鋼琴織體結構原則、規律和具體形態。
1.流動型:是最具鋼琴特點的語言類型,無論任何風格流派與作家作品,都是必不可少的語言類型。所區別的是流動的速度與節奏方面,流動順序與方式的改變,和聲與調性、和弦外音、音響結構組織變化所導致的流動形態各異等。這其中,如何建立中國風格的流動形態,就成為鋼琴語言民族化的重要途徑。
2.織體型:包括單一織體與復合織體兩類。單一織體的個性化空間相對狹小,需要結合中國音樂語言進行創造。除此之外,更多見的是不同織體的復合。這就需要通過不同音區上的不同織體,編織出鋼琴織體的特殊形態。由于每層織體均具有不同的變數,導致復合起來的織體形態變化無窮。這說明織體型鋼琴語言是鋼琴化特點的重要部分,也是鋼琴語言民族化的重要內容。
3.復調型:是在鋼琴上彈奏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旋律所構成的鋼琴語言類型。它區別于織體的復制特點,是一種旋律之間的重復、變化、對比、對抗關系。這是鋼琴作為多聲部樂器所具有的超越所有單聲部獨奏樂器的優勢。復調型織體又區別于復調寫作,它較之嚴格的復調作品更靈活,使鋼琴織體獲得了更多獨立性、層次性與表現力。
4.復合型:是指將上述旋律與復調,單一織體與多層織體通過縱橫組織而復合的織體類型。這不僅使鋼琴的表現力大幅提升,同時也增加了演奏的效果與技術難度,并成為鋼琴音樂創作的主要陳述方式與呈現方式和鋼琴音樂民族化的必經之路。1934年賀綠汀的《搖籃曲》就通過旋律層、節奏和聲層、流動織體層、低音層構成了中國鋼琴音樂早期民族化的成功嘗試。
(三)鋼琴語言的拓展
鋼琴語言的拓展通常可以通過借鑒樂隊思維與組織方式或其他方式進行,但首先要考慮到鋼琴性能與潛能的可能性,在鋼琴演奏技術的極限范圍的有效空間內進行。
1.縱向拓展:是同類或不同類鋼琴織體通過音區的變化與擴大進行的拓展。如汪立三1979年的《濤聲》開始處,就將鋼琴音域的縱向拓展瞬間從小字四組b到大字二組A,幾乎到達極限。這首描寫唐朝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宣揚佛法的作品中,表現了堅忍不拔的氣概和驚心動魄的震撼。
2.橫向拓展:這種拓展需要先后順序的上行或下行進行,這就需要跑動或移動的一種呈階梯式或是斜線式的拓展狀態。其移動的速度與節奏的密度決定了拓展的幅度。如朱踐耳1955年的《流水》主要運用了這種拓展方式。作品既受古琴曲《流水》影響,又以民歌《小河淌水》為主題,并通過織體的橫向拓展,將最初的小溪潺潺,逐漸發展至一條起伏澎湃的大河。
3.縱橫交替拓展:是指上述兩種拓展方法通過相互交替進行的方式進行陳述,構成縱橫交替的方式。這就提供了鋼琴語言拓展的思路與空間,這種寫作技術在鋼琴語言民族化的過程中,同樣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如朱工一1952年的《A小調序曲——小溪》32-42小節,就是這種方式。
4.縱橫復合拓展:是指將縱向與橫向拓展同時陳述的一種方法,這就將鋼琴語言完全置于開放的空間。這種拓展的思路與技術,需要更高的專業技術理論與創新能力的支撐。如陳其綱2000-2004年的《京劇瞬間》無論為作曲家、演奏家,還是鋼琴教學與欣賞、傳播,都具有挑戰性。其題材的選擇與鋼琴語言的民族化程度更是值得稱道。
(四)鋼琴語言的含量種類
由于音樂表現的需要,并不是每首作品都一定要達到高難度的技術極限,這就需要對樂曲的含量進行控制與合理搭配,使之能夠運用得恰如其分。
1.技術含量:技術程度與難度通常要根據需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還要與相關的其他含量和指標相匹配。如技術程度、類型,理解能力、表現能力等。但昭義1973年的民歌主題變奏曲《放牛娃的故事》是為兒童所作的,其中自始至終避免八度的使用,僅此就應理解為技術含量的控制。
2.藝術含量:屬于音樂表現范疇,在鋼琴程度的不同階段,學習者對音樂內容的理解能力與表現能力,正同前所述需要與技術程度、彈奏能力和水平、風格把握、個性特色相統一,與音樂修養、文化程度相匹配。在寫作中同樣需要進行把握和控制。
3.風格含量:是指音樂風格的定向、定位和把握能力,更具有人文精神與情懷。在鋼琴語言中,風格含量可通過多種側面進行表達,如時代、地區、作曲家、調性和聲、旋律節奏、織體形態等,要做到風格鮮明、統一而富有特色,就不僅需要進行準確把握與控制,更需要開發與創造。
4.個性含量:個性化創新在與鋼琴語言的民族化、國際化互通的基礎上把握含量,既有鮮明個性,又具有傳播的可能性與可行性。既要彰顯個性獨樹一幟,又要避免由于獵奇和對某些新技法食之不化所造成的不知所云。
二、鋼琴語言的民族化
鋼琴語言的民族化是由外而內的民族化途徑,它與民族語言鋼琴化的由內而外,恰好構成了兩條路線的終極目的殊途同歸。這對于正確理解鋼琴音樂民族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民族化的內涵
是指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吸取外來文化先進成果的基礎上,建設、充實和發展中國文化的過程。鋼琴音樂的民族化,需要通過鋼琴語言的民族化才能實現。
1.民族意識的覺悟:是鋼琴語言民族化過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標志。中國鋼琴音樂的民族化,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從宏觀到微觀,從理念到行動都走出誤區和局限,走上自尊、自強、自信的道路。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實現自立于世界民族音樂文化之林的目的。
2.民族語言的應用:就是運用民族的音樂元素與外來文化相融合,創作出既具有中國音樂文化內涵,又符合鋼琴藝術的表現規律的中國鋼琴音樂。這就需要把握音樂創作的核心技術,將豐富多彩的民族語言通過作曲家的個性化創造化為中國鋼琴音樂。
3.民族精神的貫穿:民族精神是長期歷史進程和積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識、性格、文化、價值觀念和價值追求等共同特質,是一個民族凝聚力、生命力和創造力的集中體現。中華民族的創造精神必須通過鋼琴語言民族化的技術轉換與創新融合所構成的有效載體中才能最終實現。
4.民族神韻的核心:鋼琴語言民族化的核心不僅僅是對外在民族樂器等音響模擬的形似,而是注重音樂內在的神韻,以及內心世界對真善美的追求和對中華文化精髓的切實理解和感受。通過內在韻味的含蓄與空靈,對音樂感悟的由內而外,去探尋中國音樂的最高境界。
(二)民族化的滲透
中國鋼琴語言的民族化所經過的漫長的入鄉隨俗的過程,說明文化的融合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的對話,需要相互磨合與滲透,才能最終為我所用。
1.引進:是將外來的東西,通常是指先進的技術或理念引入并學習和消化的過程,在中國鋼琴音樂發展歷程中,是屬于學習的起步階段。在早期中國鋼琴作品中,甚至二十世紀某些無調性作品中,幾乎都存在與中國音樂文化相距甚遠的印象,這說明文化藝術的引進需要消化才能發揮作用。
2.附加:在民族化之初,是一種附加式的外科手術。在鋼琴語言民族化的早期,通過和弦結構上改造,如附加音、替換音、換加音;大小調式的五聲化,如削弱功能性、增加色彩性、五聲性進行等。使得引進與消化成為這一時期的焦點,在早期鋼琴作品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3.改良:是指去掉引進技術中與中國音樂風格與審美有不適和沖突的部分,使之更適合音響風格與音樂表現的需要。這是一種在原有框架下的調整、修訂和補充。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在鋼琴音樂民族化中收到明顯的效果。
4.平衡:是將中西音樂理論與應用合二為一,并在此基礎上達到平衡的臨界點。在這種結合的早期實踐中,新疆風格的作品比例較大。如桑桐1947年創作的《在那遙遠的地方》,丁善德1950、1955年創作的《第一、第二新疆舞曲》,石夫1957年創作的《第一新疆組曲》,郭志鴻1958年創作的《新疆舞曲》等等。僅在二十世紀50年代前的實踐,就說明了新疆音樂的語言特征具有鋼琴語言民族化的優勢與捷徑。
(三)民族化的融合
是指不同物質通過熔化而合融成一體,是一種從事物內部合二為一的結果。來自歐洲的鋼琴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在相融合中,必將誕生嶄新的中國鋼琴音樂文化。
1.適應:在融合的前提下,中西音樂文化經過在中國百年的消化,逐漸找到技法服從內容,內容決定技法的共識,最早在賀綠汀1934年創作的《牧童短笛》中率先實現,較之1915年趙元任的《花八板與湘江浪》《和平進行曲》相比,完全是里程碑式的劃時代的中國鋼琴音樂作品,時至今日,依然是歷久彌新。
2.默認:是指在中西鋼琴音樂融合過程中,一種既無明顯不適,也無明顯融合;既無明顯沖突,也無明顯障礙的中性風格。這點在前述新疆風格鋼琴作品中即有所體現,而在應用二十世紀作曲技法創作的中國現代作品中,這種情況則更為多見。
3.結合:將西方鋼琴音樂文化與中國民族音樂傳統由外而內的不斷結合,從中華民族音韻中萃取精華,從中提煉出中國鋼琴音樂的新語言。在此基礎上,伴隨世界音樂文化發展的步伐,創作出具有濃郁中國民族風格和超越傳統音樂范式的優秀中國鋼琴作品。
4.融會:是一種真正的中西文化在新的交流與碰撞中,再經過融會而達到合二為一的結果。這就使來自歐洲的鋼琴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相融合中,創造了嶄新的中國鋼琴音樂文化。如陳怡1984年以廣西侗族素材創作的《多耶》,權吉浩1984年以朝鮮族特有的音樂元素創作的《長短的組合》等。這類作品更具有中國鋼琴音樂的國際化視野。
(四)民族化的自主創新
是一種以中華文化主體為文化認同基礎的,以中華母語為核心的最高境界。在這里一切音樂語言和技術,都成為表達思想、情感、內容的工具。
1.理念:樹立以中華文化為中心的理念,將中國鋼琴音樂的創作置于世界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視中華音樂文化為世界音樂文化的一元,并以雙向交流為舞臺,在互動互惠中謀求自身的發展。
2.方法:對于鋼琴音樂的構思與寫作,是以鋼琴這件樂器為工具,從其本身的特性出發,創作出符合鋼琴藝術特點,表達作曲家真情實感、技術水準、藝術追求與個性特色的,并非刻意和標簽化的中國鋼琴音樂作品。
3.語言:隨著時代的更疊、觀念的更新、技術的更替,盡管總的趨勢是不斷向前的,然而,對于人而言,必定受自身和自然的局限性,只能是感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因此,不斷求新、求變才是發展主題。
4.靈魂:一切藝術的靈魂都是源自文化。文化的結晶是文明,鋼琴音樂就是文化長河中的文明的浪花。當鋼琴融入中國文化之后,在一百年間漫長的入鄉隨俗的過程中,已經取得了突破,已經有了她的靈魂,更有了她的體魄。以此為核心構成真正的中國鋼琴文化,并成為世界鋼琴文化中當之無愧的一元。
三、結語
綜上所述,在鋼琴語言民族化的過程中,不僅與民族語言鋼琴化構成殊途同歸,同時也為鋼琴音樂的中國化與國際化探索新思路,尋求新途徑。在鋼琴語言民族化過程中:
首先,努力掌握鋼琴語言的特點與規律,是鋼琴語言民族化的技術基礎、語言基礎和表達基礎。只有夯實這一基礎,才能真正找到實現鋼琴音樂的民族化的出發點。
其次,努力掌握作曲技法的傳統基礎、民族基礎和現代基礎,在構成鋼琴音樂語言的物質基礎的前提下,提高中國鋼琴音樂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與應用能力。
第三,超越民族音樂元素運用中,對外在音響的模擬、依附和依賴的思維方式與審美定勢,注重內在聲韻、情韻與神韻的表達,使中華文化的璀璨在世界舞臺上綻放。
因此,鋼琴語言的民族化不僅需要中國作曲家的努力,更需要相關藝術鏈的鋼琴教育與教學、鋼琴音樂的傳播與普及、鋼琴文化發展的氛圍與氣候,才能使中國鋼琴語言民族化的道路越走越亮堂。
參考文獻:
[1]童道錦,蒲方編選.百花爭艷——中華鋼琴100年[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5.
[2]李海虹,楊韻琳.中國鋼琴獨奏作品百年經典(1913-2013)[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