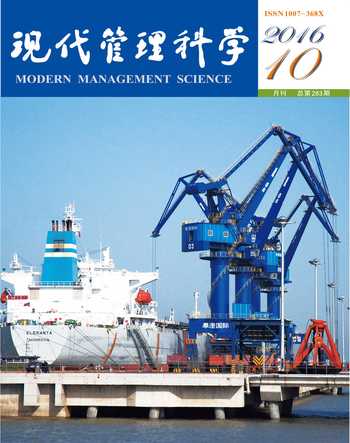經濟“新常態”下我國區域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轉型研究
蔣先玲 趙一林

摘要:中國經濟“新常態”面臨過剩產能消耗緩慢、市場機制運行不暢以及出口導向型經濟難持續等諸多挑戰,尤其是區域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導致經濟結構轉型困難。文章對29個省、市、自治區的經濟結構進行回歸分析和聚類分析,發現城市化水平對區域經濟的貢獻度最高,相關系數高達0.940 3,其次是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東南沿海地區普遍進入工業化高級階段(Chenery第4階段),城市化水平較高,中西部地區多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Chenery第3階段),民營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此,建議加大對科技型、創新性民營企業的政策支持,實現由政府引導為主、社會資本為輔的產業結構轉型引導體系,促進區域資源整合和產業結構升級。
關鍵詞:經濟新常態;結構轉型;區域經濟增長;供給側改革
一、 引言
自2014年經濟“新常態”概念提出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雙去”(去產能、去杠桿)疊加、“三低”(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并存的“新常態”,宏觀經濟形勢不容樂觀,表現為生產成本不斷上升、資本邊際效率下降、市場機制運行不暢,出口導向型增長難以持續等問題。2015年我國GDP同比增長6.9%,經濟增速整體處在回落后趨穩的弱勢狀態,總量增速彈性很小,傳統產業尚未找到新的增長模式,尤其是區域經濟發展失衡,從而導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困難。
從長期經濟發展來看,“新常態”經濟應該最終表現為區域產業經濟圈、創新型企業成為經濟主要推動力、傳統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發展出現新的增長點,傳統產業形成可持續發展模式等。然而,就目前中國經濟形勢而言,尋找新常態的“長征”才剛剛開始。宏觀經濟處于增速換擋期,勞動力人口占比不斷下降,資本成本逐步上升,人力資本及產業附加值增長緩慢,全要素生產率逐漸下降,并且傳統投資領域大多面臨產能過剩,發展空間有限。解決我國區域經濟失衡、促進經濟結構轉型是促進“去產能、去杠桿”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因此,本文基于產業結構轉型視角,對“新常態”下中國區域經濟結構差異化進行分析,探究優化區域產業結構升級和資源配置的有效途徑。
二、 文獻綜述
從已有文獻來看,國內學者大多對“新常態”的特征、經濟表現、形成機制等進行研究,但是,對“新常態”背景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及結構轉型的研究,還缺乏實證數據分析的支持。如李揚、張曉晶(2015)從產業周期視角,研究新常態經濟面臨的問題,并建議通過提高創新驅動力、調整產業結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經濟效率的提高。金碚(2015)指出要形成“公平-效率”的“新常態”關系,促進經濟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動”向“創新驅動”發展。劉偉和蘇劍(2014)建議采取以供給管理為主、需求管理為輔的定向“微刺激”政策體系,促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的實現。齊建國等(2015)指出,在經濟增速換擋過程中促進消費、投資、進出口的“三駕馬車”平穩轉型長。此外,陳彥斌(2014)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微刺激”政策效果已經出現“邊際遞減”效用,應該加強對供給側改革的支持力度,優化產能配置,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此外,國內外學者圍繞產業結構差異、溢出效應、增長效應及作用路徑等深入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存在一定聯系。如Xiu等(2014)證實了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存在滯后性,城鄉要素錯配阻礙了城鄉產業結構調整。干春暉等(2011)指出產業結構升級帶來的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是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侯新爍等(2013)通過測算經濟結構轉變的空間溢出效應,分析產業結構轉型對經濟增速的影響,并建議統籌考慮周邊地區的發展路徑,實現“區域板塊”的經濟增長。袁江和張成思(2009)分析中國的經濟周期與經濟結構的關系,發現經濟總量擴張伴隨著結構轉變。陳曉光和龔六堂(2005)則證實了中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轉變之間的關系類似于“駝峰型”。項俊波(2008)將區域經濟結構、投資、消費、金融、國際收支等指標納入中國經濟結構失衡指數,并用宏觀數據進行論證。由此看出,新常態下我國區域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文獻仍處于空白。因此,本文將通過多元回歸分析、聚類分析法對我國產業結構失衡進行研究,為區域經濟格局轉型提供借鑒。
三、 實證檢驗
1. 樣本來源與選取。本文基于產業結構轉型視角,選取WIND數據庫中2015年我國29個省及直轄市的宏觀經濟數據,將影響因素設定為第二產業占比(x1)、第三產業占比(x2)、城市化程度(城市人口占該省份總人口的比重,記為x3)以及民營經濟發展水平(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總產值占該省份工業總產值比重,記為x4),建立經濟發展函數為,其中Y=f(x1、x2、x3、x4)為該省份人均GDP。
2. 偏相關性分析。我們對人均GDP、x1、x2、x3、x4進行偏相關性分析,得到各個指標間的偏相關系數:(1)人均GDP和第二產業占比、第三產業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系數分別是-0.131 9(P=0.495 2)、0.639 0(P=0.000 2)、0.940 3(P=0.000)、0.265 7(P=0.163 6),人均GDP和第三產業占比及城市化程度具有顯著較強的正相關性;(2)第二產業占比和第三產業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系數是-0.576 1(P=0.001 1)、-0.290 9(P=0.125 8)、0.398 7(P=0.032 2);(3)第三產業和城市化程度、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系數分別是0.695 6(P=0.000 0)、-0.192 5(P=0.317 2);(4)城市化程度和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系數是0.179 2(P=0.352 4)。
由此看出,城市化程度和人均GDP相關系數高達0.940 3,城市化進程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刺激作用明顯;第二產業比重和第三產業比重、民營經濟發展程度也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城市化程度受人均GDP、第三產業發展程度影響較高,表現為顯著的正偏相關系數;但是,民營經濟發展程度目前主要依賴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對于民營經濟拉動作用不足。
3. 回歸分析。為了進一步探究所選宏觀經濟指標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我們對人均GDP及自變量x1、x2、x3、x4進行對數化處理后,并進行回歸分析:
LnPGDP=3.101 4+0.2733 2x1+0.204 4x2+1.734 2x3+0.289 8x4
(16.29) (2.39) (1.03) (10.27) (1.26)
R2=0.910 1,F=60.71。
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方程擬合程度較高(R2=0.910 1),回歸顯著性較好,在影響人均GDP的宏觀經濟因素中,城市化水平的貢獻度最高,其次分別是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這也說明我國區域經濟結構失衡、民營經濟對經濟貢獻率不足。
4. 聚類分析。根據Hollis B. Chenery(1986)提出的工業化階段理論,對工業經濟發展階段劃分如下:準工業化階段(初級產品生產階段)、工業化階段(工業化初級階段、工業化中級階段、工業化高級階段)、后工業化階段(發達經濟初級階段、發達經濟高級階段)。由此,根據x1、x2、x3、x4四個宏觀指標,對我國29個樣本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現狀進行聚類分析(采用軟件為STATA),以便區分不同經濟結構類型(見表1),分析結果如下。

(1)第I類包括我國三大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人均GDP都在10萬元以上,已經進入發達經濟初級階段(Chenery第5階段)。從產業結構來看,3個直轄市第一產業占比僅在1%左右,遠遠低于其它省份水平;第三產業發展迅速,其規模已遠遠超過第二產業,尤其是北京的第三產業占比甚至高達79.7%。同時,3個直轄市的城市化程度普遍較高,位于82.3%~89.6%之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但是,民營經濟發展水平不足,以北京為例,其民營經濟發展水平占比為48.7%,不及江浙地區。
(2)第II類包括浙江和江蘇。作為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省份,該兩省人均GDP在2015年達到7.8萬元~8.8萬元,進入了工業化高級階段(Chenery第4階段)。從產業結構來看,第一產業占比很小,僅為5%左右;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程度類似,所占比重均在45%左右,且第三產業占比呈現增長態勢。另外,城市化程度遠遠低于第I聚類,處于65%左右,達到中等國家水平。但是,浙江和江蘇兩省的民營經濟發展程度是全國最高水平,在72%~74%之間,對經濟貢獻率很高,是該省份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3)第III聚類包括福建、廣東、遼寧和山東。這些省份正處于從工業化中級階段(Chenery第3階段)邁向工業化高級階段(Chenery第4階段)的過程中,是我國重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人均GDP在6.4萬元~6.3萬元間,第二產業仍然處于核心地位,第三產業也具有了相當的比重。但是,城市化水平較低,在46.1%~52.8%之間。民營企業發展也十分迅速,有望成為該聚類新的增長動力。
(4)第IV聚類包括重慶、吉林和湖北,集中于我國中西部內陸地區,人均GDP在5.1萬元~5.3萬元之間,均處于Chenery第3階段,即工業化中級階段。第三產業發展較為緩慢,尤其是吉林省第三產業比重僅為37.4%、民營經濟占比為28.5%。該區域的城市化程度較低,民營經濟對經濟發展有一定的貢獻。但是第三產業發展不足、民營經濟占比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這些省份的經濟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速的提高。
(5)第V聚類主要包括我國的中西部省份,其中西部省份4個,中部省份1個,人均GDP在4.0萬元~4.8萬元之間,尚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Chenery第3階段)。第一產業比重在8.6%~23.1%左右,尤其是海南的第一產業占比高達23.1%,該比重在全國僅次于黑龍江的46.4%;第二產業對區域經濟貢獻率較高,內蒙古及陜西均超過50%。此外,民營經濟對經濟貢獻率不足,嚴重阻礙了經濟結構的轉型,經濟發展欠缺新增長點,城市化發展水平較低。
(6)第IV聚類包括我國7個東中部省份,包括黑龍江、河南等。這些地區人均GDP在3.5萬元~3.9萬元之間,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Chenery第3階段),且第一產業占比較高,尤其是作為東部老工業化地區的黑龍江,第一產業占比高達46.4%,是全國最高值;第二產業是該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除黑龍江占比20.5%外,其余的第二產業普遍占比在40.1%~51.5%之間;民營經濟發展不足,城市化進程處于中西部的平均水平45%左右。總體上,這些省份經濟發展水平較沿海地區低,且私營企業發展停滯,經濟仍以重工業為主,結構化轉型難度較高。
(7)第VII聚類包括貴州、云南和甘肅,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人均GDP僅有2.6萬元~3.0萬元左右,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的起步期。第一產業占比普遍高于10%,第三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第一、二、三產業結構在15∶55∶30左右,工業經濟較為落后。同時城市化水平較低,民營企業占比僅在26.6%~32.6%左右,總體上,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工業化水平有待提高。
四、 結論及建議
本文通過對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人均GDP、第二產業占比、第三產業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營經濟發展程度進行回歸分析和聚類分析,得到主要結論如下。
(1)偏相關性結果顯示:城市化程度和人均GDP相關系數高達0.940 3,城市化進程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刺激作用明顯;第二、第三產業、民營經濟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相關性;城市化程度受人均GDP、第三產業影響較高,但民營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刺激作用不足。
(2)多元回歸結果顯示:在刺激區域經濟發展上,城市化水平的貢獻度最高,其次分別是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第二產業及第三產業。
(3)聚類分析顯示:北京、上海、天津已經邁入發達經濟初級階段(Chenery第5階段),城市化水平較高;浙江和江蘇是工業化高級階段(Chenery第4階段),民營經濟發展程度最高;其余省份多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Chenery第3階段);貴州、云南和甘肅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的起步期,普遍以第二產業為主,民營經濟發展水平較低。
基于以上分析結果,對當前“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產業結果轉型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發揮產業結構優化在改善區域經濟失衡、刺激經濟增長中的主導作用。優化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是區域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同時,建議完善中西部地區的生產力布局,依照當地資源優勢建立支柱產業,推動民間資本對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的拉動作用。
第二,放寬對科技型、創新性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條件,加大優惠政策的鼓勵力度,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便利的融資渠道和產業引導,特別要鼓勵民企通過聯營、參股、控股、特許經營等方式聯合國企,形成混合型企業集團。同時,鼓勵社會資本如VC(風險投資)、PE(私募股權)的投資,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融資渠道。
第三,以改善供給結構為重點,促進社會資源從勞動密集型產業流向知識、資本密集型產業,加快區域資源整合。在技術要素供給方面,提高企業的科研創新成果的轉化和研發能力;在資金要素方面,實現由政府引導為主、社會資本為輔的產業引導體系,促進民間資本對產業升級的帶動,加快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
參考文獻:
[1] 陳曉光,龔六堂.經濟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J].經濟學:季刊,2005,(2):583-604.
[2] 陳彥斌.中國經濟“微刺激”效果及其趨勢評估[J].改革,2014,(7):5-14.
[3] 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1,(5):4-16.
[4] 侯新爍,張宗益,周靖祥.中國經濟結構的增長效應及作用路徑研究[J].世界經濟,2013,(5):88-111.
[5] 金碚.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工業使命[J].中國工業評論,2015,(2):10-14.
[6] 李揚,張曉晶.“新常態”:經濟發展的邏輯與前景[J].經濟研究,2015,(5):4-19.
[7] 劉偉,蘇劍.“新常態”下的中國宏觀調控[J].經濟科學,2014,(4):5-13.
[8] 齊建國,王紅,彭緒庶,等.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內涵和形成機制[J].經濟縱橫,2015,(3).
[9] 秦天程.新常態下影響經濟轉型的制約因素分析[J].當代經濟管理,2015,37(3):34-37.
[10] 項俊波.中國經濟結構失衡問題的分析與思考[J].新華文摘,2009,(1):23-29.
[11] 袁江,張成思.強制性技術變遷、不平衡增長與中國經濟周期模型[J].經濟研究,2009,(12):17-29.
[12] 王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的總體特征研究[D].天津:南開大學學位論文,2010.
作者簡介:蔣先玲(1965-),女,漢族,湖北省潛江市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貨幣銀行、國際金融;趙一林(1991-),女,漢族,山東省臨沂市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公司金融。
收稿日期:2016-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