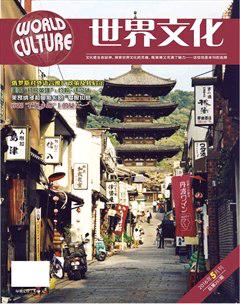何處是邊疆
李歐


“亞利桑那(Arizona)”來自西班牙語“áridazona”,意思是“干燥不毛之地”。這個州,南部大多數地方為沙漠、戈壁、荒漠,不過不是撒哈拉沙漠那樣的沙漠,而是常常被稱為“疏草沙漠”,有稀稀拉拉的仙人掌和季節性的草生長;北部是科羅拉多高原和高山地區。這個州的大多數地方是不“適宜人居住”的,甚至在美國建國后,也長期人煙稀少。它是美國本土最后建立的州,即美國本土最后開發的州。
奇怪的是,近一百年來,亞利桑那州人口卻增長迅速,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長率遠超其他各州。更有意思的是,它的鄰近各州——與墨西哥接壤的各州,如加利福尼亞州、德克薩斯州,人口增長也很快;但與它相比,卻有一個明顯的差異,這些州近幾十年遷徙而來的主流是拉美移民,主要是講西班牙語的墨西哥人,以及中美洲人、南美洲人。西班牙語,幾乎快成為那些州的第二語言。以至于當代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居然為此而擔憂,在他影響極大的《我們是誰》一書中,對于拉美移民的涌入,持嚴厲批評態度,深深憂慮會因此改變美國的特性,會對盎格魯-新教的美國文化核心構成重大威脅,改變已經形成的美國民族性,甚至分裂美國。
亞利桑那州有著目前美國最嚴厲的打擊非法移民的法律,而且也不是拉美移民實現“美國夢”的優質空間,雖然與墨西哥也有著漫長的邊境,不過其迅速增加的人口,同樣主要是“移民”,但卻多是來自美國的中部,甚至東部、北部的盎格魯-撒克遜族裔的白人,已經幾代人都是“遷徙”的美國公民。
這是否是建構美國的“邊疆精神”在暗中發揮作用?這是否是建構了美國的“西進運動”的最后的回響?在美國人的集體無意識中,邊疆荒漠既是文明應該征服的巨獸,又是精神危機時的避難所。亞利桑那州,資源相對貧乏,氣候相對惡劣,似乎沒有什么可吸引人的特性,但卻是美國本土的“最后的邊疆”! 直到1912年,它才建州。確實,很多由美國人 “開拓邊疆”的精神而支撐的大計劃,在亞利桑那州策劃、實施。例如,上個世紀下半紀開始的“索諾蘭沙漠計劃”——對亞利桑那州的南部的索諾蘭沙漠,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和保護,甚至試圖在這個沙漠中建立類似“伊甸園”的群體性的大型建筑。其實,州首府鳳凰城以及亞利桑那州的第二大城市圖森都處于這個沙漠中。
眾所周知,美國并不缺乏“生存空間”,在美國自駕車漫游,美國的地廣人稀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東部曾經的老殖民區和少數幾個大城市的核心區,不要說與歐洲相比,就是比起中國來,也毫無繁華熱鬧之感,就是一個近乎荒涼的“巨大農莊”。適合開發的空間,充裕到可以隨意浪費,有必要去開發沙漠嗎?而且該計劃的重心和目的是“保存開發重要的自然區域,為保護文化和歷史資源提供基礎和服務,以幫助確保我們的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傳統,仍可延續”——這難道是美國人的“憂患意識”?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另一個世界聞名的大工程:“Biosphere Two”——可譯為“第二生物圈”。它的基本構想是當人類移民月球或者火星時,建設一個足以供人類生存的封閉環境。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建,延續至今,有人稱之為是與人類登陸月球相配套的邊疆開拓。科幻電影中已經有這樣的虛構式敘事,為觀眾所熟悉。而在現實中,它結結實實地矗立在亞利桑那州的沙漠里。二十多年來,已經有了重大進展,科學家們全面地觀察了,在人工制造的完全封閉的建筑群環境里,地球上各類生物:人、動物、昆蟲、植物,將怎樣生存,能夠怎樣生存。這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人類最偉大的實驗之一,人類抬頭向前,將會逐漸證實它的重要性。實驗還在繼續,而且已經有了商業價值:旅游景點。
1893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特納在其撰寫的,或許是美國歷史文獻中最負盛名的論文《邊疆在美國歷史中的重要性》中論述道:美國史就是一部向西部邊疆的開拓史,“邊疆精神”構成了美國的民族性。一百年后,在1992年出版的當代美國學者集體撰寫的《構建美國》一書中,作者們仍然宣稱:“美國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西進運動中不斷向西擴張的邊疆。”另一位作者甚至稱“可以把魯濱遜看作是我們共同的祖先”。于是,甚至 “美國與科學的關系看起來總是以探險為中心”。“邊疆精神”仍然是美國精神的核心構成,這是一個由邊疆來定義未來的國家。于是,年輕好斗的美國人發自內在的沖動,促使他們西進美國本土最后的邊疆——亞利桑那州。或許,在國際活動中,美國常常被其他國家認為好斗,大概也與這種“邊疆精神”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亞利桑那州三分之二的人聚集在鳳凰城和圖森兩大城市區。鳳凰城,以常住人口計算,上個世紀初,不過是一個數萬人的偏僻邊疆小城,1990年已經成為美國第九大城市,2010年超過費城,成為美國第五大城市。按照目前這種增長率,十年后,鳳凰城完全有可能超過芝加哥,而成為美國第三或者第四大城市。20世紀以來,紐約、芝加哥這些東部老牌大城市,人口增長甚慢,新興城市洛杉磯、休斯頓,尤其是鳳凰城卻發展迅速。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美國大城市,如西雅圖、亞特蘭大、舊金山、波士頓、邁阿密等,無論面積還是人口,實際上現在都不及鳳凰城的一半。有意思的是,美國前四名的大城市:紐約、洛杉磯、休斯頓,都面朝大洋,芝加哥瀕臨五大湖——“北美地中海”,正所謂“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唯獨鳳凰城,深處內陸,置身于沙漠、荒漠中,而且是美國城市中有名的“火爐”。七八月份的天氣,幾乎每天氣溫都在40℃以上。據說,其干燥、炎熱的程度,即使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大城市中,也只有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伊拉克的巴格達,可以與之相提并論。
它建立在鹽河河谷,據考古發掘,幾千年前就有人類(印第安人)活動;但鹽河近幾百年來,基本上是半干涸的。上個世紀“羅斯福水壩”解決了水源供應問題,現代城市得以建立;后又再修一座水庫,位于鳳凰城的直轄區“坦佩”城內,即稱之為“坦佩湖”,成為鳳凰城的一道風景。亞利桑那州近一半的人生活在此城及其附近,雖然,這仍是不怎么適宜人居住的空間。
現代大城市常常與高樓群甚至摩天大廈群直接相聯系,而鳳凰城十層以上的“高”樓,寥寥可數;絕大多數是三層以下的木建筑,無論是在商業區,還是行政區,更不用提住宅區。“大城市——高樓大廈”這種印象,應是上個世紀60年代前的美國城市所構建的;而現在美國城市的擴張,尤其是西部新興城市,主要是橫向鋪開,離散的建構;城市郊區化,郊區城市化,才是城市建設的主流。“高樓林立”絕非是對這種大城市的描述,在這種城市里,四層以上就算高樓。駕車在鳳凰城漫游,第一印象,這是一個“擴張版”的鄉鎮。當很多后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紛紛競爭著建設一個比一個高、一個比一個大的高樓群,來展示雄心與強盛時,美國人已經失去了用高樓來象征 “欲與天公試比高”,試圖挑戰上帝的興趣。
更為有意思的是鳳凰城的生長模式。一般城市的建成,有起點,有中心,有郊區邊緣,而鳳凰城則既無中心,也無起點。粗略瀏覽,如一大群農莊和小鎮的組合版。機場就在市區內;而繁華商業區則在邊緣;“坦佩湖”類似中心,但向北不到兩公里就是“帕帕戈”——原生態的沙漠地貌;而“帕帕戈公園”周圍仍是市區。封閉式的高速公路,縱橫交錯在市區內。因而,公路上不到兩公里必有進出口。一般而言,城市的生長是市區向四方郊區的擴張,而鳳凰城似乎是郊區向城區的逆襲版;或者可稱之為市區與郊區互博而成,這種動態的互博生長,時時都在進行中。
西海岸城市,新崛起的西部城市,如更有代表性的美國第二大城市洛杉磯,實際上,也大致如是。它不過不到十幢的摩天大樓,絕大多數建筑也在四層以下。當代中國的游客,常感嘆:遠不如中國繁華!洛杉磯也是既無中心,也無起點,它們就如一條大河,奔流到一個低洼,匯集起來,隨性漫開,擴張而成為一個大城市。

在這種城市里,幾乎可以說是無公交系統,盡管有幾條公交路線,甚至還有輕軌電車,但不過是一種點綴。在這種城市里沒有中心,工作上班者,來自各點線,去往各點線。復雜而精心設計的車道,沒有哪個區域特別擁堵。在這種城市里生活,家用轎車就如手機、電腦一樣,幾乎是人人必備之物。甚至可嘆,沒有腳可以,沒有汽車大不可以。腿有問題,可用輪椅,稍微改裝的轎車,可方便上下。美國是“輪椅者的天堂”,處處都有專為輪椅者修建的設施。沒有車,則購物、進餐都是大問題,處處困難。汽車是流動的房子,在汽車里,既在“家”又在路上,隨時可開拔。
而東部的老牌大城市,如紐約、芝加哥、波士頓,則符合現代大城市的固有標準印象,高樓林立,人煙稠密,公共交通系統發達。如果它們可稱為“現代”城市,而西部大城市,則可以稱為“后現代”城市,代表著未來城市的模樣,引領新的城市建設潮流。
不過西部城市,更可能是“邊疆精神”的表現,東部大城市老矣。相對美國歷史而言,已經“經典化”定型了,缺乏那種朝氣勃勃的開拓沖動,那種不愿定型,不愿停止,隨時準備打包前行的沖動。當代著名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曾評說:“(美國)作為一種文明,長期以來它一直是一位帶行李的游客……在它面前展現著無限美好的未來,只等著它去把握。”他們不是游牧民族隨著季節遷徙,而是被理想、信仰、甚至幻覺激勵著,“邊疆”在前,一切未定,只能前行。
回顧歷史,所謂美國的邊疆開拓,就是成千上萬的人,各自謀求生存發展的人。自發組織,自由前行,群集而又隨時準備分離,群居而又適當分散……從而建構起城鎮、城市。美國的建構,是先有群聚的流動的協議群體,向西開發,再有國家政府;先有城鎮建設,再有農村建設。
“邊疆精神”的實質就是永遠沒有固定邊疆。前行,前行,機會在召喚,平等競爭的機會在召喚。被理想,有時是被幻想所激勵,向未知空間前進。美國人有一種非理性的、帶點病態的深層恐懼,不敢停下,唯恐落后,從而失去“機會”,被“天定命運”所拋棄,被上帝所拋棄。據有關資料記述,美國人很少有在一所房子內居住五年以上的。開拓得快,拋棄也快。當代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布爾斯廷在影響極大的《美國人》一書中陳述:僅在1852年到1912年間,在邊疆運動中,美國人建立后又拋棄的城鎮,就超過2500個。典型的如弗吉尼亞州的詹姆斯登,是英國移民在北美的第一個“永久性”定居地,曾作為該州首府。一百年后,那里只剩下一排排空房,風與“鬼魂”在其間相伴游蕩。底特律、匹茲堡,這些美國如雷貫耳的重要城市,在本世紀,或許就已經在走向被拋棄之路,至少已經在走向衰敗。
美國的“邊疆”就是沒有“邊疆”,但是卻有方向,那就是“西進”。背靠大西洋—歐洲,面朝太平洋,西進,西進,是美國永恒的主旋律。四百年來,有一次“轉身”:第一次世界大戰;兩次“ 側身”: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不是現在才“重返亞太”,而是一直眼睛就盯著亞太。
當前面已無可開拓的空間時,也可能側身向沙漠、荒漠,于是涌向亞利桑那州……涌向天空:月球、火星、更遙遠的太空,于是有了“挑戰者”,有了“阿波羅”……于是有了Biosphere Two。 邊疆構建了美國,也構建了美國精神:驕傲、好斗、剽悍。更重要的是個人至上,甚至宣稱“個人是一切的根基”。美國是個人合作立約而成群體,由群體而建成國家。而開拓西部的“ 優先權原則”,也造成美國人對落后的恐懼,對停滯的恐懼,甚至認為,不再向前開拓,美國性就消失了。

邊疆精神,在美國普通公民的顯著表現之一,就是喜愛工作。衡量經濟的指標,對于歐洲是社會福利狀況,對于發展中國家則是GDP;而對于美國,首先是“失業率”。任何失業率的高漲,政府都會惶惶不安。這是美國力量的根源所在。進一步,是追求超越“工作”的“事業”,工作是朝九晚五,每周五天;“事業”是每天24小時,每周七天。工作是要求做的,事業是想要做的。
“邊疆精神”,使美國人真正強大的力量表現在何處?
是開著皮卡,奔波勞作在荒野,強悍的六七十歲的大爺大媽。
是赤腳穿著一雙“人字拖”,昂然坦然,前往萬里外的他國異鄉;在越洋飛機,緊皺眉頭,埋首電腦,工作不息的妙齡少女。
是五十攝氏度高溫中,在不準用空調的“快遞”貨車上,快速地跳上跳下的帥小伙子。
是66號公路上的,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中的喬德,而不是66號公路上的,凱迪亞克的《在路上》中的狄安·莫里亞蒂;是庫柏“皮裹腿”系列中的納蒂·邦波,而不是大衛·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爾頓·考爾菲德。
是杰克·倫敦的《熱愛生命》,而不是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
是硅谷,而不是迪斯尼。
甚至,是在車庫里揮汗的比爾·蓋茨,是在公園里徘徊的喬布斯;不是邁克爾·喬丹,不是麥當娜·西科尼。
希望這強悍的、驕傲的民族,不再用“邊疆精神”去與各國對抗,從而迷失了方向,而是去仰望太空,踏上“天路”,去登火星、測銀河,仍可引領世界前行。
世界各民族、各國家,都有自己的“邊疆”意識,或邊疆精神,只是內涵有異,表現有異。人們常常稱中國人是“安土重遷”,是“居”的民族,其實中國人也有自己的“邊疆精神”,不然,在這小小地球上,為什么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華人?美國人的“邊疆精神”是強暴的,強力介入的;而中國人則是融入的,適應的,隨彎就曲,如水流瀉地,水潤萬物,不動聲色,卻是無隙不入的。與美國人相同的,僅僅在于中國的“邊疆精神”,就是沒有“邊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