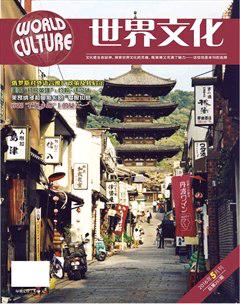西方思想家寓言式假說故事
劉暢
寓言是用比喻性的故事來寄寓意味深長的道理,給人以啟示的一種文學體裁。其運用的修辭手段是比喻,黑格爾認為 “寓言歸根到底是一種比喻的藝術” 。而假說則是根據已知的事實和原理,對自然和社會現象及其規律性提出的推測和說明,得到一個暫時性但是可以被接受的解釋。寓言式假說,即以寓言故事的形象方式來表達自己思想學說的某種假設。在此,所謂“某種假設”通常是作者核心觀念的表達,具有整體性、系統性、創新性。由于其學說的抽象、深奧、難解,所以寓言故事的形象介入使得其所要表達的思想觀點通俗易懂,達到了積極的思想修辭效果。這里,介紹幾個西方思想家寓言式假說的故事。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認為,國家應當由哲學家來統治,因為哲學家可以看到世界的真相 —— 理念。柏拉圖哲學的核心概念是“理念”,故其哲學亦被稱為“理念論”。所謂理念,就是能夠代表某一類事物或思想的觀念,其特點有三:一是先驗抽象性,理念代表的是事物的共性,是對實際事物的一種概括和抽象,理念是一切事物的原型,它是最完美的、真實的、永恒不變的本質。二是它不依賴具體事物而存在,它既存在于事物產生之前,也存在于其消亡之后。三是理念在最初存在于具有最高和諧的精神原則之中。如床、桌子、橋、大、小、真、善、美等,這些理念存在于出生之前,后天的學習和認知不過是對這些先天理念的回憶而已。理念是世界的真相,但理念很深奧,一般人意識不到,也就難以看到世界、事物的真相,他們看到的只是事物的影子。為了說明這個道理,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有這么一個著名的洞穴比喻來解釋“理念論”:
那些缺乏哲學理念的人可以比作是關在洞穴里的囚犯,他們只能朝一個方向看,因為他們是被鎖著的;他們的背后燃燒著一堆火,他們的面前是一座墻。在他們與墻之間什么東西都沒有;他們所看見的只有自己和他們背后的東西的影子,這些都是由火光投射到墻上來的。他們不可避免地把這些影子看成是實在的,而對于造成這些影子的東西卻毫無觀念。最后有一個人逃出了洞穴來到光天化日之下,他才第一次看到了實在的事物,才察覺到他此前一直是被虛幻的影像所欺騙。如果他是適于做衛國者的哲學家,他就會感覺到他的責任是再回到洞穴里去,回到他從前的囚犯同伴那里去,把真理教給他們,指示給他們出來的道路。但是,他想說服他們是有困難的,因為離開了陽光,他看到的影子還不如別人那么清楚。(伯特蘭?羅素:《西方哲學史》)

雷特?哈定(1915—2003)是美國著名的生態學家,他創立了世界上第一部《生態法》,其成名之作為1968年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論文《共有地悲劇》。文章揭示了一種人類共有資產的集體困境,哈定指出:“在共享公有物的社會中,每個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這就是悲劇的所在。每個人都被鎖定在一個迫使他在有限范圍內無節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毀滅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會當中,每個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后“公有物自由給所有人帶來了毀滅”,這就是所謂的“共有地悲劇”,或“哈定悲劇”,也稱“集體陷阱”“零和博弈”。集體陷阱,或“零和博弈”,有三個基本假設:(1)參與行為者都是理性人。(2)理性人在行動時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3)追逐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終會導致集體利益的損失。
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曾說:“凡是屬于最多數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人們關懷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為說明這個抽象的道理問題,哈定在《公共地悲劇》中“虛構”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片茂盛的公共草場,政府把這塊草地向一群牧民開放,這些牧民可以在草場上自由地放牧他們的牛。隨著在公共草地上放牧的牛逐漸增多,公共草地上的牛達到飽和。此時再增加一頭牛就可能會使整個草場收益下降,因為這會導致每頭牛得到的平均草量下降。但每個牧民還是都想再多養一頭牛,因為多養一頭牛其增加的收益歸這頭牛的主人所有,而增加一頭牛帶來的每頭牛因草量不足的損失卻分攤到了在這片草場放牧的所有牧民身上。于是,對于每個牧民而言,增加一頭牛對他的收益是比較劃算的。在情形失控后,每個牧民都會不斷增加放牧的牛,最終由于牛群的持續增加,使得公共草場被過度放牧而造成退化,從而不能滿足牛的食量,并導致所有的牛因饑餓而死,因此成為一個悲劇。”
哈定寓言式的悲劇揭示了:在每個人都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社會,其結局必然是悲劇性的。其深刻之處在于,這種災難是群體的而非個人的,是大家都能看得到,卻又難以避免的,是普遍存在的,而非僅僅是局部的個案。例如世界氣候變暖和愈演愈烈的霧霾現象。
又如李普曼在《公共輿論》中指出,新聞輿論是一種“擬態環境”。由于多種原因,我們作為一般讀者很難直接“看到”真相,新聞報道構成了一種“虛擬環境”,塑造著我們頭腦中關于外部世界的“圖像”,左右著我們對于外部世界的認知。他指出:“回過頭來看,對于我們仍然生活在其中的環境,我們的認識是何等的間接。我們可以看到,報道現實環境的新聞傳給我們有時快,有時慢;但是,我們總是把我們自己認為是真實的情況,當作現實環境本身。…… 在所有這些實例中,我們必須特別注意一個共同的要素,那就是在人與他的虛擬環境之間的插入物。他的行為是對于虛擬環境的一種反應。……但因為在社會生活的層次上,所謂人對于環境的調整當然是通過各種虛構作為媒介來進行的。這里所說的虛構,我并不是指撒謊,我指的是不同程度地由人們自己描繪的環境。由于真正的環境總起來說太大、太復雜,變化得太快,難于直接去了解它。我們沒有條件去對付那么多難以捉摸、那么多的種類、那么多的變換的綜合體。然而我們必須在那種環境中行動,我們必須先把它設想為一個較簡單的模式,我們才能掌握它。”為了說明這一道理,李普曼在《公共輿論》一書中“虛構”了一個故事 :
“1914年,有一些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住在一個海島上。那個海島不通電報,英國的郵船六十天才來一次。9月里,郵船尚未來到,島上的居民仍在談論不久前報紙上報道的關于即將審判凱勞克斯夫人槍擊加斯頓?卡爾默特的事。因此,9月中旬的一天,全島的居民都聚集在碼頭上,比往常更急于想從船長那里知道判決的情況。可是,他們了解到的卻是英國已經和法國訂立了神圣同盟,向德國開戰已六個多星期了。在這不可思議的六個多星期中,島上的英、法居民和德國居民實際上已是敵人了,但他們相處得還是像朋友一樣。……當他們還沒有從任何方面得到會打亂他們生活的消息以前,在這一段時間,人們仍然根據他們對歐洲的舊有認識來處理事物。每一個人都有一段時間照舊在適應環境,而實際上這種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
另一例證,是英國著名動物學家、人類行為學家德斯蒙德?莫里斯的代表作《人類動物園》。在書中,作者從動物學觀點為出發,對現代都市生活和現代人行為進行了批判性的考察,并將人類社會比作一個龐大的動物園。其云:

“隨著現代生活壓力變得越來越沉重,受困的都市居民時常把自己居住的這個擁擠的世界比喻為‘混凝土叢林。誠然,若以此來比喻都市稠密的建筑群,確實很精彩,但就生活形態而言,任何一個研究過真正的叢林生活的人都肯定會說,這一比喻是很不準確的。……我們不應把都市居民比作野生動物,而應該把他們比作被關在籠子里的動物。現代人類動物已不再生活在適合于這一物種的自然環境中了。他們已遭囚禁。囚禁他們的不是動物管理員,而是他們自己的聰明才智。他們自己營造了一座龐大而喧囂的‘動物園,并置身于其中。在那里,他們時時都有因為過度緊張而倒斃的危險。”
“人類動物園”的首要問題是擁擠,怎樣才算擁擠,這并沒有固定的客觀標準。擁擠和密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密度是指在一定區域內的人數,而擁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主觀感覺。研究表明,擁擠影響人的復雜工作能力,也對社會行為有消極影響,如影響人與人的接近,影響提供幫助。擁擠引起高度生理激動。心理學家伊萬斯1979年做過一項實驗研究,讓十個人擠在一間小房間內,待上3.5小時。之后發現被測試者脈搏加快、血壓升高。心理學家埃普斯坦等人1981年也做過一項實驗研究,讓被測試者三周內三次處于擁擠狀態,他們都報告說感到緊張不安,感到煩躁,生理激動也較高。對此,莫里斯在《人類動物園》一書中從動物學角度做出了類比式的解釋: “一大群同類動物被關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里,隨即就會產生嚴重問題,就會出現相互傾軋、相互傷害乃至相互殺戮現象;當然,也會出現神經錯亂。不過,實際上即使是由最無經驗的人管理的動物園,也不會像現代都市那么擁擠。任何一個動物管理員都知道,過度擁擠會使動物行為失常,所以要是有人建議他把一群猴子—— 或者一群食肉動物,或者一群嚙齒動物 —— 關在一個小籠子里以節省空間,他一定會驚訝地搖著頭說,這種建議簡直愚不可及。然而,人類卻自愿地這么做了。他們大群大群地擁擠在都市的狹小空間里,每天熙熙攘攘地掙扎著,卻幾乎沒有人真正想離開那里。” 在此,善意的嘲諷溢于言表。除了擁擠,還有孤獨。擁擠,是就“人類動物園”這一整體而言;而孤獨,則是就每一個單個人而論。莫里斯指出:“在真正的動物園里,動物發現自己被孤獨地囚禁在籠子里,此時它雖能看見或者聽到其他籠子里的動物,卻不能和它們真正有所交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類都市生活的社會環境幾乎和動物園環境完全相同。都市生活使人感到孤獨,這種危險可謂眾所周知。在龐大的、非個人化的群體中,人很容易產生失落感,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然分群和部落式的個人關系很容易變形、分裂甚至崩潰。在一個村莊里,人與人之間不是熟識的朋友,就是熟識的敵人,反正是沒有陌生人的。然而,在都市里,許多人甚至連自己的鄰居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但對于大多數‘人類動物園成員來說,這種出現在都市熱鬧生活中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互隔離,卻使他們意外地感到既緊張又痛苦。”
將人比作動物,將人類社會的精華 —— 都市比作擁擠不堪的動物園,并不是本書的目的,在這種比喻之下,作者其實是想揭示一個困擾人類的悖論 —— 我們所謂的進步其實是在付出了高昂代價之后獲得的,恰如《人類動物園》作者莫里斯所說:“我在本書中所要表明的僅僅是:為了不斷滿足我們的這些欲望,我們也為此付出了越來越高的代價,而且我們總會找到聰明的方法來加以支付的,不管這代價有多高。總之,在人類與自然的這場賭賽中,賭注越下越大,風險越來越高,速度也越來越驚人,雙方都有點氣喘吁吁了。但不管怎么說,這仍是世界上最激動人心的一場賭賽。要想吹哨來結束它,那當然是愚蠢之舉,但我們可以換一種方式來進行這場賭賽。再說,要是能進一步了解參賽雙方的本性,我們就可能使自己得益,就可能避開風險而不致使人類這一物種陷于滅頂之災。”
《人類動物園》與《裸猿》《親密行為》被稱為“裸猿三部曲”,主要從動物行為學的角度研究人類行為,揭示人類社會的弊端和缺陷,批判視角中不無諷刺意味,擊中了人類的弱點。如在《裸猿》中,莫里斯指出,在已知的193種猿猴中,只有一種猿猴全身赤裸,他們自詡為“智人”,實際卻是“裸猿”。于是,他寫的每個字都成為受了創傷的“智人”爭論的對象,一度《裸猿》成為禁書,地下流通的書被沒收,教會將其付之一炬,因為它使人類進化的思想遭到譏笑,它無情地諷刺了人類獨尊的觀念,而這,卻讓“裸猿三部曲”成為暢銷書。三十年后,當《裸猿》再版時,莫里斯依然倔強,他在序言中聲稱一字不改,因為盡管我們創造了瑰麗的文明,仍然受制于基本的生物規律。

此外,從邊沁到福柯的“全景敞視主義”也為我們理解什么是“寓言假說”提供了一種佐證。“全景敞視”建筑,是英國哲學家耶利米?邊沁(1748—1832)構思的一種由“權力技術”構成的建筑。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對邊沁“全景敞視”建筑構造的基本原理做了介紹:“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戶,對著環形建筑。環形建筑被分成許多小囚室,每個囚室都貫穿建筑物的橫切面。各囚室都有兩個窗戶,一個對著里面,與塔的窗戶相對,另一個對著外面,能使光亮從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監督者,在每個囚室里關進一個瘋人或一個病人、一個罪犯、一個工人、一個學生。通過逆光效果,人們可以從瞭望塔的與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觀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這些囚室就像是許多小籠子、小舞臺。在里面,每個演員都是煢煢孑立,各具特色并歷歷在目。敞視建筑機制在安排空間單位時,使之可以被隨時觀看和一眼辨認。總之,它推翻了牢獄的原則,或者更準確地說,推翻了它的三個功能 —— 封閉、剝奪光線和隱藏。它只保留下第一個功能,消滅了另外兩個功能。充分的光線和監督者的注視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為黑暗說到底是保證被囚禁者的。可見性就是一個捕捉器。”
其后,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將邊沁的這一思想延伸,把其從具象的監獄建筑延伸到抽象的社會學范疇,提出了 “全景敞視主義”的概念:
“但是,全景敞視建筑不應被視為一種夢幻建筑。它是一種被還原到理想形態的權力機制的示意圖。它是在排除了任何障礙、阻力或摩擦的條件下運作的,因此應被視為一種純粹的建筑學和光學系統。它實際上是一種能夠和應該獨立于任何具體用途的政治技術的象征。如果說西方的經濟起飛始于導致資本積累的技術,那么或許也可以說,人員積聚的管理方法導致了一種脫離傳統的、講究儀式的、昂貴和粗暴的權力形式的政治起飛。那些陳舊的權力形式很快就被廢棄了,被一種巧妙的、精致的征服技巧所取代。我們可以說,規訓(紀律)是一種能夠用最小的代價把肉體簡化為一種‘政治力量同時又成為最大限度有用的力量的統一技巧。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造成了規訓權力的特殊方式。它的征服各種力量和肉體的一般公式和技巧,即‘政治解剖學能夠運用于極其多樣化的政治制度、機構和體制中。”
“微觀權力”觀念及其分析方法,是福柯思想中最有價值的理論遺產。福柯認為,權力分析應從國家機器、王權、司法權等傳統觀念中走出來,要“砍掉國王的頭顱”,而代之以一種多元性、多極化的“微觀權力”觀。他指出:“權力無處不在。這并不因為它有特權將一切籠罩在它戰無不勝的整體中,而是因為它每時每刻、無處不在地被生產出來,甚至在所有關系中被生產出來。權力無處不在,并非因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為它來自四面八方。” 因此,他認為邊沁的“全景敞視”道出了權力之“政治技術”的本質,指出:“這是一種重要的機制,因為它使權力自動化和非個性的權力不再體現在某個人身上,而是體現在對于肉體、表面、光線、目光的某種統一分配上,體現在一種安排上。這種安排的內在機制能夠產生制約每個人的關系。…… 因此,由誰來行使權力就無所謂了。……全景敞視建筑是一個神奇的機器,無論人們出于何種目的來使用它,都會產生同樣的權力效應。” 但是福柯的創新在于,他沿用邊沁的“全景敞視”觀念,但又有所延伸。他認為,所謂“全景敞視”不應僅僅局限于特定空間,如監獄,而是延展、彌漫到了社會的各個角落。例如:
“它在使用上具有多種價值。它可以用于改造犯人,但也可以用于醫治病人、教育學生、禁閉瘋人、監督工人、強制乞丐和游惰者勞動。它是一種在空間中安置肉體、根據相互關系分布人員、按等級體系組織人員、安排權力的中心點和渠道、確定權力干預的手段與方式的樣板。它可以應用于醫院、工廠、學校和監獄中。凡是與一群人打交道而又要給每個人規定一項任務或一種特殊的行為方式時,就可以使用全景敞視模式。除了做必要的修改外,它適用于‘建筑物占用的空間不太大,又需要對一定數量的人進行監督的任何機構。”
這樣,所謂“全景敞視”就印證了他“權力無處不在”的觀點,使得權力變成一種“關系中的存在”,它具有滲透性、生產性與創造性,可以延伸到任何地方,這又明顯超越了邊沁的“全景敞視”,福柯說:“為了行使這種權力,必須使它具備一種持久的、洞察一切的、無所不在的監視手段。這種手段能使一切隱而不現的事物變得昭然若揭。它必須像一種無面孔的目光,把整個社會機體變成一個感知領域:有上千只眼睛分布在各處,流動的注意力總是保持著警覺,有一個龐大的等級網絡。按照巴黎市長的意見,巴黎的這個網絡應包括48名警察分局局長,20名視察員,定期付酬的‘觀察員,按日付酬的‘密探,領賞錢的告密者,另外還有妓女。這種不停的觀察應該匯集成一系列的報告和記錄。在整個18世紀,一個龐大的治安文本借助于一種復雜的記錄組織愈益覆蓋了整個社會。”
綜上,柏拉圖、哈定、李普曼、莫里斯、福柯等幾位學者,時代不同,國籍各異,其思想(理念論、共有地悲劇、擬態環境、人類弱點、微觀權力)無疑是深刻的,但是,抽象高深的論述畢竟不容易理解,于是思想家們運用了類似比喻修辭的方法,讓寓言式假說參與到思想活動中來,用一個通俗易懂的故事使其觀點形象化,使讀者更加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