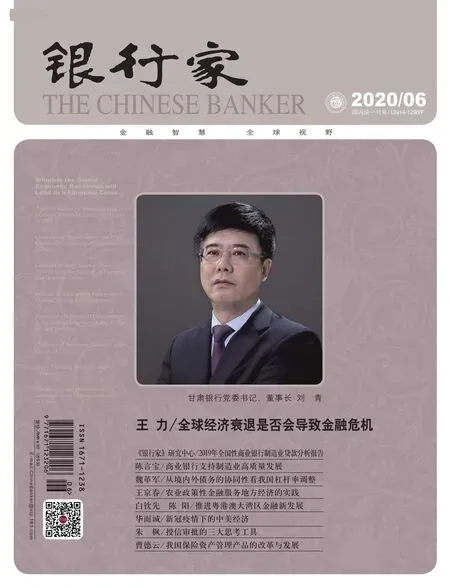總損失吸收能力及其他自救措施是定時炸彈
監管者與銀行家們已經達成了一項協議,系統性重要銀行必須持有相當數量的額外“總損失吸收能力”,但是這些額外的資本將以成本低于股權資本的方式來籌集。市場對此反響熱烈,銀行在收益率跌至谷底的情況下發行了新的自救證券。這些新金融工具的本意是保護納稅人,免于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救助銀行,但實際上它們并不管用,還會將新的市場參與者一股腦的卷入下一場金融危機的中心。
金融危機難以預測,不過它的一個早期征兆或許是監管者的傲慢。2015年11月9日,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宣布了對30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最低“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資本監管要求,并稱這是徹底解決“大而不能倒”問題的必由之路。自2019年1月1日起,這些銀行“總損失吸收能力”占風險加權資產的比例不得低于16%,在2022年1月1日,這一指標將上升至18%。但FSB允許新興市場國家的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分別在2025年1月1日和2028年1月日達到上述監管要求,不過這對他們來說仍然任重而道遠。修正后的巴塞爾協議Ⅱ與巴塞爾協議Ⅲ規則均已要求國際銀行資本充足率水平不低于風險加權資產的10.5%,這使得銀行資本充足率有額外5%~7%需要以TLAC的形式持有,但這部分資本與巴塞爾協議中要求的股權資本不同——開始時并不是股權資本,但在危機中必須實現自動減記或可轉換為股權資本,讓銀行能夠在保持資本充足率的情況下持續經營。這一措施意圖在于幫助銀行在不影響市場穩定也無需納稅人救助的情況下渡過難關。TLAC協議墨跡未干,銀行就匆匆忙忙開始發行這類“自救”證券,而投資者則報以滿腔熱情。這類證券的十年收益率一度接近2.5%。遺憾的是,這些自救證券可能導致金融系統更加不安全。
在被誤導的情況下,依賴自救證券可謂是用心良苦。全球經 融危機中,我們目睹了私人部門的魯莽冒險如何轉化為公共債務的事實,由于政府的大范圍“救市”行為,銀行與金融系統在接下來一段時間內過度開展私人借貸業務。對公共債務持續性的關注及其是否過度的討論,也將不同程度的導致“緊縮”政策。由于銀行家過去的輕率冒險行為,國家不得不縮減福利,這已經極大地影響到了公眾、政治家和金融監管者。制定相應措施來保護納稅人勢在必行。使用“自救”證券的本意是讓納稅人在更少的情況下才需要救市,承擔更低的成本,同時抑制金融機構由于寄希望于政府救市而產生的冒險動機。本文解釋了為何自救工具自救不會起作用,以及更糟糕的,為什么它會引發金融危機并使其蔓延至更難以解決的領域。納稅人的福利將會進一步降低。打個比方來講,自救證券就如同糊弄人的假黃金,表面的金屬光澤看起來很像是黃金,然而,它內里卻是能夠引發火災的硫化鐵。解釋清楚為何自救證券以及其他類似的自救手段對保護金融系統與納稅人無效之后,我們為什么必須用央行流動性、臨時國有化、抑制證券投資以及創建壞賬銀行等一系列復雜的工具才會明了。這才是在已經爆發的金融危機中保護納稅人的最可靠的手段。
政策周期
監管改革具有周期性。在一場重大的金融危機(比如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大刀闊斧改革的時機就成熟了。經濟繁榮時期那些“這次將不一樣”的蠱惑人心的口號在泡沫破滅時被“永遠不再”的憤怒咆哮取代。危機是多數金融改革的緣由。比如,銀行必須公布審計過的賬戶可以追溯到1856年英國皇家銀行的倒閉。1907年美國“金融恐慌”則直接導致了1913年美聯儲的創立。1929年股災催生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從此美國開始了50多年的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業經營的局面。1974年6月德國赫斯塔特銀行戲劇性的倒閉之后,G10國家的銀行監督者們創建了巴塞爾委員會。
金融改革的正確時機就在危機剛剛結束之時。如果未能及時抓住這一機遇,那么正確的改革通常會被錯誤的改革所淹沒。監管者們忙于為金融危機滅火,通常很快就能從技術角度認識到危機起源。盡管被那些認為危機源頭的存在缺陷的銀行監管規定就出自巴塞爾銀行委員會之手,他們還是早在2009年4月提出了有意義的改革藍圖——僅在雷曼兄弟銀行倒閉7個月后。《巴塞爾協議Ⅲ》嘗試解決《巴塞爾協議Ⅱ》沒能解決的問題,并將監管推向正確的方向,特別是在資本流動性的關鍵領域。
然而如果沒有抓住改革機遇,政策周期將會轉向。納稅人的錢被用于救助富有的、偷稅漏稅的銀行家,隨后財政赤字引起社會保障支出削減,這時正義的道德憤慨演變為可理解的怒火。當部分銀行家的個人卑劣惡行被暴露之后,這種怒火被煽動得更為激烈,憤怒破壞了我們之前形成的對問題出在哪的共識,也引發了公眾對政府救市行為的強烈抵觸。納稅人不再愿意扮演最后貸款人或者擔保人。公眾怒吼著要求實施嚴厲的懲罰,要求采取對國家和納稅人依賴程度更低的解決方法。在這種環境下,未經嚴格檢驗的自救工具及其他類似的金融工具得以大行其道。
為何自救不僅無效反使危機變得更糟
自救證券也被叫做混合債券、“COCOS”或者“出局債券”。從本質上來說,自救證券在經濟形勢良好的時候是一張帶息債券,但在經濟衰退時,如果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比率低于預定水平,證券將會自動觸發轉化為股權資本,其償付級別低于全部債務,并承擔全額損失的風險。這種股權注入自動稀釋了現有股權。監管者也批準了其他會在更早階段觸發的金融工具,它將停止支付利息而不是轉換為股權。這些金融工具是有條件觸發的、可轉換為股權的資本工具(所謂的COCOS)。自救證券也可能作為官方救助機制的一部分,在任何公共資本注入之前先行救市,正如歐盟在2012~2013年塞浦路斯救助案例中的行為。混合債券也可能作為當局認可的一種監管資本形式,承擔自救義務。自救證券承諾將在早期整頓即將破產的銀行,把金融危機的沖擊與納稅人風險敞口降到最低。這一切看起來再合適不過了。公眾認為銀行家們用別人的錢下注來大肆冒險,贏了錢歸自己,輸了則讓納稅人買單,這一印象給了決策者采取“自救措施”強烈的政治正確性。
自救措施與危機的演化
如果銀行危機從個別銀行的倒閉開始(可能是一個流氓交易員的滑稽動作引起的),但倒閉的事實會引起恐慌蔓延,將其他銀行也卷入危機漩渦,此時自救措施就起作用了。但這種情況只存在于教科書中,或者是存款保險制度實施之前。而且,今天的監管者們很善于應對單一銀行倒閉。對于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而言,收拾好這類局面不過是日常事務。1995年英國巴林銀行倒閉案也是典型常例。但現今的銀行危機并不是如此發生(從單一銀行倒閉開始),恰恰相反,在危機之前,幾乎所有銀行都表現的非常安全,資本水平充分滿足了監管標準。這就說明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與其他監管者們的工作必定有所疏漏。就在上次金融危機之前兩年(2005年),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達到了歷史新高,并采用了新的、明智的、市場化的風險管理技術,發達國家監管當局秘密會議與央行金融穩定報告中均不認為此時銀行是金融體系的脆弱點。然而,繁榮很快就結束了,幾乎所有銀行同時陷入了困境。
自從數千年前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誕生了谷物期貨交易以來,根本性的金融創新就甚為罕見,大多數金融創新不過是換湯不換藥。自救證券并沒什么新鮮的,不過是市場化的保險工具而已。在新的術語包裝之下,自救證券成為巴塞爾協議Ⅱ的思想核心,將風險予以市場定價作為抵御金融危機的防御前線,并催生了一系列風險管理技術如風險價值(VaR)與信用風險價值(Credit VaR)。金融危機是市場失靈的結果,使用市場價格來保護我們免受市場失靈自然行不通。金融危機往往爆發于市場預期最不可能之時。如果市場預期很可能會有危機——比如數十年以來,由于美國存在大額貿易赤字而預期美元將會崩潰——危機往往不會發生或者影響很小。自救證券的投資者們與信用評級機構在經濟繁榮階段往往會低估風險,然后面對衰退手足無措。
盡管經濟尚未完全擺脫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投資者們還是積極排隊購買COCO證券,雖然其收益率處于歷史低點,但比幾乎為零的銀行短期存款或者國庫券還是好多了。在2015年2月到3月初,金融穩定委員會公布TALC細節幾個月之前,歐洲的一批銀行發行了為期10年的次級債券,它們試圖為這些符合TALC標準的金融工具培育新市場。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從投資者處為其30億歐元的債券得到了165億歐元的訂單——目前所售出的最大一筆自救證券;德意志銀行為其12.5億債券吸引了44億歐元訂單,成交價僅高于同期政府債券210個基點;法國興業銀行12.5億歐元債券吸收了38億歐元,超出190個基點;法國巴黎銀行的15億歐元債券吸引了55億歐元,超出170個基點。2015年那個時候,盡管存在為風險定價的困難,投資者們對收益的渴望還是將票面利率壓低到了2.6%。真有人相信如此吝嗇的回報率,以及遍地都是的無風險資產,抵得上未來10年任何時間銀行可能需要資本注入的風險嗎?
在經濟穩定時期,自救證券投資者將會樂觀地估計其價值,并將其作為其他投資與支出的抵押。當導致價格劇跌的事件發生時,自救證券投資者將會承擔巨額損失。當自救證券投資者面臨大量損失可能性,總體不確定性將會急劇上升,市場參與者將會進入風險規避模式。隨后相應資產的大甩賣會帶來價格進一步下跌,從而進一步惡化銀行的償付能力。
存在若干導致上述集體風險規避行為的不同機制。市場會尋找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或者在陷入困境的機構存在風險敞口或資產的其他金融機構。當金融市場處于下行階段之時,某些自救證券可能會意外地轉換為股權,同時其他類似的自救證券都會被降低評級,這正是一條危機傳染的路徑。這類似于全球金融危機中債務擔保債券(CDOs) 的降級與亞洲金融危機中主權政府債券的降級。
在病態恐慌的環境下,市場參與者們無法獲得能夠緩解恐懼信息,從而往最糟糕的方向想。有時侯銀行其實并未真正倒閉,仍然觸發了自救,更糟糕的是多家銀行同時為了防止倒閉風險同時執行自救,同時其他銀行的自救證券因此被降級,市場風險偏好逆轉與不確定性增強導致危急在金融市場集中爆發。相比處理僅涉及幾家銀行而言,應對波及整個金融市場的危機要困難的多。自救證券的倡導者為它辯護道,歐盟需要1500億歐元來彌補銀行損失,而對應數量的自救證券完全可以接受,也不會帶來不穩定性。這是在金融危機的灰燼業已冷卻良久之后方能確認的金額。但在危急爆發之中,自救的自救功能觸發之時,在各種不確定性沖擊之下市場幾乎癱瘓,對損失的預計往往遠遠高于市場穩定之后實際發生的金額。
誰該買自救證券?
誰應該購買這些自救證券,這是個關鍵而又惱人的問題。出于金融穩定性的考量,其他銀行或者像對沖基金一樣從銀行獲得杠桿的投資者不該購買,他們會在償付能力最差的時候被迫支出最多,增加由于流動性短缺而引起火速變現資產的可能性。或許長期投資者可以持有這些自救證券,監管者被這種意見所打動。這不過是把領取養老金者推下車來保護納稅人罷了。然而,過去的就過去了,無論如何防范,一旦危機真的到來,就將面臨艱難的抉擇,巨額的資金損失由養老金領取者來承擔——養老金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而且他們的政治影響不可小覷——還是把責任推給未來的納稅人算了吧。
投資理論認為,自救證券非常不適合長期投資者。類似于壽險公司或者養老基金理應持有風險隨時間下降的資產——比如公共和私人股本從長期看來就很有優勢。它們應該遠離風險隨時間上升的資產,就如自救證券。自救證券所含風險在發行時要遠遠小于發行后的一年或數年中。
自救建議或許有它的政治意義卻一點也不經濟。表面上,它存在的理由是保護納稅人。但是正如2008年9月雷曼兄弟銀行與2013年春季塞浦路斯銀行的案列所示,以授權“債權人自救”的方式來解決金融危機,比起納稅人買單、政府臨時直接介入代價要高得多。英國勞埃德銀行與蘇格蘭皇家銀行與美國國際集團的經驗也充分證明這一點(它們在次貸危機中并未使用類似自救的方式,其中美國政府接管AIG還實現227億美元利潤)。一旦監管失敗金融危機降臨,我們就不得不直面殘酷的事實,僅有納稅人支持的政府才具有足夠的資產、良好的信用與充分的時間來解決問題。
普遍的情況
不僅僅是自救證券無效,任何其他試圖將外部救援內部化的嘗試,其后果都只會比預計的更糟。從理論上看,流動性是一種公共產品,而長期的經濟實踐表明了由私人部門提供公共產品必然出現供給不足。在危急中,公共部門能夠以相對低得多的代價創造流動性。由私人部門解決流動性供應的效率的效率要遠遠低于公共部門供應。在流動性凍結、資產價格暴跌的時期,幾乎不可能從金融系統或金融機構內部為銀行獲取渡過困境的全部流動性與資本。此時銀行僅能扮演存款保險箱的角色,在有限的空間內茍延殘喘,無力創建新的信用來擺脫困境。如果我們把系統性金融危機定義為規模大到無法由金融機構自行解決的危機,將有助于理解這一概念。另一種視角就是金融危機是一種同質化問題,與城市交通擁堵、建筑物由于內部拉力坍塌這類“系統性問題”有其共通之處。流動性危機是由于同質化的行為——每個人都急切地想要逃離危機,從而急劇地提高了流動性需求。竹子與蛛網能夠承擔很大的壓力是由于其內部復雜的特性決定的。相似的,我們可以通過異質化的行為來提高金融系統的彈性。
流動性危機爆發之時,我們需要擁有并愿意在此時提供流動性的角色(來救市)。上述描述非常契合中央銀行,但私人組織的養老基金與壽險公司似乎也能滿足要求。由于養老基金與壽險公司所承擔的多為長期債務,它們在銀行流動性危機中是潛在的最佳異質市場參與者。如果允許,它們能夠扮演重要的金融體系加固者角色。現在的保險與養老基金監管賦予它們與銀行類似的估價與風險管理原則,使得它們成為了(在危機中)與銀行一樣試圖避險的同質化角色,而不是在短期投資者們拋售相關資產時愿意接手的異質化角色。
結論
自救證券的支持者認為,由于知道公共救助的存在,銀行就會冒更大的風險。這種言論乍聽起來很有道理,但經不起仔細推敲。大多數所謂的外部救援實施之后,銀行股東們的財產將會所剩無幾,債權人也會遭受債權大幅減記。中央銀行始終堅持救助的是銀行,而不是銀行家。更清楚明白地說,實施外部救援的同時,伴隨著極大的可能性是對銀行原管理層實施大清洗。而且,替代自救的并不是什么無條件救助。長遠來看,保護納稅人的方式還是那熟悉的、經過驗證的老三樣。
按照桑頓(Thornton)和巴杰特(Bagehot)關于最后貸款人的理論,公共部門應該在流動性干涸時,向那些具有合理抵押物的金融機構提供充分的流動性。此項措施能夠很好地幫助那些經營穩健,資產不良率低且流動性好的金融機構度過困境。可惜的是,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不多。
危機到來之時,金融機構按其持有的流動性會迅速分裂為兩個陣營。對于那些流動性不足的機構,市場風險偏好趨向厭惡,持有的部分資產無法定價,都為其余資產蒙上了陰影。在當前的歐債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通貨緊縮與80年代末的美國儲貸危機中都可以發現這種趨勢,金融機構依靠監管寬容,用變賣速動資產償還流動負債的方式堅持下去,對流動性差的資產則完全寄希望于市場風險回避情緒的消散或經濟形勢變好。這些機構通過消極應對在危機中幸存,它們的資產負債表好像是上鎖了一樣。這些“僵尸銀行”不僅拒絕增加新的貸款,反而在每次經濟形勢好轉之時變賣資產,最終成為經濟復蘇的負擔。要解決這批金融機構帶來的問題,經過檢驗的方法就是創建一個“壞銀行”,以低于歷史成本三分之一的價格購買它們拋售的資產,然后等待公共部門介入救市。在彌補了購買資產的支出后,殘余的利潤就能夠返還(給變賣資產的銀行)。雖然賣出危機之前的價格已不現實,蒙受損失的銀行股東們還是能夠從流動性的注入與不確定性的降低中得到安慰。創建“壞銀行”的目標是為了讓剩下的“好”銀行能夠募集到私人資本與流動性。將壞賬進行打包重組也能吸引到有能力注入流動性的長期投資機構。如果預期經濟將會回穩,長遠看來有利可圖,這些長期投資機構將愿意購買這些資產(經過打包重組的壞賬),這才是吸引私人資本注入流動性的最佳方式。
為了鼓勵銀行將壞賬賣給壞賬銀行,同時不再通過消極等待來股東損失最小化,首先應該要求他們以市價賣掉那些沒有長期資金來源的資產以募集額外資本。但還有這么一些(問題特別嚴重的)銀行,即使壞賬銀行購買了它們的資產,如果沒有政府部門的支持也難以生存下去。面對這種情況,日本及其他銀行業危機的經驗表明公共資金的連續注入被證明是高昂的失敗不之舉。國有化政策是不敢公開宣揚的政策,但是對納稅人而處理這些金融機構成本最小、速度最快的辦法還是暫時的國家接管——僅涉及及少量資本注入。美國存款保險公司(FDIC)式的做法通常是開除管理層,趕走股東,債權人的受償順位變為次級,以及重組和重構,以備讓這些機構可以重新在市場出售找到新買家。
(本文選自美國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網站,原文發表在巴特沃茨(Butterworths)國際銀行與金融法2016年3月號上,作者阿維納什·帕薩德(Avinash D Persaud)是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和總部在倫敦的智力資本的主席,也是華威委員會主席。譯者為中山大學數學學院毛珩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