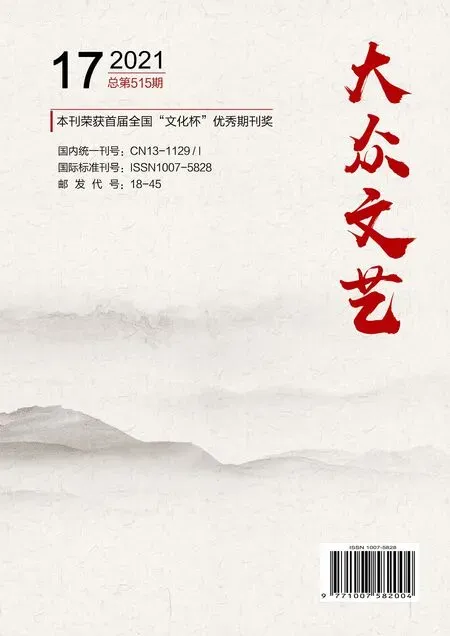論畢飛宇鄉(xiāng)村小說(shuō)中的女性想象
田 祝 (淮陰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 223300)
論畢飛宇鄉(xiāng)村小說(shuō)中的女性想象
田祝(淮陰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223300)
畢飛宇通過(guò)眾多個(gè)性鮮明的女性形象寫(xiě)出了女性的悲劇性生存境遇與生存體驗(yàn)。在他的女性想象之中,恐懼已經(jīng)成為鄉(xiāng)村女性普遍的生存感受,面子給女性帶來(lái)生存撫慰的同時(shí)又具有虛幻性的特點(diǎn),而對(duì)男權(quán)反抗與認(rèn)同的矛盾使得女性落入一個(gè)悖論性的生存怪圈。本文試圖從文化視角對(duì)女性的生存悲劇進(jìn)行分析,進(jìn)而揭示出女性悲劇命運(yùn)的深層文化根源。
畢飛宇;女性;文化;反思
畢飛宇是一個(gè)非常關(guān)注女性生存境遇的作家。他在日常化的書(shū)寫(xiě)中塑造了眾多個(gè)性鮮明的鄉(xiāng)村女性形象,寫(xiě)出了特定歷史時(shí)期鄉(xiāng)村女性獨(dú)特的生存境遇與生存體驗(yàn)。在此過(guò)程中,他把筆觸伸向人的內(nèi)心深處,在對(duì)女性悲劇性生存體驗(yàn)的冷峻逼視中展示出一個(gè)真實(shí)的女性生存景觀,并借此拷問(wèn)人性,反思文化,進(jìn)而揭示出女性悲劇命運(yùn)的深層文化根源。
一、恐懼:普遍的生存體驗(yàn)
畢飛宇通過(guò)對(duì)生活瑣事的日常化描摹寫(xiě)出了中國(guó)女性甚至是整個(gè)中國(guó)人身上潛藏著的深層生存感受——恐懼。在其小說(shuō)中,恐懼是鄉(xiāng)村女性普遍的生存體驗(yàn),它就像一個(gè)幽靈盤(pán)踞在女性的心靈深處。這種恐懼有著多重的內(nèi)涵,一方面表現(xiàn)為對(duì)強(qiáng)權(quán)的恐懼,害怕遭到欺凌;另一方面從文化來(lái)看,是女性對(duì)不被認(rèn)同的恐懼。這是傳統(tǒng)的文化觀念對(duì)中國(guó)女性所形成的壓抑與桎梏以及她們對(duì)這種文化觀念的內(nèi)在認(rèn)同的體現(xiàn)。
這種恐懼首先是對(duì)強(qiáng)權(quán)的恐懼,具體表現(xiàn)為女性對(duì)當(dāng)?shù)貜?qiáng)權(quán)人物的懼怕,害怕遭到他們的侮辱,而極端男權(quán)化的文革鄉(xiāng)村背景更是凸顯了這一生存體驗(yàn)。《玉米》中的村支書(shū)王連方可以說(shuō)是王家莊的“土皇帝”,他就是強(qiáng)權(quán)的化身,他在王家莊為所欲為,對(duì)女性任意欺凌,恐懼已經(jīng)蔓延到王家莊的每個(gè)角落。“王連方最大的特點(diǎn)是所有的人都怕他。他喜歡人家怕他,不是嘴上怕,而是心底里怕。你要是咽不下去,王連方有王連方的辦法,直到你真心害怕為止。”1面對(duì)裕富家的含淚懇求,他反而是“虎下了臉來(lái)”,十分囂張地說(shuō),“隨便你,反正每年都有新娘嫁過(guò)來(lái)”。即使是當(dāng)有慶撞見(jiàn)他與自己老婆的丑事時(shí),他也若無(wú)其事地說(shuō)著“這邊快了,就好了”,并吩咐有慶在外面歇會(huì)兒。王連方的無(wú)恥行徑歸根到底是建立在人們對(duì)權(quán)力的畏懼和屈服的基礎(chǔ)上的。積淀千年的傳統(tǒng)等級(jí)觀念使“懂事”的王家莊人認(rèn)同了強(qiáng)權(quán),也默許了王連方的行為。正因?yàn)槿绱耍瑹o(wú)論是那些被侮辱的婦女還是她們的家人,才會(huì)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這種恐懼感甚至影響到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上面。當(dāng)彭國(guó)梁第一次到玉米家時(shí),周圍圍觀的人們?cè)谟衩走M(jìn)家門的時(shí)候讓開(kāi)了一道縫隙,與之相對(duì)比的是在王連方進(jìn)家門的時(shí)候人們卻是讓開(kāi)了一條道,一道縫隙與一條道的區(qū)別充分說(shuō)明了對(duì)強(qiáng)權(quán)的恐懼已經(jīng)滲入到王家莊人的骨髓。不僅鄉(xiāng)村女性有這樣的恐懼感受,那些來(lái)到鄉(xiāng)村的女知青也有這樣恐懼體驗(yàn),小說(shuō)中的女知青對(duì)于鄉(xiāng)村的記憶往往與暴力聯(lián)系在一起,如《那個(gè)夏季那個(gè)秋天》中的童惠嫻被耿長(zhǎng)喜強(qiáng)暴,《蛐蛐 蛐蛐》中代課的女知青被第五生產(chǎn)隊(duì)的隊(duì)長(zhǎng)綁在扁擔(dān)上侮辱九次等,女知青記憶中的恐懼感一直圍繞在當(dāng)事人或旁觀者的心靈深處,成為她們永遠(yuǎn)無(wú)法擺脫的噩夢(mèng)。
其次,這種恐懼還是對(duì)不被認(rèn)同的恐懼。幾千年來(lái),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huì)里,女性一直被視作男性的附庸,是男性泄欲和傳宗接代的工具。男權(quán)社會(huì)強(qiáng)加給女性的關(guān)于“三從四德”的規(guī)定已經(jīng)成為女性自覺(jué)不自覺(jué)的主動(dòng)訴求,成為女性是否得到男權(quán)社會(huì)認(rèn)同的標(biāo)準(zhǔn),而最直接的表現(xiàn)就是不能留下把柄。一旦有了把柄,就會(huì)被排除在群體之外,一輩子抬不起頭來(lái)。《玉米》中有慶家的對(duì)于別人發(fā)現(xiàn)她不能生孩子的恐懼以及被王連方侮辱的女性對(duì)玉米的恐懼,都是害怕自己的把柄被人知曉,失去做人的尊嚴(yán),而不能傳宗接代則是她們最大的把柄,是致命的缺陷,正因?yàn)槿绱耍坝袘c家的當(dāng)初是一個(gè)心氣多么旺的姑娘,風(fēng)頭正健,處處要強(qiáng),現(xiàn)在處處不甘,處處難如人意了”,而為了懷孕而吃藥的行為也變得偷偷摸摸,她不想讓人知道她在吃藥,不想讓人知道她有這樣的把柄,害怕被人發(fā)現(xiàn)。即便是像王連方的老婆施桂芳生不出兒子也會(huì)覺(jué)得美中不足。她從第一次懷孕時(shí)的自豪、放肆,“拿自己特別地當(dāng)人”,到后來(lái)對(duì)丈夫的沾花惹草視若不見(jiàn),在鄰居們面前也得陪著笑臉而顯出低眉順眼、客客氣氣的樣子,都是因?yàn)椤斑B著生了幾個(gè)丫頭,她確實(shí)是怕了”,“家里沒(méi)有香火,到底是他們家的話把子”。生不出兒子的事實(shí)使得施桂芳一直處于恐懼之中,這是一種自己作為女人的身份得不到認(rèn)同的恐懼。但當(dāng)她一旦走出生不出男孩的陰影之后,施桂芳就“有了底氣,身上就有了氣焰”,更有了一種“大功告成之后的懈怠”。這種對(duì)把柄的恐懼感還表現(xiàn)為擔(dān)心自己的隱私被人所知道的恐懼,即使是對(duì)于一向在村里高高在上的玉米來(lái)說(shuō)也不止一次有過(guò)這樣的恐懼感受,特別是在她的父親王連方出事之后,玉秀和玉葉被村里人侮辱的事被村里人告訴了遠(yuǎn)在千里之外的彭國(guó)梁,面對(duì)彭國(guó)梁的“你是不是被人睡了”的責(zé)問(wèn),玉米感到了一種恐懼,她感覺(jué)有一種看不見(jiàn)的手在向她伸了過(guò)來(lái),“村里人不僅替玉米看彭國(guó)梁的信,還替玉米給彭國(guó)梁寫(xiě)信”,她所認(rèn)為是私密性的東西對(duì)村人已經(jīng)再無(wú)絲毫秘密可言,已經(jīng)給人留下了把柄。而玉米之所以能夠抱著弟弟站在被她父親睡過(guò)的女性門前揭發(fā)就是因?yàn)樗莆樟诉@些女人們的把柄。女性對(duì)把柄的懼怕既是女性對(duì)男權(quán)文化的屈從與認(rèn)同,更是男權(quán)社會(huì)對(duì)女性壓制的具體表現(xiàn)。
二、面子:虛幻的生存慰藉
面子是畢飛宇想象女性、揭露女性真實(shí)生存境遇并進(jìn)行文化反思的一個(gè)重要,作者的深刻之處在于通過(guò)面子問(wèn)題涉及到了中國(guó)人的深層民族文化心理。“面子不僅涉及到個(gè)人在其關(guān)系網(wǎng)中的地位高低,而且涉及他被別人接受的可能性,以及他可能享受到的特殊權(quán)力。”2小說(shuō)中,面子問(wèn)題已經(jīng)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回避的話題,它與個(gè)人的社會(huì)認(rèn)同以及在群體中的自我身份定位密切相關(guān),甚至成為影響人們生活方式的一個(gè)重要因素。王連方給玉米找對(duì)象,對(duì)面子的關(guān)心甚于對(duì)女兒幸福的考慮,哪怕被革職后,他在面對(duì)如何謀生的問(wèn)題時(shí)還在為面子問(wèn)題糾結(jié)。玉米在考慮讓郭家興給她安排工作時(shí),開(kāi)始想做糧食收購(gòu)站的司磅員后來(lái)又想讓玉秀去做這份工作,考慮的就是為家里掙回一份面子,讓王家莊人只要來(lái)鎮(zhèn)上,都能夠看見(jiàn),即便是在對(duì)待自己與飛行員彭國(guó)梁的愛(ài)情問(wèn)題時(shí)也是考慮面子多于長(zhǎng)相。彭國(guó)梁長(zhǎng)相不好:瘦,顯老,拱嘴,但因?yàn)橛辛孙w機(jī)的襯托就使得玉米“恨不得一口就把這門親事定下來(lái)”,而隔了千山萬(wàn)水的戀愛(ài)方式更是讓玉米的愛(ài)情具有示范性,在得到村里人羨慕的同時(shí)也讓玉米有了面子。
與面子相關(guān)的是丟臉,丟面子。“丟臉是團(tuán)體對(duì)不道德或社會(huì)所不同意之行為的責(zé)難。嚴(yán)重?fù)p害社會(huì)道德規(guī)范之事,一旦為大眾知悉,便構(gòu)成個(gè)人品格上的污點(diǎn),同時(shí)引發(fā)大家的互相責(zé)難。”3對(duì)于女性而言,判斷是否丟臉是以是否違反傳統(tǒng)文化倫理對(duì)女性的社會(huì)以及性別界定為標(biāo)準(zhǔn)的。如果違反那就是丟臉,會(huì)遭到大眾輿論上的批評(píng)與責(zé)難。在男性價(jià)值為主導(dǎo)的社會(huì)文化語(yǔ)境中,男女關(guān)系方面的不檢點(diǎn)可以說(shuō)是女性身上難以被抹去的污點(diǎn),這意味著她們將成為異類而招致群體的攻擊,最終被排除在群體之外。為了不使自己脫離所在群體而被孤立,王家莊的女性對(duì)面子分外敏感,一方面不想別人發(fā)現(xiàn)自己的把柄,另一方面又竭力刺探別人的隱私,在獲得別人把柄的同時(shí)獲得一種精神上的優(yōu)越感,使得自己處于道德的制高點(diǎn),在他人的污點(diǎn)的確證中實(shí)現(xiàn)自我的群體認(rèn)同與自身身份的確認(rèn)。因此,她們對(duì)刺探別人的隱私有著異乎尋常的熱情,《玉秧》中的玉秧,《玉米》與《阿木的婚事》中的老師與村民都是如此。《玉米》中的王家莊到處布滿了窺視的目光,彭國(guó)梁的信總是全村先看了一遍,然后才輪到她玉米。刺探別人的隱私,捏著別人的把柄,看著別人恐懼的目光,是她們最為樂(lè)衷的事。窺探欲得到滿足后,她們就會(huì)擺出一副天知地知的派頭,有一種捏著他人把柄后的得意,在對(duì)別人的痛處加以踐踏的同時(shí)獲得自我認(rèn)同的快感。
值得注意的是,畢飛宇的小說(shuō)還揭示了一種獨(dú)特的面子邏輯,而這正是中國(guó)獨(dú)特生活哲學(xué)的表現(xiàn),反映出人們面對(duì)生存困境時(shí)的無(wú)奈與自欺欺人。小說(shuō)中無(wú)論是在城市抑或是在鄉(xiāng)村,判斷是否丟面子的關(guān)鍵不在于是否有丟臉的行為,而是在于是否為公眾所知。即使是為大眾知悉,但只要沒(méi)有當(dāng)面指出就不算丟了臉面,即使有些事情大家心知肚明,但只要不說(shuō)出來(lái),就可以當(dāng)做沒(méi)有這回事。這種心理不僅在女性身上存在,在男性身上也存在,如《玉米》《阿木的婚事》《武松打虎》中的許多人都知道自己的老婆曾經(jīng)被村里的當(dāng)權(quán)者睡過(guò),但只要沒(méi)有人挑明了,他們就可以裝著不知道。正如作者在《家里亂了》中所寫(xiě)的那樣,“丟臉面的事從來(lái)就這樣,只要沒(méi)人知道,丟了可以再撿回來(lái),重新貼到臉上去的。”4面子已經(jīng)成為女性苦難生活的一塊遮羞布,讓她們暫時(shí)忘卻現(xiàn)實(shí)的疼痛而帶來(lái)某種生存慰藉。
三、抗?fàn)幣c認(rèn)同:悖論中的生存悲劇
女性是男權(quán)社會(huì)的弱者,在男性為主導(dǎo)的社會(huì)文化之中始終擺脫不了被男性壓制與囚禁的命運(yùn)。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yùn),許多女性試圖通過(guò)獲取權(quán)力來(lái)凸顯自身的價(jià)值與女性的主體地位。但值得深思的是女性獲得權(quán)力的方式都離不開(kāi)對(duì)于男性的依賴以及對(duì)于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的認(rèn)同,她們?cè)趯?duì)男權(quán)的反抗與認(rèn)同的矛盾中落入一個(gè)悖論性的生存怪圈而漸漸迷失。
小說(shuō)中的女性面對(duì)壓抑的生存處境,她們努力抗?fàn)帲鴬Z取權(quán)力成為其主要的手段。在王家莊人眼中,玉米是高高在上有權(quán)力的,她可以在家里管教妹妹,在王家莊指責(zé)與其父親有染的女性,在斷橋鎮(zhèn)安排妹妹玉秀進(jìn)糧食收購(gòu)站做司磅員等。而與玉米相比,吳蔓玲作為大隊(duì)支部書(shū)記權(quán)力更大,她可以影響王家莊許多人的命運(yùn),可以決定知青混世魔王的去留,可以相對(duì)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從深層次來(lái)看,玉米與吳蔓玲所擁有的權(quán)力都與她們對(duì)男性的依附有關(guān),她們都是依靠男性來(lái)獲得權(quán)力,得到社會(huì)輿論的認(rèn)同,這在玉米的身上表現(xiàn)得比較明顯。在玉米的身后都有一個(gè)男性的身影,她的權(quán)力是與其身上的男性標(biāo)簽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王家莊,她身上貼的標(biāo)簽是村支書(shū)的女兒,未來(lái)的飛行員妻子;在斷橋鎮(zhèn),她身上貼的標(biāo)簽是革委會(huì)副主任的妻子;哪怕在家里,她身上貼的標(biāo)簽是王連方的長(zhǎng)女,而這其中恰恰沒(méi)有她自己身份的定位。在家里她依附于王連方這個(gè)一家之主,在家外她依附于父親王連方與丈夫郭家興這兩個(gè)擁有權(quán)力的男性。而吳蔓玲的威信也不是由于自己的親和力建立起來(lái)的,而是洪主任的一句戲言“前途無(wú)量”。可以看出,女性的獨(dú)立離不開(kāi)對(duì)于男性的依賴,女性自我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依附于男性的肯定與認(rèn)同。
作者并沒(méi)有停留在對(duì)女性依附性生存策略的表面書(shū)寫(xiě)之中,他不僅僅揭示出女性在追求自由的過(guò)程中對(duì)男權(quán)文化的抗?fàn)幰约皟?nèi)心的煎熬與疼痛,而是進(jìn)一步揭示出她們?cè)趯?duì)男權(quán)的抗?fàn)幣c認(rèn)同之間搖擺的悲劇性的生存悖論。為改變自己的生存處境,她們有的利用身體來(lái)?yè)Q取家人以及自己的安全;有的出賣自己的肉體,用自己的身體換得權(quán)力;有的甚至為得到男權(quán)社會(huì)的認(rèn)同而主動(dòng)放棄自己的女性身份。具體來(lái)說(shuō),玉米就是利用自己的身體來(lái)獲得權(quán)力的典型。對(duì)于權(quán)力,玉米自己有著清醒的認(rèn)識(shí),小時(shí)候的耳濡目染讓她確定地知道權(quán)力的重要。在父親出事,妹妹被侮辱、自己的愛(ài)情遭到背叛的情況下,她決然地選擇去做郭家興的填房來(lái)保護(hù)自己與自己的家人,她對(duì)自己結(jié)婚對(duì)象的要求只有一個(gè)——那就是“有權(quán)”。只有依附于郭家興這個(gè)有權(quán)的男人,她們家才會(huì)繼續(xù)保持以前的地位。玉米做了郭家興的填房,看似無(wú)限風(fēng)光,但卻是以出賣自己的肉體與女性的尊嚴(yán)為代價(jià)的。女性對(duì)男權(quán)文化的反抗結(jié)果卻是導(dǎo)致她們向男權(quán)進(jìn)一步靠攏與順從。正如小說(shuō)中玉秀所感受的那樣,“別看玉米在王家莊的時(shí)候人五人六的,到了這個(gè)家里,玉米其實(shí)什么都不是。”另外,她之所以可以站在受她父親侮辱過(guò)的女人門前示威、揭發(fā),所倚仗的不僅是他父親作為村支書(shū)所具有的權(quán)力,還依仗男權(quán)為中心價(jià)值體系中對(duì)女性貞潔方面的要求,甚至在家中她對(duì)妹妹的管束也是依仗傳統(tǒng)文化倫理中的長(zhǎng)幼有序觀念以及父親的默許。而《平原》中的吳蔓玲一直試圖通過(guò)自己的努力來(lái)實(shí)現(xiàn)自己的價(jià)值,她在言行舉止等各方面向王家莊人靠攏,壓抑自己的情感渴望,甚至放棄女性的身份,提出“要做男人,不做女人”的口號(hào),她一次次放棄離開(kāi)王家莊的機(jī)會(huì),堅(jiān)信只要堅(jiān)持住,她就會(huì)“前途無(wú)量”,她試圖以擁有權(quán)力來(lái)確證女性獨(dú)立的同時(shí)也是以放棄女性的主體意識(shí)為代價(jià)的,在追求女性獨(dú)立的過(guò)程中女性獨(dú)特的生理、心理方面的特征被忽視、被壓抑,男性社會(huì)對(duì)女性官員的角色定位左右著她的人生,結(jié)果只能是她在追逐權(quán)力的過(guò)程中逐漸迷失。可以看出,一方面女性試圖努力擺脫男性對(duì)他們的傷害,體現(xiàn)女性自身存在的意義,但另一方面她們的抗?fàn)幱质橇硪环N形式的對(duì)男性的順從,是對(duì)她們所反抗的價(jià)值體系的一種回歸與確認(rèn)。而這種生存的悖論最終導(dǎo)致女性在抗?fàn)幹兄饾u迷失,直至異化。
總之,畢飛宇的女性想象注重日常生活瑣事的描摹,在女性的不甘、掙扎以及疼痛的書(shū)寫(xiě)中反思文化對(duì)女性生存境遇的影響,并進(jìn)一步揭示出鄉(xiāng)村女性悲劇性的生存悖論:面對(duì)強(qiáng)大男權(quán)文化傳統(tǒng),她們一方面不斷努力抗?fàn)巵?lái)實(shí)現(xiàn)自身的價(jià)值,但另一方面,她們用來(lái)反抗男權(quán)的基礎(chǔ)卻是對(duì)以男性為主導(dǎo)的價(jià)值體系的認(rèn)同,與女性意識(shí)的覺(jué)醒相伴的卻是自我的淪喪。
注釋:
1.畢飛宇.《玉米》.作家出版社,2005:38.
2.3.黃光國(guó)等著.《面子:中國(guó)人的權(quán)力游戲》.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4:20、40.
4.畢飛宇.《畢飛宇文集·輪子是圓的》.江蘇文藝出版社,2004:188.
田祝,(1973-),男,漢族,江蘇阜寧人,淮陰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副教授,文學(xué)碩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
本文為江蘇省教育廳社科基金項(xiàng)目:“文化視野中的畢飛宇小說(shuō)研究”(編號(hào):2012JSB75000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