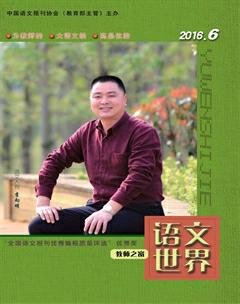語(yǔ)文:人話·人性·人文
葉水濤
荷蘭童話《小約翰》里,小約翰聽(tīng)到兩種菌類在爭(zhēng)論,他從旁說(shuō)了一句:“你們倆都是有毒的。”菌們便驚喊道:“你是人嗎?這是人話啊!”魯迅先生評(píng)論說(shuō):“從菌類的立場(chǎng)看起來(lái),的確應(yīng)該驚喊的。人類因?yàn)橐运鼈儯攀紫茸⒁庥谟卸净驘o(wú)毒,但在菌們自己,這卻完全沒(méi)有關(guān)系,完全不成問(wèn)題。”
語(yǔ)文,無(wú)論口頭之語(yǔ),還是書面之文,都是人之所言,說(shuō)的是人話,講給人聽(tīng),或給人看。語(yǔ)文,首先要有人的立場(chǎng)。語(yǔ)文教學(xué)是教師與學(xué)生的對(duì)話,是人與人情感的交流、思想的切磋。這種對(duì)話、交流與切磋須憑借語(yǔ)言,語(yǔ)言越準(zhǔn)確生動(dòng),越能吸引人、打動(dòng)人,越能起到交流、切磋的效果。語(yǔ)文無(wú)疑是人的工具,服務(wù)于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也為生命成長(zhǎng)的精神需要,必須培養(yǎng)學(xué)生語(yǔ)言文字的運(yùn)用能力,這是語(yǔ)文教學(xué)的根本任務(wù)。語(yǔ)言是人類的文化創(chuàng)造,語(yǔ)文學(xué)科是使人格完善、人性美好的人文學(xué)科。人類的話語(yǔ)區(qū)別于菌類的話語(yǔ),全在人性之有無(wú),而非語(yǔ)言運(yùn)用水平之高下。語(yǔ)文教學(xué)必須聚焦于人。
語(yǔ)文教學(xué)如果偏執(zhí)于工具性,形式化地聚焦于“語(yǔ)用”,就可能南轅北撤、適得其反。語(yǔ)言是存在的家園,抽掉思想性,便無(wú)所謂語(yǔ)言;抽掉人性,語(yǔ)言便不復(fù)有任何價(jià)值。語(yǔ)言運(yùn)用的水平,緊緊地關(guān)聯(lián)著人的思想水平與情感的豐富性。語(yǔ)文教學(xué)不能導(dǎo)向于無(wú)源之水、無(wú)本之木的文字游戲。語(yǔ)文并非純粹的交際工具,它有美育的使命,有著更新人們感性經(jīng)驗(yàn)和情感世界的意義。
博爾赫斯的小說(shuō)文本晦澀難解,但他文學(xué)批評(píng)的文字平易從容,表述精準(zhǔn)、簡(jiǎn)約,顯示出如秋夜星空般的清朗寧?kù)o和深邃、冬日暖陽(yáng)般的溫情和寬容氣度。他評(píng)價(jià)羅曼·羅蘭:“他的優(yōu)點(diǎn),道義上的多于文學(xué)上的,用他愛(ài)聽(tīng)的幾個(gè)詞匯之一來(lái)說(shuō),就是‘泛人道主義的多于句法上的。”對(duì)羅蘭的藝術(shù)成就不無(wú)微詞,卻又委婉表達(dá)了對(duì)作品人道精神的稱贊。這是語(yǔ)言的藝術(shù),取決于他藝術(shù)的眼光和思想的高度。
語(yǔ)言是人情、人性的自然流露。兒童的語(yǔ)言習(xí)得和語(yǔ)文學(xué)習(xí),要從說(shuō)真話開(kāi)始。語(yǔ)文教學(xué)大可不必處處標(biāo)榜偉大和高貴,事事扯上服務(wù)與奉獻(xiàn),刻意地掛上各種招牌,如魯迅先生所諷刺的,吃西瓜也念念不忘國(guó)家領(lǐng)土被分割。海德格爾說(shuō):“詞語(yǔ)破碎之處無(wú)物存在。”語(yǔ)文教學(xué)要扣住語(yǔ)言,要突出對(duì)語(yǔ)言的品味,加強(qiáng)語(yǔ)言的訓(xùn)練,著眼對(duì)特定語(yǔ)境中詞匯、句式的理解。非如此不能讀懂文本,非如此不能掌握語(yǔ)言,非如此不能達(dá)到心靈的溝通——作者包含其間的言外之意與題外之旨。
1978年3月,楊絳飽含心血的譯作、72萬(wàn)字的《堂吉訶德》出版,這是直接從西班牙文譯為中文的第一個(gè)版本,人們排著長(zhǎng)隊(duì),將首印的10萬(wàn)冊(cè)搶購(gòu)一空。《堂吉訶德》為楊絳帶來(lái)了極高的社會(huì)聲譽(yù)。西班牙授予她“智慧國(guó)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勛章”,國(guó)內(nèi)學(xué)界對(duì)她更是好評(píng)如潮。然而,卻有一位年輕的翻譯工作者,對(duì)照著詞典說(shuō)楊絳的翻譯多有不當(dāng)之處,自稱能比楊絳譯得準(zhǔn)確。
語(yǔ)言不僅有規(guī)范性的工具之“用”,更有獨(dú)創(chuàng)性的人文之“思”。翻譯并非不同語(yǔ)言之間的簡(jiǎn)單轉(zhuǎn)換,更不是詞典條文的忠實(shí)詮釋,而是以詩(shī)意的形式建立一個(gè)人性的世界。高明的文學(xué)翻譯是使死亡的語(yǔ)言復(fù)活,使凝固的概念燃燒,從而以獨(dú)特的心智去尋覓存在的意義,并將沉淪的人性喚醒。海德格爾認(rèn)為,語(yǔ)言必須超越一切規(guī)范,才能回歸“思”的本質(zhì)。這是語(yǔ)言魅力之所在,當(dāng)然也是語(yǔ)文教學(xué)價(jià)值之所在。
借名人以炒作,激起了人們共同的憤怒。而楊絳只是云淡風(fēng)輕地說(shuō):“他譯得比我好。我老了,不能拜他為師了。”這種淡泊、泰然、優(yōu)雅的語(yǔ)言,顯然是精神的境界而非僅是說(shuō)話的藝術(shù)了。可見(jiàn),對(duì)一種語(yǔ)言的把握,須先有人文的情懷,才能有“語(yǔ)用”的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