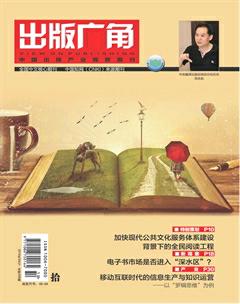基于使用與滿足理論的受眾需求研究
楊淑娥 陳敬慧
【摘要】社交媒體的繁榮帶來(lái)了紅包的火熱。在微信飛速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微信紅包一開始就受到廣大用戶的熱捧。微信紅包與春晚聯(lián)手,走過(guò)2014年、2015年,來(lái)到2016年,締造了移動(dòng)支付領(lǐng)域的奇跡。本文通過(guò)簡(jiǎn)述微信紅包的起源和發(fā)展,從使用與滿足理論重點(diǎn)探求微信紅包的受眾需求。
【關(guān)鍵詞】微信;微信紅包;受眾
【作者單位】楊淑娥,陜西財(cái)經(jīng)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陳敬慧,吉林工商學(xué)院。
在2014年1月閃亮登場(chǎng)的微信紅包,在2015年春節(jié)繼續(xù)演繹傳奇,2016年更是擔(dān)當(dāng)主角,掀起全民瘋搶紅包的熱潮。新年發(fā)紅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習(xí)俗,紅包寄托了親朋好友的祝福,而伴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微信紅包開始興起。跨界融合、去中心化等特點(diǎn)顛覆了人們的傳統(tǒng)認(rèn)知,滿足了受眾需求,一種全新的移動(dòng)生活方式悄然興起。
一、微信紅包的起源和發(fā)展
2014年1月27日,騰訊旗下微信正式推出微信紅包,主要用于紅包的收發(fā)、提現(xiàn)和查閱相關(guān)記錄。微信紅包有兩種:一種是群紅包,一種是普通紅包。群紅包發(fā)送方法為用戶事先設(shè)定金額及紅包個(gè)數(shù),隨機(jī)分配金額,群里其他人只要點(diǎn)擊群里的紅包圖案即可瘋搶紅包;普通紅包發(fā)送方法即用戶隨意設(shè)定金額并輸入祝福話語(yǔ),定向發(fā)送給個(gè)人。
據(jù)統(tǒng)計(jì),2014年即有500萬(wàn)人參加紅包活動(dòng),春晚峰值每分鐘被拆開紅包數(shù)量2.5萬(wàn)個(gè),用戶領(lǐng)取到的紅包總計(jì)2000萬(wàn)個(gè)。
2015年,據(jù)微信團(tuán)隊(duì)披露,除夕當(dāng)天,微信紅包收發(fā)總數(shù)為10.1億,是去年的200倍,QQ紅包收發(fā)量達(dá)到6.37億。微信與央視春晚的互動(dòng),引發(fā)全民互動(dòng)的熱潮。
2016年的春節(jié)再一次被微信紅包引爆。根據(jù)騰訊網(wǎng)統(tǒng)計(jì),除夕夜參與收發(fā)微信紅包人數(shù)為4.2億,收發(fā)總量高達(dá)80.8億個(gè),是2015年春節(jié)除夕當(dāng)日的8倍。
二、微信紅包背后的使用與滿足理論
微信紅包為何能夠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受眾,究竟?jié)M足了受眾什么需求?使用與滿足研究把受眾成員看作是有著特定“需求”的個(gè)人,把他們的媒介接觸活動(dòng)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動(dòng)機(jī)來(lái)“使用”媒介,從而使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的過(guò)程[1]。人們接觸傳媒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他們的特定需求,這些需求具有一定的社會(huì)和個(gè)人心理起源;實(shí)際接觸行為的發(fā)生需要兩個(gè)條件:一是媒介接觸的可能性,二是媒介印象,即媒介能否滿足自己的現(xiàn)實(shí)需求,這是建立在以往媒介接觸的經(jīng)驗(yàn)之上的;根據(jù)媒介印象,人們選擇特定的媒介或內(nèi)容開始具體的接觸行為[1]。
根據(jù)中國(guó)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信息中心(CNNIC)第37次《中國(guó)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fàn)顩r統(tǒng)計(jì)報(bào)告》顯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國(guó)網(wǎng)民規(guī)模達(dá)6.88億,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達(dá)50.3%,互聯(lián)網(wǎng)用戶數(shù)量飛速膨脹,這就具備了受眾接觸媒介的可能性;媒介印象,即媒介能否滿足自己現(xiàn)實(shí)需求的評(píng)價(jià),根據(jù)2014年、2015年受眾對(duì)于微信紅包的參與和體驗(yàn),微信受眾對(duì)于微信紅包已經(jīng)有了自己的認(rèn)知和評(píng)價(jià),尤其是其互動(dòng)性、娛樂性和新穎性等媒介印象更加能夠吸引受眾參與其中。
三、火熱的微信紅包對(duì)受眾的需求滿足分析
1.高黏度社交功能滿足社交需求
作為一款極受歡迎的社交軟件,企鵝智酷2016版《微信數(shù)據(jù)化報(bào)告》顯示:超過(guò)9成微信用戶每天都會(huì)使用微信;6成以上用戶每天打開微信超過(guò)10次;55%的用戶每天使用微信超過(guò)1小時(shí);32%的用戶每天使用微信超過(guò)2小時(shí)。2015年,55.1%的微信用戶好友數(shù)在100人以上,200人以上的微信用戶比例最高,達(dá)28%。在微信社交平臺(tái)上迅猛發(fā)展起來(lái)的微信紅包本身具有極高的社交性,自然構(gòu)建了用戶的人脈體系。用戶搶紅包的過(guò)程進(jìn)一步促進(jìn)了彼此的交流和互動(dòng)。
社會(huì)認(rèn)同理論是由英國(guó)社會(huì)心理學(xué)家提出的,該理論認(rèn)為,人們對(duì)于積極的社會(huì)同一性有著不懈的追求[2]。每個(gè)人都不希望被排斥,都希望和團(tuán)體保持一致。人人都在發(fā)紅包,人人都在搶紅包,大家共同參與的感覺使得受眾不會(huì)有一種被排斥感和孤獨(dú)感。微信紅包成為春節(jié)期間親朋好友彼此聯(lián)絡(luò)感情、分享喜悅的情感利器。只要有人發(fā)紅包,群里氣氛立馬活躍。作為具有社會(huì)性的人,需要?dú)w屬感和認(rèn)同感,收發(fā)紅包實(shí)質(zhì)上是一種用戶社交行為,是一種包含著彼此溫度的情感鏈接。由熟人關(guān)系建立起來(lái)的微信朋友圈,本身的小眾化、私密性等特征具有超強(qiáng)的信息黏合度,重新搭建了人際傳播的橋梁。群紅包瘋搶過(guò)程中,每個(gè)人發(fā)紅包和收紅包的數(shù)量清晰可見。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用戶搶的紅包數(shù)量越多,象征著人際關(guān)系越好,微信紅包被賦予了較高的社交屬性,將用戶重新拉回人際傳播的軌道。
微信最大的優(yōu)勢(shì)在于其關(guān)系鏈,市民的消費(fèi)習(xí)慣和生活方式逐步被新的潮流所改變。無(wú)論是點(diǎn)對(duì)點(diǎn)的傳播方式,還是群聊中點(diǎn)對(duì)面的傳播,本質(zhì)上都是一種共享和互動(dòng),是傳受雙方彼此平等的交流和對(duì)話。
2.紅包的趣味性滿足受眾對(duì)娛樂的需求
無(wú)論是點(diǎn)對(duì)點(diǎn)普通紅包的發(fā)放,還是群里拼手氣紅包的發(fā)放都獲得了大家的追捧。在這個(gè)一切皆?shī)蕵返淖悦襟w時(shí)代,微信紅包平臺(tái)單個(gè)發(fā)放紅包最大金額為200元,群紅包也不會(huì)超過(guò)2000元,物質(zhì)意義并不大,而蘊(yùn)含在其中的發(fā)紅包和搶紅包的個(gè)性體驗(yàn)卻讓人們樂此不疲。比如,拼手氣紅包,只要有人發(fā)紅包,即會(huì)引發(fā)大家爭(zhēng)先恐后地點(diǎn)擊。在紅包發(fā)放中,紅包數(shù)量往往低于群內(nèi)人員數(shù)量,這就要求大家眼疾手快、先到先得,第一時(shí)間拼搶,而且微信紅包設(shè)計(jì)的“手氣最佳”更是不斷調(diào)動(dòng)了參與者的積極性。
娛樂與趣味性是微信紅包最為突出的特性之一。用戶在搶奪紅包的過(guò)程中,獲得了情緒上的消遣和放松,身體和心理得以減壓。微信群紅包金額和人數(shù)的不確定性更是增加了微信紅包的趣味性和互動(dòng)性。在湖南電視臺(tái)曾經(jīng)制作的一期“微信紅包為什么這么火”的節(jié)目中,受訪者均表示搶紅包是為了圖開心,和金額大小無(wú)關(guān)。而發(fā)紅包者很多時(shí)候也不是抱著發(fā)紅包的目的,而是為了一種娛樂,希望享受紅包被瘋搶的愉快感覺。從心理學(xué)上來(lái)說(shuō),游戲不僅能夠令人感到愉快,還能夠消弭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各種不快[3]。
3.新穎獨(dú)特的形式滿足受眾全新的體驗(yàn)需求
受眾新型的傳播交流方式,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基于微信平臺(tái)上的微信紅包,自誕生之日即具有引領(lǐng)潮流的創(chuàng)新性。從空間上而言,無(wú)論天涯海角,用戶輕輕按下發(fā)送,紅包即刻飛到對(duì)方手中;從時(shí)間上而言,無(wú)論逢年過(guò)節(jié)還是平淡的日子,用戶想發(fā)就發(fā)、隨時(shí)隨地,毫無(wú)顧忌;從意義上而言,傳統(tǒng)的紅包僅僅在過(guò)年的時(shí)候由長(zhǎng)輩發(fā)給晚輩,微信紅包不僅僅在新春佳節(jié)來(lái)臨之際被廣泛發(fā)送,還可以用來(lái)給朋友發(fā)送祝福,或者給愛人傳遞愛意。
微信這一社會(huì)化媒體平臺(tái)為受眾提供一種新的內(nèi)容形態(tài)和傳播模式,注重個(gè)人體驗(yàn),逐步將話語(yǔ)權(quán)由權(quán)威媒體轉(zhuǎn)移至受眾個(gè)體,受眾積極性被調(diào)動(dòng)。發(fā)紅包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習(xí)俗,微信電子紅包將傳統(tǒng)春節(jié)紅包的發(fā)送和人們普遍使用的電子錢包相結(jié)合,并且通過(guò)設(shè)計(jì)紅包游戲的環(huán)節(jié),將游戲的手法應(yīng)用到微信紅包之中,符合受眾求新鮮、求新穎的心理。人們的注意力已經(jīng)由關(guān)注紅包的金額大小轉(zhuǎn)移到微信紅包游戲所帶來(lái)的新鮮感上面來(lái)。紅包不再是長(zhǎng)輩的特權(quán),傳受雙方地位平等,任何一個(gè)微信用戶都可以成為紅包的給予者。微信拼手氣紅包設(shè)計(jì)的玩法相當(dāng)吸引人,發(fā)放者設(shè)定金額和個(gè)數(shù),微信紅包隨機(jī)分配,這種完全隨機(jī)的設(shè)置帶給大家的個(gè)性化體驗(yàn)更為重要。在重視個(gè)性化傳播的新媒體環(huán)境下,微信紅包給用戶帶來(lái)全新的體驗(yàn)意義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紅包的物質(zhì)意義。
4.鮮明的利益性滿足企業(yè)和普通用戶對(duì)于利益的需求
微信紅包對(duì)于企業(yè)利益的滿足體現(xiàn)在:自2015年春節(jié),騰訊與央視春晚合作,提供搶紅包入口,用戶通過(guò)搖一搖春晚專題互動(dòng)頁(yè)面,春晚主持人在節(jié)目進(jìn)行中用語(yǔ)言引導(dǎo)用戶進(jìn)入微信搖一搖,紅包并非由微信提供,而是由廣告主贊助。用戶搶到的紅包將進(jìn)行廣告提示“某某企業(yè)給你發(fā)了一個(gè)紅包”,然后通過(guò)分享好友,讓好友助力拆紅包,通過(guò)紅包多次分享到微信群和朋友圈等社交網(wǎng)絡(luò),廣告主在微信裂變式傳播中獲得較好的品牌營(yíng)銷效果。據(jù)《2015春晚微信紅包品牌召集簡(jiǎn)案》顯示,廣告品牌商有兩種參與方式:一種是品牌包段,即能夠參與春晚相關(guān)時(shí)段的品牌獨(dú)占和零點(diǎn)紅包;一種是隨機(jī)紅包,即只參與零點(diǎn)紅包,品牌曝光根據(jù)紅包占比來(lái)衡量。春晚和微信新媒體平臺(tái)合作,通過(guò)微信搖一搖給所有觀眾發(fā)放紅包,廣告悄然映入受眾眼簾。通過(guò)微信綁定銀行的用戶不斷增加,也給微信帶來(lái)不小的盈利。
微信對(duì)普通用戶利益的滿足表現(xiàn)在:美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霍曼斯的“社會(huì)交換理論”認(rèn)為,社會(huì)互動(dòng)過(guò)程中的社會(huì)行為是一種交換行為,不僅包括物質(zhì)商品的交換,還包括贊許、榮譽(yù)或聲望等非物質(zhì)的交換[4]。微信紅包滿足了部分受眾貪圖小便宜的心理,每當(dāng)搶到紅包時(shí),這些受眾總會(huì)有一種錢包又鼓了一點(diǎn)的感覺。而互聯(lián)網(wǎng)營(yíng)銷的一種有效手段就是讓用戶占便宜,試圖滿足對(duì)方利益最大化的心理。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曬出用戶獲獎(jiǎng)紅包金額,央視春晚、微信攜手眾多品牌贊助商派出5億現(xiàn)金紅包,更是吸引很多用戶的目光,體現(xiàn)出用戶的求利心理。
5.收發(fā)微信祝福紅包滿足了用戶傳承文化的需求
過(guò)年發(fā)紅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習(xí)俗。電子紅包緊隨潮流,將傳統(tǒng)春節(jié)紅包與互聯(lián)網(wǎng)結(jié)合,在跟隨新媒體社交網(wǎng)絡(luò)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也沒有遺忘春節(jié)的傳統(tǒng)。微信紅包源自科技發(fā)展,但這種創(chuàng)新根源上來(lái)自傳統(tǒng)春節(jié)紅包習(xí)俗。雖然電子紅包在傳播方式和傳播對(duì)象上與傳統(tǒng)習(xí)俗有異,但其祝福語(yǔ)的發(fā)送也是希望借助紅包的喜氣祈福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能夠平平安安、順順利利。
北京大學(xué)心理學(xué)博士李松蔚曾說(shuō):“在網(wǎng)上的關(guān)系中,我們能傳遞的只有冷冰冰的數(shù)據(jù),最終,我們找到了一種帶有溫度的數(shù)據(jù),就是紅包。這讓我想起小時(shí)候的新春游園會(huì),獎(jiǎng)品不值錢,卻總能收獲比錢更多的快樂。新時(shí)代的人類想出這種新的聯(lián)結(jié)方式,也算是一樁好事。” [5]從文化意義上來(lái)講,大家搶的是新年的祝福和運(yùn)氣。包餃子、放鞭炮和壓歲錢作為傳統(tǒng)習(xí)俗,再加上微信紅包好友之間的互動(dòng)和祝福,新年氣氛有漲無(wú)落。傳統(tǒng)文化的精粹也需要我們代代傳承并且不斷被賦予新的生機(jī)和活力。
6.發(fā)搶紅包的互動(dòng)性滿足受眾參與的快感
網(wǎng)絡(luò)虛擬社區(qū)為受眾營(yíng)造了一種交互體驗(yàn)的虛擬情境。微信紅包最吸引人之處在于“搶”。“搶紅包”激發(fā)了用戶內(nèi)在的獵食心理,人們參與搶紅包的主動(dòng)性被調(diào)動(dòng),在搶電子紅包的過(guò)程中,受眾能夠充分體驗(yàn)到參與的快感。搶紅包作為全民狂歡的新民俗,如果自己不去參與或多或少都有一種被逐漸舍棄的孤單感,并且在微信紅包瘋搶的過(guò)程中,傳播者和接受者彼此身份不斷轉(zhuǎn)換,受眾的主動(dòng)性被激發(fā),完全顛覆了傳統(tǒng)的春節(jié)紅包單向發(fā)放、單向接收的方式。每當(dāng)微信群里出現(xiàn)一句簡(jiǎn)單的“發(fā)紅包了!”,無(wú)數(shù)好友紛紛開搶,彼此不斷“發(fā)”,不斷“搶”,這也促進(jìn)了親朋好友之間的情感互動(dòng)交流,烘托了節(jié)日氣氛。
7.微信紅包簡(jiǎn)捷性滿足受眾快節(jié)奏的生活需求
在快節(jié)奏的信息時(shí)代,人們主動(dòng)選擇媒介并且希望在接觸媒介的過(guò)程中快捷、清晰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而微信紅包的設(shè)計(jì)恰恰符合受眾的需求。微信紅包既可以直接發(fā)送至微信好友,也可以直接發(fā)送微信群,發(fā)送步驟相當(dāng)簡(jiǎn)單。用戶只要點(diǎn)擊微信紅包,輸入個(gè)數(shù)、金額,將祝福語(yǔ)寫好,綁定一張銀行卡,輸入相應(yīng)金額和支付密碼即可完成支付,將紅包傳遞給對(duì)方。微信紅包簡(jiǎn)單易用,無(wú)任何高難度門檻限制,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紅包。微信紅包接收方式則更為輕松,即便尚未開通銀行卡也可以直接領(lǐng)取,用戶只要想提現(xiàn),直接綁定銀行卡即可。現(xiàn)實(shí)中,在以微信和支付寶為代表的移動(dòng)互聯(lián)APP影響下,我們正越來(lái)越習(xí)慣、依賴移動(dòng)互聯(lián)技術(shù)所帶來(lái)的各種便利[6]。
微信平臺(tái)基礎(chǔ)上的微信紅包點(diǎn)燃了全民的參與熱情。高黏度社交功能滿足了受眾社交需求;紅包的趣味性滿足了受眾的娛樂需求;新穎獨(dú)特的形式滿足了受眾全新的體驗(yàn)需求;鮮明的利益性滿足各類用戶對(duì)利益的需求;收發(fā)微信祝福紅包滿足了用戶傳承文化的需求;發(fā)搶紅包的互動(dòng)性滿足了受眾參與的快感;發(fā)搶微信紅包的簡(jiǎn)捷性滿足了受眾快節(jié)奏的生活需求。微信紅包在迅猛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用戶資金的安全隱患、用戶身體機(jī)能下降和現(xiàn)實(shí)交流被淡化等問題。因此,微信紅包之“紅”固然讓受眾喜愛,令客戶青睞,但其發(fā)展過(guò)程中還需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監(jiān)管和防范,讓以微信紅包為代表的新型交流傳播模式持續(xù)“紅”下去。
[1]郭慶光. 傳播學(xué)教程 [M]. 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8:180.
[2]孫科炎. 社交心理學(xué)[M]. 北京:中國(guó)電力出版社,2012:4.
[3]唐映紅. 紅包照耀中國(guó)[EB/OL]. http://dajia.qq.com/ blog/469069070381283,2015-01-19.
[4]薛可,余明陽(yáng). 人際傳播學(xué)[M]. 上海:同濟(jì)大學(xué)出版社,2007:91.
[5]幸暉暉,王衛(wèi)明.“紅包大戰(zhàn)”參與者的行為與動(dòng)機(jī)分析[J]. 東南傳播,2015(7).
[6]仝冠軍. 從“二馬之爭(zhēng)”想到出版改革[J]. 出版廣角,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