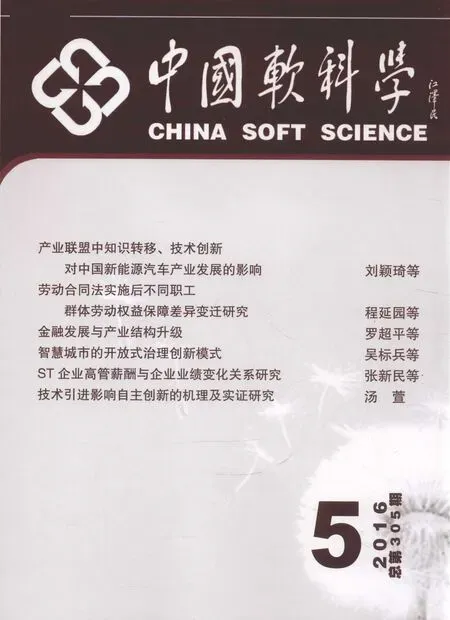全球經濟失衡:來自國際貨幣失衡的解釋
王 芳,李霄陽
(中國人民大學 財政金融學院,北京 100872)
?
全球經濟失衡:來自國際貨幣失衡的解釋
王芳,李霄陽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北京100872)
全球經濟失衡具體表現為美國經常賬戶差額的持續惡化。本文在現有文獻基礎上,深入研究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偏離世界經濟貿易格局而引起的國際貨幣失衡問題,進而探討了國際貨幣失衡與全球經濟失衡之間的關系。首先,構建了高度簡化的理論分析框架,并推導證明:在美國貿易地位下降而美元國際地位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美國經常賬戶惡化將不可避免。該判斷與歷史經驗相吻合。其次,本文構造了用于測度國際貨幣格局偏離貿易格局程度的貨幣失衡指標,使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進行時間序列分析,發現國際貨幣失衡與全球經濟失衡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作者認為,只有提升新興貿易大國貨幣地位,降低貨幣失衡程度,才能實質性地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
全球經濟失衡;國際貨幣失衡;特里芬難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美國經常賬戶差額再一次發生持續惡化。這被認為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具體表現(de Rato, 2005)[1],很多學者對其形成的原因與產生的影響深感憂慮。Wolf (2004)[2]將美國持續惡化的經常賬戶逆差稱為“不可持續的黑洞”,Obstfeld 和 Rogoff (2005)[3]則認為這種失衡現象是懸在全球經濟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意為時刻存在的危險。典出古希臘傳說故事,希臘原文Δαμóκλειο σπáθη。中文也稱“懸頂之劍”。
全球經濟失衡有著諸多的經濟危害。在效率方面,美國通過資本賬戶借入資金來平衡經常賬戶逆差,導致資本從相對稀缺的發展中國家匯集到了資本相對充足的美國。從全球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這種安排是低效率的。在公平性方面,美國通過持續的擴大債務規模為經常賬戶逆差進行融資的做法,客觀上侵害了其債權國的利益,這種安排同樣被視為是有失公允的。除此之外,美國經常賬戶逆差自身的可持續性,也對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構成了潛在威脅。如果該問題最終以國際收支危機甚至貨幣危機的形式爆發,那么國際貨幣體系將難免再次陷入激烈動蕩。
全球經濟失衡的危害并不局限在經濟層面,還會引發不同國家間的意見分歧和政策摩擦。美國將其經常賬戶的惡化歸結為發展中國家對本幣的刻意低估;而發展中國家則責怪美國過度消費,產生巨大的投資-儲蓄缺口。雙方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大有劍拔弩張之勢,以至于時任IMF總裁都要公開呼吁各國應避免在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上相互指責(de Rato, 2005)。
想要探究全球經濟失衡的本質,并找出合適的解決辦法,必須從分析全球經濟失衡的成因入手。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國際金融理論與歷史經驗,提出國際貨幣格局偏離世界經濟貿易格局而引起的國際貨幣失衡是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形成機制。更進一步地,還通過構建相關指標,使用計量方法證明了美元超級貨幣地位偏離美國貿易地位對美國經常賬戶惡化的解釋力,并為實質性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指明了方向。
二、文獻綜述
已經有大量學者針對全球經濟失衡展開研究,從不同視角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形成原因給出了解釋。
一部分學者從美國的交易對手方入手,試圖用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特點來解釋全球經濟失衡。比如,Obesfeld 和 Rogoff(2005)認為,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低估本幣追求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是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本原因;美國和歐洲是此類行為的受害者。Bernanke(2005)[4]認為全球經濟失衡是由于中國過度儲蓄導致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實際上向美國提供了具有補助性的貸款,只要正確地配置這些信用,美國可實質上受益。
也有一些學者嘗試從美國自身經濟的特征出發解釋全球經濟失衡的成因。Caballero(2006, 2009)[5-6]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世界各國對高質量金融資產的需求增加,而美國在創造高質量金融資產方面的比較優勢,是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即全球經濟失衡的關鍵。Hausmann 和 Sturzenegger(2005)[7]發現,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產生的大量收益沒有被記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他們類比物理學中的概念,將這部分收益稱為“暗物質”。在他們看來,由于“暗物質”的存在,全球經濟失衡程度有可能被高估了,而實際上對于美國經常賬戶問題無需過度擔心。
Blanchard等人(2005)[8]則綜合考察了美國和新興市場國家兩方面的證據。他們認為,美國對外國商品服務需求的增加,以及其他國家對美國金融資產需求的增加,共同造成了全球經濟失衡的結果。
以上三個視角基本涵蓋了全球經濟失衡成因的主流解釋,但是都沒有涉及“美國經常賬戶逆差與新興市場國家有什么不同”的問題,當然也沒有追究這背后的原因。熟悉國際金融危機理論的人都知道,經常賬戶惡化是預警新興市場國際收支危機或貨幣危機的重要指標,源于這些國家在國際交易中不能直接使用本幣的“原罪”(original sin)。[9]*“原罪”為圣經詞匯,意為先祖犯下的后世無法洗脫的罪行。在國際金融領域,被用以特指廣大發展中國家無法以本幣在國際市場籌集資金,導致不可避免的貨幣錯配問題和金融體系脆弱性(Eichengreen et al, 2003)。與廣大新興市場國家不同,經常賬戶惡化幾乎從不被視為美國將發生國際收支危機或貨幣危機的先行指標。這是否因為美國不存在“原罪”或與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的超級貨幣地位有關?
根據Dooley等人(2004)[10],美元超級貨幣地位是指“由于亞洲等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實行以美元為錨貨幣的固定匯率制度,使美元成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名副其實的超級貨幣”,也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Ⅱ”或“新美元本位制”。事實上,對美元超級貨幣地位的批評一直不絕于耳。比如,McKinnon(2010)[11]就毫不諱言,“新美元本位制”是一個所有人都不喜歡的制度安排。
對美元超級貨幣地位的質疑首先集中于它的不可持續性,而這種不可持續性對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經濟體系的穩定性構成了潛在威脅。Roubini和Sester(2005)[12]從資金供給的角度進行分析,指出美元資產的收益不足夠彌補美元貶值的風險,導致各國央行和私人部門對美元資產的持有少于美國平衡經常賬戶逆差的融資需求,這將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Ⅱ”的崩潰。Hall和Tavlas(2013)[13]從資金運用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美元的超級貨幣地位會導致全球范圍內美元流動性泛濫,引發大宗商品價格泡沫和資產泡沫,甚至造成全球性金融危機,使得“布雷頓森林體系Ⅱ”同樣難逃崩潰的命運。
對美元超級貨幣地位的另一種批評在于它的不平等性。具體表現為:在利益分配的問題上,中心國家(美國)享有了更多的利益;而在風險承擔的問題上,周邊國家卻被輸出了大量風險。李揚(2005)[14]指出美元超級地位事實上將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邊緣化”,對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問題負有責任。在實證方面,Mishkin(1998)[15]針對墨西哥危機前的經濟數據分析,表明了墨西哥銀行與企業負債的美元化與貨幣錯配導致了該國90年代的銀行危機。同時,Yeyati(2003, 2006)[16-17]指出金融美元化的國家,在貨幣需求上表現的更為不穩定,產出增長更為緩慢,波動更大,更易受到銀行危機的傳染,而金融深度卻沒有明顯提升。De Nicoló等人(2003)[18]同樣提供了實證證據,證明了銀行系統美元化的國家,總體上面臨著金融體系更加不穩定的問題。除此之外,美元匯率波動同樣可以通過影響大宗商品價格,將風險輸出至其他國家。如譚小芬等(2015)[19]指出,美元實際匯率的波動會顯著的影響國際原油價格的變化。
雖然美元超級貨幣地位賦予了美國大量特權,并使美國在不平等的國際貨幣體系中處于優勢地位,但是優勢地位也并非免費的午餐。Devereux等人(2007)[20]運用博弈論的方法,證明了美元超級貨幣地位使美國免受匯率傳導引發的風險,然而缺少了相關約束,反而導致美國在支出方面配置的低效率,長遠看這使得美國經濟受損。
上述三方面問題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聯系的。Mckinnon(2010)指出,“美元本位制”中的不平等,使得美國錯誤的貨幣政策危害全球經濟,同時引發美國自身和其他國家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唯一的出路是:美國通過“國際化”其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穩定自身及全球經濟。尹應凱和崔茂中(2009)[21]全面分析了美元超級貨幣地位中各種問題之間的聯系,認為美元超級貨幣地位的生存基礎會帶來其生存影響,然而生存影響反過來會動搖其生存基礎,這種沖突導致了美元超級貨幣地位的不可持續。
雖然大量學者研究了美元超級貨幣地位的危害,但僅有少數研究者提出了美元超級貨幣地位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的觀點。而且這方面的研究一般缺少系統性的理論解釋或實證支持。
Bibow(2008)[22]明確指出美元的超級貨幣地位使得美國作為債務國卻享有正的投資收益,并且能夠在經常賬戶持續逆差的情況下,仍然保持外債占GDP比例相對穩定。這項研究嘗試將國際貨幣體系中存在的問題與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置于同一個分析框架,但是沒有具體討論二者之間相互作用的機制。Palley(2015)[23]對全球經濟失衡和美元國際地位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在結構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框架下,強調全球經濟失衡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不可避免的結果——在供給方表現為勞動力向新興市場集中,產生新的生產范式;在需求方表現為購買力向發達國家集中,造就美元超級貨幣地位。由此可見,在Palley的研究中,全球經濟失衡與美元超級貨幣地位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即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層面的不同表現。
國內學者姚枝仲(2003)[24]曾提到,美元是國際結算和官方外匯儲備的關鍵貨幣,這種超級貨幣地位是美國長期維持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袁冬梅和劉海云(2007)[25]也從美元特殊的國際地位出發對全球經濟失衡進行了研究。她們認為,從供給方面看,美元超級貨幣地位使美國維持著巨額貿易逆差而不受外匯儲備短缺的制約和金融危機的威脅,從需求方面看,其他追求美元儲備的國家需要依靠貿易順差和過度儲蓄來擺脫不利處境;在兩者共同作用下,全球經濟出現失衡,表現為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持續擴大。
既有文獻對美元超級貨幣地位與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擴大之間關聯性的討論還很不充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雖然注意到全球經濟失衡與美元特殊國際地位之間的相互支持作用,但卻忽略了在美元國際地位幾乎保持不變的情形下,美國經常賬戶由順差轉變為逆差的經驗事實,所以單純從美元超級貨幣地位解釋全球經濟失衡缺乏合理性。第二,已有研究對于全球經濟失衡與國際貨幣失衡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缺乏理論和實證層面的有力證據。
Triffin(1960)[26]曾提出,非居民持有國際外匯儲備的一個主要動機在于方便對外支付、清償國際債權債務。因此,本文嘗試從國際貨幣格局調整滯后于世界經濟貿易格局變遷的角度來探討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及其解決辦法。[27]*Mckinnon(2001)在分析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的形成時,提到了逆差需要有美元地位支持。雖然沒有對支持途徑加以論證,但這一觀點與本文的分析邏輯基本吻合。
三、理論分析
在討論非居民對國際貨幣的需求時,Triffin(1960)指出,黃金早已無法為世界經濟提供充足清償手段……只有通過貨幣儲備中外匯部分的“國際化”來解決……將哪個國家的主權貨幣用作國際儲備是儲備持有者自由選擇的結果,他們做選擇時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安全的”可獲得貨幣資產上,也就是那些主要債權國發行的貨幣。
這段文字表明非居民持有國際貨幣的目的是用于清償國際間債權債務關系,以解決黃金短缺所造成的不便。也就是說,從官方角度來看,對國際貨幣的需求源自于要為私人部門順利完成對外支付做好預先準備。一國的國際貿易,會增加非居民對其的支付,進而引致非居民對該國貨幣的需求。這會增加該貨幣的使用與持有,提升貨幣的國際地位。所以說,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本質上來源于其發行國的國際貿易,一國的貨幣地位也應當與其貿易地位相適應。
所以,當國際貿易格局發生改變時,國際貨幣格局必須隨之調整。如不然,則會出現國際貨幣失衡,對發行國經常賬戶產生不利的影響。特別是當貨幣發行國的貿易地位下降時,非居民使用其貨幣清償債權債務的需求隨之減少。此時如果貨幣格局調整滯后于貿易格局調整,該貨幣將被非居民過度持有,或者說非居民持有的貨幣,超出了日常支付、清算的需要。這部分貨幣會以資本的形式流回發行國,造成發行國的資本賬戶順差與經常賬戶逆差。
當美國的貿易地位出現下滑,而美元仍維持原有高地位時,將導致新興經濟力量在進行貿易、清償債權債務時過度使用美元。貿易份額不斷上升的新興經濟力量積累的巨額美元儲備資產,遠遠超過對外進口支付或債務償還需要,全都表現為美國的資本凈流入。為滿足其他國家對國際清償力的需要,美國仍要保持對外凈支付;但是資本賬戶的美元凈流入,使得美國只能通過經常賬戶向非居民輸出美元。而與之相伴的,便是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擴大,全球經濟失衡問題變得突出。
簡而言之,美國貿易地位下滑,美元繼續占據超級國際貨幣地位,二者之間的不匹配導致美國經常賬戶惡化,使全球經濟失衡問題被觸發并激化。本文將構建一個高度簡化的理論分析框架來說明上述過程。

對持有美元儲備的國家來說,新增的美元儲備以資本的形式流回美國,表現為美國資本和金融賬戶流入。以FAUS表示美國資本賬戶余額,則有:
(1)
等式兩邊同時除以EXTotal,得到:
(2)

(3)
記美國經常賬戶余額為CAUS。由國際收支平衡式CAUS+FAUS=0,可以得到:
(4)
將式(3)和(4)聯立方程組,解得:
(5)
在式(5)等號兩側同時對t取微分,整理得到:
(6)
由此證明,在美國貿易地位下降而美元國際貨幣地位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美國必然要面對經常賬戶惡化的結果,也即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將不可避免。
四、歷史經驗
美國歷史上曾經歷過兩次經常賬戶惡化,分別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以及牙買加體系下。與理論分析類似,歷史經驗同樣表明,美元超級貨幣地位本身并不會惡化美國的經常賬戶。然而,當美國貿易地位受到沖擊而美元地位調整滯后時,美國經常賬戶就會明顯惡化。
(一)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美國經常賬戶惡化
Triffin(1960)曾專門討論了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對西歐經常賬戶明顯惡化的問題,這也是他之后一系列重大發現的研究起點。他特別注意到西歐經濟競爭地位相對上升所產生的影響,認為西歐經濟和貿易發展打破了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在國際貿易和國際貨幣供求方面的舊有均衡。西歐經濟競爭力提高,對美國減少進口增加出口,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美國向世界其他國家出口商品和服務。這表明國際經濟和貿易格局已經調整,美國出口份額下降,西歐出口份額上升。但由于美元是當時唯一的國際儲備貨幣,西歐對其他國家貿易活動也需要使用美元完成債權債務清償,所以國際貨幣格局并未改變。特里芬難題由此顯現。
當世界貿易格局變遷致使特里芬難題出現時,關鍵國際貨幣發行國會“面對艱難的重新調整問題”,比如是否削減對外援助計劃或逆轉以前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等。Triffin認為,關鍵國家的政策調整如果成功,經常賬戶問題可以解決,但“將終止這個國家以前做過的貢獻,再不能將國際清償能力維持在一個合適的水平上”。言外之意是,如果國際貨幣格局跟上世界貿易格局的調整節奏,美國經常賬戶惡化并非必然結果。這樣看來,巨額經常賬戶逆差事實上是美國經濟政策權衡的結果,是在世界貿易格局已經發生重大調整后繼續保持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壟斷地位必須支付的代價。
(二)牙買加體系下的美國經常賬戶惡化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國際貨幣格局開始緩慢調整。隨著德國馬克、日元等貨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其國際使用程度逐步提高。在國際經濟和金融領域的貨幣替代影響下,“一超多元”的牙買加體系漸漸形成。
圖1為世界主要國家的進出口百分比堆積圖。從中可以看出,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后期,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貿易份額的變動不大,說明二戰結束后發生的世界貿易格局變遷在這段時間進入相對穩定期。在貿易格局較為穩定而國際貨幣格局緩慢調整的背景下,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問題雖然有所顯現但還基本可控。美國貿易地位與二戰后相比盡管已經顯著下降,但是相對優勢仍然存在。因為這時期歐洲的經濟和金融一體化尚未完成,力量比較分散,日本則既有國內市場深度不夠的先天缺陷,又受到廣場協議和泡沫經濟等各種現實困擾,都不足以形成對美國的有效挑戰。所以,如同經常賬戶問題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初期沒有明顯表現一樣,在牙買加體系投入運行近30年的時間里,國際貨幣格局與世界貿易格局基本吻合,作為關鍵國際貨幣發行國,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問題也暫時得以引而不發。
然而,世界貿易格局的相對穩定期幾乎就在新舊世紀交替時宣告結束。美國進出口貿易份額相繼明顯降低,相對優勢似乎也已喪失,貿易地位迅速下滑。挑戰美國貿易優勢的力量主要來自于兩方面。其一,歐洲經濟與貨幣同盟的建立在貿易領域發揮聚合效應,大有取代美國獲得相對貿易優勢地位的勢頭。其二,新興市場經濟體迅速崛起,以中國為代表的眾多發展中國家走上了外向型經濟發展道路,明顯擠占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進出口市場份額。
但是在國際經濟和貿易格局發生重大調整之時,國際貨幣格局卻繼續保持“一超多元”的基本結構,再次顯著滯后于貿易格局變遷。歐元區貿易地位可能已經超越美國,但是歐元的國際使用水平僅僅相當于美元的一半。由于國際貿易、國際金融交易仍然以美元為最大計價結算貨幣,所以美元自然也成為最大的國際儲備貨幣。在此背景下,美國經常賬戶再次惡化,全球經濟失衡再次凸顯。
五、實證檢驗
理論分析與歷史經驗一致表明,美國經常賬戶惡化是國際貨幣格局滯后于世界貿易格局調整的集中反映。前者被普遍稱為全球經濟失衡,后者在本文中被定義為國際貨幣失衡。
(一)指標構造和含義
首先需要分別定義兩個指標,以測度美國經常賬戶惡化的程度以及國際貨幣格局滯后于貿易格局調整的程度。

圖1 世界進出口貿易格局(1970-2011年)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全球貿易數據。
第一,經濟失衡指標,用于測度美國經常賬戶惡化的程度。其符號和數據關系為:
經濟失衡指標等于美國經常賬戶差額與GDP的比值,經常賬戶順差時該指標為正數,經常賬戶逆差時該指標為負數。全球經濟失衡指標的數值變大,說明美國經常賬戶有好轉,反映全球經濟失衡程度降低;指標的數值變小,說明美國經常賬戶惡化,反映全球經濟失衡程度升高。

貨幣失衡指標的分母部分,是美元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所占比重,反映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以此代表指定時期的國際貨幣格局。該指標的分子部分,是美國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反映了美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以此代表指定時期的世界貿易格局。
貨幣失衡指標被定義為美國在世界貿易格局中的地位與美元在國際貨幣格局中地位的比值,即衡量美元貨幣地位偏離美國貿易地位的情況,也就是國際貨幣格局滯后于世界貿易格局調整的程度。若貨幣失衡指標等于1,意為美元地位與美國貿易地位相匹配,不存在貨幣失衡。若貨幣失衡指標小于1,說明相對于美國的貿易地位,美元貨幣地位是偏高的,也即存在著國際貨幣格局調整滯后于貿易格局的情況;而且指標數值越小,說明國際貨幣格局偏離世界貿易格局的程度越高。*由于在美國貿易地位下滑的同時,美元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始終居于壟斷性的高比例,所以在我們的研究期間內,貨幣失衡指標的數值沒有出現過大于1的情形。在現實中,美國出口比重遠遜于美元充當儲備資產的比重,貨幣失衡指標小于1。總體而言,貨幣失衡指標的數值變大,說明國際貨幣格局與世界貿易格局的偏離程度減小,反映貨幣失衡程度降低;指標的數值變小,說明二者偏差程度增大,反映貨幣失衡程度升高。*從經濟含義出發,貨幣失衡指標在定義時也可以將分子分母調換位置。本文所使用的定義方法,使得我們對于貨幣失衡指標和全球經濟失衡指標的變動在理解上可以保持一致,即指標數值變大代表失衡程度降低,指標數值變小代表失衡程度升高,從而方便下文對二者均衡關系的解釋,也讓圖示顯得更加直觀。
(二)數據描述
由于IMF從1999年開始披露外匯儲備季度數據,本文選取1999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三季度的全球官方外匯儲備數據。此外,美國經常賬戶差額、GDP、對外出口以及世界出口總額等數據,均為以現價美元記錄的未經季節性調整的原始數據。數據來源包括IMF的WEO、IFS和COFER數據庫,以及NBER數據。
圖2展示了1960-2013年間經濟失衡指標的變動趨勢。可以看到,美國經常賬戶差額從70年代中期起開始惡化,至80年代后期有所改善。但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在維持一段時間較低水平之后,從90年代后期開始迅速惡化,全球經濟失衡程度較之以往表現得更加嚴重。直到次貸危機擴大為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情況才再度有所緩和。
德、日兩國經濟在二戰結束迅速復蘇,到70年代中期都已經發展成為國際貿易大國。但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初,兩國貨幣在國際范圍內使用程度還都非常有限,而80年代中后期則是德國馬克和日元步入國際化軌道的重要時間節點。根據前文分析可知,在美國貿易份額已經緩慢下降而德國馬克、日元的貨幣份額尚未提升之際,貨幣失衡指標的數值逐漸變小,國際貨幣格局偏離世界貿易格局的程度提高。而當德國馬克和日元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的份額逐步上升之后,國際貨幣格局發生變化,貨幣失衡指標的數值變大,貨幣失衡程度降低。
90年代起,歐洲經濟與貨幣同盟產生的貿易聚合效應,以及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國際貿易中的迅速崛起,嚴重沖擊了美國的相對貿易優勢地位。但是在歐元尚未得到國際金融市場認可、新興市場貨幣被徹底排除在國際貨幣之外的情形下,貨幣失衡指標迅速下滑,國際貨幣格局調整嚴重滯后于世界貿易格局。直到次貸危機爆發前后,國際貨幣體系出現新的一輪調整,歐元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份額逐漸上升,人民幣等其他貿易大國貨幣更多地在國際范圍內使用,美元儲備份額略有下降,貨幣失衡指標才緩慢回升。

圖2 經濟失衡指標(1960-2013年)
直觀地看,貨幣失衡指標與經濟失衡指標的走勢在總體上是趨同的(見圖3)。在觀察期內的絕大多數年份里,當貨幣失衡變得嚴重時,經濟失衡也趨于嚴重;而在貨幣失衡較為緩和時,經濟失衡也表現出緩解的跡象。
(三)實證分析結果
對貨幣失衡指標與經濟失衡指標二者關系的檢驗,分作以下四個步驟進行。第一,ADF單位根檢驗。第二,Johansen協整分析。第三,選擇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估計貨幣失衡與經濟失衡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第四,對二者之間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
首先進行變量平穩性檢驗。根據ADF單位根檢驗結果可知(見表1),經濟失衡指標和貨幣失衡指標均不是平穩序列,但同時屬于一階單整過程。*PP檢驗結論與此一致。對于同階單整的非平穩序列,可以運用協整分析方法,以考察兩者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其次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考慮到經濟失衡指標與貨幣失衡指標本身可能存在有趨勢,同時沒有理論支持二者的協整向量存在有確定性趨勢,所以選擇允許變量存在線性趨勢而協整向量僅包含截距項的模型。根據AIC、BIC以及LR法則,最終確定滯后階數為2。如同表2所示,跡檢驗和最大特征根檢驗結果均表明,經濟失衡指標與貨幣失衡指標之間存在一組協整關系。*運用基于殘差的EG檢驗方法,同樣發現二者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顯著性水平為10%。
接下來使用VECM模型對協整向量系數和調整系數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及其標準差如表3如示。據此可以將經濟失衡指標與貨幣失衡指標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寫作:
Imba_Economyt=0.5787Imba_Currencyt-0.16118
說明在長期中,經濟失衡指標和貨幣失衡指標存在正向的相關關系,而且二者間均衡關系十分顯著(p=0.0000)。

圖3 經濟失衡指標和貨幣失衡指標(1999-2013年)

變量ADF值p值結論Imba_Economyt-0.66030.8479不平穩Imba_Currencyt-0.32360.9144不平穩ΔImba_Economyt-9.97690.0000平穩ΔImba_Currencyt-7.53440.0000平穩

表2 協整檢驗結果
**意為5%的顯著性水平
誤差修正反映出二者在短期中的動態調整過程。對于上一期偏離均衡點的誤差,兩個變量均會進行負向修正。經濟失衡指標的修正較大,且在統計上顯著(p=0.0002)。貨幣失衡指標修正略小,且統計上的顯著性較差(p=0.1005)。
這說明,從長期看來,全球經濟失衡與國際貨幣格失衡存在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維持美元在國際貨幣格局中與其貿易不相稱的超高地位,與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存在沖突。
最后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分析兩個變量之間的互動機制。由于格蘭杰因果檢驗所判定的“因果關系”實際上反映了兩個變量變化在時間上的先后順序,因此也可以認為二者間存在“預測關系”。
由表4可知,兩個變量之間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而貨幣失衡對經濟失衡的預測性十分顯著。這意味著,國際貨幣格局滯后于世界貿易格局的調整,可以視為全球經濟失衡的先行指標。這一發現同時也說明,“一超多元”的國際貨幣體系和現有的國際貿易格局并不匹配。只有通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升新興貿易大國貨幣的國際地位,并適當降低美元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份額,才能使國際貨幣格局調整跟隨世界貿易格局變遷方向,有效緩解國際貨幣失衡程度,從而破解全球經濟失衡的困局。

表3 VECM模型估計結果

表4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另一方面,全球經濟失衡會加劇國際貨幣格局偏離世界貿易格局的程度。美國通過巨大的經常賬戶逆差向國際社會輸出美元,的確有助于鞏固美元地位,但是美國經濟份額和貿易份額滑入低谷的客觀現實,勢必拉大了美元儲備份額與美國貿易份額之間的差距,導致貨幣失衡更加嚴重。這實際上就是現階段美元國際化“貿易流出—資本回流”模式的真實寫照。
六、結論
本文以理論分析和歷史經驗分析為基礎,指出國際貨幣格局調整滯后于世界貿易格局變遷是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機制,并通過實證檢驗對此觀點予以支持。本文認為,美國經常賬戶惡化并不被視為美國將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預警指標,關鍵在于美元高居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超級貨幣地位,即使美國經濟和貿易地位已經在明顯下滑。但恰恰正是國際貨幣失衡——美元貨幣地位與美國經濟貿易地位的持續偏離,造成了全球經濟失衡——美國經常賬戶不斷惡化。
具體地,本文得出以下幾點結論。第一,國際貨幣失衡與全球經濟失衡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長期均衡關系。第二,在美元國際化“貿易流出—資本回流”的模式下,全球經濟失衡會進一步加劇國際貨幣體系偏離世界貿易格局(即貨幣失衡)的程度。第三,國際貨幣失衡對全球經濟失衡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國際貨幣格局滯后于世界貿易格局調整是全球經濟失衡的觸發機制,美元貨幣地位偏離美國貿易地位可以視為美國經常賬戶惡化的先行指標。
上述發現,不僅闡釋了全球經濟失衡的成因,而且為解決這一問題指明了方向。新世紀以來,國際貿易格局已經顯著變化,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貿易格局中的份額與發達國家已經幾乎持平。但是由于“一超多元”的國際貨幣格局至今沒有明顯改觀,所以全球經濟失衡難以避免。只有通過將新興貿易大國貨幣納入國際貨幣體系,適當降低美元儲備份額,緩解貨幣失衡程度,才能解決全球經濟失衡難題。不久前,IMF執董會決定自2016年10月起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這不僅是對過去五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肯定,也應當視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起點。顯然,這樣的調整是順應世界經濟貿易格局變遷方向的,對于糾正全球經濟失衡勢必將發揮積極作用。
[1]de Rato, R. Correcting Global Imbalances—Avoiding the Blame Game[Z]. Remarks befor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ew York, Feb.23,2005.
[2] Wolf, M. America on the comfortable path to ruin[N]. Financial Times,Aug.17,2004.
[3] Obstfeld, M. and K.S. Rogoff. Global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and exchange rate adjustments[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C]. 2005(1): 67-146.
[4] Bernanke, B.S.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Z]. Speech, 2005, 28(6):665-671.
[5] Caballero, R.J. On the Macroeconomics of Asset Shortages[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06(12753).
[6] Caballero, R.J. and A. Krishnamurthy. Global Imbalances and Financial Fragi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2):584-588(5).
[7]Hausmann, R. and F. Sturzenegger. Dark matter makes the US deficit disappear[N]. Financial times, 2005, 8: A15.
[8] Blanchard, O.J., F. Giavazzi and F. Sa. The US Current Account and the Dollar[J]. Cepr Discussion Papers, 2005, 28(6):665-671.
[9]Eichengreen, B., R. Hausmann and U. Panizza. Currency Mismatches, Debt Intolerance and Original Sin: Why They Are Not the same and Why it Matters [J]. NEBR Working Paper No. 10036, October 2003.
[10]Dooley, M.P., D. Folkerts-Landau and P. Garber.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04, 9(4): 307-313.
[11] McKinnon, R.I. Rehabilitating the unloved dollar standard[J].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010, 24(2): 1-18.
[12]Roubini, N. and B. Setser. Will the Bretton Woods 2 regime unravel soon? The risk of a hard landing in 2005-2006[J].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Oxford University, 2005, 6.
[13] Hall, S.G. and G.S. Tavlas. The Debate About the Revived Bretton-Woods Regime: A Survey and Extension of th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3, 27(2): 340-363.
[14]李揚, 余維彬. 經濟全球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儲備管理[J]. 經濟學動態, 2005(8):9-17.
[15]Mishkin, F.S.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rises: 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J]. Nber Working Papers, 1996:29-62.
[16]Yeyati, E.L. Financial Dedollarization: A Carrot and Stick Approach[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3.
[17]Yeyati, E.L. Financial dollarization: evaluating the consequences[J]. Economic Policy, 2006, 21(45): 61-118.
[18] DeNicolo, G., P. Honohan and A. Ize. Dollarization of the Banking System: Good or Bad?[J].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3 (3116).
[19] 譚小芬, 張峻曉, 李玥佳. 國際原油價格驅動因素的廣義視角分析:2000-2015——基于TVP-FAVAR模型的實證分析[J]. 中國軟科學, 2015(10):47-59.
[20]Devereux, M.B., K. Shi and J. Xu. Global monetary policy under a dollar standard[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71(1): 113-132.
[21] 尹應凱, 崔茂中. 美元霸權: 生存基礎, 生存影響與生存沖突[J]. 國際金融研究, 2009 (12): 31-39.
[22] Bibow, J.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non-) order and the global capital flows paradox[J].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531, 2008.
[23] Palley, T.I. The theory of global imbalances: mainstream economics vs structural Keynesianism[J]. 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 2015, 3(1):45-62.
[24] 姚枝仲.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J].世界經濟,2003(3): 12-15.
[25] 袁冬梅, 劉海云.美元特權對美國貿易逆差的影響探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7(1):102-107.
[26] Triffin, R. 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 The Future of Convertibility[M]. Yale University Press, Inc, 1960.
[27] McKinnon, R.I. The international dollar standard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C].2001(1): 227-239.
(本文責編:莫默)
Global Imbalance: an Expla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Imbalance
WANG Fang, LI Xiao-yang
(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
Global imbalance is indicated by the persistent deterioration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imbalance caused by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e further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imbalance and global imbalance. First, we buil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prove that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terioration is unavoidable when the US trade status declines while its currency maintains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This conclusion f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Second, we construct an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rchitecture and trade architecture. Using an error correction model,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imbalance and global imbalance. We conclude that the global imbalance can be resolved only if major player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have more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imbalance is resolved.
Global Imbalanc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Imbalance; Triffin Dilemma;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Reform
2015-10-14
2016-04-11
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重點項目 (編號15JGA013)。
王芳(1974-),女,黑龍江哈爾濱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F113
A
1002-9753(2016)05-014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