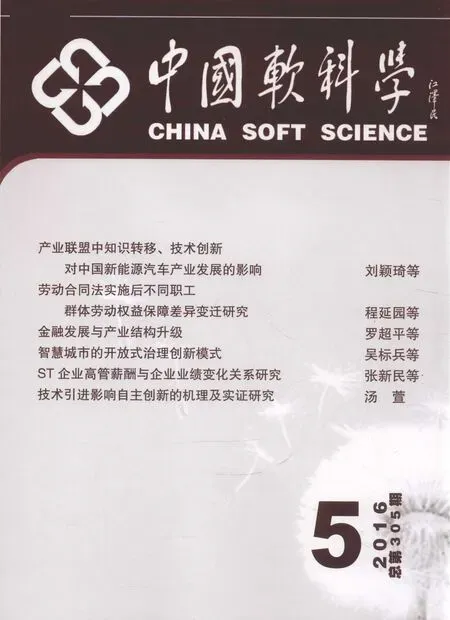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包容性創(chuàng)新與消費增長
黃衛(wèi)東,岳中剛
(南京郵電大學(xué) 管理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46)
?
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包容性創(chuàng)新與消費增長
黃衛(wèi)東,岳中剛
(南京郵電大學(xué)管理學(xué)院,江蘇南京210046)
信息技術(shù)的廣泛應(yīng)用究竟是以線上渠道替代實體零售,還是刺激了新增消費?本文從包容性創(chuàng)新視角提供了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與消費增長的分析框架和理論假說,利用我國2004-2013年的省級面板數(shù)據(jù),考察了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促進(jìn)消費增長的邊際效應(yīng)和普惠效應(yīng)。實證研究表明,從總量而言,信息技術(shù)普及率對居民消費的效應(yīng)顯著為正;從結(jié)構(gòu)而言,中西部地區(qū)的消費者將從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中獲益更多。研究結(jié)論對于我國實施“互聯(lián)網(wǎng)+”戰(zhàn)略促進(jìn)消費增長和區(qū)域均衡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
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包容性創(chuàng)新;消費增長
一、引言
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主的信息技術(shù)的廣泛應(yīng)用,推動了供應(yīng)鏈系統(tǒng)以及消費網(wǎng)絡(luò)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發(fā)展,并以電子商務(wù)的業(yè)態(tài)模式形成了全國統(tǒng)一大市場(畢達(dá)天和邱長波,2014)[1]。然而,交易技術(shù)和商業(yè)模式的顛覆式改變,對于大眾消費者尤其是信息基礎(chǔ)設(shè)施薄弱地區(qū)的消費者而言,究竟是帶來便捷渠道的“信息紅利”還是拉動消費差距的“數(shù)字鴻溝”,目前仍存在較大爭論。Bhavnani等(2008)認(rèn)為,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會強化發(fā)達(dá)個體的信息優(yōu)勢和知識優(yōu)勢,使落后個體進(jìn)一步面臨信息貧困與知識貧困的威脅。這意味著信息技術(shù)的應(yīng)用似乎并不能自動縮小數(shù)字鴻溝,反而可能擴大原有的差距[2]。如Shiu和 Lam(2011)采用1978-2004年中國22個省級面板數(shù)據(jù)研究發(fā)現(xiàn),電信發(fā)展與經(jīng)濟增長的因果循環(huán)關(guān)系僅發(fā)生在富裕的東部地區(qū)省份[3]。張紅歷等(2010)基于空間經(jīng)濟學(xué)的研究認(rèn)為,信息技術(shù)發(fā)展的網(wǎng)絡(luò)效應(yīng)使得區(qū)域間逐漸形成緊密的空間聯(lián)系結(jié)構(gòu),對縮小由數(shù)字鴻溝所造成的社會發(fā)展不平衡有著獨特優(yōu)勢[4]。大量基于亞洲、非洲等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的實證研究也表明,手機、互聯(lián)網(wǎng)及其融合發(fā)展的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等信息技術(shù)的普及能夠幫助市場更好地發(fā)揮作用,給更多的人特別是低收入人群帶來福利的增加,是解決弱勢群體需求的包容性創(chuàng)新(Jensen,2007;Conley和Udry,2010;李坤望等,2015)[5-7]。所謂“包容性創(chuàng)新”是指通過創(chuàng)新解決社會發(fā)展中的弱勢群體本身的權(quán)利的貧困和所面臨的社會排斥,即通過創(chuàng)新促進(jìn)經(jīng)濟發(fā)展成果惠及大多數(shù)人(George等,2012)[8]。Aker(2010)統(tǒng)計分析了西非國家尼日爾(Niger)2001-2006年谷物市場,發(fā)現(xiàn)移動電話普及率導(dǎo)致市場價格和價格離散度分別降低了4.5%和10%,而且市場效率提高也增加了農(nóng)民收入,對生產(chǎn)者與消費者都是一種帕累托改善[9]。Qiang等(2009)實證研究了120個國家移動電話對人均GDP的影響,發(fā)現(xiàn)移動電話普及率每增加10%,將使發(fā)展中國家經(jīng)濟增長0.81個百分點,發(fā)達(dá)國家則為0.60個百分點[10]。
近年來,隨著網(wǎng)絡(luò)消費方式的興起,沃爾瑪?shù)葰W美零售商通過“收縮門店”和“啟動線上”打造全渠道零售平臺來推動消費增長。我國也大力加強信息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以“互聯(lián)網(wǎng)+”戰(zhàn)略促進(jìn)線上線下互動的O2O消費(譚曉林等,2015)[11]。根據(jù)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信息中心(CNNIC)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截止2015年12月,我國網(wǎng)民規(guī)模達(dá)到6.88億,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為50.3%;網(wǎng)絡(luò)購物用戶達(dá)到4.13億,網(wǎng)民進(jìn)行網(wǎng)絡(luò)購物的比例達(dá)到60%;手機網(wǎng)絡(luò)購物用戶規(guī)模增長迅速,達(dá)到了3.40億,手機網(wǎng)民進(jìn)行網(wǎng)絡(luò)購物的比例由2014年42.4%提升至54.8%。在此背景下,我國居民消費是否享受到了互聯(lián)網(wǎng)應(yīng)用所帶來的“信息紅利”?目前國內(nèi)普遍關(guān)注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對實體零售的替代效應(yīng),而缺乏對居民消費總量“邊際效應(yīng)”的關(guān)注。此外,盡管我國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的省間差異從1997年的3.37下降到2014年的0.24,但從CNNIC對全國城市O2O發(fā)展水平的測算情況來看,東部一線城市的綜合實力、環(huán)境因素、應(yīng)用水平、發(fā)展?jié)摿Ψ矫婢I(lǐng)先于中西部的二、三線城市。那么互聯(lián)網(wǎng)的覆蓋、手機的使用、O2O消費的便捷和低成本,是否更多地惠及了我國商業(yè)設(shè)施嚴(yán)重欠缺的中西部地區(qū)的居民消費,即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是否具有包容性創(chuàng)新的“普惠效應(yīng)”?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網(wǎng)絡(luò)化與社會化購物方式的興起與消費增長
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以及網(wǎng)絡(luò)購物方式的日益盛行,消費者的購物渠道從“線下”到“線上”的大規(guī)模遷移,使實體零售商陷入了“展示廳”的困境。所謂“展示廳”(showrooming),是指消費者先到零售實體店查看和體驗意向商品,然后通過線上渠道以較低的價格購買該商品的行為,即“先逛店后網(wǎng)購”,這種現(xiàn)象也被稱為“零售服務(wù)的橫向外部性”或“信息搭便車”(Shin,2007)[12]。根據(jù)麥肯錫2015年對中國不同級別城市以及廣大農(nóng)村地區(qū)共計約6.3億互聯(lián)網(wǎng)用戶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實體店的展示效應(yīng)對30%的消費者而言尤為明顯,這些消費者會在店內(nèi)瀏覽體驗商品并同時用手機進(jìn)行價格比對,最終只有16%的消費者會選擇在門店購買此產(chǎn)品。“展示廳”困境反映了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對實體零售店的沖擊,也迫使其向線上線下融合的全渠道零售商轉(zhuǎn)型發(fā)展,為消費者提供多元化的消費選擇。以全球最大的實體零售商沃爾瑪為例,在中國市場推出了O2O服務(wù)平臺“速購”,該平臺包括手機APP、顧客自提貨的門店“速購服務(wù)中心”以及線上線下多種移動電子支付方式,充分結(jié)合了線下實體店的現(xiàn)場提貨優(yōu)勢以及線上購物的搜尋便捷優(yōu)勢。“阿里+蘇寧”、“京東+永輝”等并購模式也反映了全渠道是零售業(yè)發(fā)展的必然趨勢,線上線下的效率互補效應(yīng)既提升了市場覆蓋范圍和流通效率,也滿足了眾多消費者線上下單、線下取貨的市場需求,這必將促進(jìn)消費潛力的釋放。
隨著社交網(wǎng)絡(luò)和購物行為的互動融合,使得社會化網(wǎng)絡(luò)推薦成為影響我國大眾消費決策的重要因素,其消費流程也表現(xiàn)為“3S模式”:首先在社會化網(wǎng)絡(luò)媒體(如微博、虛擬社區(qū)等)上分享(share)朋友或口碑推薦,然后通過搜索網(wǎng)站搜尋(search)商品信息,最后去實體零售店查看或體驗(see)商品。2012年,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信息中心對中國網(wǎng)絡(luò)零售市場的調(diào)查表明,無論是消費者熟悉的商品還是不熟悉的商品,網(wǎng)絡(luò)評論對消費選擇的影響都是最大的,分別有44.8%和34.7%的消費者受此影響,遠(yuǎn)超過商品價格、物流與售后服務(wù)、購物經(jīng)驗等影響因素。由此可見,網(wǎng)絡(luò)評論已經(jīng)成為潛在消費者了解商品或服務(wù)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企業(yè)了解消費者需求以及促進(jìn)商品銷量的營銷媒介。Duan等(2008)認(rèn)為,社交網(wǎng)絡(luò)對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為知曉效應(yīng)和推薦效應(yīng)[13]。所謂“知曉效應(yīng)”是指社交網(wǎng)絡(luò)傳遞了商品存在的信息,使消費者知道、關(guān)注和選擇該商品,而“推薦效應(yīng)”是指社交網(wǎng)絡(luò)可以塑造消費者對商品的態(tài)度和認(rèn)知,進(jìn)而影響其購買決策。Trusov等(2009)比較了社交網(wǎng)絡(luò)與傳統(tǒng)營銷對新顧客獲取的效應(yīng),發(fā)現(xiàn)社交網(wǎng)絡(luò)等口碑推薦的長期彈性為0.53,是事件營銷的20倍,媒體營銷的30倍[14]。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企業(yè)充分利用這種從線上至線下的社交商務(wù)模式,借助龐大的社交用戶人口構(gòu)建數(shù)字化的直銷網(wǎng)絡(luò),銷售依賴口碑推薦的經(jīng)驗型商品如化妝品、服裝、保險產(chǎn)品等。
綜合上述分析,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引致的網(wǎng)絡(luò)零售不僅僅是實體零售的替代渠道,對消費增長產(chǎn)生了廣泛的波及效應(yīng),表現(xiàn)為促使實體零售加快業(yè)態(tài)現(xiàn)代化升級,拉低整體零售價格以及提升整體消費規(guī)模等。根據(jù)麥肯錫研究院2011年對我國266個城市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的統(tǒng)計分析,網(wǎng)絡(luò)消費量較高的城市整體消費量通常更高,約有61%的網(wǎng)絡(luò)零售是從實體零售商轉(zhuǎn)移而來的消費,而39%的網(wǎng)絡(luò)零售則來自于網(wǎng)絡(luò)化和社會化購物方式刺激產(chǎn)生的新增消費。為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1:信息技術(shù)的廣泛應(yīng)用使得線上線下渠道融合發(fā)展,提升了消費市場的交易效率,進(jìn)而促進(jìn)了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
(二)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的包容性創(chuàng)新與消費增長
與日韓、臺灣地區(qū)相比,我國的線下傳統(tǒng)商業(yè)體系發(fā)展并不完善,尤其是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和農(nóng)村地區(qū),線下商業(yè)渠道不僅分布密度較低,更在價格、商品數(shù)量、品質(zhì)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以每百萬人擁有社區(qū)便利店鋪數(shù)量為例,日本是388家,臺灣地區(qū)是425家,中國城市平均為54家,而且中國城市便利店單店效率遠(yuǎn)低于日本和臺灣。傳統(tǒng)商業(yè)體系的發(fā)展滯后極大地制約了居民消費需求的釋放,而構(gòu)建在互聯(lián)網(wǎng)之上的電子商務(wù)平臺則具有跨區(qū)域、無邊界的天然優(yōu)勢,將這些受到抑制的消費需求納入到全國統(tǒng)一大市場。與專業(yè)市場或?qū)嶓w零售不同,電子商務(wù)平臺突破了貨架空間的限制,增加市場規(guī)模的邊際成本基本為零。從市場效率而言,來自不同區(qū)域的消費者均可以借助商務(wù)平臺提供的智能搜索工具進(jìn)行商品檢索和篩選,增加了價格透明性以及提高了市場的匹配能力,有助于市場效率的改善。根據(jù)阿里研究中心測算,網(wǎng)絡(luò)零售的交易效率是實體零售的4倍,同樣1元的投入成本,實體零售完成的商品成交額是10.9元,而網(wǎng)絡(luò)零售完成的商品交易額是49.6元。由此可見,電子商務(wù)彌補中西部地區(qū)以及鄉(xiāng)鎮(zhèn)實體零售相對落后的局面,使這些區(qū)域的消費者獲得與一、二線城市消費者的同等待遇和機會,實現(xiàn)“無差別消費”。
隨著智能手機、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的快速發(fā)展和日益普及,其便利性使我國中西部以及偏遠(yuǎn)地區(qū)的消費者跨越PC端電子商務(wù),直接進(jìn)入移動商務(wù),加速縮小了地區(qū)之間的數(shù)字鴻溝和消費差異。2014年,基于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消費額增速最快的100個縣域中,有75個來自中西部,其中較集中的省區(qū)有西藏(16個)、四川(13個)、云南(9個)、甘肅(7個)、陜西(5個)。麥肯錫發(fā)布的《2015年中國數(shù)字消費者調(diào)查報告》顯示:盡管互聯(lián)網(wǎng)在三、四線城市和農(nóng)村普及率較低,但這些地區(qū)的大部分?jǐn)?shù)字消費者都在使用電子商務(wù),網(wǎng)購的比例分別達(dá)到了68%和60%。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全國統(tǒng)一大市場形成,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我國長期以來存在的市場分割問題,而且使得我國獨具優(yōu)勢的大國市場效應(yīng)顯現(xiàn),釋放了龐大的內(nèi)需消費潛力,尤其為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的消費者參與市場提供了統(tǒng)一的準(zhǔn)入條件、交易規(guī)則、信用制度、信息服務(wù)等。根據(jù)麥肯錫研究院的統(tǒng)計測算,電子商務(wù)對消費增長的促進(jìn)作用在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尤為明顯,這些地區(qū)網(wǎng)絡(luò)消費的57%是新增消費,遠(yuǎn)高于39%的全國均值。為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2: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的包容性創(chuàng)新效應(yīng)為欠發(fā)達(dá)地區(qū)消費者參與統(tǒng)一大市場提供便捷渠道,釋放和促進(jìn)了這些地區(qū)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
三、研究設(shè)計與計量模型
為了實證檢驗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異質(zhì)性對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程度,本文選取了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qū)2004-2013年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信息技術(shù)普及率以及物流配送等相關(guān)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這些數(shù)據(jù)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與《中國通信統(tǒng)計年度報告》。根據(jù)上述理論分析以及待檢驗的研究假說,本文構(gòu)建的面板數(shù)據(jù)計量方程如下:
lnaretaili,t=α+β1ICTi,t+β2Logistici,t+β3Crossi,t+β4Controli,t+εi,t
其中,lnaretail為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計量方程的被解釋變量;ICT為區(qū)域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程度的相關(guān)變量,本文選取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移動電話普及率、人均郵電業(yè)務(wù)量三個指標(biāo)衡量;Logistic為物流配送的相關(guān)變量,本文選取交通密度、人均城市道路面積、每萬人擁有公共汽車數(shù)量、客運量、貨運量等指標(biāo)進(jìn)行量化;Cross為相關(guān)解釋變量與區(qū)域變量的交叉項,本文將區(qū)域變量界定為二維虛擬變量,參考我國統(tǒng)計分類標(biāo)準(zhǔn),上海、廣東、遼寧等11個省市為東部地區(qū),其它區(qū)域為中西部地區(qū),并將東部地區(qū)的省份設(shè)定為基準(zhǔn)組,賦值為0;Control為控制變量,本文選取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固定資產(chǎn)投資比重作為計量模型的控制變量;ε為誤差項。相關(guān)變量的選取與界定如下:
(1)被解釋變量及測度。本文主要關(guān)注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對居民消費總量的促進(jìn)關(guān)系,為此選取了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作為被解釋變量,以此衡量居民消費總量及其隨區(qū)域與時序變化狀況。
(2)解釋變量及其測度。本文選取的關(guān)鍵解釋變量為信息技術(shù)的應(yīng)用程度以及與電子商務(wù)配套的物流配送發(fā)展?fàn)顩r。目前信息技術(shù)的應(yīng)用主要是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術(shù)(包括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大數(shù)據(jù)等)在經(jīng)濟、社會生活各部分的擴散和應(yīng)用過程,為此本文用各省市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移動電話普及率和郵電業(yè)務(wù)量來測度信息技術(shù)的應(yīng)用程度。居民消費所依托的商業(yè)基礎(chǔ)設(shè)施有三個層次:交易技術(shù)、信息通訊和物流配送,網(wǎng)絡(luò)零售的正常運作有賴于物流配送發(fā)揮其支撐功能。考慮到31個省份的區(qū)域差異,為了減弱指標(biāo)選取造成的估計偏差,本文借鑒劉秉鐮和劉玉海(2011)的處理方法,以交通密度即“單位面積的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反映區(qū)域內(nèi)交通便捷程度,以人均城市道路面積、每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反映物流配送可達(dá)程度,以客運量、貨運量來反映區(qū)域物流總量狀況[15]。
(3)其他控制變量的選取。盡管消費理論經(jīng)歷了絕對收入理論、相對收入理論、生命周期理論、持久收入理論的變遷,但可支配收入一直是影響消費增長的關(guān)鍵因素。考慮本文以區(qū)域為研究對象,為此選取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固定資產(chǎn)投資占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的比重作為控制變量,分別從微觀層面反映該區(qū)域居民消費能力以及該區(qū)域的經(jīng)濟發(fā)展?fàn)顩r。
考慮到不同變量水平值的巨大差異,在實際估計過程中,本文對被解釋變量以及解釋變量中移動電話普及率、客流量、貨流量、人均郵電業(yè)務(wù)量、人均可支配收入取了自然對數(shù)。各關(guān)鍵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見表1。
表2的皮爾遜相關(guān)性檢驗結(jié)果顯示,除人均郵電業(yè)務(wù)量(lnats)之外,計量模型的主要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相關(guān)性。譬如,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Rnet)與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lnaretail)的相關(guān)系數(shù)為0.8918,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區(qū)域交通密度(Dtraffic)與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lnaretail)的相關(guān)系數(shù)為0.6245,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由于郵電業(yè)務(wù)量統(tǒng)計范圍主要包括函件、固定電話等傳統(tǒng)信息通信方式,與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主的現(xiàn)代信息方式相關(guān)性較弱,為此呈現(xiàn)負(fù)的弱相關(guān)趨勢。

表1 關(guān)鍵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

表2 主要變量的Pearson相關(guān)性檢驗結(jié)果
注:***、**和*分別表示顯著性水平為1%、5%和10%。
四、實證結(jié)果與分析
(一)回歸方法
在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中,固定效應(yīng)模型假定個體不可觀測的特征與解釋變量相關(guān),隨機效應(yīng)模型則假定個體不可觀測的特征與解釋變量不相關(guān)。本文采用Hausman檢驗選取回歸模型,若Hausman檢驗的P值大于5%的顯著性水平,則采用隨機效應(yīng)模型(Re),否則采用固定效應(yīng)模型(Fe)。
(二)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與消費增長的邊際效應(yīng)
為了檢驗假說1,本文利用前面設(shè)定的計量模型,首先回歸估計了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對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表3中模型(1)和(3)的回歸結(jié)果驗證了假說1。模型(1)在有效控制了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固定資產(chǎn)投資比重這兩個影響居民消費的控制變量后,采用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的相關(guān)變量作為解釋變量進(jìn)行面板回歸。回歸結(jié)果顯示,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Rnet)、移動電話普及率(lnrmobile)分別在5%和1%顯著水平上對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lnaretail)有正向影響,傳統(tǒng)的郵電業(yè)務(wù)量(lnats)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信息技術(shù)的廣泛應(yīng)用盡管形成了對實體消費的部分替代,但擴大了有效消費需求。
模型(2)檢驗了線上渠道高度依賴的物流配送發(fā)展?fàn)顩r對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面板回歸結(jié)果顯示,除客流量(lnpassger)以外的物流配送變量均在1%的顯著水平上正向影響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lnaretail)。為此,本文進(jìn)一步構(gòu)建模型(3),綜合估計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以及物流配送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回歸結(jié)果顯示: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Rnet)每提高1%,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lnaretail)將增長1.76%,即二者的彈性系數(shù)為1.76;移動電話普及率每提高1%,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lnaretail)將增長0.15%,這也說明了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對居民消費增長的邊際效應(yīng)尚有巨大的發(fā)展空間。此外,物流配送的關(guān)鍵變量也顯著地促進(jìn)了居民消費增長,這意味著信息基礎(chǔ)設(shè)施與物流基礎(chǔ)設(shè)施共同支撐的線上渠道是刺激居民消費增長的引擎。
(三)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與消費增長的普惠效應(yīng)
為了檢驗假說2,本文采用Rnet×Mwest這一交叉項來衡量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的區(qū)域差異對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lnaretail)的影響,用lngoods×Mwest來衡量物流配送的區(qū)域差異對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lnaretail)的影響。表3中模型(4)的估計結(jié)果顯示: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與中西部虛擬變量交叉項(Rnet×Mwest)系數(shù)為0.665,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信息技術(shù)的廣泛應(yīng)用是一種包容性創(chuàng)新,消除了全國商業(yè)流通業(yè)布局不夠均衡的問題,更多地惠及了中西部地區(qū)的居民消費,從而驗證了假說2。進(jìn)一步將各省市網(wǎng)絡(luò)平均購買水平排名與平均消費水平排名進(jìn)行比較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見表4),云南、貴州、廣西是兩項排名差異較大的三個省份,2014年這三省的居民平均消費水平分別為第29位、30位和27位,但網(wǎng)絡(luò)平均購買水平排名分別為第7位、第10位和第18位。這也意味著信息技術(shù)的廣泛應(yīng)用,則從“供給側(cè)”一端促進(jìn)了中西部地區(qū)消費能力的釋放并帶動消費的整體增長。然而,貨流量與中西部虛擬變量交叉項的系數(shù)為-0.104,且在1%水平下顯著,這表明中西部地區(qū)物流配套的相對滯后制約著居民消費的增長,而互聯(lián)網(wǎng)改造下的消費經(jīng)濟必將從“需求側(cè)”一端促進(jìn)這些區(qū)域基礎(chǔ)設(shè)施的完善,從而形成消費增長與物流網(wǎng)絡(luò)完善的良性循環(huán)機制。

表3 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對消費增長的影響分析(2004-2013)
注:***、**、*分別表示參數(shù)估計在1%、5%、10%的水平下顯著,括號內(nèi)的數(shù)值為標(biāo)準(zhǔn)誤。
表3中模型(5)和(6)分別對東部地區(qū)樣本和中西部地區(qū)樣本進(jìn)行面板回歸,關(guān)鍵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影響關(guān)系及顯著性水平和模型(4)基本一致,這反映了本文的研究結(jié)論具有較強的穩(wěn)健性。在模型(5)中,移動電話普及率(lnrmobile)的系數(shù)為-0.045,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模型(6)中該變量的系數(shù)為0.028,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東部地區(qū)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較高,通過個人電腦網(wǎng)絡(luò)購物與智能手機網(wǎng)絡(luò)購物的替代效應(yīng)顯著,而中西部地區(qū)受限于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消費者進(jìn)行網(wǎng)絡(luò)購物更多地采用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的方式,因此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更大程度地惠及了中西部地區(qū)居民的消費增長。這一研究結(jié)論與麥肯錫發(fā)布的《2015年中國數(shù)字消費者調(diào)查報告》一致,該報告反映互聯(lián)網(wǎng)在三四線城市和農(nóng)村普及率較低,但智能手機的迅速普及為這些地區(qū)的消費者網(wǎng)絡(luò)購物提供了工具。阿里研究院發(fā)布2014年“雙11”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表明,中西部地區(qū)相對東部地區(qū)更倚重“手機搶購”,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成交額在網(wǎng)絡(luò)消費總額中占比排名前十的城市全部來自中西部地區(qū),前100城市里中西部地區(qū)則占據(jù)了76個。
五、研究結(jié)論與政策啟示
為了分析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與消費增長的關(guān)系,進(jìn)而挖掘其背后的傳導(dǎo)機制,本文從包容性創(chuàng)新視角提供了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與消費增長的分析框架和理論假說,利用中國2004-2013年的省級面板數(shù)據(jù),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1)信息技術(shù)的日益普及對居民消費的效應(yīng)顯著為正,且與物流配送形成O2O商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共同促進(jìn)消費增長;(2)信息技術(shù)的廣泛應(yīng)用具有普惠效應(yīng),與東部地區(qū)消費者相比,中西部以及偏遠(yuǎn)地區(qū)的消費者將從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中獲益更多。這兩點顯著支持了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對消費增長以及內(nèi)需擴大的疊加效應(yīng),也顯著地釋放了這些地區(qū)的消費潛力。其深層次原因可歸結(jié)為:
(1)電商應(yīng)用的互動性提升了用戶體驗水平,也拉近了生產(chǎn)者和用戶之間的距離,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用戶需求,帶動用戶消費潛能增長;
(2)電商應(yīng)用能充分展示產(chǎn)品的多樣性,一方面加劇產(chǎn)品的競爭,另一方面通過多維度信息采集和設(shè)計理念的碰撞提升了產(chǎn)品設(shè)計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
(3)智能終端所蘊含的個性化,輔之以大數(shù)據(jù)分析,可以更深層次挖掘用戶需求,加之交易技術(shù)和商業(yè)模式的創(chuàng)新,消費市場的效率和水平得到明顯提升,從而滿足了多樣化的消費需求與消費升級;
(4)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區(qū)域產(chǎn)品的特質(zhì)在電商平臺下可以低成本展示和營銷,同時高便攜性的終端為偏遠(yuǎn)地區(qū)用戶需求的表達(dá)提供便利,有利于將數(shù)字鴻溝進(jìn)一步彌平。

表4 典型省市居民網(wǎng)絡(luò)平均購買水平與平均消費水平排名比較
數(shù)據(jù)來源:根據(jù)阿里研究院和國家統(tǒng)計局?jǐn)?shù)據(jù)整理,括號內(nèi)為居民平均消費水平排名。
我國十三五規(guī)劃明確提出“發(fā)揮消費對增長的基礎(chǔ)作用,著力擴大居民消費,促進(jìn)流通信息化、標(biāo)準(zhǔn)化、集約化”。在全球經(jīng)濟新常態(tài)的背景下,統(tǒng)一而龐大的國內(nèi)市場是我國經(jīng)濟轉(zhuǎn)型升級的重要依托,而信息技術(shù)的廣泛應(yīng)用正成為釋放大國市場消費潛力的引擎(李建偉,2015)[16]。而政策的有效引導(dǎo),可以更好地發(fā)揮本土市場優(yōu)勢,為我國創(chuàng)新驅(qū)動的經(jīng)濟轉(zhuǎn)型提供內(nèi)生動力。
從全國范圍看,需要著力推進(jìn)電子商務(wù)平臺建設(shè),在扶持綜合型電商平臺提供優(yōu)質(zhì)公共服務(wù)的同時,鼓勵發(fā)展專業(yè)型平臺。越來越多的企業(yè)和個人通過以電子商務(wù)平臺為核心的新商業(yè)基礎(chǔ)設(shè)施降低交易成本、共享商業(yè)資源、創(chuàng)新商業(yè)服務(wù),也極大地促進(jìn)了居民消費的快速增長。而專業(yè)型平臺有利于行業(yè)信息采集和運行趨勢實時發(fā)布,影響國際市場產(chǎn)品定價權(quán)。根據(jù)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調(diào)查,網(wǎng)上銷售價格平均比線下價格低6%-16%,2011年網(wǎng)絡(luò)零售將全國的平均零售價格拉低了0.2%-0.4%,2012年則拉低了0.3%-0.6%。平均零售價格的降低意味著相對購買力增加,進(jìn)而刺激了消費增長,這種收入效應(yīng)對消費的刺激在欠發(fā)達(dá)的中西部地區(qū)將更為明顯。2014年7月,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fā)布的《中國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互聯(lián)網(wǎng)對生產(chǎn)力與增長的影響》預(yù)計,2013年至2025年,互聯(lián)網(wǎng)將幫助中國提升GDP增長率0.3-1.0個百分點[17]。這意味著互聯(lián)網(wǎng)經(jīng)濟不是一個靠刺激內(nèi)需的短期投資思維,而是內(nèi)生驅(qū)動的經(jīng)濟體,是解決中國經(jīng)濟長期發(fā)展問題的新范式。
而東部和中西部由于信息化的不同影響特征,政策的側(cè)重點也應(yīng)有所不同。從東部地區(qū)的信息化領(lǐng)先優(yōu)勢看,信息技術(shù)與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的深度融合,可以整合優(yōu)化行業(yè)資源、節(jié)省交易成本、促進(jìn)市場需求與生產(chǎn)供給的“精準(zhǔn)對接”,避免生產(chǎn)過剩或供給不足,促進(jìn)資源有效利用,即成本集約基礎(chǔ)上市場需求側(cè)的增長。另一層面,信息化提升產(chǎn)品的技術(shù)水平、加速傳統(tǒng)生產(chǎn)方式變革,形成創(chuàng)新驅(qū)動的新業(yè)態(tài)和新模式,通過供給側(cè)改革提升全要素生產(chǎn)率,推動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邁向中高端。
據(jù)此,東部地區(qū)一是推進(jìn)兩化深度融合,將加快新興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作為拉動我國內(nèi)需增長的重要引擎。加快信息在服務(wù)業(yè)和制造業(yè)中的滲透速度,有效地降低了社會交易成本,促進(jìn)了社會分工協(xié)作,提高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挖掘和提升消費潛力,改變消費行為、企業(yè)形態(tài)和社會創(chuàng)造價值的方式。
二是加大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創(chuàng)新力度,引爆社會創(chuàng)新。通過稅收和資金等政策,引導(dǎo)產(chǎn)品和服務(wù)創(chuàng)新;構(gòu)建電子商務(wù)科技創(chuàng)新體系,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核心技術(shù)和創(chuàng)新產(chǎn)品;建立院校與企事業(yè)單位合作人才培養(yǎng)機制,為電商發(fā)展提供人才保障,通過電商帶動信息化、網(wǎng)絡(luò)化和大數(shù)據(jù)分析,從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化變革提升企業(yè)創(chuàng)新能力。
三是營造良好的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環(huán)境,促進(jìn)企業(yè)電商應(yīng)用和業(yè)務(wù)創(chuàng)新互動提升。引導(dǎo)企業(yè)從關(guān)注生產(chǎn)和銷售轉(zhuǎn)向更加關(guān)注用戶需求和產(chǎn)品設(shè)計,以增強企業(yè)在產(chǎn)業(yè)價值鏈中的主導(dǎo)地位,支持企業(yè)的設(shè)計數(shù)字化、裝備智能化、生產(chǎn)過程自動化等智慧制造和智慧服務(wù)全過程,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推進(jìn)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
而中西部地區(qū)則須抓住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帶來消費增長的普惠效應(yīng),結(jié)合區(qū)域特色以及資源優(yōu)勢,加大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尋求產(chǎn)業(yè)分工中的合理定位。把握消費結(jié)構(gòu)升級的趨勢,鼓勵依托資源和特色優(yōu)勢催生出新的商業(yè)模式甚至新的商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進(jìn)一步影響和加速區(qū)域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的“電子商務(wù)化”,促進(jìn)和帶動經(jīng)濟整體增長。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有可能借助互聯(lián)網(wǎng)經(jīng)濟實現(xiàn)東部和中西部的錯位發(fā)展,實現(xiàn)“換道超車”,成為“網(wǎng)上WTO”規(guī)則的制定者。
據(jù)此,中西部地區(qū)則應(yīng)注重:一是提高中西部以及農(nóng)村地區(qū)互聯(lián)網(wǎng)尤其是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這不僅對消費增長有較大的促進(jìn)空間,而且有利于縮小區(qū)域發(fā)展差異。2014年,中國東部地區(qū)移動電話普及率達(dá)到113.4部/百人,而中、西部地區(qū)移動電話普及率分別為85.4部/百人和78.7部/百人,區(qū)域差距仍然較大。此外,盡管寬帶和3G網(wǎng)絡(luò)已遍布我國東部大城市,但中西部以及農(nóng)村地區(qū)的互聯(lián)網(wǎng)覆蓋程度仍然參差不齊。2014年,我國家庭寬帶滲透率僅為40.9%,遠(yuǎn)落后于美國(70%)和德國(61%)等發(fā)達(dá)國家。我國城市寬帶用戶凈增1021萬戶,是農(nóng)村寬帶用戶凈增數(shù)的7.5倍,城鄉(xiāng)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差距依然較大。為此,政府應(yīng)在中西部以及農(nóng)村地區(qū)擴展寬帶和3G+基礎(chǔ)設(shè)施,提供類似“家電下鄉(xiāng)”方式的激勵方案,加快互聯(lián)網(wǎng)應(yīng)用的廣度與深度,以釋放積累的消費需求以及促進(jìn)區(qū)域均衡發(fā)展。
二是加強交通運輸、商貿(mào)流通、電商、快遞企業(yè)等相關(guān)物流服務(wù)網(wǎng)絡(luò)和設(shè)施的共享銜接,加快完善中西部地區(qū)物流體系,發(fā)展第三方配送和共同配送,重點支持老少邊窮地區(qū)物流設(shè)施建設(shè),提高流通效率。加強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地集配和冷鏈等設(shè)施建設(shè)。克服區(qū)域消費瓶頸,帶動區(qū)域消費增長。
三是依托資源和區(qū)域特色,鼓勵依托互聯(lián)網(wǎng)的商業(yè)模式創(chuàng)新,以此拉動消費實現(xiàn)包容性增長。目前我國城鄉(xiāng)居民消費結(jié)構(gòu)正處于快速升級的新階段,農(nóng)村電商快速崛起。2014年,中國農(nóng)村電商銷售額已超過1400億元人民幣,消費結(jié)構(gòu)正處在生存型消費向發(fā)展型消費、傳統(tǒng)消費向新型消費、物質(zhì)型消費向服務(wù)型消費升級的重要時期。新技術(shù)的采納和商業(yè)模式的轉(zhuǎn)變往往是相生相伴的。中西部地區(qū)更需依托信息技術(shù)的包容性創(chuàng)新明確合理的產(chǎn)業(yè)定位,實現(xiàn)區(qū)域快速發(fā)展。
四是提高消費信息的有效供給與引導(dǎo),增強農(nóng)民對有效信息的利用能力,進(jìn)一步縮小“二級數(shù)字鴻溝”,使農(nóng)民享受到“信息紅利”。與信息的可接入性被稱為“一級數(shù)字鴻溝”相對應(yīng),“二級數(shù)字鴻溝”則是信息的利用和鑒別能力,未來要進(jìn)一步提高信息技術(shù)的普惠效應(yīng),利用公共服務(wù)的方式提升信息服務(wù)和共享的質(zhì)量,促進(jìn)“二級數(shù)字鴻溝”的消除。
[1]畢達(dá)天,邱長波.B2C電子商務(wù)企業(yè)——客戶間互動對客戶體驗影響機制研究[J].中國軟科學(xué),2014(12):124-135.
[2]Bhavnani A,Won-Wai Chiu R,Janakiram S,et al.The role of mobile phones in sustainable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R].World Bank,2008.
[3]Shiu A,Lam P.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its regions [J].Regional Studies,2011,42(5):705-718.
[4]張歷紅,周勤,王成璋.信息技術(shù)、網(wǎng)絡(luò)效應(yīng)與區(qū)域經(jīng)濟增長:基于空間視角的實證分析[J].中國軟科學(xué),2010(10):112-123.
[5]Jensen R.The digital provide:Information technology,market performance and welfare in the south indian fisheries sector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7,122(3):879-924.
[6]Conley T,Udry C.Learning about a new technology:Pineapple in Ghan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1):35-69.
[7]李坤望,邵文波,王永進(jìn).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礎(chǔ)設(shè)施與企業(yè)出口績效[J].管理世界,2015(4):52-65.
[8]George G,McGahan A M,Prabh J.Innovation for inclusive growth: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 research agenda [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2,49(4):661-683.
[9]Aker J.Information from markets near and far:Mobile phones and agricultural markets in Niger [J].Applied Economics.2010(2):46-59.
[10]Qiang C,Z W Rossotto,C M.Economic impacts of broadband [C].//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2009:Extending reach and increasing impact.World Bank,2009:35-50.
[11]譚曉林,趙定濤,謝偉.企業(yè)電子商務(wù)采納的影響機制研究[J].中國軟科學(xué),2015(8):184-192
[12]Shin J.How does free riding on customer service affect competition? [J].Marketing Science,2007,26(4):488-503.
[13]Duan W,Gu B,Whinston A B.Do online reviews matter?-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panel data [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8,45(4):1007-1016.
[14]Trusov M,Bucklin R E,Pauwels K.Effects of word-of-mouth versus traditional marketing:findings from an internet social networking site [J].Journal of Marketing,2009,73(5):90-102.
[15]劉秉鐮,劉玉海.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與中國制造業(yè)企業(yè)庫存成本降低[J].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2011(5):69-78.
[16]李建偉.居民收入分布與經(jīng)濟增長周期的內(nèi)生機制[J].經(jīng)濟研究,2015(1):111-123.
[17]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中國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互聯(lián)網(wǎng)對生產(chǎn)力與增長的影響[R].麥肯錫咨詢公司,2014.
(本文責(zé)編:辛城)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Inclusive Innovation and Consumption Growth
HUANG Wei-dong,YUE Zhong-gang
(CollegeofManagement,NanjingUniversityof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s,Nanjing210046,China)
Does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bstitute online retail for brick-and-motor retail,or promote newly increased consump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theoretical hypothe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consumption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innovation.Using the data for the period 2004-2013,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marginal effect and inclusive effect of consumption growth promo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This paper finds the adoption ra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luences positively gross consumption and brings more benefits to the consumers in West-middle regions.The conclusions have mor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 for the strategy of Internet plus to promote consumption growth and reg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inclusive innovation;consumption growth
2015-10-21
2016-04-12
國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項目資助(71302168)。
黃衛(wèi)東(1968-),男,江蘇連云港人,南京郵電大學(xué)管理學(xué)院教授、社會科學(xué)處處長,博士,研究方向:產(chǎn)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
F49
A
1002-9753(2016)05-016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