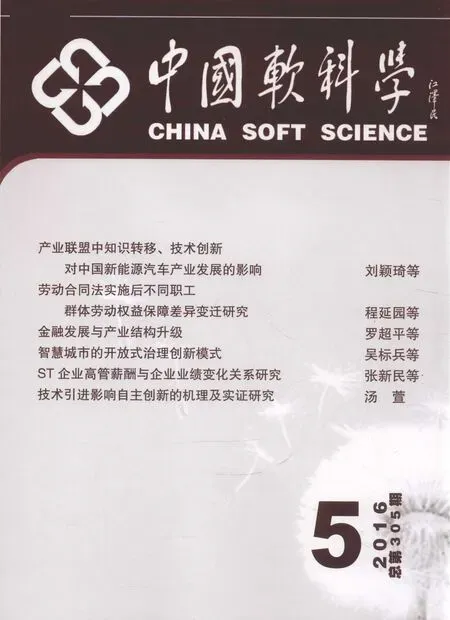勞動合同法實施后不同職工群體勞動權益保障差異變遷研究
程延園,宋皓杰,王甫希,謝鵬鑫,王 暢,尹 奎
(1.中國人民大學, 勞動人事學院,北京 100872; 2. 羅格斯大學, 管理與勞動關系學院, 美國 新澤西州 08854)
?
勞動合同法實施后不同職工群體勞動權益保障差異變遷研究
程延園1,宋皓杰1,王甫希2,謝鵬鑫1,王暢1,尹奎1
(1.中國人民大學, 勞動人事學院,北京100872; 2. 羅格斯大學, 管理與勞動關系學院, 美國新澤西州08854)
本研究基于2007年與2012年中國職工狀況調查,采用比率差異檢驗法分析了《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后,不同文化程度、戶籍身份與就業身份的職工群體在各項勞動權益保障上的差異變化。結果顯示勞動合同法的制度力量推動了不同勞動者群體在某些勞動權益保障方面的差異日益縮小,但在多數勞動權益狀況上,差異現象依然顯著。
勞動合同法;勞動權益;差異化;趨同;趨異
一、文獻綜述與問題提出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在經歷了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后進入了快速增長軌道,但GDP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各種社會矛盾也日益顯現,其中勞資矛盾成為突出問題。現實中,“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往往導致職工履行了對企業的義務職責,企業卻難以保證勞動者的權利,尤其是弱勢勞動者群體的合法權益。自21世紀以來,血汗工廠、拖欠工資、超時勞動等報道不絕于耳。而且這種勞動權益侵害現象常見于農民工以及文化程度較低的靈活性就業群體中。這些職工群體為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的高速發展了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但是同時也因為自身的弱勢地位,更易遭受不公平待遇,合法勞動權益極易受到侵害。 為了解決法律保護工人權利不足的問題,促進勞動關系的正規化,進入 2000 年以來各政府部門開始思考修訂已有相關法律政策。2007年6月29日,醞釀已久的《勞動合同法》應運而生,以堅持和突出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為立法宗旨,全面強化了勞動關系矛盾的源頭治理,為相對弱勢職工的勞動權益提供了強有力的立法保障。
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國內外眾多學者對該法案的勞動權益保障效應進行了分析。有研究者認為勞動合同法妥善處理了企業效率與保護弱者的公平之間的平衡關系,使新的勞動管理體系體現出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著眼解決了現實勞動關系中用人單位不簽訂勞動合同、拖欠工資、延時加班等諸多侵害勞動者利益的問題,是對勞動者地位弱化等社會問題的理性回應[1-3]。Li和Freeman(2014)通過對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后珠三角農民工開展的調研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新法的實施顯著提升了農民工的社會保險覆蓋率,降低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發生率[4]。Gallagher, Giles 和 Park等(2014)通過對比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后兩次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調查數據,發現新法實施后,相對弱勢勞工的勞動權益保障得到顯著改善,城鎮職工與農民工以及不同文化程度職工群體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差異趨于消失[5]。
但是也有學者對新法的勞動權益保障效應產生質疑,認為在政府主導的各種價值分配以及與此有關的各種公共政策中,弱勢群體的愿望和利益不容易得到及時有效的反映,嚴格的勞動保護雖然提高了一般勞動者的福利,但卻是以犧牲就業弱勢群體的福利為代價,從而加劇了社會差距[6-7]。研究者指出,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更有利于城鎮職工勞動權益的保障,新法實施后,企業在勞動合同簽訂方面會采取歧視性策略:與人力資本價值高、談判能力較強的員工簽訂正式的書面勞動合同;同時,與談判能力較弱的農民工簽訂非全日制勞動合同甚至達成口頭協議,以替代正式的書面合同[8-9]。一些數量更大的弱勢群體的勞動權益保障仍然受到損害,如勞務派遣員工與非勞動派遣職工群體具有同工不同酬等現象、農民工的加班加點問題仍然存在,甚至更為嚴重[10]。已有研究基于人力資本理論與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對該差異產生的原因進行了描述。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個體知識、技術和能力積累的結果,是企業核心競爭優勢形成的重要組成。由于農民工等相對弱勢就業群體的人力資本程度較低,法律意識薄弱,在勞動力市場上就業能力和談判能力也較弱。因此,對于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主要目標的企業而言,更傾向于吸納和保留城鎮職工、受教育程度水平較高的職工以及管理者等職工群體,為他們提供相對更多的勞動權益保障[11-12]。此外也有研究者從勞動力市場分割的視角指出勞動力市場可以劃分為一級勞動力市場和次級勞動力市場。在一級勞動力市場,雇員人力資本存量高,工作條件好,工資福利待遇高,員工就業穩定并有晉升機會;而在次級勞動市場,雇員人力資本存量低,工作條件差,企業對其要求苛刻且監督管理任意專橫,工資福利待遇低。由于農民工等相對弱勢職工群體人力資本較低,多位于次級勞動力市場,因此其勞動權益也相對更難得到保障[13]。
學界的研究為本文奠定了堅實的研究基礎,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已有實證研究調查范圍偏小,主要針對某個或某些城市或區域數據開展研究,尚缺乏全國范圍內的調查數據。第二,以往的實證研究,盡管對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后不同職工群體的勞動權益保障差異進行了描述分析,但是較少通過對比說明該差異特征的變化趨勢。第三,已有研究在對差異現象進行理論闡釋時,較多基于靜態視角依托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對勞動權益保障的差異現象進行闡釋,未基于動態視角考慮企業所處制度環境的變遷。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明確規定,要切實保障職工取得勞動薪酬、休息休假、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與社會保險的權利。在勞動合同法背景下,對不同勞動者群體的勞動權益保障狀況進行差異分析,既是對當前中國職工群體基本權益保障狀況的考察,也是理解勞動合同法制度實踐效應的重要基礎。本文利用2007年與2012年共八萬余名的中國職工狀況調查數據,對比了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后,不同年齡、文化程度、戶籍身份與職工身份特征的勞動者群體在各項勞動權益保障狀況上的差異,基于組織制度理論對該差異變遷背后的原因進行了探析。
二、 研究方法
(一)數據收集
本文數據來源于《第六次中國職工狀況調查》和《第七次中國職工狀況調查》,分別由中華全國總工會于2007年和2012年在全國范圍內多階段分層隨機抽樣調查統計。2007年,全總調查辦公室與國家統計局合作在北京、山西、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廣東、四川、云南、山西、甘肅、新疆等15個省(區、市)進行總數為42000個樣本的全國職工問卷抽樣調查,即在以上每個省(區、市)的城市住戶中,入戶對2000名職工做文件抽樣調查;在農民工相對集中的10個省(區、市)抽選一定數量的企業各做1200名農民工的文件抽樣調查。其中,男性占57.4%,女性占42.6%,大專以下文化程度職工占74.2%,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職工占25.8%,五十以上職工占9.0%,五十以下職工占91.0%。
2012年全總調查辦公室組織各省(區、市)總工會在北京、內蒙古、遼寧、江蘇、浙江、安徽、附件、山東、河南、湖北、廣東、重慶、四川、山西、甘肅15個省(區、市)進行總數為45000個樣本的全國職工問卷抽樣調查,在每個省會城市抽選40個單位、每個地級市抽選40個單位,每個縣(市)抽選10個單位。在直轄市中,每個城區抽選40個單位,每個郊區(縣)抽選10個單位,原則上每個單位各調10名職工。兩次調查問卷的有效回收率分別為100%和99.6%,具體樣本特征描述性分析如表1所示。其中,男性占51.1%,女性占48.9%,大專以下文化程度職工占52.6%,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職工占47.4%,五十歲以上職工占7.4%,五十以下職工占92.6%。

表1 各項職工勞動權益保障指標的操作性定義
(二)統計方法
本研究從2007年和2012年《中國職工狀況調查》中選取了13項反映職工勞動權益的關鍵性指標,具體內容涉及勞動合同簽訂權益、勞動薪酬權益、休息休假權益、勞動安全保護權益、社會保障權益,各項指標的操作性定義如表1所示。以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戶籍身份的職工群體為研究對象,采用獨立樣本比率差異Z檢驗分析了不同特征的職工群體在各項勞動權益保障指標上的差異。
三、研究結果
(一)不同戶籍身份職工群體勞動權益保障間的差異
如表2、表3所示,《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后,不同戶籍身份職工的勞動權益保障差異如下:第一,在勞動合同簽訂上,勞動合同法實施后,相對城鎮職工,企業更不傾向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或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實施后,農民工未簽訂勞動合同的人數比例與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人數比例均顯著低于城鎮職工。第二,在勞動薪酬權益上,勞動合同法實施后,農民工的工資拖欠與工資收入水平均有所改善。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人數比例降至與城鎮職工群體無顯著差異,并且企業支付農民工未達最低標準工資的人數比例始終顯著低于城鎮職工。第三,在休息休假權益上,農民工的延時加班,勞動超負荷現象始終嚴重。農民工每天或經常加班的人數比例以及八小時工作制內不能完成勞動定額的人數比例始終顯著高于城鎮職工。第四,在勞動安全衛生權益上,盡管農民工簽訂的勞動合同中未規定勞動安全條款的人數比例始終顯著低于城鎮職工。但是,勞動合同法實施后,農民工未參加安全培訓的人數比例顯著較高,由13.30%顯著上升至24.82%,而城鎮職工群體則由24.85%、下降至3.27%。第五,在社會保險權益上,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狀況較差。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后,企業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的人數比例始終顯著低于城鎮職工。2007與2012年,企業為農民工繳納五險的人數比例由13.86%-43.88%上升至42.81%-67.44%,但為城鎮繳納社會保險的人數比例由22.21%-71.00%大幅上升至58.86%-84.68%。

表2 2007年城鎮職工與農民工職工群體在各項勞動權益保障狀況上的差異

表3 2012年城鎮職工與農民工職工群體在各項勞動權益保障狀況上的差異
(二)不同文化程度職工群體勞動權益保障的差異
如表4、表5所示,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后,不同文化程度職工的勞動權益保障差異如下:第一,在勞動合同簽訂權益上,結果顯示,2007年與2012年,較高文化程度職工未簽訂勞動合同的人數比例始終較低,但是,其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的人數比例則由19.57%下降至16.86%,反之,較低文化程度職工的人數比例則由16.33%上升至18.48%。第二,在勞動薪酬權益上,較低文化程度的職工薪酬保障狀況始終較差。企業拖欠其工資的人數比例以及支付其未達當地最低標準工資的人數比例均顯著高于較高文化程度職工。第三,在休息休假權益上,結果顯示職工的文化程度越低,延時加班狀況越嚴重。勞動合同法實施后,盡管不同文化程度職工群體在八小時內難以完成勞動定額的人數比例上差異不顯著,但是文化程度較低的職工群體每天或經常加班的人數比例始終顯著較高。第四,在勞動安全保護權益上,較高文化程度職工簽訂的勞動合同中未規定勞動安全條款的人數比例始終顯著較高。此外,盡管不同文化程度職工群體未參加任何安全培訓的人數比例差異趨于消失,但是二者狀況均有所惡化,未參加培訓的人數比例分別由18.11%、20.74%上升至23.62%、24.14%。第五,在社會保險權益上,職工的文化程度越低,社會保障越差。結果發現,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后,企業為較低文化程度職工繳納社會保險的人數比例為14.71%-49.84%,45.05%-67.08%,均顯著低于較高文化程度的職工群體。
(三)不同就業身份職工群體勞動權益保障的差異
如表6、表7所示,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后,不同就業身份職工的勞動權益保障差異如下:第一,在勞動合同簽訂權益上,相對于普通職工,管理人員始終處于相對優勢,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人數比例始終顯著較高,未簽訂合同的人數比例始終顯著較低。第二,在勞動薪酬權益上,盡管新法實施前后,管理人員與普通職工被拖欠工資的人數比例均較低,且差異不顯著。但是2012年,普通職工的基本工資水平狀況顯著惡化,以最低基本工資標準為例,企業支付普通職工的工資低于該標準的人數比例由顯著低于轉換為顯著高于管理人員。第三,在休息休假權益上,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后,管理者與普通職工的加班狀況均較為頻繁。二者每天或經常加班的人數比例始終無顯著差異,管理者的工作負擔加重,在八小時工作日內未能完成勞動定額的人數比例由低于普通職工,上升至與普通職工差異不顯著。第四,在勞動安全權益上,普通職工的保障狀況轉差。普通員工簽訂的勞動合同中未規定勞動安全條款的人數比例由與管理人員無顯著差異上升為顯著較高,并且從未參加安全培訓的人數比例也始終顯著高于管理人員。第五,在社會保險權益上,普通職工的保障狀況同樣較差,他們簽訂的勞動合同中未規定社會保險條款的比例始終顯著高于管理人員,持有社會保險的人數比例顯著低于管理人員。新法實施前后,企業為普通員工繳納社會保險的人數比例由23.24%-57.51%上升至2012年的63.46%-87.77%,而為管理人員繳納五險的人數比例則由39.22%-79.02%上升至74.70%-93.64%。

表4 2007年不同文化程度職工群體在各項勞動權益保障狀況上的差異

表5 2012年不同文化程度職工群體在各項勞動權益保障狀況上的差異

表6 2007年管理者與普通職工群體在各項勞動權益保障狀況上的差異

表7 2012年管理者與普通職工群體在各項勞動權益保障狀況上的差異
四、結果討論
(一)勞動合同法實施后不同職工群體勞動權益保障的差異呈現趨同趨勢
結果顯示,勞動合同法實施后,不同職工群體在某些勞動權益保障狀況上的差異趨于消失,呈現出趨同的趨勢。相對弱勢職工在某些勞動權益保障狀況上顯著改善,如新法實施后,較低文化程度的職工群體的勞動關系趨于穩定,不同文化程度職工群體簽訂無固定合同的人數比例差異基本消失,農民工的工資拖欠降低至與城鎮職工無顯著差異。
究其原因,組織制度理論是組織研究中理解、分析和預測組織行為的重要視角。該理論認為組織行為不僅受到經濟利益最大化目標的驅動,而且受到外部制度環境的影響,如法律政策的影響。制度環境要求組織服從“合法性”機制,采取那些在制度環境下理所當然的做法,而不管這些做法對組織運作是否有效率[14]。Scott(2008)進一步分析了合法性機制的三大要素,認為制度主要通過強制性、規范性與文化認知性因素對組織產生影響[15]。盡管在文化認知因素上,由于我國曾經歷過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權力本位、關系本位、人情本位意識仍然濃厚,導致法治文化建設是一個長期而漸進、曲折而艱苦的過程,勞動合同法難以在短期內通過構建社會共享的法制文化理念對企業產生“合法性”影響。但是勞動合同法的出臺通過強制性與規范性兩方面增強了制度的“合法性”。
具體而言,強制性因素意味著制度通過制定規則、監督承諾和獎懲行動來規制企業行為。勞動合同法對勞動者的各項權益進行了明確規定,加大了懲罰力度,迫使和威懾資方不得不守法。在勞動合同簽訂權益上,第十條、第十四條明確規定了勞動合同的書面形式與簽訂期限,對企業不及時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行為追究法律責任;此外還擴大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適用情形,以促使勞動關系更加長期穩定。在勞動薪酬權益保障上,第十七條、第三十條、第八十五條明確規定了薪酬是勞動合同簽訂的必備條款,并規定基本工資不得低于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用人單位拖欠勞動薪酬或者未足額支付的,勞動者可依法向當地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在休息休假權益保障上,第十七條、第三十一條規定明確規定工作時間是勞動合同的必備條款,要求用人單位應當嚴格執行勞動定額標準,不得強迫或者變相強迫勞動者加班,以此規制長時間加班現象。在勞動安全權益保障上,第三十二條規定用人單位需要嚴格執行國家勞動標準提供相應的勞動條件和勞動保護。在社會保險權益保障上,第十七條、第四十九條將社會保險作為合同簽訂內容的必備條款,為社會保險的辦理和征繳提供了法律基礎。此外,勞動合同法頒布后,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強有力措施,開發了一系列與勞動合同法配套的法律法規,形成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例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安部也針對農民工聯合開展了工資支付情況專項調查,也有一些地方實施了建設工程務工人員工資保障金制度,對農民工按時拿到足額工資進行幫助[16]。在規范性因素方面,勞動合同法也通過構建集體共享的價值觀和規范增強了對企業的合法性影響。保護員工的勞動權益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組成,勞動合同立法從勞動合同的訂立、履行和變更、解除和終止方面規定了企業要保護勞動者權益[17-18]。政府在制定勞動合同法過程中,將草案向全社會公布,公開征求意見,中國普通工人和市民向政府提交了19萬條針對該法律的建議,支持新法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19]。對新法草案的討論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提升了勞動者的權利意識,促使保護勞動者權益成為社會共識。
綜上,勞動合同法制度的出臺增強了企業所處制度環境的合法性。在制度合法化機制的作用下,組織行為完全受制度的約束, 投機行為的可能性降低, 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從人治轉向法治模式[20]。勞動合同法規定該法案一視同仁適用于所有勞動者,不因勞動者身份不同而有所差別[21]。這些制度環境的變化對組織行為提出新的調整。無論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程度是否能夠為組織帶來最大化的經濟效益,組織均應當依據勞動合同法為所有職工提供勞動權益保障,以獲得“合法性”。因此,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在合法性機制的影響下,企業逐漸提升了保護農民工等弱勢職工勞動權益的意識,使得不同職工群體獲取勞動權益保障的差異逐漸縮小。
(二)勞動合同法實施后不同職工群體勞動權益保障的差異呈現趨異趨勢
但是結果發現,在絕大多數勞動權益保障方面,不同戶籍身份、教育水平以及普通職工和管理者之間仍然存在顯著差異,這種差異甚至呈現出擴大的趨勢。盡管勞動合同法普遍約束和規定了勞動者的權益,但是處于弱勢地位的職工群體,如年長、大專以下文化程度的職工、農民工與普通職工,在多數勞動權益指標上仍然處于顯著劣勢。
究其原因,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制度的實施效應是由占據不同利益的個人和群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決定的,不同利益位置的當事人會對制度變遷作出不同的反應,受到制度所涉及的各方主體的行為邏輯不同的影響,制度的實施效應便會呈現出差異化的效果[22],因此,以勞動合同法為背景,政府、企業與勞動者群體三方的互動,會讓不同類型職工群體的勞動權益保障產生差異化效應。首先,對于政府而言,由于缺乏良好的監督與執行,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效果受限,進而削弱了制度對組織的“合法性”影響[23]。由于各地推動新法實施的力度不一或者選擇性執法,勞動監察人員數量嚴重不足,勞動合同法難以取得較好的執行效力,弱化了制度的強制性與規范性影響,進而為組織的脫耦行為滋生了場域空間。在該背景下,企業更易產生部分遵從行為,僅僅為人力資本較高程度的職工提供勞動權益的保障,而忽視相對弱勢職工群體的勞動權益。其次,對于企業而言,仍然難以擺脫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效率邏輯的限制。企業在遵守勞動合同法,主動為勞動者付出較高成本的同時,也會評估勞動者帶來的預期收益。由于文化程度較低的職工、農民工與普通職工的人力資本較低,其工作可替代性強,為企業可能帶來的預期收益較低,因此,企業更易忽視和規避對相對弱勢職工群體的保障,側重于保障人力資本較高的職工群體的勞動權益。最后,對于勞動者而言,農民工等相對弱勢勞動者群體長期處于社會底層,法制觀念薄弱,文化程度較低,主動維權意識較差。盡管勞動合同法賦予了勞動者保障勞動權益的權利,但是這些勞動者卻無法積極主動的利用法律武器積極主動的維權。
綜上,在政府對法律監管不嚴、企業效率邏輯的慣性以及相對弱勢勞動者維權意識薄弱的相互作用下,勞動合同法對勞動權益的保障效應仍然難以惠及相對弱勢職工群體。其一,在勞動合同簽訂權益上,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11,13],勞動合同法實施后仍然有大量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群體,這些群體主要有:大專以下文化程度職工、農民工和普通職工。這些職工的文化水平較低、法律意識薄弱,加之其流動率高的特點,企業往往不會主動要求與其簽合同。同時,本研究通過訪談發現,農民工不簽訂勞動合同的原因不只是老板不愿意簽合同,更多的是在他們自身,其中很多人維權意識淡薄,認為只要按時拿到工資和加班費這些基本的利益,簽沒簽書面合同并不重要[24]。此外,由于農民工和普通工人人力資本價值偏低,在勞動力市場可替代性較強等特點,使這類弱勢職工群體簽訂無固定勞動合同的比例也較低,難以與企業建立長期穩定的勞動關系。其二,在勞動薪酬權益上,結果發現中低文化程度的職工群體由于維權意識薄弱,人力價值較低,基本工資更易低于當地規定的最低工資、也更容易被拖欠工資。而文化程度較高的職工更易獲得高穩定性、高規范性的工作[25]。其人力資本價值較高,從而薪酬權益更多可以通過市場調控的力量得以保障。其三,在休息休假權益保障上,一方面可以發現在企業之間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下,管理人員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工作時間確保工作績效,所以與普通職工在延時加班方面的差異并不顯著;另一方面可以發現,企業為了爭取利潤最大化,謀得生存發展,通常會犧牲底層員工的利益。這些職工往往是文化程度較低的職工或農民工群體,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力較低,并面臨來自家庭和生活的雙重壓力,經濟需求較高,對工作的需要更大,寧愿在忍受加班上做出讓步,因此面對加班情況更容易默默接受[26-27]。此外,也是由于其文化素質較低,自我保護意識較差,更容易受到企業維權行為的侵害。其四,在勞動安全權益保障上,由于企業對維護職工安全的意識淡薄,且開展安全生產培訓將增加用工成本,而文化程度較低的職工、農民工與普通職工群體流動性較強,勞動關系不穩定,因此多數中小民營化企業從用工成本上考慮并不愿主動在安全培訓方面投入,致使農民工等成為安全事故的高發人群;另一方面,從職工角度看,農民工、年輕或普通職工群體受教育水平總體較低,缺乏必要的安全知識和自我防范意識,加之就業壓力大,往往會忽視自己安全生產培訓的權益。其五,在社會保險權益保障上,當前企業中,小微私營企業比重較大,其經濟實力較弱,會大幅度增加企業直接用工成本,企業基于利潤最大化考慮,會采取投機行為規避繳納社會保險,尤其是為人力資本程度較低的職工群體繳納。另一方面,由于這類職工的工作流動性較大,勞動關系不穩定,且其自身參保意識薄弱,更愿意接受直接增加的工資,而非繳納難以轉移且收益不確定的社會保險[28]。相關實證研究表明,農民工群體因其經濟承受力不足、對社會保險可持續性的預期不確定、對未來保險關系能否順利轉續持懷疑態度,這些非理性預期因素均是其不愿意參加社會保險的因素[29]。
本文的研究表明,勞動合同法的制度力量推動了不同勞動者群體勞動權益保障的差異呈現日益縮小的趨同趨勢,但該法律制度實施的效果并不均衡,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職工群體,如大專以下文化程度的職工、農民工與普通職工,在多數勞動權益保障方面,仍然處于顯著劣勢。趨同的原因在于企業受到制度合法化壓力的影響以及趨同機制的作用;趨異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勞動監察不力、勞動者的維權意識薄弱以及企業“效率邏輯”慣性的阻礙,這些原因共同削弱了新法實施在勞動者權益保障方面的效應。
[1]程延園. 《勞動合同法》:構建與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J].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5):104-110.
[2]常凱,邱婕. 中國勞動關系轉型與勞動法治重點——從《勞動合同法》實施三周年談起[J]. 探索與爭鳴,2011(10):43-47.
[3]喬健. 邁向 “十二五” 時期中國勞動關系的現狀和政策取向[J].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11,25(3):8-13.
[4]FREEMAN R B,LI X.How Does China’s New Labor Contract Law Affect Floating Workers?[J].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4, 53(4): 711-735.
[5]GALLAGHE M, GILES J, PARK A, WANG M, et al. China’s 2008 Labor Contract Law: Implement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workers[J]. Human Relations, 2015, 68(2): 197-235.
[6]陳東,劉金東. 勞動保護有助于縮小就業弱勢群體的相對收入差距嗎——以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為例[J]. 財貿經濟,2014(12):111-120.
[7]彭向剛,袁明旭. 論轉型期弱勢群體政治參與與社會公正[J].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07,47(1):63-70.
[8]CHENG Z, SMYTH R, GUO F,et al. The impact of China’s new Labour Contract Law on socioeconomic outcomes for migrant and urban workers[J]. Human Relations, 2015, 68(3): 329-352
[9]何一鳴, 羅必良. 政府監督博弈, 企業協約權利管制與農民工雇傭權益保護——以《勞動合同法》 為例[J]. 中國農村經濟,2011(6):26-36.
[10]姚先國. 權利的邊界——反思《勞動合同法》[J]. 經濟學動態, 2011, 5:37-39.
[11]孟凡強,吳江.我國勞動力市場勞動合同簽訂的影響因素與戶籍差異[J]. 產經評論,2013(1):125-134.
[12]李永周,譚園,張金霞. 企業異質型人力資本的體驗性特征及應用研究[J]. 中國軟科學,2011(12):147-156.
[13]宋林,亓同敏. 我國農民工勞動合約簽訂率低的原因分析——基于勞動力市場分割和產業分割的分析框架[J]. 華東經濟管理,2014,28(12):34-40.
[14]ZUCKER L G. Institutional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7, 13: 443-464.
[15]SCOTT W 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From professional dominance to managed care[J].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16]莫南. 工資支付保障金:讓農民工少流淚[J]. 浙江人大,2010(2):64-66.
[17]白曉明. 《 勞動合同法》 社會價值分析——基于勞動者, 企業, 社會長期利益的視角[J].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0(1):100-107.
[18]周怡青,關于公司法與勞動合同法中社會責任規則的比較分析[J]. 法制與社會,2014 (3):25-26.
[19]LIANG Z P. What is legislation for?[J]. Economic Law and Labor Law. 2008, 9:19-24.
[20]王君玲. 試論《 勞動合同法》 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積極效應[J]. 黑龍江社會科學, 2008(4):175-177.
[21]王美艷. 勞動合同法的實施: 問題和對策建議[J]. 貴州財經學院學報. 2013(1):23-31
[22]周雪光, 艾云. 多重邏輯下的制度變遷: 一個分析框架[J]. 中國社會科學, 2010, (4):132-150.
[23] CUI F, GE Y, JING F, et al. The effects of the Labor Contract Law on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J].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2013, 10(3): 462-483.
[24]魏建,肖永潑. 勞動合同法與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意愿[J]. 理論學刊, 2013(10): 93-98.
[25]李濱生. 我國職工工資收入影響因素分析[J]. 中國勞動, 2010(2):20-22.
[26]朱亭瑤. 落地未生根: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與出路[J]. 蘭州學刊, 2013, (3):137-142.
[27]趙萬一. 中國農民權利的制度重構及其實現途徑[J]. 中國法學, 2012(3):5-17.
[28]張暉, 何文炯. 進城, 流動與保障——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綜述[J]. 浙江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7, 37(2):128-133.
[29]孟穎穎. 有限理性的農民工社會保險需求與風險偏好研究——農民工社會保險參與率不足的一個解釋[J]. 經濟管理, 2011(10):159-166.
(本文責編:辛城)
Research on the Disparity of Labor Rights Security among Different Worker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Labor Contract Law
CHENG Yan-yuan, SONG Hao-jie, WANG Fu-xi, XIE Peng-xin,WANG Chang, YIN Kui
(1.SchoolofLaborandHumanResource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2.SchoolofManagementandLaborRelations,RutgersUniversity,NewJersey,US08854)
Drawing on national survey data of more than 80000 workers conducted by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 (ACFTU) in 2007 and 2012 respectively, this article uses proportion difference test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labor rights security among worker group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employment status. The results shows the trend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The convergence is seen in that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employee groups in some aspects of labor rights narrowed. The divergence is seen in that the protection of most labor rights of employee groups with low educational level, migrant workers or ordinary employment status are still in significantly relative disadvantage.
Labor Contract Law; labor rights security; diversity; convergence; divergence
2015-11-05
2016-05-10
程延園(1963-),女,漢族,湖北襄陽人,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研究方向:人力資源管理與勞動關系。通訊作者:宋皓杰。
D922.52
A
1002-9753(2016)05-0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