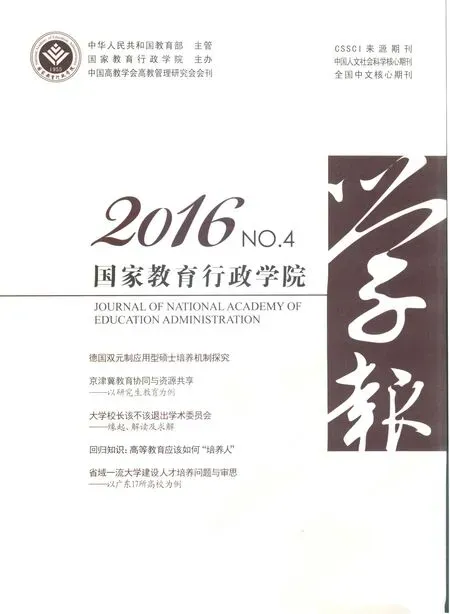國家戰略、一流大學(學科)與科學精英的契合
——基于對我國高等教育兩大戰略實施的理解
范冬清(南京師范大學,江蘇南京210097)
國家戰略、一流大學(學科)與科學精英的契合
——基于對我國高等教育兩大戰略實施的理解
范冬清
(南京師范大學,江蘇南京210097)
為進一步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在“211”、“985”工程之后,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學科)建設以國家戰略的形式發布。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與高等教育領域的重大工程配套疊加,助力大學(學科)向一流邁進。國家戰略、一流大學(學科)與精英人才三者處于共同話語體系,在績效取向與公共性訴求上達成一致。運用系統思考可促成戰略、大學(學科)及科學精英的良性循環,縮短與高等教育強國的差距。
世界一流大學(學科);科學精英;國際競爭力;科研績效;系統思考
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既是大學行為又是政府行為。2015年10月24日,國務院公布《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簡稱“雙一流方案”),指出當前迫切需要在高等教育領域加強資源整合,實施創新。與雙一流方案相呼應的是,《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早在2008年發布。此意見指出人才是第一資源,在綜合國力競爭中具有決定性作用,并將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定位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中央層面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簡稱“千人計劃”)要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用5-10年時間,在國家重點創新項目、學科、實驗室等,引進一批戰略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201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綱領性人才文件——《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進一步指出千人計劃是“重大人才工程”之一。
在國家戰略高度,世界一流大學(學科)的建設與高層次人才的匯聚密不可分,相互對應,互為條件,相互支持。世界一流大學(學科)建設以五年為周期分三步推進,則科學精英人才的匯聚強度也須相應增強。國家戰略、一流大學(學科)與科學精英三者既在績效取向上具有一致性,又在實現大學公共性上相耦合,可經由系統思考打造良性循環體系,以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綜合實力。
一、機遇與挑戰:我國高等教育綜合競爭力分析
我國高等教育綜合實力與高等教育強國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根據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簡稱ESI),至更新到2015年約十年的統計,從各項國際指標來看,我國的論文數僅次于美國,排在世界第二,數量優勢突出,分別是德國的1.7倍,英國的1.9倍。然而,我國以這么大的論文基數,在總被引頻次上除了落后美國外,不敵德國和英國,尤其在篇均被引頻次上,在表1中排名最末,且與歐洲小型高等教育發達國家丹麥(17.61)等相差甚遠;僅與韓國(8.83)、印度(7.48)、巴西(7.40)相當。據湯森路透發布的《2014年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科研精英》研究報告(基于2002-2012年全球論文引文數據),甄選出大量高被引論文(在同年度同學科領域中被引頻次排名位于全球1%的論文),在全球3215位“高被引科學家”中僅有111位在中國大陸任職。[1]
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計算不同排名段大學各指標表現,發布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簡稱ARWU)2015年榜單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4所大學進入世界前150名。由于此榜單上排名前100位的可稱為世界一流大學,其原創性研究水平的學術指標具有領先優勢,如2013-2014年排名前100名的大學,即有若干名獲獎校友、數名獲獎教師、近30名高被引科學家、每五年發表近60篇N&S論文、每年被SCIE&SSCI索引的論文在4500篇左右。排名200名以內的大學也有可能具備上述特征。[2]以此來看,中國的一些大學離世界百強距離并不遙遠。
綜合來看,雙一流方案的提出,是基于我國高等教育綜合競爭力在客觀上具備了一定的基礎和實力上提出的。但從整體數據來看,與高等教育強國相比,我國科學家學術影響力、大學和科研機構、學術聲譽仍亟需得到巨大提升。
從更高的角度而言,國家戰略對我國的大學敢于做出預設,與世界一流大學(學科)在全球性的學術環境中展開競爭,以及在國際人才市場中角逐,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國在經濟上的崛起,可凝聚實力以創造高等教育的一流績效。然而,我國的崛起是經濟上的單方面崛起,迫切需要提升高等教育與文化的軟實力與影響力,以促進綜合國力的平衡發展。

表1 ESI論文國際指標比較(2005年1月-2015年8月)
二、戰略驅動:科學精英的匯聚體現大學的一流水平
科學精英的匯聚是世界一流大學成長的重要變量。世界一流大學最顯著的三個特征是人才高度聚集、充足的資源和順暢的管理。[3]經費的投入、政策的支持、高等教育良好環境的構建、社會的參與、大學內部結構的優化治理等等這些要素綜合產生作用的結果,就是為有效形成支持性的精英人才吸引、使用、留住機制體制,以使得大學在激烈的高等教育競爭場域中集結實力,能產生區別于其他一般大學的學術績效。科學精英是世界一流大學的中心驅動力,具有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無可比擬的地位。
從現代高等教育計量學的角度來看,科學精英的產出與績效常被用作大學評估活動的可操作性指標或基準,績效水平可反映出在對應的大學機構、學科領域、國家或地區的科學精英匯聚情況。如ESI是在當今世界范圍內普遍得到認可的重要評價指標工具之一,用于衡量大學等學術機構、國家或地區國際學術水平及影響力。之所以如此,最為主要的原因是科學精英匯聚程度及產出的績效能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大學的卓越性,與此同時,科學精英的數量、學術績效的產出在國際意義上具有通用的可比較性、可視化、易于被測量,選取這些指標作為標準具備公平性及說服力。受到國際廣泛關注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簡稱ARWU),相對于其他大學排行榜得到相對較高的國際認可,主要原因也在于強調指標的客觀性、穩定性和透明性。其全部使用6項客觀指標對世界大學進行排名:具體而言,除了獲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的校友折合數指標反映出大學的教育培養質量,其他5項指標,即高被引科學家數、在《Nature》和《Science》上發表的論文數、被科學引文索引(SCI)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收錄的論文數以及師均表現,[4]均與在這些大學工作的科學精英的表現密切相關,科學精英在這些指標中的綜合表現,能較為合理全面地體現出大學的領先程度。這類計量方法主要從以科學精英為主體的角度去反映與衡量大學的卓越,得以形成較高的國際影響與轉載,可以看出科學精英的匯聚是一流大學(學科)成長、維持及發展的關鍵性要素這一理念,在全球高等教育系統,獲得廣泛認同。
既基于科學精英的匯聚是體現大學一流水平的重要表征,又考量到科學精英是推動大學卓越的重要驅動力,國家對科學精英具有強烈的選擇偏好。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對精英人才的選擇偏好是多元的且具有定向性。具體而言,一是內生性偏好。由于本身高等教育系統質量相對發達國家而言水平較低,科學精英培養的過程顯得更為艱難與漫長;其雖作為科學精英的生產者主體顯得力不從心,但不會放棄培養的可能性。二是外生性偏好。因為科學精英可通過多種途徑提升國家競爭力,對科學精英的偏好較之一般的人才優先,這一目標可以通過投入成本較為快速地引入其他國家已培養出的高端人才而實現。除了生產者和需求者之外,國家位居于精英人才與大學之間扮演中介者,憑借在國際體系中不可替代的擔保形象,發揮最大的影響力,發布戰略規劃、移民政策、建立國家榮譽制度等高端人才激勵保障機制,使得科學精英即使對相關的大學不是特別深入理解,也能基于國家發布的權威信息,形成偏向于正面的接收態度及產生較為樂觀的預設。
三、共同話語體系:戰略、一流大學(學科)與科學精英在績效取向與公共性訴求上達成一致
1.戰略、一流大學(學科)與科學精英在績效取向上相契合
對于國家而言,科學精英與一流大學這兩種類型的獲得在效益上具有統一性。國家既可以從獲取科學精英回流的最大可能性上提高本身教育系統內人才培養效益,又能通過加大對外籍外裔的引才力度去滿足國家專項發展所需及提升人才對于國家創新的貢獻度;國家以一流大學(學科)為重要載體筑巢引鳳,通過平臺重塑實行高端人才的引進,實施開放性的人才戰略與本土戰略相整合,不僅可在大學內孵化科研團隊,促使產學研結構優化升級,而且能挖掘及實現高端人才的最大教育附加價值,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雙一流方案是國家為達成提升高等教育綜合實力及國際競爭力目標而實施的重大戰略,通過總結“211”、“985”工程以及“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和“特色重點學科項目”等重點工程產生的“身份固化、競爭缺失、重復交叉”問題,以及對此類工程使得“一批重點高校和重點學科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帶動了我國高等教育整體水平的提升,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的肯定評價基礎上,實施的一項尤其強調績效和效率性的政策。具體而言,一是相比之前的高等教育領域重大工程,大學(學科)作為參與主體在范圍上更為放開,競爭愈發激烈,突出績效導向,績效勝出者留下來繼續參與競爭,并擁有更多的受資助機會。二是通過建立健全績效評價機制,打破了“211”、“985”工程的身份保護慣例,參與主體的危機感加重。三是不斷完善政府、社會、大學相結合的共建機制,形成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即哪些大學(學科)在多方共建機制上做得完善、順暢,緊密圍繞、服務與貼合學科發展中心任務,則更有機會在奔一流的方向上實現關鍵環節的突破。
雙一流方案在效率與效果兩方面進行了預設,即在執行和評價上做出了規劃。從“預期政策效率”這一指標來看,是指在分三步走的計劃時間內,高等教育系統目前的綜合實力與競爭力向戰略方案中預先設定的一流目標發展所被改變的程度,由此可在限定時間區間內,去跟進戰略的實施節奏。同時,對政策效果也做出了預估,設置了數量和質量的要求。由此,經由效率與效果的雙重規劃與評估,需要有科學的績效預算,預估成本與收益,以使得資源投入與戰略計劃的實現相統一。
科學精英相比學術能力一般的人員,能有更好的項目工作領導力及產生較好的效率,或在同等時間內產出更領先的科研績效去提升大學的競爭力。與此相應的,是人才成本的相對較大投入,但基于對科學精英產出的估值,成本遭到浪費可能性的降低,以及現有一流大學依賴科學精英取得成功的經驗,大學的此項付費被認為是可效仿的、可行的、理性的,且符合市場規則。科學精英是具有較大學術生產力的特殊人才,那么大學就應該滿足科學精英的各項合理要求,體現出對高端人力的認同與尊敬;并且在相應的內部治理結構與管理方式上進行組織革新,以回應科學精英的相關需求,如更多的認同、激勵、溝通及協作,以使得其個人績效目標與大學的期望值達成一致,最終促使大學可持續追趕一流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科學工作本身的特質也蘊含了績效要求。科學成果的呈現方式符合學術職業本身的發展邏輯,能表明科學精英的自我實現程度或者科研團隊的學術生產能力。根據科林斯(Collins)所言,科學是一種很強大的專門職業。科學領域的工作結果越是不可預計,與其他技能相比,倚仗特定專業技能去降低不確定性的程度越大,對于雇主(大學及國家)而言,這種對降低不確定性的把控能力則顯得越發具有價值和重要,則專業群體的權力也就越大。[5]科學精英符合專業群體的特征,對其科研活動的目標和規程具有較高的自主權。然而,與在科學領域資質平庸的從業者一樣須被考量的是,科學精英的這種自主權也受到規制。換言之,發表的論文數量,期刊的權威程度,被同行的引用頻次等,是被國際通用于說明科學精英及其團隊影響力的主要衡量指標。科學家之間存在一種特殊的張力,“本質上說,現代科學是一些受到聯合控制的新知識生產系統,其中研究人員為了從特定同行群體獲得聲譽,必須對知識作出新貢獻。”[6]由此可見,科研工作事業自身對效率與產出的追求,與大學對一流績效的渴望,不謀而合。
2.戰略、一流大學(學科)與科學精英在實現公共性上形成合力
現代大學常面臨自主性與公共性的沖突。一方面,大學本身的獨立利益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大學最為重要的功能和價值應該是它的公共性,應體現、維護和發展社會的公共利益。[7]高等教育領域雖然不像軍事或者環境領域那樣直接關系重大安全及民生,但在大眾化及普及化時代,大學出現的問題會較為廣泛地影響相關國民及家庭,大學的卓越程度直接關系到當代和下一代的受教育情況,因而其公共性具備正當性。當大學維護自主及發展自身利益與被要求承擔公共職責之時,矛盾會得以凸顯。對于我國而言,公立大學是我國高等教育系統的承擔主體,且研究型大學又處于公立大學的頂端部分,盡管經費來源日趨多渠道,但主要仍是由財政提供支持,加之研究型大學是“雙一流”戰略的主要對象,與政府及社會互動較之一般大學更具深度與廣度。研究型大學的公共性特征與應承擔的社會職責更為突出。對于這類高等教育的高端提供者,其一流程度可通過簡單的市場測試來評價,即看看這些大學在經濟社會中所顯示出來的卓越價值。[8]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全球高等教育競爭環境日趨激烈,各類大學排行榜定期發布,以及社會對大學績效的關注,使得享受了較多公共資源的研究型大學面臨巨大壓力。
雙一流方案與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兩大戰略的實施,在大學自身的發展預設與我國對大學的“新的額外要求”于價值觀和現實意義層面,可在很大程度上達成一致。國家促使科學精英在大學匯聚,并非是削減大學利益或約束大學職能,而是一種激勵性的舉措及可持續發展策略,或是化解大學發展瓶頸之良策。盡管對于大學而言,為了將自身塑造為人才磁場,需構建科學的內部治理結構與人才評價機制、行政部門須與學術部門更好地協作,以及在資源、團隊、項目管理上標準更高且效率更快;但這些應對行動于大學實現跨越式發展本身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大學發展的歷史性機遇所在,可通過國家戰略的實施,在整體上提升競爭力。外部的積極影響會推進大學內部的治理,使得最先領悟并實施變革、基礎較好或具有特色的大學(學科)在政策中獲益。與此同時,一方面,對科學成果來說,如默頓強調的“科學在本質上是公共性的而不是私有的”。[9]另一方面,由于國家兩大戰略具有持久而廣泛的公眾關注度,使得大學因科學精英有效引進而形成的科研績效及公共收益,為社會所見且為輿論所支持,會使得社會較為認可大學的公共效益;由此改變“收益與成本的不對稱”現象。大學內部組織與外部環境在戰略實施過程中可密切配合、相互影響,互傳能量。若一流的資源、國家層面的支持性戰略、科學精英都集中于大學,而大學仍處于較低辦學水平,這與公共利益相違背,對于社會而言是一種不公正。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性的實現也與大學內部的成本投入相關聯。除了財政資助,大學在雙一流戰略的執行過程中,也需要承擔一定的成本。尤其對于某些層次較低的大學而言,由于經費緊張但又有重點發展某個學科的目標,可能將本用于發展其他事項的經費調撥為人才引進配套經費,以追逐并效仿其他院校做法。因而須承擔一定的風險。但從整體來看,雙一流方案定位為以一流為目標,以績效為杠桿,表明仍然是以研究型大學為實施主體,其資源優勢是毋庸置疑的,用于高端人才的經費不會淪落到舍此即彼的境遇。由于大科學(如涉及國家安全、人類發展的巨大而昂貴的科學事業)主要由實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學承擔,政府對科研經費的決定影響高等教育系統層級結構的劃分及科學的走向。雙一流方案強調以學科為基礎,有特色且敢于改革的學科可參與進來。盡管較之以往,身份固化的情形會得以改善,然而,一流的設定畢竟只是定位為少數的大學群與學科群。一些發展勢頭較猛的優勢特色學科、少量轉型成功的教學研究型大學與少數的新型大學才有可能進入補充梯隊。在一流大學(學科)的建設中,財政撥款體制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應既注重效率又要兼顧公平,使得某些追趕一流水平的特色學科擺脫身處層級較低大學的掣肘,獲得脫穎而出的機會,得到科學精英的青睞,在整體層面也符合改革、績效、多元、動態、開放的改革思路。這是另一重意義上的公正。
四、系統思考:打造戰略、大學(學科)及科學精英的良性循環
在國家戰略層面,系統思考是必要的,為了實現確定提升高等教育國家競爭力這一總體目標,須以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學科)為實現路徑。其緣于切合當前高等教育的現實發展狀況與差距,一流的數量終歸是動態意義上的少數,不易于模糊預設的以一流為焦點,有利于選擇及管理;應堅持在一流的定位上進行規劃及考察;易于在同一水準、背景、策略上整合價值觀及增強執行力;一流的明確指向性,使得在未來的實施過程中易于實現前瞻性及進行評估;且一流應是全球意義上的一流,須在國際指標上具備說服力,能生動直觀地體現高等教育綜合實力的上升程度,并以其示范性帶動高等教育其他層級的提升。在更具體的操作層面上,大學將世界一流設定為發展目標,則細化到學科領域預設了高端的人才需求與吸納目標,“一個優秀的學者之所以選擇某所大學安身立命,通常主要是被這所大學某個優秀的學科所吸引”。[10]于是在戰略層面上,人才計劃與各種創一流高等教育工程前后出臺,相輔相成,自是理所當然。
對于大學而言,在成長中應該考慮與國家戰略及科學精英的相互作用。由國家戰略、大學、科學精英組成的環路結構,能在一流的方向上產生不斷增強的過程。“正反饋”系統能在很大程度上實現良性循環,國家戰略愈發導向明晰,促進科學精英高效引進,便能促進大學科研績效的產出,科研排名的提升促使大學有信心投入更多的資源以爭取更多更尖端的人才,國家再基于每個計劃周期的完成狀況,在撥款、考核、評價上做出相應調整,以支持這一系統順利運行。值得注意的是,“增長極限模式”也是存在的。正反饋系統運行到一定階段,老齡化對學術績效產生負效應、科研經費的增長速率放緩、團隊本身擴容導致管理難度增大、科研活動本身的日趨復雜及其他國家出臺更具競爭性的引才政策等限制性因素,都有可能影響大學科研績效。因此,一方面,大學內部的變革在改善本反饋系統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視,如在完善大學內部治理、構建社會參與機制、推進國際交流與合作上進行改革,重新調整分工與權力以完善協作模式,撬動正反饋的動力機制。另一方面,正反饋系統在某個階段運行受到阻礙,這本身是一個共性問題,需要大學保持開放的認知態度,并理解其本質;即使相對跌落名次,能總體保持在一定的區間,仍然是所在領域的重要參與者及推動者,在反思的同時也值得肯定。
在對應意義上,一流大學(組織)與科學精英(成員)屬于高度戰略依賴型關系。良禽擇木而棲,科學精英因其在同行間難以追趕的卓越學術能力,對一流大學的成長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例如,一流大學(學科)能壟斷某些金字塔頂端的科學家,其便較為長久地擁有了這些學科領域的話語權,以及相關的科技轉化衍生品的資源優勢。科學精英也需要唯有一流大學才能提供的支持科研所需的條件,如團隊、平臺、實驗投入,以及與優秀同行可比擬的學術環境。假如一流大學是極少數的幾所,則科學精英對這類平臺的依賴性愈發增大,這一專業群體內部的相互競爭程度愈發激烈。大學組織在現代高等教育競爭中趨于復雜,既須協調學術與行政的權力關系,又要調適內部治理與外部管控的關系,各種發展思路與備擇路徑縱橫交錯。盡管如此,其在方向上是清晰的,即一是超越自身,二是參照卓越大學的發展態勢,能達到預設的一流水平。于科學精英而言,其在專業領域雖按照各自適切的學術規程操作,對成果的獨創性、領先性卻擁有與生俱來的追求。一流大學與科學精英在戰略目標上是高度契合的,由此,基于共同的目標,可加快磨合的過程以達成卓有成效的協作。
在高等教育國際環境趨于復雜的當下,國家戰略、一流大學(學科)與科學精英處于共同話語體系。對于我國而言,雖然在世界一流大學榜單上有所表現尚需假以時日,但大學無論是在之前入選“211”、“985”工程、“2011計劃”,還是參與今后的“雙一流”建設,都被社會視為非常重要的榮譽,并被大學所珍視。經過遴選后入選“千人計劃”的科學精英也被認為是處于主流科學圈并擁有較高的聲譽。國家兩大戰略的發布,使得科學精英的規模化引進與大學的群體升級互為鋪墊,互相作用,互為因果。互為支撐的兩大戰略作為國家重要公共政策的組成部分,對于我國高等教育的整體質量提升具有重大的意義。無論哪一參與主體,在現代高等教育改革潮流中,都應重視對一流的理解及追求,認同領先的價值,秉持卓越的信念,參與并推動圍繞著一流科學績效為核心而進行的各項高等教育改革。
[1]2014年全球最具影響力中國大陸科學家分析報告出爐[N/OL].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官網.http://www.cutech.edu.cn/cn/rxcz/2015/06/ 1433758378098359.htm,2015-06-09.
[2]程瑩.世界大學學術排名解析(2013-2014)[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33.
[3]Salmi,J.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M].Washington,DC: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09.
[4]關于世界大學學術排名[EB/OL].http: //www.shanghairanking.cn/aboutarwu.html.
[5][6]理查德·惠特利.科學的智力組織和社會組織(第二版)[M].趙萬里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40.89.
[7]謝維和.認識新時期大學的公共性[N].中國教育報,2008-01-28.
[8]菲利普·G·阿特巴赫等.為美國高等教育辯護[M].別敦榮,陳藝波譯.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7.133.
[9]彼得·什托姆普卡.默頓學術思想評傳[M].林聚任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58.
[10]王建華.學科的境況與大學的遭遇[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4.前言1-2.
(責任編輯田曉苗)
On the Congruity of National Strategy,World-Class University (Discipline),and Science Elitism: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Strateg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Fan Dongqing
To further enhance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hina presses ahead with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disciplines).A systematic state strategy for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formulat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211”and“985”projects.The new strategy lays emphasis on recruiting high-level talents and continuing the“211”and“985”projects in the facilitating universities(disciplines)to achieve world-class status.This author finds that the state strategy,world-class university(discipline)plan,and science elitism are congruent to each other in their orientations,realization means,and outcome effects.Therefore,it is feasible to include the three in a whole strategy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mutual promoting between science elitism and the state strategy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disciplines.
world-class university(subject);science elitism;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scientific performance;systematic thinking
G648
A
1672-4038(2016)04-0071-07
2016-02-20
南京師范大學2015學年“博士生優秀選題”資助項目
范冬清,女,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