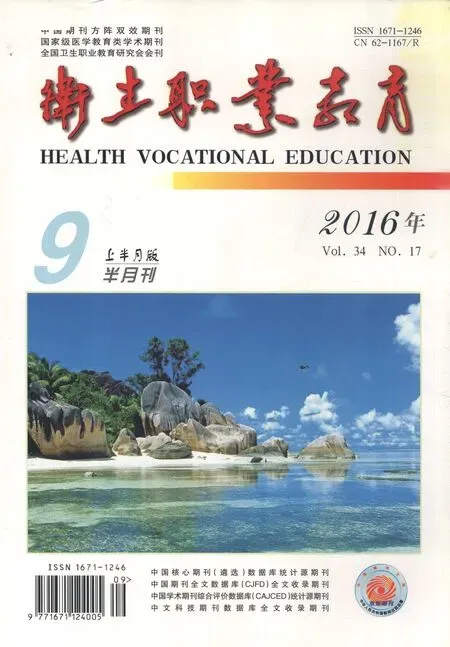醫學生成人依戀與人際關系的相關研究
裴志珍,張靈聰
醫學生成人依戀與人際關系的相關研究
裴志珍,張靈聰*
(閩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福建 漳州 363000)
目的 探討醫學生成人依戀與人際現狀的特點和相互關系,為促進醫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發展提供依據。方法 選用親密關系體驗問卷、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對贛南醫學院一至三年級303名學生進行調查。結果 醫學生成人依戀與人際關系存在顯著相關。醫學生成人依戀傾向與人際困擾呈顯著正相關,依戀焦慮和依戀回避對人際困擾有顯著的預測作用。結論醫學生成人依戀與人際關系顯著相關,是影響其人際關系的重要變量。
醫學生;成人依戀;人際關系
人際關系是人與人之間在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直接的心理上的關系或距離,反映了個人尋求滿足其社會需求的心理狀態[1]。良好的人際關系有助于個體的整體發展。醫學生擁有較高的專業技術,要想畢業后在工作崗位上做出一番成績,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是必須的。
依戀理論為我們從深層次了解人際困擾產生的根源并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提供了依據。最早的依戀理論由精神分析學家John Bowlby于19世紀60年代提出,他把依戀定義為“一種個體與具有特殊意義的朋友形成牢固的情感紐帶的傾向,它能為個體提供安全和安慰”。由于依戀貫穿于人的一生,具有相對穩定性,我們可以通過了解醫學生的成人依戀風格來間接追溯其早期的依戀經歷[2]。
已有的依戀理論方面的研究非常豐富,對依戀與人際關系的研究也有相應報道,但具體深入到不同依戀風格與各種人際關系是如何對應的研究并不多見,而在此領域針對醫學院校學生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研究以依戀理論為基礎,運用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親密關系體驗問卷(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 Inventory,ECR)對醫學院校大學生人際關系和成人依戀的相關性進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醫學生依據自身的依戀特點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另一方面希望能為醫學院校開展有針對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據,進而指導醫學生加強自我認識,建立健康的人際交往關系。
1 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從江西省贛南醫學院在讀醫學生中隨機抽取320名作為調查對象,共收回有效問卷303份,回收率為94.69%。其中男生154人,女生149人。
1.2研究工具
1.2.1親密關系體驗問卷(ECR)由Brennan、Clark、和Shaver等在1998年編制的親密關系體驗問卷是目前使用廣泛、評價高的自陳式問卷之一。ECR有36道題,依戀焦慮和依戀回避兩個分量表各18題。該問卷采用七級評分(從非常不贊成到非常贊成),Brennan等報告的依戀回避維度的α系數為0.94,依戀焦慮維度的α系數為0.91[3]。本研究采用了田瑞琪(2004)在其碩士論文研究中修訂的ECR量表,修訂后回避維度和焦慮維度的α系數分別為0.81、0.80,重測系數分別為0.805、0.820[4]。
1.2.2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 本研究選用的人際困擾的診斷量表為鄭日昌等編制的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分為4個分量表:人際交談困擾、交際與交友困擾、待人接物困擾、異性交往困擾。4個因子的α系數在0.56~0.68,校正后的分半信度在0.51~0.63,皮爾遜相關統計分析表明,每個分量表與總量表的相關在0.69~0.81[5]。
1.3研究方法
將調查對象批量集中后當場發放問卷,由心理學本科生按指導語規范操作,當場收回,測試時間為25分鐘。數據采用SPSS
16.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主要有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
2 結果
2.1醫學生成人依戀與人際關系的總體狀況
親密關系體驗問卷,醫學生依戀焦慮分量表得分高于依戀回避分量表得分。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醫學生交際與交友困擾分量表得分最高,其次是異性交往困擾,最后是人際交談困擾和待人接物困擾(見表1)。

表1 醫學生成人依戀和人際關系量表得分(x±s,分)
2.2醫學生成人依戀類型分布
醫學生成人依戀類型人數分布中,恐懼型(47.52%)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專注型(23.43%)、冷漠型(20.46%)、安全型(8.58%),其中專注型和冷漠型比例很接近(見表2)。
2.3成人依戀和人際困擾的性別差異
為研究醫學生成人依戀和人際困擾各分量表得分的性別差異,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待人接物困擾分量表,男生得分顯著高于女生(P<0.05);異性交往困擾分量表,男生得分顯著高于女生(P<0.01),其他各分量表性別差異不明顯(見表3)。

表2 醫學生成人依戀類型分布

表3 醫學生性別差異檢驗結果(x±s,分)
2.4成人依戀與人際困擾的相關分析
對人際困擾與依戀焦慮、依戀回避做皮爾遜相關分析,結果見表4。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總分與ECR所測量的依戀焦慮和依戀回避分量表得分存在顯著相關性,相關系數分別為0.403、0.228(P<0.01)。依戀焦慮分量表得分與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的各分量表得分均存在顯著相關性,即依戀焦慮分量表得分越高,個體在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各分量表的得分越高,存在的人際困擾越大。依戀回避分量表與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各分量表得分也有顯著相關性,即依戀回避得分越高,個體在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的各分量表得分越高,人際關系越不理想,困擾越多。

表4 醫學生成人依戀與人際困擾的相關矩陣
2.5醫學生成人依戀各維度對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各因子的回歸分析
以ECR兩個分量表和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4個因子分別為自變量與因變量,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依戀回避進入人際交談困擾、待人接物困擾、異性交往困擾為因變量的回歸方程;依戀焦慮進入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各因子為因變量的回歸方程(見表5)。

表5 醫學生成人依戀對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各因子的線性回歸分析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醫學生成人依戀類型分布不均衡,安全型個體占8.58%,恐懼型占47.52%,專注型和冷漠型分別占23.43%和20.46%。國內外的研究結果大都是安全型的。如Lopez于2001年在人數為245的大一樣本中實測RQ,所得依戀比例為安全型占46%,恐懼型占20%,專注型占15%,冷漠型占19%[6];Creasy在2001年采用AAI對145對戀人進行測量,發現安全型占40%,未解決型占26%[7];何紅娟2007年的研究顯示安全型占34.9%,恐懼型占20.9%,焦慮型占13.3%,回避型占30.9%[8];王金奎2007年的研究結果為安全型占11.9%,恐懼型占49.4%,迷戀型占23.2%,冷漠型占15.6%[9];何騰騰等2012年的研究結果為安全型占11.6%,恐懼型占47.7%,專注型占16.3%,冷漠型占24.4%。這些研究結果與本研究基本相同[10]。
本研究所獲得的醫學生成人依戀比例與之前國內外的研究不太一致,筆者認為造成這一差異可能有以下原因:(1)研究對象的差異。本研究以醫學生為調查對象,之前國內外有關成人依戀的研究很少針對醫學生這一特殊群體,醫學生比普通大學生學業壓力、就業壓力更大,初入社會的人際困惑更多。(2)使用的測量工具不同。Lopez的研究使用的是關系問卷(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RQ),Creasy采用的工具是AAI,而田瑞琪使用的是自己修編的親密關系體驗問卷。(3)中外文化差異。中國人在人際交往中提倡含蓄、謙虛,不提倡張揚個性和外露自己的負性情緒,同時也不倡導像外國人一樣有身體的親密接觸。
醫學生成人依戀和人際困擾性別差異的顯著性檢驗發現,醫學生依戀維度不存在性別差異,這與大多數已有相關研究相同。Lopez采用ECR研究也發現性別與依戀焦慮和依戀回避都沒有關系[11];Creasy采用AAI訪談發現依戀類型性別間沒有顯著性差異[7];田瑞琪2004年研究發現男生和女生無論在依戀回避還是在依戀焦慮維度都沒有顯著差異;郭慶同2007年的研究也發現依戀類型不存在性別差異[12]。但也有研究結果表明,不同的依戀類型存在性別差異。如王金奎2007年的研究表明,大學男生和大學女生在依戀回避維度上得分差異顯著,依戀焦慮維度得分差異不顯著[9]。Zimmermann等2002年研究了戀愛中的成人依戀,結果發現男性依戀回避數量多于女性[13]。
依戀維度上的性別差異存在與否跟社會傳統文化等有關系,不同的地域可能存在較大差異,具體影響模式有待深入研究。
對醫學生成人依戀和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各因子的相關性及回歸分析發現,依戀回避與人際交談困擾、交際與交友困擾、待人接物困擾和異性交往困擾都相關,說明依戀回避維度得分較高的醫學生更有可能面臨人際關系困擾。依戀焦慮與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4個因子也都相關,焦慮指標高,個體自我評價偏低,在與人交往中會有很大的不安全感,難以建立一種良好的人際關系。因此,依戀回避進入了以人際交談困擾、待人接物困擾、異性交往困擾為因變量的回歸方程,依戀焦慮在對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各因子的回歸分析中表現出了顯著的預測作用。
4 結論
研究結果表明,醫學生成人依戀與人際關系呈顯著相關,依戀焦慮和依戀回避對人際關系有顯著預測作用。根據該研究結果,我們可以先了解醫學生的依戀類型,在此基礎上開展心理健康教育,以改善其人際關系。另外,我們也可以從改變個體的依戀類型著手,從源頭減少人際困擾。同時,還要考慮個體的依戀類型具有的相對穩定性,所以咨詢周期必定較長且見效較慢,咨詢師和來訪者都要明白這點,以免欲速則不達。
[1]陸衛明,李紅.人際關系心理學[M].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
[2]張楠.地方院校大學生成人依戀與人際關系的相關研究[J].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8):66-67.
[3]李同歸,加藤和森.成人依戀的測量:親密關系經歷量表(ECR)中文版[J].心理學報,2006(3):399-406.
[4]田瑞琪.大學生成人依戀的測量及相關人格研究[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04.
[5]鄭日昌.大學生心理診斷[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6]Lopez.Adult attachment orientations and college student distress: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blem coping styles[J].Journal of Counseling Development,2001(79):66-67.
[7]Gray Creasy.Associationgs between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and conflictmanagement behavior in romantic couples[J].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2002,49(3):365-375.
[8]何紅娟,陳志霞.成人及童年依戀類型與婚姻質量的相關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2007.
[9]王金奎.大學生成人依戀的調查及與情緒調節、人際關系困擾的關系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2007.
[10]何騰騰,鞏文兵,繆艷君,等.大學生成人依戀與人際交往的相關性分析[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2(5):782-784.
[11]Frededrick G Lopez.Adult attachment orientations,self-other boundary regulation,and splitting tendencies in a college sample[J].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2001,48(4):440-446.
[12]郭慶同.大學生成人依戀與人格特質及應對方式的相關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07.
[13]Peter Zimmermann.Fabienne Becker-Stoll.Stability of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s during adolescence:the influence of ego-identity status[J]. Journal of Adolescence,2002(25):107-124.
(*通訊作者:張靈聰)■
G455
B
1671-1246(2016)17-00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