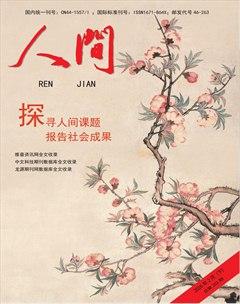淺談中國古代的教育智慧
李芷東
摘要:明朝王陽明提出:“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澆灌。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量要傾,便浸壞它也”。
關鍵詞:因材施教;學思并重;啟發誘導
中圖分類號:G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2-0151-01
中國古代的教育智慧是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無論是在永恒經典的“四書”之中,還是在荀子的《勸學》,老子的《道德經》中,都有我們今天在教育領域中進行理論創造的源頭活水。
中國古代教育家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概括和總結自己的經驗,針對教學中所遇到的問題,逐步深化了對教學規律的認識,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教學原則和方法。
一、因材施教
教學中首先遇到的問題是統一的培養目標和教學要求與教學對象的不同特點之間的矛盾。教學必須從實際出發,適應不同的教學對象,才能使學生各盡其材。這正是古代教育家提出因材施教的客觀基礎和條件。
孔子最早注意到教學中的這一矛盾,并實行因材施教。其基本含義有二:一是教學要從學生的實際水平和個性特點出發。學生同樣問仁、問孝、問政,他的回答難易、詳略、繁簡各不相同。有時學生問同一個問題,他的答案卻截然相反,根據是兩人個性特點不同。二是在堅持統一標準和共同要求的前提下,善于發現、注意培養、鼓勵發展學生的某些專長。他弟子三千,賢人七十有二,同樣身通六藝,但于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又各有所長。孟子也十分注意因材施教,提出“教亦多術”,重視了教學方式也應因人而異,“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孟子 ·盡心上》)。《學記》提出“長善救失”,針對學生學習特點進行教學,“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從而深化了如何因材施教的認識。漢朝徐斡提出“導人必因其性”。他說:“大禹善水,君子善導。治水必因其勢,導人必因其性,是以功無廢而言無棄也。”他認為教學既要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又不能強其所難,勉其所不能,要注意“使辭足以達其智慧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教學時“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中論·貴言》)。宋朝張載提出教師必須知人、知德,才能因材施教,“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可后傳此。”“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正蒙· 中正篇》)。明朝王陽明提出:“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澆灌。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量要傾,便浸壞它也”(《傳習錄》下)。這些豐富的經驗和精辟論述,對后人教益頗深。
二、啟發誘導
教學是師生的雙邊活動。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積極主動性是辯證統一的。教師能否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主動性是教學成敗的關鍵。啟發式教學的核心就在于此。
孔子最早提出并實行了啟發式教學,“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十分明確地表述了啟發式教學原則的要點。他注意了解學生的認識水平和心理狀態,掌握恰當時機,控制教學的難易繁簡,利用已有的知識,運用學生熟悉的淺近事例,多方面激發學生“好學”、“樂學”的興趣,使學生始終處于“欲罷不能”的狀態,培養出一批“聞一知二”,“聞一知十”,“告諸往而知來者”的學生。孟子也很重視啟發式教學,他形象地把啟發式原則喻為“引而不發,躍如也”(《孟子·盡心上》)。他特別強調培養學生自求自得的興趣和能力。他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孟子·離婁下》)。“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孟子 ·盡心下》)。這正是啟發式教學的真諦。《學記》對啟發式教學作了最完善的發揮,“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以“喻”概括啟發式原則是相當精辟的。引導而不是硬牽著走,勉勵而不強使其屈從,講解透徹但不是告以全部現成結論。都是要調動學生的積極主動性。
三、學思并重
學習與思考是教學中的兩個決定性環節。掌握知識與發展智力又是教學的兩大主要任務。兩者是統一的,又是有矛盾的。學思并重就是尋求兩者的辯證統一。
孔子首先提出學思并重的思想。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 ·為政》)。學思并重,學思結合的思想成為中國古代教育家一致贊同和普遍遵循的教學原則。但在教學實踐中,不同學派的教育家又往往各有側重。孟子重視學,更強調思的重要性,他甚至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荀子特別強調博學,主張多見廣識,同時注重思,他所說的“思索熟察”、“虛一而靜”、“兼陳中衡”,都是強調在廣博知識基礎上發揮思考力的作用。王充最重實知,也重思考,他說:“唯精思之,雖大無難”,認為學習時“必開心意”,才能真有所得。朱熹對學習知識十分重視,尤其強調讀書,但認為必須通過思考,他提出的讀書要領“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就是強調思考的。葉適認為孔子是主張學思并重,內外結合的,后世教學各執一端,違背了這一原則,“祖習訓故,淺陋相承者,不思之類也;其穿穴性命,空虛自喜者,不學之類也”(《習學記言》)。王夫之最全面地發揮了孔子的思想,并指出:“學非有礙于思,而學愈博則思愈遠;思正有功于學,而思之困則學必勤”(《船山遺書 · 四書訓義》)。
促進學思結合的重要途徑是開展師生朋友間的問難論辯。孔子不贊成學生對老師的教導“無所不悅”的態度。認為通過詰問論辯,才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墨家更提倡辯析名理,專作《墨辯》。王充反對“信師是古”,主張“極問”,作有《問孔》、《非韓》、《刺孟》等篇,通過問難,來“證定是作”,“辯其虛實”,張載認為學習必須善于發現和提出疑點,深入思考,疑解就是進步。朱熹說:“群疑并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疑漸漸解,以致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朱子語類大全》卷十,《宋元學案》卷四十八)。王夫之認為“疑”與“信”是相反相成的,“信者以堅其志,疑者亦足以研其微。”(《讀四書大全說》)
總之,學思應當并重,在學的基礎上思,在思的統率下學,以論辯問難、生疑解疑來促進學習和加深思考。這是中國古代教育家的基本主張。
——哈爾濱市蕭紅中學教學與作業改革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