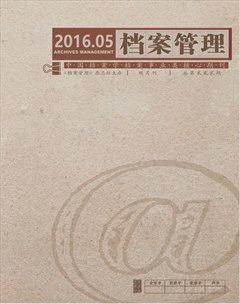論文化整合功能視角下我國古代政治文化對檔案事業的影響
任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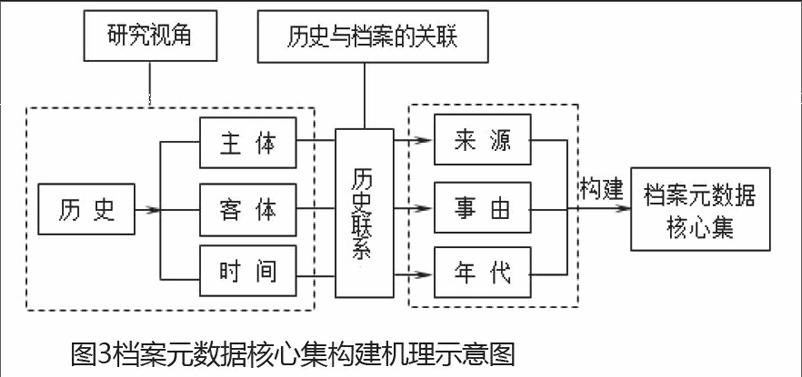
摘 要:文章以文化哲學中的文化整合思想為主軸,從價值觀整合、規范整合與結構整合三個方面分析了“大一統”“人治”“禮治”為特征的古代政治文化對我國古代檔案工作的影響,并評價三者對當下我國檔案事業發展的價值與困擾。
關鍵詞:政治文化;文化整合;檔案事業
Abstract:Taking Cultural Integration Thought of Cultural Philosophy as the mainline, this paper analyzes ancient political culture who regards "Great Unification ", "Rule of Man” and "Rule of Rite " as its characters from three aspects: integration of values, Specification and Structure, and then illuminates the effect on Chinese ancient Archives, evaluates the value and distress to modern Archives from those three political culture.
Keywords:Political Culture; Cultural Function; Archives
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我國社會形成了獨特而又穩定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根植于以封建倫理秩序為基礎的政治理念,如“人治”“禮治”,并借助于封建社會“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體制而演變為一種長久制約我國社會主體觀念與行為的社會文化。“大一統”“人治”“禮治”這三種政治文化雖各自發揮其功能,但三者又相互聯系,互相影響,并共同打造了森嚴、固化和專制的我國古代政治文化秩序。由此,筆者選擇從文化哲學理論中的文化整合功能入手,通過對我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剖析,從價值觀、行為規范與社會結構等多個角度梳理其對我國古代乃至當下檔案事業發展的影響。
1 “大一統”文化思想整合我國古代檔案價值觀
文化來源于社會主體及其從事的實踐活動,在此過程中形成的社會價值觀也隨著文化的積累與演進而不斷地整合與被整合。我國傳統社會中的組織與個人,因其各自經歷的活動與文化積累不同,其文化價值取向相對多樣且分散。只有通過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整合,才能讓松散無序的社會個體價值觀整合為一種讓社會中絕大多數人所共同接受的觀念與行為準則,這就是價值觀整合的核心思想。
在我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各種形式中,“大一統”文化價值觀的整合功能表現最為明顯和實效。這是因為我國古代社會經濟體制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該經濟體制的分散性與私有性導致社會公眾價值觀念呈現出分散且多樣的形態,而出于對政治統治長久與穩定的需要,統治階級需要通過一種基于小農經濟基礎上的統一社會價值觀約束社會主體與組織的行為。“大一統”思想最早出自于《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1]其原始意義為消滅對手,由帝王一人統治天下,后被統治階級引申為皇權威懾力的象征。這種政治思想服務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政治訴求,借助儒家思想的包裝與宣傳,使之成為封建社會時期主流的社會政治思想。“大一統”不僅是疆域、資源與人口的統一,更是社會個體價值觀及其指導下社會實踐行為的規制與整合。在此政治文化的影響下,封建君主專制和官僚體制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使民眾的個人利益與權利受到壓制與束縛,但它將社會各個階層的政治思想和價值觀有效地整合起來,從而構成了整個國家認同的政治和社會觀念,這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大一統”思想還表現在我國古代社會文化的封閉與排異,這種表現并不是一種極端民族主義思想,也不是對外來文化全盤抵制的保守思想,而是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保持自身固有文化形態的穩定性,這也是我國古代社會政治制度與社會文化保持千余年而未發生本質變化的原因之一。
殷商后期,我國真正意義的檔案工作開始形成,它隨著“大一統”政治文化思想的滲透與推廣,成為統治階級把控朝綱和牽制民眾的重要工具。“大一統”文化對檔案工作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資源的統一,即政府形成的所有檔案都歸當權者所有,所有檔案都要向中央移交,并集中管理,特別是涉及到土地、人口、資源、兵役和賦稅等方面的檔案更需要定期向中央檔案機構移交。國家壟斷社會核心信息資源一方面用于牽制地方資源的配置,另一方面通過對地方政治與經濟的掌控,鞏固其管理的統一性。其二,管理的統一,即各地各部門形成的檔案資源移交到中央檔案機構集中保管,通過設置嚴密和繁瑣的管理制度統一管理所有檔案。我國歷朝所設置的中央檔案庫,如石渠閣、后湖黃冊庫和皇史宬等都屬于集中管理檔案資源的專門機構,資源的統一衍生出管理的統一,管理的統一維護了檔案資源的利己性,便于政府對資源的進一步優化與使用。其三,利用的統一,因檔案資源歸統治階級所有,任何檔案的利用行為都需要得到皇帝的應允,并在利用程序的監控下有限地開展,這決定了我國古代社會檔案價值實現的封閉性與單一性。“大一統”思想構建了我國古代社會的政治和社會治理秩序,它對我國檔案事業的影響是根深蒂固、難以僭越的。需指出的是恰恰得益于檔案資源的高度統一及國家修史行為的養成,我國古代社會才有了可供追溯的完整歷史,這為中華民族文化體系的構建與傳承奠定了基礎。
當下我國檔案管理體制實行的是集中制管理體制。從字面意思來看,集中制與“大一統”思想差別不大,都是將檔案集中到政府指定的機構,由其負責集中管理與利用。但集中制是建立在現代意義的管理體制基礎上,其管理主體的屬性與封建社會時期政府的集權性是完全相悖的;其管理的目的并不在于維護管理階層的集權統治,而是最大限度的集中檔案資源,通過規范的手段開展社會利用;其服務對象也并不僅僅局限在政府機構,而是整個社會組織與個人。但囿于歷史慣性的思維,檔案機構極易受到“大一統”思想的誤導而出現只集中保管、不提供利用,只追求數量、不追求質量,只看重效率不注重效果的行為傾向,而這都需要檔案機構摒棄“大一統”之弊,樹立現代性的檔案管理價值觀,進而激發檔案事業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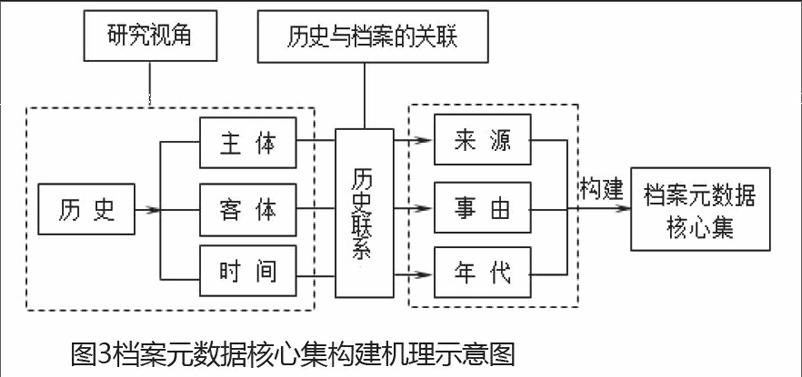
2 “人治”文化思想構筑檔案事業基本架構
價值觀對主體行為的塑造與約束是一種內化的手段,而外化的手段則需要社會規范的制定與執行。通過對不同社會結構和文化表征的整合,分散的、多樣化的行為規范逐漸趨于系統化、協調一致化,這使得整個社會組織和個人漸漸被納入到國家規定的軌道體系中,并開啟同一化的社會行為模式,這就是規范整合。在我國古代政治文化中,“人治”文化的規范整合功能表現得最為明顯。“人治”文化的核心是封建皇帝制,以及由此促生的一整套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體系,并輔之以封建官僚體系及其選官用官機制。殷商后期開始,我國社會開始從“神權”時代向“人權”時代轉型,以皇帝為核心的皇權至上思想逐漸成為統治階級駕馭萬民、治理國家的核心思想,由此構建的中央集權體制為皇權至高無上與穩固提供了保障。在中央集權體制的映射與約束下,朝野重臣和普通百姓無不體現出極強的思想凝固性與行為規范性。對于我國古代檔案事業來講,規范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檔案形成與管理的規范性,但也同時在檔案保管與利用方面滲透著“人治”文化的強制性與約束性。這主要表現為:其一,鑒于皇帝的權威性與官僚體制的層級性,文書檔案的形成被劃分為若干種形式,從中央到地方所有品階的官員依據其自身官職的大小依次一律使用相應的文書種類和檔案移交形式,以此彰顯政治制度嚴謹性與權威性,進一步鞏固皇權的至高無上。其二,制定嚴格的文書與檔案工作制度,保證文書制作與處理、檔案移交與保管的嚴密性。歷代王朝極其重視文書與檔案工作制度規范的制定,目的在于利用強有力的制度規范保證文書與檔案工作對統治階級的尊重與專屬性,擴大皇帝對這一重要管理利器的控制幅度,提高中央對地方的實際管制與社會治理的效度。其三,控制檔案的利用范圍,規范檔案利用的通道。我國整個古代社會的檔案利用只專屬于統治階級,任何形式與名義的檔案利用歸根結底都指向于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一方面統治階級利用檔案的相對集中性,嚴格控制檔案利用群體;另一方面制定嚴苛的檔案利用制度與法規,約束普通百姓對檔案的利用,營造社會對檔案的敬畏氛圍。規范整合的出發點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是對皇帝權威性的維護。這種文化功能的弊端十分明顯,即規范整合限制了社會管理階層與社會公眾的價值觀念,通過嚴苛的政治制度嚴格束縛社會主體的文化思想與多樣化的文化行為。雖然規范整合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檔案與檔案工作的完整與安全,保證檔案利用的相對獨立性,但完全封閉且僵化思維的社會檔案認知與行為都是對檔案與檔案工作社會屬性的漠視與否定。
由古代社會傳承下來的規范整合思想對當代檔案工作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我國古代檔案工作受迫于統治階級的權威而呈現出封閉性的特點。這種檔案價值認知深埋于社會主體觀念之中,使得現代檔案事業發展難以擺脫“官方”色彩而真正融入社會;其次,過于規范與嚴苛的檔案工作制度從古傳承至今,雖能有效保障檔案工作的規范性與效率的提升,但冗繁的檔案整理程序與僵化的檔案利用服務方式束縛了檔案事業向社會轉型的步伐;再次,受古代檔案用于官方且完全對外封閉思想的影響,我國檔案的社會開放范圍與幅度相對保守,對檔案社會開放的論證與鑒別工作易受此思想影響而難以放開手腳。現代意義上的“人治”思想不再是利用檔案牽制與控制人的思想與行為,而是要以社會主體為檔案事業開展的核心,從社會主體的利用需求去規范檔案工作流程,從社會主體的行為指向去設計多樣化的檔案價值實現路徑,這才是規范整合作用于當代檔案工作的文化精髓。
3 “禮治”文化思想拓展檔案功能的實現空間
價值觀整合為社會個體塑造了支配其行為的觀念導向,規范整合為社會個體參與社會實踐構建了制度與行為規范體系,而結構整合則恰恰在兩者基礎上將社會各種制度、約定和規范整合形成了嚴密而又極具中國特色的文化結構。它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存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社會主體的價值導向與實踐行為。“禮治”文化是結構整合下的產物,它的核心是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源自于父系氏族社會時期的父系家長制,即按照血緣關系分配國家權力,并建立世襲統治的制度。在我國古代社會中,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將社會各個階層、官宦臣子和家族群體牢牢控制在以皇權為核心的結構框架內,使我國整個古代社會政治體系在此基礎上協調運作,并行不悖。“禮”源自氏族社會末期的祭祀儀式。《說文解字》中提到:“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2]西周時期,“禮”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規范,后被引申為社會公認的合式的行為規范。受“禮治”文化影響,我國古代政治體系在宗法制度的牽引下呈現出極其嚴密且封閉的特點。作為政治活動的產物,檔案及檔案工作自然也會受此影響,主要表現在:其一,譜牒檔案是社會文化結構整合的產物。“禮治”文化借由儒家的思想,將“仁”植入到對其的解釋中。隨著儒家思想在古代社會中文化統治地位的確立,以仁釋禮、將“禮治”確立為社會普遍接受的一種精神信仰,將禮的強制規定與仁的自我要求融為一體,進而濃縮為影響社會主體行為的道德規范。正是在如此強勢的道德約束下,我國古代社會逐漸形成了依托于宗法制度的政治格局,宗法關系與政治行政混溶不分。譜牒檔案建立在我國宗法制度對祖上輩分與宗親關系價值認知基礎上,通過古代官員選拔機制而得以普及。它彰顯了封建社會的門第與世家輩分關系的結構約制對我國古代社會政治結構的影響。其二,對封建王權的畏懼與崇敬衍生了對皇帝工作與生活的記注制度。史官記注制度源自于西周時期,經過數以千年的演化已成為封建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史官記注制度為后世王朝留下了大量可供參考與反思的政治策略,也為史學家編修國史和評價皇帝言行得失提供了史實依據。如漢代時期開始編修的皇帝起居注是專門記錄皇帝言行的記錄物,而后成為歷朝史官記錄皇帝言行的常備工具。其三,為前朝修史彰顯封建王朝更替的敬祖之心。為前朝修史是每一新朝之初必行之事,這種行為一方面表現出新朝始皇帝對前朝覆滅因果聯系的訴求,另一方面則彰顯統治階級對祖宗前輩的敬畏之心。“數典不忘祖,制史以為國”成為歷朝開國皇帝在對待前朝歷史的真實寫照。由此而形成的利用歷史文獻以修史的傳統得以形成并傳承。社會結構整合框定了檔案除保留備考之外的社會功能,雖然我國古代編史修志的初衷并不是為了傳承歷史,但是其形成了攢史、編史與修史的思想與技法,為我國近現代檔案工作社會功能與結構的建構奠定了基礎。
我國古代“禮治”文化將社會結構規劃為層次明晰且難以逾越的道德壁壘,封建禮教的殘酷雖壓抑了古代社會公眾的思想開放與價值認同,但是卻造就了我國連續不斷的斷代歷史及眾多周邊史料匯編文獻,也奠定了我國古代檔案工作非政治之工具的基調。我國現代檔案事業的積淀一部分來自于民國時期現代意義政府管理的構建,另一部分則來自于禮治文化熏陶下形成史料編纂思想的積淀。前者延伸了檔案管理工具的功能,使其真正成為政府行政辦公的信息傳遞與參考的工具,后者傳承了檔案治史的文化功能,借助社會主體文化需求與檔案社會文化價值認同的提升而使檔案信息內容融入社會文化傳播之中。需要強調的是基于古代“禮治”文化思想的道德壁壘是古代中國封建社會唯一支撐的精神支柱,其非理性的內因是時代的需要,而現代社會對社會實踐活動的記錄則是出于對歷史的尊重,其內因是社會主體作為文化個體的價值追求與文化寄托。“禮”的精髓猶在,“治”的顯性趨于收斂,這是社會文化進步的核心要件與必然要求。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化哲學視閾下當代中國檔案文化研究” (項目編號:16CTQ035),黑龍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學校青年創新人才培養計劃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