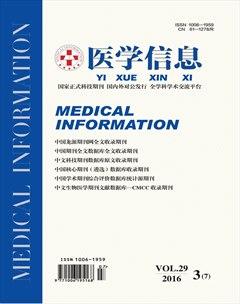近10年有關卒中后抑郁動物實驗的研究進展
車有路 章顯寶 肖偉
摘要:近年來隨著卒中后抑郁的發病率與日俱增,有關卒中后抑郁的動物實驗研究報道日益增多,相關文獻層出不窮。筆者通過查閱相關文獻,從卒中后抑郁的發病機制,動物模型的建立,針刺干預,中藥以及西醫藥物治療卒中后抑郁等幾個方面概述近10年有關卒中后抑郁動物實驗的研究進展,并提出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卒中后抑郁;動物實驗研究;綜述
卒中后抑郁(post stroke depression,PSD)是腦卒中后的最常見的并發癥之一,是腦卒中患者最常見的心理障礙,其患病率可高達20%~60%。卒中后抑郁可嚴重損害腦卒中患者的認知功能,影響患者的預后情況,增加患者癡呆及自殺的風險,給患者的家庭及社會帶來沉重的壓力。現將近10年關于卒中后抑郁的動物實驗研究進展綜述如下。
1 卒中后抑郁的發病機制
PSD的發病機制復雜,涉及神經生物學、解剖學和社會學、心理學等諸多因素。在20世紀80年代,Robinson等就提出,腦內參與情感調節的5-HT能神經元和NE能胞體位于腦干,其軸突通過丘腦和基底節到達額葉皮質,腦卒中病變累及上述部位可影響5-HT能神經元和NE能神經元及其通路,導致兩種遞質水平降低而引起抑郁。Moller等利用正電子發射型計算機斷層顯像(PET)間接估計了5-HT受體活性,研究發現在急性卒中后5-HT神經遞質出現代謝的異常,尤其在邊緣系統和中縫核5-HT代謝的顯著下降,可能與抑郁的發生相關。臨床上使用5-輕色胺再攝取抑制劑可緩解PSD的癥狀,進一步支持PSD與單胺類神經遞質下降有關的觀點。Terroni等根據MRI研究結果顯示病灶影響邊緣-皮質-紋狀體-蒼白球-丘腦神經環,尤其是前額葉腹側和背側扣帶回皮層、海馬、杏仁核等易產生PSD,且以左側為著,而這種情況未見于腦橋背部和小腦。說明前額葉背外側皮質環路在情緒 的調節中起著重要作用,腦內該區域白質纖維連接的改變可能也會影響情緒調節過程。這與控制情感的神經環路主要分布在額顳葉、邊緣系統和腦干腹部及其皮層下聯系纖維的研究結果相一致。有學者認為,腦卒中"突如其來"的發生和其嚴重程度,使患者的工作和日常生活能力改變甚至喪失,導致患者心理應激障礙、心理平衡失調,由此對抑郁癥的產生有一定的作用。
2 卒中后抑郁動物模型的建立
有關卒中后抑郁的動物模型的建立,近年來國內文獻報道多為復合模型即在卒中基礎上結合相應應激刺激構建PSD模型。裘濤等[1]采用雙側頸總動脈永久性結扎后予以行為限制制作PSD大鼠模型,觀察大鼠自發性行為改變,海馬區單胺類神經遞質的變化。結果顯示:模型組大鼠水平運動得分、垂直運動得分、清潔動作次數與假手術組比較顯著下降(P<0.05;P<0.01),海馬區5-HT、5-HTAA、DA、NE水平與假手術組比較下調(P<0.05)。結論:大鼠雙側頸總動脈永久性結扎結合行為限制,可為卒中后抑郁的實驗及臨床研究提供較為理想的動物模型。劉福友[2]等采用大腦中動脈線栓法制備局灶性腦缺血大鼠模型,在此基礎上結合孤養、中度的不可預測應激處理(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CUMS)復合制備腦卒中后抑郁大鼠模型。運用糖水實驗、敞箱實驗、被動躲避實驗評定腦卒中后抑郁大鼠的興趣感變化、自發活動和探究行為等抑郁行為學改變。采用熒光分光度法測定大鼠腦內單胺類神經遞質水平。得到的結果是:①腦卒中后抑郁組腦卒中后第7,14d的體質量顯著低于正常對照組(P<0.05;P<0.01);②腦卒中后抑郁組糖水消耗量顯著低于正常對照組(P<0.01);③腦卒中后抑郁大鼠敞箱活動低下,被動躲避缺陷;④腦卒中后抑郁組雙側額頂皮質及腦干的去甲腎上腺素、5-羥色胺顯著降低。結論如下:在局灶性腦缺血大鼠模型的基礎上復合孤養和應激處理可以制備出較理想的腦卒中后抑郁大鼠模型。范文濤[3]等選取SD成年大鼠,采用單側頸總動脈不全結扎制備局灶性腦缺血模型,聯合孤養和小劑量利血平皮下注射制備腦卒中后抑郁癥模型。結果提示:腦卒中后抑郁癥動物模型腦內單胺類神經遞質含量降低;行為學表明活動減少,快感缺乏。充分模擬腦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核心癥狀,動物死亡率低,實驗重復性好,操作性較強,是腦卒中后郁抑癥的理想模型。李晶等[4]采用頸內動脈線栓再灌注法制備局灶性腦缺血大鼠模型,結合孤養和慢性不可預見的溫和性應激方法制備PSD大鼠模型,以體重、蔗糖水試驗、曠野試驗,Morris水迷宮試驗結果作為判定抑郁狀態的指標。結果顯示模型組和抑郁組大鼠體重明顯低于對照組,蔗糖水飲用量、曠野試驗水平和垂直運動與對照組相比明顯減少,有顯著差異(P<0.01),模型組和抑郁組相比沒有顯著差別。結論是用頸內動脈線栓再灌注法制備局灶性腦缺血大鼠模型,結合孤養和慢性不可預見的溫和性應激方法制備的PSD模型大鼠同時具備了腦缺血和抑郁的特點,經抗抑郁藥物治療后癥狀明顯改善,說明PSD模型制備成功。
3 針刺干預PSD大鼠的實驗研究
卒中后抑郁患者不僅有精神障礙癥狀而且還存在肢體的活動障礙,采用體針治療卒中后抑郁可以顯著促進患者肢體的恢復,平衡患者臟腑的陰陽,調節患者氣血的虛實。龔燕等[13]采用單側頸總動脈不全結扎聯合孤養和小劑量利血平皮下注射制備復合型PSD大鼠模型。觀察各組大鼠的行為學變化;利用熒光分光光度法測定各組大鼠大腦海馬區NE和5-HT含量。結果顯示,與正常組相比,模型組大鼠糖水消耗量和腦內NE、DA含量均明顯下降。電針能使PSD大鼠糖水消耗量和腦神經遞質NE、DA含量明顯增加。得到的結論是:電針治療PSD大鼠的機制可能與提高其海馬區5-HT和NE含量有關。孫培養等[14]選擇通督調神針法干預卒中后抑郁大鼠。結果:造模完成時,模型組和針刺組蔗糖水飲用量、水平及垂直運動得分、血漿中單胺類神經遞質的含量均較正常組降低,Zea Langa神經行為學評分提高,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P<0.05);治療4w時,與正常組和針刺組比較,模型組大鼠蔗糖水飲用量、水平及垂直運動得分、血漿中單胺類神經遞質的含量均降低,Zea Langa神經行為學評分提高,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P<0.01),而正常組與針刺組比較無統計學差異(P>0.05)。得到的結論如下:通督調神針法可以改善PSD模型大鼠的行為,提高其血漿單胺類神經遞質含量,提示通督調神針法治療PSD機制可能是通過調節血漿單胺類神經遞質含量。劉丹等采用免疫組化法檢干預卒中后抑郁大鼠的研究進展測大鼠5-HT1AR及BDNF含量的變化,觀察從痰論治針刺選穴對預處理組治療組的干涉作用。結果顯示:針刺治療組及針刺預防組5-HT1AR與正常組接近,但明顯低于模型組。針刺治療組及針刺預防組BDNF在額葉皮質的表達則顯著升高,卒中組大鼠BDNF表達低于針刺治療組,但仍顯著高于模型組。得到的結論是:模型組大鼠的5-HT1AR表達增加而BDNF的表達降低。從痰論治選穴,可以通過降低5-HT1AR的表達,增強BDNF的表達功能,對卒中后抑郁起到治療和治療作用。
4 中醫藥物干預PSD大鼠的實驗研究
中醫認為卒中后抑郁屬于"中風"與"郁證"范疇,由于受到軀體病殘的困擾,最終情緒抑郁。裘濤等[1]采用雙側頸總動脈永久性結扎后予以行為限制制作PSD大鼠模型,隨機分為模型組、滌痰開竅解郁組、氟西汀組,并設假手術組,采用RP-HPLC-熒光檢測法測定大鼠海馬區單胺類神經遞質的變化,并觀察大鼠自發性行為改變。結果發現模型組大鼠行為能力下降(P<0.01or0.05),海馬區5-HT,5-HIAA,DA,NE水平下調(P<0.05)。鹽酸氟西汀、滌痰開竅解郁湯治療后糖水試驗均較模型組有改善,腦內單胺類神經遞質水平提高(P<0.05)。因此,滌痰開竅解郁湯可以改善卒中后抑郁大鼠的行為及腦內單胺類神經遞質水平。沈曉明等對成年雄性SD大鼠采用雙側頸總動脈永久性結扎后予以行為限制的方法制備PSD大鼠模型,將造模成功的雄性SD大鼠隨機分為模型組、假手術組、氟西汀組以及舒郁顆粒高、中、低劑量組共6組,分別給予蒸餾水、氟西汀溶液及舒郁顆粒高、中、低(2.4,1.2,0.6g·kg-1)劑量i·g,22d后觀察大鼠自發性行為改變、海馬區單胺類神經遞質及TNF-α,IL 1β含量的變化。通過檢測大鼠行為學變化,舒郁顆粒高、中、低劑量組與氟西汀組各項指標無明顯差異,與模型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檢測大鼠腦組織海馬區單胺類神經遞質及炎癥因子的含量,與模型組比較,舒郁顆粒高、中、低劑量組NE、DA、5-HT水平上升有顯著性差異(P<0.05),TNF-α及IL 1β含量均顯著下降(P<0.05),而與假手術組無明顯差異;與氟西汀組各項指標無明顯差異。可知舒郁顆粒可明顯改善卒中后抑郁大鼠的行為,提高卒中后抑郁大鼠模型海馬單胺類神經遞質水平,降低炎癥細胞因子含量水平。樊蔚虹等選用健康雄性SD大鼠100只,隨機分為三組,即柴胡疏肝散治療組、PSD模型組和正常組。除正常組外,其余兩組首先線栓法制備MCAO模型,并按longa評分標準進行評分,手術1w后開始復合制備PSD大鼠模型,同時柴胡疏肝散組(7.875g·kg-1·d-1),i·g,21d,模型組蒸餾水i·g。免疫組化法檢測大鼠海馬組織Bcl-2,Bax蛋白表達。結果顯示與正常組比較,模型組Bax蛋白陽性表達升高,Bcl-2蛋白表達下降(P<0.01);柴胡疏肝散組與模型組比較,則明顯下調Bax蛋白表達(P<0.01),上調Bcl-2蛋白表達(P<0.01)。結論:柴胡疏肝散可通過下調Bax、上調Bcl-2蛋白的表達而抑制神經細胞凋亡,從而發揮對PSD的治療作用。
5 西醫藥物干預PSD大鼠的實驗研究
PSD的西醫藥物治療包括原發病、并發癥和抑郁癥的治療。患者因需同時服用治療腦卒中、高血壓或其他并發癥的藥物,故在選擇藥物時,應選擇相互作用小的藥物,所以新型抗抑郁劑有一定優勢,更適于神經系統疾病所致繼發性抑郁的治療。趙立波等采用CUMS結合孤養建立抑郁模型,MCAO術建立卒中模型PSD模型組和氟西汀組大鼠先建立卒中模型后建立抑郁模型,腹腔注射相應藥物進行干預,連續給藥21d后,用酶聯免疫法和免疫組化SABC法檢測給藥后各組大鼠腦組織中5-HT,NE,NGF的表達。結果顯示與假手術組比較,抑郁模型組和PSD模型組大鼠腦組織中5-HT,NE,NGF表達均明顯降低(P<0.01);與抑郁模型組和PSD模型組比較,氟西汀組大鼠腦組織中5-HT,NE,NGF表達均明顯升高(P<0.01),且氟西汀組與假手術組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可知氟西汀能顯著提高PSD模型大鼠腦組織中5-HT,NE,NGF水平。用Morris水迷宮試驗評價大鼠空間學習與記憶功能,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分析海馬CA3區BDNF的表達。結果顯示:與對照組比較,模型組大鼠學習能力顯著下降(P<0.05);而且BDNF陽性細胞數也較對照組下降,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PSD大鼠經文拉法辛5,10及20mg·kg-1·d-1治療后,認知功能和BDNF表達均顯著提高。得到的結論如下:文拉法辛能改善卒中后抑郁大鼠學習記憶障礙;這可能與增加海馬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有關。
6 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展望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在論述PSD發病的因素時各有側重,具體的發病機制尚未明確。現在多數學者認為其發病是由多種原因通過多種機制所致,與心身疾病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相一致,可能是神經生物學因素和社會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目前,關于PSD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動物實驗的基礎上,制備的動物模型主要以缺血性卒中為主,但卒中的發病類型包括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關于出血性卒中后抑郁動物模型的制備相對較少,這方面的研究信息相對缺失。并且,一般情況下卒中后抑郁患者多合并高血壓病、血脂異常等基礎病,而這些在動物模型身上無法一一體現;同時,在動物實驗造模、治療、取材的過程中,都有可能出現一些輕微的誤差,如取材的不完整性等。這些都有可能導致實驗結果存在一定的誤差,以至于影響實驗的準確性。
其次,關于卒中后抑郁治療方法頗多,有針灸、中醫藥物、西醫藥物等。腦卒中后抑郁屬于"中風"與"郁證"范疇,運用中醫藥物治療時,應綜合分析患者實際病情,并概括患者分型,從而辯證論治。針灸療法治療卒中后抑郁一方面可以幫助患者殘肢的功能恢復,間接有利于患者抑郁狀態的改變,另一方面疏肝行氣、調和陰陽,又起到直接改善患者情緒的作用。西醫藥物治療PSD的治療原則是早期、單一藥物、綜合、個體化、長期系統用藥。目前運用較為廣泛的是:三環類抗抑郁藥、5-HT再攝取抑制劑、NE再攝取抑制劑等,但西醫藥物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副作用。
因此,尋求PSD的發病機制以及制備理想的PSD模型,尋找治療PSD有效的方法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相信隨著分子生物學、神經生物學等基礎學科的發展和西醫學技術的不斷介入,卒中后抑郁的發病機制研究正從多層次、多角度不斷深入。假以時日,肯定能提出卒中后抑郁的最佳治療方案。
參考文獻:
[1]裘濤,陳眉,代建峰,等.腦卒中后抑郁癥動物模型的建立與評價[J].中國行為醫學科學,2006,15(1):12-13.
[2]劉福友,楊石,陳衛垠,等.腦卒中后抑郁大鼠模型的建立[J].中國臨床康復,2006,10(42):91-94.
[3]范文濤,王倩.腦卒中后抑郁癥動物模型的建立[J].長春中醫藥大學學報,2007,23(1):15-17.
[4]李晶,馬滌輝,沙瑩,等.PSD大鼠模型的建立及米氮平對其行為學的影響[A].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第十一屆全國神經病學學術會議論文匯編[C].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2008:2.
編輯/蔡睿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