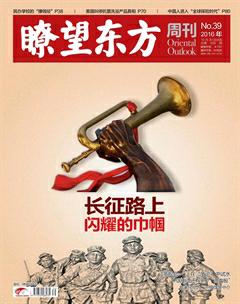“多規(guī)合一”,在“爭論”中試水
蘆垚
越是爭得厲害,將來肯定越好用
在廣東,佛山市南海區(qū)與順德市、中山市、東莞市并稱為“四小虎”。
1993年,南海區(qū)啟動了農(nóng)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嘗試通過成立股份合作社,將土地折價入股,村民則憑股權(quán)證定期分紅。南海區(qū)各村由此走上了只提供土地不參與企業(yè)經(jīng)營的道路。
“當(dāng)時每個村都在發(fā)展集體經(jīng)濟,六個輪子(縣、鎮(zhèn)、管理區(qū)、經(jīng)濟社、聯(lián)合體、戶)一起轉(zhuǎn),村村點火,村村冒煙。”南海區(qū)國土局副局長薛佩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這為南海區(qū)的農(nóng)村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奠定了基礎(chǔ)。
但后來,這卻成為阻礙南海區(qū)進一步發(fā)展的障礙。
長期以來,自下而上的發(fā)展導(dǎo)致了嚴重的土地碎片化,難以發(fā)揮土地的最大效益。1988年,南海區(qū)建設(shè)用地比例為11%。到了2014年,這一比例為51%,其中,集體建設(shè)用地比重占建設(shè)用地總面積71%。這導(dǎo)致南海區(qū)地均GDP僅為每平方公里4.3億元,在珠三角地區(qū)僅為中等水平。
不僅如此,寄生于集體用地的“租賃經(jīng)濟”還阻礙了城市建設(shè)與環(huán)境品質(zhì)的提升。由于規(guī)劃矛盾導(dǎo)致生態(tài)空間管控不明確,生態(tài)用地不斷遭到蠶食,部分河涌水質(zhì)較差,中心區(qū)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偏低。
“南海區(qū)就好比一個運動員,雖然強壯,但身體也有病患,而集體建設(shè)用地問題就是病中之病。因此必須節(jié)約集約利用土地,提高土地效率。”薛佩華說。
而2014年年底,隨著南海區(qū)成為國家“多規(guī)合一”的28個試點之一,這一旨在推動建立“統(tǒng)一銜接、功能互補、互相協(xié)調(diào)的規(guī)劃體系”的改革,正在一步步解決其用地難題。
規(guī)劃“打架”
南海區(qū)用地散、亂不僅有歷史因素,也有著復(fù)雜的體制性因素。
“一方面,是因為利益主體太多,導(dǎo)致了用地的碎片化。但從深層看,也是因為作為‘龍頭的規(guī)劃政出多門,各部門之間按照各自的行業(yè)標(biāo)準(zhǔn)和不同的要求進行管理及審批,缺乏緊密的溝通和協(xié)調(diào),導(dǎo)致了土地難以得到集約有效的規(guī)劃。”薛佩華說。
數(shù)據(jù)顯示:在南海區(qū),土地利用總體規(guī)劃和城市規(guī)劃之間的建設(shè)用地差異圖斑達12.2萬個,總面積166平方公里,占全區(qū)建設(shè)用地的30%;環(huán)保規(guī)劃、林班規(guī)劃以及交通、水利等部門的專項規(guī)劃與城市規(guī)劃、土地規(guī)劃的空間差異也十分明顯。
造成這些規(guī)劃差異的,是南海區(qū)60多種空間規(guī)劃。
南海區(qū)的問題并非孤例。事實上,在全國各地,這一困惑普遍存在。
“在全國范圍內(nèi),這一問題都很突出,這顯示出空間規(guī)劃亟需統(tǒng)籌。”廣州市城市規(guī)劃勘測設(shè)計研究院規(guī)劃設(shè)計一所副所長朱江說。
數(shù)據(jù)顯示:在國家層面,與空間有關(guān)的規(guī)劃研究有八十多種,如國家電網(wǎng)、電力、水利、交通、公路、道路、教育、旅游、文化、遺址保護等規(guī)劃。
不同規(guī)劃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打架”現(xiàn)象,這直接影響到各地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由于各層級、各部門之間的規(guī)劃存在某種程度的不一致,前些年,在某個城市,曾經(jīng)發(fā)生過城區(qū)下面被劃為大型采礦區(qū),當(dāng)時新建的機場因此面臨地下被掏空的風(fēng)險。
標(biāo)準(zhǔn)不一與利益矛盾
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和土地資源的日益緊張,空間規(guī)劃的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顯得日益迫切。
2013年12月,習(xí)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城鎮(zhèn)化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建立統(tǒng)一的空間規(guī)劃體系、限定城市發(fā)展邊界、劃定城市生態(tài)紅線”,“按照促進生產(chǎn)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tài)空間山清水秀的總體要求,形成生產(chǎn)、生活、生態(tài)空間的合理結(jié)構(gòu) ”,“在縣市通過探索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城鄉(xiāng)、土地利用規(guī)劃的‘三規(guī)合一或‘多規(guī)合一,形成一個縣市一本規(guī)劃、一張藍圖,持之以恒加以落實”。
2014年年底,“多規(guī)合一”試點工作正式啟動。
根據(jù)國家發(fā)展改革委、國土資源部、環(huán)境保護部、住房城鄉(xiāng)建設(shè)部等部委聯(lián)合發(fā)出的關(guān)于開展市縣“多規(guī)合一”試點工作的通知,全國28個試點地區(qū),開始通過開展試點工作,探索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規(guī)劃、城鄉(xiāng)規(guī)劃、土地利用規(guī)劃、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等規(guī)劃“多規(guī)合一”的具體思路。
然而,要把數(shù)十項規(guī)劃合而為一,并不容易。
多規(guī)合一的難題之一,是各個規(guī)劃標(biāo)準(zhǔn)不一。
“即便不同部門想達成一致的目標(biāo),但因為標(biāo)準(zhǔn)不同,執(zhí)行起來就不一樣。”朱江告訴本刊記者。
比如,在對水庫的認定上,城鄉(xiāng)規(guī)劃和土地總體利用規(guī)劃就不同。土地總體利用規(guī)劃中,水庫是建設(shè)用地,但是在城鄉(xiāng)規(guī)劃中,水庫是非建設(shè)用地。
在28個試點地區(qū)中,國土部指導(dǎo)的試點地區(qū)榆林市是面積最大的一個。在當(dāng)?shù)赝七M試點工作的過程中,首先碰到的問題,就是標(biāo)準(zhǔn)不統(tǒng)一。
“標(biāo)準(zhǔn)的統(tǒng)一是應(yīng)該先行的事情。標(biāo)準(zhǔn)一致了,其他才可以做到一致。”陜西榆林市發(fā)改委總工程師楊揚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我們光是做標(biāo)準(zhǔn)轉(zhuǎn)換,就花了兩個月時間。”
林業(yè)規(guī)劃和土地規(guī)劃的矛盾,是榆林空間規(guī)劃的主要矛盾之一。
例如,在榆林林業(yè)局的統(tǒng)計中,全市共有3800畝林地,而在當(dāng)?shù)貒辆值慕y(tǒng)計中,只有1800畝林地。林業(yè)局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依據(jù)的是林業(yè)部門的標(biāo)準(zhǔn),而國土部門的統(tǒng)計則是依據(jù)國家標(biāo)準(zhǔn)。
“有些我們認為是耕地、草地的,林業(yè)部門認為是林地。”榆林市國土資源局總規(guī)劃師李東堂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我們算了下,3800畝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基本上是把農(nóng)田草地都算進去了。”
之所以存在土地利用類型之爭,不僅是因為統(tǒng)計標(biāo)準(zhǔn)因素。
此前,為了鼓勵植樹造林,國家對林地有相應(yīng)的補貼,因此,各地的林地申報自然越來越多。
“國家有林業(yè)規(guī)劃的目標(biāo),但是,也有耕地保護的目標(biāo),落實在基層,就會造成宜林地和耕地保護之間的矛盾。”李東堂說。
榆林地處環(huán)境脆弱地區(qū)。長城橫穿榆林城而過,在長城以北,是毛烏素沙漠南緣風(fēng)沙草灘區(qū),面積約15813平方公里,占榆林市面積的36.7%;在長城以南,則是典型的黃土高原地貌,縱橫交錯的溝壑,極易流失水土。正是因此,宜林地在當(dāng)?shù)赝恋刂姓紦?jù)相當(dāng)大比重。
但是,被譽為“中國科威特”的榆林,也是典型的資源型城市。當(dāng)?shù)夭粌H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還有中國陸上探明的最大整裝氣田陜甘寧氣田。
建設(shè)用地就是生產(chǎn)力。煤炭開采、煤化工項目,都得用地。因此,有人認為“有些林地劃到城市規(guī)劃的區(qū)域,影響了榆林的發(fā)展”。
“對榆林人來講,資源開發(fā)重要還是生態(tài)保護重要?沒有資源開發(fā)哪有榆林今天的經(jīng)濟發(fā)展?但是,沒有65年的治沙也沒有今天的榆林城。”榆林市委副書記高中印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多規(guī)合一的難度在哪兒?各個規(guī)劃都有法律依據(jù),從自己的角度出發(fā)看都是對的,放在一起看就有差異沖突。”
爭論越充分,規(guī)劃越科學(xué)
要實現(xiàn)“多規(guī)合一”,不僅要把各個部門的標(biāo)準(zhǔn)統(tǒng)一到一張規(guī)劃圖上,還要在所有利益相關(guān)方之間進行協(xié)調(diào)、平衡,進而在一張規(guī)劃圖上統(tǒng)合各方主張。
在本刊記者走訪的數(shù)個國土部指導(dǎo)的試點地區(qū)中,整合“多規(guī)”技術(shù)銜接,統(tǒng)一各類數(shù)據(jù)基礎(chǔ),協(xié)調(diào)“多規(guī)”差異之難,讓參與者印象深刻。
“為了繪就這一張規(guī)劃圖,我們要考慮生態(tài)保護的需求,要考慮工業(yè)園區(qū)的用地需求,要考慮地下礦產(chǎn)開采的需求,要考慮地上城市建設(shè)的需求,要考慮園區(qū)和油氣管線走廊的安全距離,甚至還要考慮作為文物大市的文物保護的需求。”高中印說。
“所以我們的第一個體會就是,必須形成強有力的協(xié)調(diào)機制。”高中印說。
為推進試點工作,榆林市成立了試點工作領(lǐng)導(dǎo)小組,從其組員構(gòu)成可見對這項工作的重視:市委書記任組長、市長和市委副書記任副組長、常務(wù)副市長任辦公室主任,市人大、政協(xié)相關(guān)領(lǐng)導(dǎo)參與,市級各相關(guān)部門負責(zé)人、各縣(區(qū))委書記為成員。
此外,領(lǐng)導(dǎo)小組辦公室下還專門設(shè)立了綜合協(xié)調(diào)、業(yè)務(wù)專責(zé)兩個工作組,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工作組分別設(shè)在市委改革辦和市發(fā)改委,而非國土、住建或環(huán)保部門,“正是因為這些部門不具備協(xié)調(diào)能力”。
作為專家組副組長,楊揚說,2015年的8個月時間里,他大概開了200次會,“有些會,吵架吵得都開不下去了。”
“協(xié)調(diào)矛盾不開會不行。為什么以前的規(guī)劃是軟性的?以前的規(guī)劃,各個部門都沒有意見,這導(dǎo)致規(guī)劃本身的科學(xué)性就不足。‘多規(guī)合一經(jīng)過多次爭論以后,肯定是個科學(xué)協(xié)調(diào)的共識。越是爭得厲害,將來肯定越好用。”高中印說。
神木縣有兩個工業(yè)園區(qū),在規(guī)劃中有一部分最終劃進了生態(tài)線內(nèi)。“雖然從經(jīng)濟上來說可能有損失,但大家到現(xiàn)場一看,反對者自己就覺得沒有道理了,因為那里是重要的水源涵養(yǎng)區(qū)。”李東堂說。
“規(guī)劃的變化,必然牽涉到一些市場主體的利益,各方都需要妥協(xié)。由于規(guī)劃變化,導(dǎo)致有些企業(yè)的利益受損,這是下一步要解決的問題。”高中印說。
而當(dāng)一張規(guī)劃圖確定之后,矛盾將會被一勞永逸地解決。
“事實上,越到基層,越認同‘多規(guī)合一的重要性。尤其是企業(yè),因為他們得到實惠了。否則,按照以前的規(guī)劃,可能出現(xiàn)發(fā)改委批了,國土局批了,花了幾年時間建設(shè),最后卻因為涉及水源地保護而被否定掉,白白遭受損失。”楊揚說。
在南海區(qū),會場同樣成為推進試點繞不過去的“戰(zhàn)場”。
在寸土寸金的珠三角腹地,土地牽涉到的利益更巨大。
“區(qū)政府層面召集了不下100次會,哪個部門也不可能協(xié)調(diào)這項工作。”薛佩華說。
佛山下轄7個鎮(zhèn)1個街道,所有鎮(zhèn)都位居全國百強鎮(zhèn)榜單的前50名,其中兩個鎮(zhèn)還是全國前十。
試點工作開始后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控制開發(fā)用地。具體流程是,把總的用地量劃給各鎮(zhèn),再由各鎮(zhèn)分別協(xié)調(diào),分別確定需要“保”哪些項目“棄”哪些項目。
“‘多規(guī)合一先把用地規(guī)模分配給鎮(zhèn)里,由鎮(zhèn)里面統(tǒng)籌。其中,開發(fā)哪里不開發(fā)哪里,如何平衡很重要。”南海區(qū)九江鎮(zhèn)國土所所長劉冠勛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但是,在協(xié)調(diào)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要“保”的太多了,只能多次再統(tǒng)籌。最后,總共協(xié)調(diào)了4輪,區(qū)長為每個鎮(zhèn)開一天會,整整一周的會之后,才完全統(tǒng)籌好。
反向規(guī)劃定底線
“多規(guī)合一”的過程,并非相關(guān)利益方的自由博弈。
“關(guān)鍵是要科學(xué)妥協(xié),有原則地妥協(xié)。”高中印對本刊記者表示。
如何妥協(xié)才算科學(xué)?
榆林的做法是“先瘦身后強身”。
“以前,工業(yè)園區(qū)的規(guī)劃,一劃就是近百平方公里。現(xiàn)在我們說,不怕要地,但是你得告訴我這塊地要干什么。沒那么多事做,占地面積自然而然就下來了。以前就是盲目求大,所以容易膨脹。而當(dāng)園區(qū)面積及城市開發(fā)邊界被壓縮之后,耕地、水資源保護面積自然就大了。”高中印說。
這是規(guī)劃思路的變革。
“我們大的思路是,首先以反向規(guī)劃的理念,對國土空間開發(fā)進行科學(xué)評價,確定哪些適宜開發(fā)哪些不適宜。這個調(diào)子定好以后再繼續(xù)。”高中印表示。
國土開發(fā)適宜性分析后的結(jié)論是,榆林市適宜開發(fā)的土地面積占總面積的8.6%,而目前已開發(fā)的只有不到4%。
不僅是榆林,本刊走訪的幾個國土部指導(dǎo)的試點地區(qū),在做好“多規(guī)”技術(shù)銜接、協(xié)調(diào)“多規(guī)”差異的同時,都開展了區(qū)域資源環(huán)境承載力評價,在此基礎(chǔ)上,這些地區(qū)基本完成了強化空間規(guī)劃底盤管控,統(tǒng)籌各類規(guī)劃要求,構(gòu)建空間規(guī)劃指標(biāo)體系的探索。
摸底基礎(chǔ)上的反向規(guī)劃理念,帶來的是規(guī)劃的引導(dǎo)作用強化。
榆林市國土局局長姚宏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過去是規(guī)劃跟項目走。因為某塊地離城市近,方便,就把項目建設(shè)在那里。現(xiàn)在是項目跟著規(guī)劃走,要服從統(tǒng)一的空間規(guī)劃安排。”
朱江告訴本刊記者,“多規(guī)合一”主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解決合什么的問題,另一個,就是劃定底線。“簡單講,‘多規(guī)合一就是在底線控制下的博弈。”
在中央城鎮(zhèn)化工作會議上,習(xí)近平總書記強調(diào)“有些農(nóng)用地是不能動的、硬性的,在這個前提下再來考慮城鎮(zhèn)化規(guī)劃,要避開這些農(nóng)業(yè)用地”,“切實保護耕地、園地、菜地等農(nóng)業(yè)空間,劃定生態(tài)紅線”,“盡快把每個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開發(fā)邊界劃定”,這也成為南海區(qū)開展“多規(guī)合一”工作的坐標(biāo)原點。
在試點過程中,南海區(qū)先劃定了永久基本農(nóng)田保護、生態(tài)保護、城市開發(fā)邊界三條紅線,在底線控制的基礎(chǔ)上,再進行用途管控。
從這個角度看,在未來的空間規(guī)劃體系中,“管底線”的土地利用總體規(guī)劃意義重大。
有專家建議,應(yīng)嚴守資源保護底線,充分發(fā)揮土地利用總體規(guī)劃的統(tǒng)籌管控作用,以第二次全國土地調(diào)查及連續(xù)變更的最新土地利用現(xiàn)狀為“底圖”。
不過,看似簡單的底線劃定也頗有講究。
“我們認為線越少越好,因為每一條線都意味著審批。而且,我們避免各種線重疊,否則就意味著很多部門管一塊地。如果那樣的話,就意味著審批一塊地要把好多部門走一遍。” 薛佩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