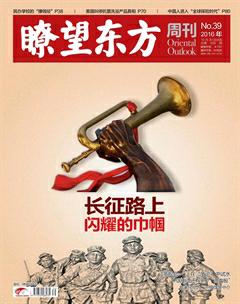作家經(jīng)紀(jì)人,不僅僅是中介
劉佳璇
作家經(jīng)紀(jì)人的工作早已超越將作品版權(quán)放到市場上標(biāo)價(jià)銷售,而是把IP做大做強(qiáng)
“在影視圈,每個(gè)月都會(huì)覺得上個(gè)月的自己是傻子。”網(wǎng)絡(luò)作家唐家三少曾說。
“IP熱”使得作家更多與資本產(chǎn)生接觸,談話核心總離不開“全版權(quán)開發(fā)”。從出版物、影視作品到衍生游戲,圍繞作家手中的IP資源,內(nèi)容變現(xiàn)的形式花樣翻新,與此同時(shí),作家也面臨著更趨復(fù)雜的商務(wù)合作環(huán)境。
懸疑小說作家閆志洋對(duì)《瞭望東方周刊》坦言,他最頭痛的就是商務(wù)談判,這些事他全部交給了自己的經(jīng)紀(jì)人梁爽。
作家經(jīng)紀(jì)人或經(jīng)紀(jì)機(jī)構(gòu)的作用越來越大,他們不僅僅是版權(quán)的中介者,更可以擔(dān)任作家的商務(wù)智囊,在版權(quán)合作過程中發(fā)揮黏合與潤滑的功能。
梁爽對(duì)《瞭望東方周刊》說:“讓專業(yè)的人做專業(yè)的事,版權(quán)開發(fā)的效果才能最大化。”
市場需求與業(yè)內(nèi)助推之下,在中國一度久喚不至的作家經(jīng)紀(jì)行業(yè),終于有了起步的態(tài)勢。
久喚而至
如果沒有經(jīng)紀(jì)人克利斯多夫·里特的運(yùn)作,《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很難憑借一己之力讓那位戴眼鏡的小巫師風(fēng)靡全球。
在歐美,作家經(jīng)紀(jì)人并不是一個(gè)新興職業(yè),有八成的大眾圖書由經(jīng)紀(jì)人進(jìn)行版權(quán)代理。這些經(jīng)紀(jì)人挖掘具有潛力的作家,代表作家和出版商討價(jià)還價(jià),替作家簽署出版合同,為作家爭取更為持久的影響力和更高的酬勞。
而在中國,作家經(jīng)紀(jì)人制度久喚不至。長期以來,作家與出版商的合作關(guān)系都依賴于作家與出版社編輯的人際往來,并沒有成熟的商業(yè)化經(jīng)紀(jì)制度。
自2012年開始,便有業(yè)內(nèi)人士呼喚,中國也應(yīng)有作家經(jīng)紀(jì)制度,但作家對(duì)此卻態(tài)度不一。作家蔡駿在2006年時(shí)已有請(qǐng)經(jīng)紀(jì)人幫忙選擇出版社的想法,而王安憶則對(duì)經(jīng)紀(jì)人的必要性保持懷疑。
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會(huì)新媒體文學(xué)委員會(huì)秘書長吳長青對(duì)《瞭望東方周刊》說:“作家協(xié)會(huì)可以幫助作家獲得版權(quán)代理的資源和上升渠道,在過去,這讓很多作家認(rèn)為經(jīng)紀(jì)人制度可有可無。”
從觀念上看,許多作家更看重專業(yè)的文學(xué)批評(píng)體系為作品所下的論斷,不能認(rèn)同從市場利潤空間來評(píng)判作品價(jià)值,而把作品交給經(jīng)紀(jì)人,相當(dāng)于將作品交給市場檢驗(yàn)。
另外,中國的圖書定價(jià)普遍偏低,除了當(dāng)紅作家,僅憑版稅,很少有人能支付得起經(jīng)紀(jì)人的費(fèi)用。按照國際出版市場的慣例,作家經(jīng)紀(jì)人在版權(quán)代理的過程中會(huì)收取10%~15%的代理費(fèi)。“此前作家所得版稅也就是幾萬元,按這個(gè)比例,經(jīng)紀(jì)人所得就更少了。”閆志洋說。
杭州師范大學(xué)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研究院院長夏烈對(duì)《瞭望東方周刊》說,總而言之,是“過去出版市場的產(chǎn)業(yè)化程度與資產(chǎn)體量不足以‘養(yǎng)活經(jīng)紀(jì)人這一行”。
自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版權(quán)價(jià)值被影視行業(yè)發(fā)掘以來,形勢開始轉(zhuǎn)變。
文學(xué)內(nèi)容被視為文學(xué)、游戲、影視、動(dòng)漫等泛娛樂產(chǎn)業(yè)集群最上游的“IP富礦”,其中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和類型文學(xué)尤甚。
梁爽說:“這相應(yīng)提升了作者的價(jià)值,也讓越來越多的作者意識(shí)到自身品牌價(jià)值及商業(yè)價(jià)值的重要性。”唐家三少早期的手機(jī)游戲版權(quán)價(jià)格是10萬元,如今已漲到1000萬元。
兩年來,找到閆志洋談商務(wù)合作的影視公司越來越多。伴隨著版權(quán)增值,版權(quán)市場越發(fā)細(xì)分與多元,對(duì)于并不擅長社交也不熟悉商業(yè)規(guī)則的閆志洋來說,面對(duì)草擬的合約,如何保障自己的權(quán)益?他越發(fā)感到,自己需要編輯、運(yùn)營、公關(guān)、法務(wù)等多種專業(yè)服務(wù)。
在夏烈看來,IP改編讓內(nèi)容生產(chǎn)從獨(dú)立創(chuàng)作走向集體工業(yè)化創(chuàng)作,更依賴于一套成熟的跨行業(yè)體制。
“在這樣的情況下,作家經(jīng)紀(jì)人這個(gè)角色就顯得必不可少了。”梁爽說。
從版權(quán)中介到職業(yè)經(jīng)紀(jì)
梁爽曾經(jīng)是圖書編輯,他回憶:“那時(shí)也會(huì)做一些類似作家經(jīng)紀(jì)的工作,但和如今差別很大。”
在出版界,版權(quán)交易并非新鮮事,只是在IP熱到來之前,出版界的版權(quán)生意較為簡單:一種是國際版權(quán)交易,主要是海外圖書引進(jìn)或國內(nèi)作品輸出;另一種則是國內(nèi)市場作者與出版商之間的版權(quán)買賣。
第二種情況下的版權(quán)交易中,經(jīng)紀(jì)制度停留在初級(jí)階段,更類似于簡單的中介:一些對(duì)出版流程很了解的“中間人”利用出版行業(yè)的基礎(chǔ)知識(shí)和行業(yè)人脈,替作者尋求出版機(jī)會(huì),替出版機(jī)構(gòu)介紹作品和作者。
業(yè)內(nèi)人士表示,“中間人”不是職業(yè)經(jīng)紀(jì),只是獲取中介費(fèi),而非與作家長期合作并為其提升商業(yè)價(jià)值,遠(yuǎn)不能起到真正的經(jīng)紀(jì)作用。
如今,伴隨文化產(chǎn)業(yè)全產(chǎn)業(yè)鏈的構(gòu)建,作家經(jīng)紀(jì)已經(jīng)不再是簡單的中介,作家經(jīng)紀(jì)人的職業(yè)特點(diǎn)也變?yōu)椤翱缃邕\(yùn)營”。
“IP概念引入后,作家經(jīng)紀(jì)人的工作就不再局限于出版這個(gè)小市場了。”夏烈說,“為什么叫‘運(yùn)營而不是‘代理或‘買賣?因?yàn)樽骷医?jīng)紀(jì)人要‘養(yǎng)IP,他的工作早已超越將作品版權(quán)放到市場上標(biāo)價(jià)銷售,而是把IP做大做強(qiáng)。”
閆志洋的商戰(zhàn)小說《賭石教父》目前已經(jīng)與蘇寧文創(chuàng)集團(tuán)達(dá)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其中,紙質(zhì)出版物由海峽出版發(fā)行集團(tuán)鷺江出版社負(fù)責(zé),電子書版權(quán)交由咪咕閱讀和蘇寧閱讀,同時(shí)還和多家影視機(jī)構(gòu)與創(chuàng)作團(tuán)隊(duì)共同孵化影視項(xiàng)目。
在這背后進(jìn)行斡旋的便是以梁爽為代表的閆志洋經(jīng)紀(jì)團(tuán)隊(duì),而這還只是作家經(jīng)紀(jì)人工作的一部分。
作家經(jīng)紀(jì)人張曉媛在開始運(yùn)營作家艾力的經(jīng)紀(jì)業(yè)務(wù)時(shí),艾力還沒有足夠的影響力,于是她策劃出“北大學(xué)霸、全國名師、青年偶像、白手起家”的作家形象,請(qǐng)俞敏洪作序,蔡康永、大冰推薦,“后續(xù)一年中,不斷有讀者反饋因?yàn)榭戳舜蟊耐扑]來買這本書”。
“相當(dāng)于你是個(gè)伯樂。”夏烈表示,經(jīng)紀(jì)人根據(jù)對(duì)市場的了解,尋找具有潛力的作者,此后還要通過運(yùn)營讓作家的社會(huì)影響力、文學(xué)聲譽(yù)獲得全方面的提升。
匯智飛鷺為閆志洋創(chuàng)立了一間工作室,梁爽說:“這是和作家長期合作的模式,實(shí)際上是一種公司雛形,去樹立作家個(gè)人的文化品牌。”
如果工作室模式能獲得成功,未來便可成長出諸如張嘉佳的“時(shí)間海”、南派三叔的“南派泛娛”這類文化公司,依托作家個(gè)人影響力以求內(nèi)容增值,簽約其他具有影響力的作家,以點(diǎn)帶面地承擔(dān)經(jīng)紀(jì)職能。
共贏,要贏的是話語權(quán)
“實(shí)際上,作家在與影視公司談判時(shí),會(huì)感到自己處在一個(gè)弱勢的地位。”閆志洋對(duì)本刊記者說。
閆志洋表示,作家在獨(dú)自寫作時(shí)場景單一,而全版權(quán)的商務(wù)合作環(huán)節(jié)很多,前端與后端的分成談不清楚,資本便會(huì)與作家構(gòu)成利益沖突,這壓縮了作者在項(xiàng)目開發(fā)時(shí)的話語權(quán)。
由此,各種版權(quán)糾紛事件頻出。一樁著名的公案是,《羋月傳》原著小說作者蔣勝男不滿電視劇編劇署名,于2015年將出品方告上法庭。
IP市場動(dòng)輒叫價(jià)千萬元,經(jīng)紀(jì)人便要充當(dāng)調(diào)和作家與資本間利益沖突的角色,在項(xiàng)目開發(fā)期間,要力保IP價(jià)值不被浪費(fèi)、保障作家權(quán)益。
梁爽在與影視公司談閆志洋作品的影視改編時(shí),對(duì)所有改編中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所提及,包括傳達(dá)作家意見,以及如何將小說中一些可能觸及政策紅線的細(xì)節(jié)轉(zhuǎn)化為可以影視化的內(nèi)容。
比起娛樂圈傳統(tǒng)的經(jīng)紀(jì)制度,作家經(jīng)紀(jì)制度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權(quán),尤其是在項(xiàng)目開發(fā)上。“作家經(jīng)紀(jì)人與作家已是利益共同體。”梁爽說。
IP的開發(fā)效果直接關(guān)乎作家經(jīng)紀(jì)人的利益。目前作家經(jīng)紀(jì)的盈利模式有兩種:一是短期收益,將版權(quán)賣給影視公司或者游戲公司,與作家共同獲得版權(quán)費(fèi),按三七或六四比例分成;二是長期收益,與影視公司聯(lián)合開發(fā)項(xiàng)目,與作家一起獲取項(xiàng)目分成。
對(duì)于經(jīng)紀(jì)人或經(jīng)紀(jì)平臺(tái)來說,發(fā)掘作家相當(dāng)于在“IP富礦”中尋找礦石,更利于自身向文化產(chǎn)業(yè)鏈下游滲透。在梁爽看來,“實(shí)際上是一種共贏”。
因此,出版社和文學(xué)網(wǎng)站都有自己的作家經(jīng)紀(jì)布局,以閆志洋的經(jīng)紀(jì)團(tuán)隊(duì)匯智飛鷺為例,便是鷺江出版社聯(lián)合素錦文化、匯智光華共同成立的。
老牌文學(xué)雜志《收獲》也在2016創(chuàng)建手機(jī)應(yīng)用“行距”,提供作者、編輯和編劇共享的經(jīng)紀(jì)平臺(tái)。
《收獲》主編程永新回憶,1988年,導(dǎo)演張藝謀曾獲得《收獲》的“首看權(quán)”,即在雜志上市前可以率先閱讀清樣,挑選他想改編的作品,此后效仿的還有導(dǎo)演姜文。余華的《活著》與王朔的《動(dòng)物兇猛》(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原著)便是如此走向影視化的。
“可是小說與影視再怎么牽手,曾經(jīng)的《收獲》編輯部都幾乎只是義務(wù)勞動(dòng),僅限于牽線搭橋。”程永新說。借由IP熱,《收獲》找到了引入影視版權(quán)代理服務(wù)的機(jī)會(huì),建立作家經(jīng)紀(jì)業(yè)務(wù),也顯示出它與作者實(shí)現(xiàn)共贏、爭取行業(yè)話語權(quán)的野心。
成熟期遠(yuǎn)未到來
在夏烈看來,僅有依托網(wǎng)站與出版社的作家經(jīng)紀(jì)機(jī)構(gòu)登場,并不能代表作家經(jīng)紀(jì)制度的成熟。
擁有最多IP的文學(xué)網(wǎng)站由于戰(zhàn)線太長,只能針對(duì)一線作者的IP竭澤而漁,導(dǎo)致二三線作者的優(yōu)質(zhì)IP難以得到有效開發(fā),也就未能有效發(fā)揮作家經(jīng)紀(jì)的作用。
“大型文學(xué)網(wǎng)站的一些經(jīng)紀(jì)合約,事實(shí)上也侵犯了一些作者的權(quán)益,有種‘賣身契的意思。”吳長青對(duì)《瞭望東方周刊》說。
一位網(wǎng)絡(luò)作家表示,自己拿著與一家大型文學(xué)網(wǎng)站的合約一算,大概千字3分錢,還要轉(zhuǎn)讓IP改編權(quán),而簽約的基本前提是一日6000字的高速更新。
總體而言,作家經(jīng)紀(jì)制度在中國剛剛起步,而整個(gè)IP市場的商業(yè)規(guī)則也尚在摸索之中,夏烈認(rèn)為:“作家經(jīng)紀(jì)制度成熟的標(biāo)志,是專業(yè)的獨(dú)立作家經(jīng)紀(jì)公司出現(xiàn),與作家形成長期的合作,引領(lǐng)一種行業(yè)規(guī)則并樹立規(guī)范。”
不過,獨(dú)立的經(jīng)紀(jì)公司并不好生存,夏烈解釋:“資本大面積進(jìn)入產(chǎn)業(yè)之后,利益太大,作家生怕‘被搶錢,對(duì)中間的經(jīng)紀(jì)公司很難建立信任。”
這需要一個(gè)行業(yè)“標(biāo)桿”的出現(xiàn)。
目前,較有影響力的獨(dú)立作家經(jīng)紀(jì)機(jī)構(gòu)之一是唐家三少好友貝志城創(chuàng)立的“大神圈”,它與顧漫、唐家三少和江南都有合作,擁有《微微一笑很傾城》《九州縹緲錄》《龍族》等多部作品的IP運(yùn)營權(quán)。
雖然“大神圈”能否成為“標(biāo)桿”尚有待觀察,但貝志城的確得到了一批知名網(wǎng)絡(luò)作家的信任——在2011年成立的作家維權(quán)聯(lián)盟中,貝志城是主要領(lǐng)導(dǎo)者和執(zhí)行人,參與過一系列版權(quán)維權(quán)事件,這是他與“大神”建立往來的緣起。
“獲得作家的信任是作家經(jīng)紀(jì)人工作中最困難的部分,需要長期經(jīng)營。”梁爽說。閆志洋曾經(jīng)找過幾個(gè)經(jīng)紀(jì)人,合作的結(jié)果都沒有讓他感到滿意。后來,與他相識(shí)于2011年的梁爽開始從事作家經(jīng)紀(jì)業(yè)務(wù),二人開始了合作。
作家經(jīng)紀(jì)人獲得作家信任的基礎(chǔ),是有良好的職業(yè)態(tài)度,懂內(nèi)容、懂市場、有人脈,還要具備專業(yè)法律素養(yǎng)。雖然越來越多影視、動(dòng)漫、游戲、衍生品領(lǐng)域的人員都加入了圈子,從業(yè)人員素質(zhì)卻還參差不齊。
IP交易價(jià)格較高、浮動(dòng)空間大,交易過程復(fù)雜且專業(yè),吳長青說:“不可否認(rèn),行業(yè)內(nèi)的確有浮躁,有騙局,有人拿著合約說得天花亂墜,也有人渾水摸魚,拿到版權(quán)代理后草率地處理IP,甚至惡性地刷話題、制造假數(shù)據(jù)。”
實(shí)際上,“作家經(jīng)紀(jì)人”或“版權(quán)經(jīng)紀(jì)人”都尚未正式列入《國家職業(yè)分類大典》,也就是說,相應(yīng)的執(zhí)業(yè)準(zhǔn)入或相關(guān)的職稱機(jī)制并未出臺(tái),也沒有配套的培養(yǎng)機(jī)制。
中國版權(quán)保護(hù)中心曾在2012年提交相關(guān)的職業(yè)立項(xiàng)申請(qǐng),并且創(chuàng)辦了相關(guān)的培訓(xùn)課程。夏烈對(duì)《瞭望東方周刊》說:“務(wù)實(shí)地講,把人才做好是第一位的,目前來看,一個(gè)成熟的獨(dú)立經(jīng)紀(jì)公司要出現(xiàn),至少還要5年時(sh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