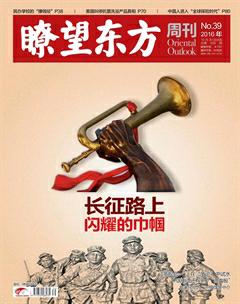民辦學校的兩難選擇:營利還是非營利
王輝輝
對于營利與否的選擇,所要考慮的不僅是辦學模式的差別,更關(guān)鍵的問題在于,政策紅利會否喪失
“看到新聞了沒,又延遲了。”2016年9月初,肖軍(化名)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對方開口就扔過來這樣一句話。
肖軍知道,對方說的是“民辦教育促進法”(以下簡稱“民促法”)修訂案三審再次延遲了。作為一所民辦職業(yè)技術(shù)學校的創(chuàng)辦人,他又陷入了焦慮。
這已不是第一次延遲。
2015年12月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十九次委員長會議,對被稱為“教育三法”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民促法”修訂草案進行了審定。最終,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修訂案順利通過并于2016年正式試行,而“民促法”修訂案卻因分歧較大未獲通過。
2016年6月,“民促法”修訂案三審被延遲。
于是,業(yè)內(nèi)盛傳修訂案有望在8月底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提交。然而,最終它仍未進入會議的正式議題范圍。
“這背后映射出的是民辦學校的分類管理困局。” 中國教育科學院教育發(fā)展與改革研究所所長吳霓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
像肖軍這樣的民辦學校舉辦者仍舊要面臨營利還是非營利的兩難選擇。
分類難題
吳霓稱,“民促法”修改一再延遲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各方分歧較大,需要充分討論。”
此次“民促法”修訂首先要解決的是民辦學校分類管理問題,最大的分歧也來自于此。
2010年出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中就曾明確提出,教育行政部門要積極探索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分類管理。
“所謂分類就是營利和非營利的區(qū)別,就是民辦教育的舉辦者能不能拿回報的問題。”北京教育科學院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王磊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他指出,在民辦教育剛剛興起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家明確規(guī)定,民辦教育的舉辦者不應以營利為目的。
甚至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在2015年12月修改之前,都分別有“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舉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gòu)”“設立高等學校不得以營利為目的”的規(guī)定條款。
但是,2002年出臺的“民促法”中又明確規(guī)定,民辦學校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結(jié)余中取得合理回報。
吳霓認為,民辦學校必須進行分類管理,但首先要弄清類別具體怎么分,“比如是不是要從階段性、是否營利性及學歷性上來分類。”
在他看來,中國的民辦教育正處于從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過渡的歷史時期,由原來“公辦”一統(tǒng)天下到現(xiàn)在逐漸形成公辦與民辦共同發(fā)展的格局,如果進行一刀切的分類,會產(chǎn)生許多問題。
以學前教育為例。教育部《2015年全國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中的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幼兒園22.37萬所,其中民辦幼兒園達14.64萬所,占比超過65%。
“這近70%的民辦幼兒園既滿足了市場的多元化需求,也暴露出了政府責任不足的問題。現(xiàn)在要做分類,是不是將其全部推向營利性?那么普惠性怎么辦?”吳霓說。
分類之后,還涉及到學校的產(chǎn)權(quán)歸屬問題。比如,如果一些投資辦學的學校想要轉(zhuǎn)變?yōu)榉菭I利性,那投資人前期的投入怎么清算?而一些原本屬于捐資辦學的學校想選擇為營利性,其產(chǎn)權(quán)歸屬又該如何算?
十倍以上的成本差
而作為民辦學校的舉辦者,肖軍關(guān)心的是,分類之后,如果自己選擇營利性辦學,還能不能享有各項優(yōu)惠政策。
2006年,技術(shù)工人出身的肖軍在中部某城市創(chuàng)辦了一所民辦職業(yè)技術(shù)學校。
“由于臨近農(nóng)村,學校開設的專業(yè)又能緊密結(jié)合當?shù)氐闹еa(chǎn)業(yè),畢業(yè)生就業(yè)情況好,剛開始的那幾年,學校生源很好。”回憶起昔日的輝煌光景,肖軍充滿了驕傲。
2012年之后,國家陸續(xù)推行職業(yè)教育的免費政策,肖軍的學校,開始經(jīng)營困難。于是,他不得不將職業(yè)學校申請變更為民辦中學。
“雖然那個時候國家已經(jīng)在提民辦學校分類管理了,但是我們學校既不屬于非營利性的捐資辦學,也不完全屬于純營利性的培訓機構(gòu),算是處在中間地帶。”肖軍坦言。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業(yè)內(nèi)專家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稱,這種“中間地帶”在民辦學校中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大部分民辦學校都處在營利和非營利的中間地帶。”
在他看來,這是因為2002年出臺的“民促法”雖然提出了“合理回報”,但對很多問題并沒有講清楚。比如什么叫合理?這個合理是工資回報還是資本增值回報?
“現(xiàn)在看,‘合理回報的提法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權(quán)宜之計。大家的想法是先讓民辦教育發(fā)展起來再說,但是此后民辦教育的發(fā)展速度和程度都遠遠超出了當時的想象。”前述專家說。
而在當時“權(quán)宜之下”分類的具體標準并沒有進行過多過細致的討論,因此也就出現(xiàn)了大量的“中間地帶”。
比如肖軍出資創(chuàng)辦的中學,雖然學校登記的是民辦非企業(yè)單位,但他是出資人,每年還是要從學校拿回一部分投資回報。
而“民促法”修訂后,肖軍勢必要在營利和非營利之間作出選擇。
“目前我更傾向于選擇營利性辦學。但如果因此不再享有優(yōu)惠政策,肯定會導致辦學成本激增,怕是很難再辦下去。”對此,肖軍顧慮重重。
前述專家告訴本刊記者,浙江溫州市作為改革的試點,在民辦學校分類管理的嘗試中,就暴露出了這一問題。
他介紹說,目前溫州全市參與分類管理改革試點的600多所民辦學校中,僅有40所選擇了營利性學校,占比不足7%,而其中真正從事學歷教育的學校只有3所。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選擇營利性辦學,就意味著失去了很多優(yōu)惠政策。而僅教學用地一項,辦學成本可能就要增加十倍。”上述專家稱。
業(yè)內(nèi)流傳甚廣的一個案例是:溫州一所民辦學校原本是按照教科用地以每畝8萬元的價格獲得了土地的使用權(quán),選擇營利性辦學以后,就要按照商業(yè)用地每畝80萬元的價格,補繳近億元的土地使用費。
“這就會極大打擊民辦教育舉辦者的積極性,最終制約民辦教育的發(fā)展。”對此,吳霓也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民辦公辦能否平等
很多像肖軍這樣的民辦學校舉辦者都在觀望,希望“民促法”修訂能夠盡早塵埃落定。
“這樣我們才好放開手腳走下一步。”肖軍說。
而王磊也了解到,由于目前政策不明,大量民間資本還不敢貿(mào)然進入民辦教育領(lǐng)域。但他還是認為,立法需要慎重,“延遲不是壞事情。”
吳霓則認為,無論什么時候,法律的修訂都是一件嚴肅的事情,需要充分考慮外部是否已經(jīng)具有了完善的法律實施環(huán)境,行業(yè)的發(fā)展狀況是否能夠適應法律要求,“如果外部的條件還不完善,法律貿(mào)然出臺反而會限制行業(yè)發(fā)展。”
“比如分類之后如何監(jiān)管的問題,現(xiàn)在的監(jiān)管體制就很難適應分類后的監(jiān)管要求。”北京師范大學一位要求匿名的民辦教育研究者指出。
按照現(xiàn)有的監(jiān)管體制,營利性的教育機構(gòu)只需在工商部門進行注冊登記就可以開門招生,至于教學質(zhì)量怎么保證,還缺乏有效監(jiān)管。
假如“民促法”修訂案出臺之后出現(xiàn)營利性民辦學校激增的情況,現(xiàn)在的民辦學校管理體制也很難滿足發(fā)展需求。
據(jù)前述研究者介紹,目前的民辦教育管理體制還不完善。
雖然教育部在發(fā)展規(guī)劃司設有民辦教育管理處,專門負責協(xié)調(diào)民辦教育的管理,但各省市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或設置專門的民辦教育管理辦公室,或?qū)⒚褶k教育融入各個學段進行管理,情況各不相同。
“就目前來看,不管是專門管理,還是融入學段管理,都存在不足。”前述研究者說。
專門管理,一個部門有限的幾位工作人員,很難對高速發(fā)展、不斷增加的民辦學校進行有效的業(yè)務指導和質(zhì)量監(jiān)管;融入學段管理,又明顯缺乏公辦、民辦一視同仁的政策環(huán)境。
比如,在教師的管理上,事實上民辦學校的教師在職稱評定、保險辦理等方面還很難享受和公辦教師同等的待遇。
“如果未來國家對民辦教育管理體制進行更好、更完善的頂層設計,融入學段的管理方式會更好,但是要做好政策配套。”吳霓說,希望屆時民辦和公辦的區(qū)別只是學校舉辦者的資金來源不同,其他方面都能一視同仁。
“這些問題要在民促法修訂的過程中充分考慮到,這就需要廣泛聽取各方的聲音,充分討論。”吳霓強調(di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