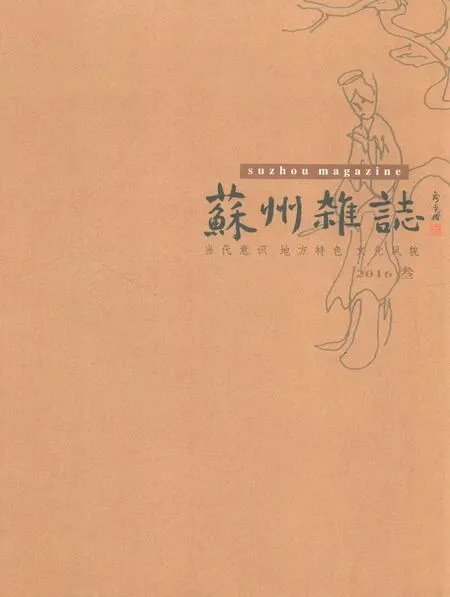像小草一樣
季海躍
像小草一樣
季海躍

《小草》封面
30多年了,當(dāng)年的文學(xué)青年,如今已是人過(guò)中年,有些已經(jīng)做了爺爺和奶奶。
記得上個(gè)世紀(jì)八十年代初,我離別校園,投筆從戎,每次回家探親,只要列車駛近姑蘇城,看到斜斜的虎丘塔,就會(huì)心跳加快,一股暖流暗暗地涌向心間,這不僅僅是對(duì)歷史古城和悠久文化的虔誠(chéng)敬仰,而是每每會(huì)勾起我當(dāng)年在蘇州財(cái)經(jīng)學(xué)校就讀時(shí),熱衷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一度成為文學(xué)“憤青”的回憶。
往事歷歷,感慨萬(wàn)千,我仿佛又回到了那至真。至純的年代……
“文學(xué)青年”在改革開(kāi)放后曾經(jīng)是個(gè)很時(shí)髦的名詞,尤其是在八十年代,那時(shí)的我們常常會(huì)驕傲地說(shuō):我喜歡文學(xué)。
記得,那是一九八一年的秋天,在蘇州財(cái)經(jīng)學(xué)校81屆新生入學(xué)典禮上,老于、韋培祥、李亞明和我第一次握手相遇,四目相視,老于粗獷老成、培祥長(zhǎng)發(fā)披肩、亞明弱不禁風(fēng),而我儼然是個(gè)班長(zhǎng),一本正經(jīng)。
正因?yàn)槭前嚅L(zhǎng)的緣故,我掌握著班里所有同學(xué)的簡(jiǎn)歷。其中老于最先引起我的注意,他來(lái)自于蘇州鐵師附中,是鐵路職工的孩子,那可是當(dāng)年打架出名的一所中學(xué),而他的長(zhǎng)相,少年時(shí)竟然和現(xiàn)在一樣,黝黑滄桑,感覺(jué)像一個(gè)不好惹的刺頭,需要嚴(yán)加提防。
想不到的是,一個(gè)月不到,我們就成了形影不離的好伙伴,起源是大家都癡迷文學(xué),熱愛(ài)詩(shī)歌創(chuàng)作。小個(gè)子亞明年長(zhǎng),大伙稱他為“亞兄”;我與老于同年同月同日生,也算是奇遇,但站在他身邊,我卻像個(gè)小弟弟,于是大家喊我的小名“阿海”;培祥崇拜西方文化,自名為“何夫”;老于最實(shí)誠(chéng),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于”名號(hào)一直沿用到現(xiàn)在,也只有他,最終成了著名作家。
在我們學(xué)校被蘇州大學(xué)合并后的某一天,好像就在老于兄的家里,大家因?yàn)樘K大的“野草”詩(shī)社沒(méi)有接納我們財(cái)經(jīng)學(xué)校的文學(xué)骨干加入,而賭氣酗酒,就在酒酣耳熱之際,我們聯(lián)袂合作了一首長(zhǎng)詩(shī),祭奠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內(nèi)容都寫(xiě)了些什么,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已經(jīng)淡忘了,但,在同學(xué)間流行后,引起了學(xué)校當(dāng)局的關(guān)注,我們的家長(zhǎng)分別被老師們叫到學(xué)校去談話,說(shuō)我們這些孩子有點(diǎn)資產(chǎn)階級(jí)自由化傾向,因此,我這個(gè)班長(zhǎng)也被免了職,降為生活委員。
這次事件促成了我們迅速成立起一個(gè)自己的詩(shī)歌社,當(dāng)年由我提議,蘇州大學(xué)的詩(shī)歌社叫“野草”,我們就叫“小草”好了,大家一致拍手通過(guò)。就這樣,我們四個(gè)人成了“小草”詩(shī)社的核心骨干,整天像小草一樣的聚在一起瘋玩,經(jīng)常上課時(shí)間擅自離開(kāi)學(xué)校,吟詩(shī)作對(duì)、游山玩水,花完了父母給的生活費(fèi)后,老于兄竟然想出個(gè)餿主意,讓大家回去,把家里節(jié)余的全國(guó)糧票偷偷的拿一點(diǎn)出來(lái),到“玄妙觀”去換現(xiàn)金,當(dāng)年的我因?yàn)槟懶。低档亓镒哌^(guò),但,最終還是被老于兄抓了回來(lái),他說(shuō):這叫作“有福同享有難同當(dāng)”。
我們創(chuàng)作的詩(shī)歌也曾經(jīng)向全國(guó)各大期刊投過(guò)稿,但都如泥牛入海,于是,自己動(dòng)手,自編自印了“小草”詩(shī)刊,每期的封面都是亞明手繪,刻板和油印則仰仗已故著名詩(shī)人葉球老兄,他有一臺(tái)當(dāng)時(shí)極為珍貴的油印機(jī)。我們的“小草”好像一共就出了四期,每期各印五十本左右,絕大部分都送給了當(dāng)年的女同學(xué)和鄰校的詩(shī)歌愛(ài)好者了,至今,只有我還保留了其中的兩期。
在那個(gè)青澀的年代,詩(shī)歌與我們仿佛就是一場(chǎng)青春期的艷遇,大家穿著廉價(jià)的花襯衫、喇叭褲,兜里掖著布滿墨跡的詩(shī)稿,從一個(gè)學(xué)校竄到另一個(gè)學(xué)校,從男同學(xué)傳遞到女同學(xué),一幫幫發(fā)燒友們,相互交流、探討乃至爭(zhēng)論,奔走于各校文學(xué)社,自詡為中國(guó)的新生代詩(shī)人。有時(shí)會(huì)為了寫(xiě)好一首詩(shī)而寢食不安,甚至還會(huì)忘了吃飯,實(shí)在餓極了,就蹲在路邊的小攤子上吃一塊錢左右的盒飯……
學(xué)校后面的梨園曾經(jīng)是當(dāng)年“小草”詩(shī)社的據(jù)點(diǎn),我們逃課、曠課、甚至裝病;讀劉心武、蔣子龍、顧城、舒婷……一時(shí)間,喧囂與浮華如同泡沫、塵世與現(xiàn)實(shí)如同云煙;寫(xiě)風(fēng)花、寫(xiě)愛(ài)情、寫(xiě)明天,寫(xiě)不盡的美麗與哀愁、孤傲與寂寞;有時(shí),還會(huì)猛烈的抨擊上夜大、攻雙文憑、讀研究生的同學(xué)們,仿佛這個(gè)浮躁的社會(huì)只有我們才是真正的清醒者。
那些年,我們班的年輕女班主任,可沒(méi)少被我們“欺負(fù)”,從她第一天來(lái)我們班上課,就讓我們這幫文學(xué)憤青掀了個(gè)下馬威:那時(shí)的我們特別喜歡看閑書(shū),而且在課堂上也看得不亦樂(lè)乎,有一次在班主任的課上,也是老于兄帶的頭,我們故意漠視老師的存在,公然地拿出文學(xué)書(shū)來(lái)看,其實(shí)老師早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我們的行為,還故意往我們的方向瞄了幾眼作善意的提醒,但我們假裝不知道,依然我行我素,終于,老于的同桌忍不住了,她偷偷地拉了拉他的衣服,這下可好,老于突然像條件反射一般地站了起來(lái),面對(duì)著那幾十雙驚愕的雙眼,脫口而出“報(bào)告老師,她不讓我看愛(ài)情書(shū)”,話音剛落,課堂里笑聲一片,男女同學(xué)個(gè)個(gè)都捧腹大笑,年輕的老師氣得當(dāng)時(shí)就淌著眼淚,掉頭離開(kāi)。
類似的事件還有好多好多,即便這樣,善良美麗的班主任還是一次次的原諒了我們,記得有一次,大雨瓢潑,她懷里緊緊抱著一大堆書(shū)籍出現(xiàn)在教室門口,她悄悄地把我們幾個(gè)叫了出去,告訴大家這些書(shū)是她專程從上海帶來(lái)給“小草”詩(shī)社的,希望能給我們提供一點(diǎn)點(diǎn)的幫助。當(dāng)時(shí)的她全身濕透,而書(shū)卻一本未濕,當(dāng)我們捧著這些留有老師體溫的書(shū)籍回到座位時(shí),大家的眼睛都是濕潤(rùn)的……老師,你好,今天的你也應(yīng)該六十開(kāi)外了,請(qǐng)?jiān)俅卧彯?dāng)年的“小草”愚昧無(wú)知和少不更事!
時(shí)至今日,曾經(jīng)天真單純、一腔熱血的文學(xué)青年們?cè)缫淹嗜チ送涨酀挠白樱瑲q月的輪回也似乎一夜之間,讓我們從青春回到了白首,也許,今生不再擁有文學(xué)之夢(mèng),也許兒女成群不再回首……
但我們依然會(huì)記得:曾經(jīng)像小草一樣的呼吸、像小草一樣的成長(zhǎng),如果今生今世我們沒(méi)能成為一個(gè)驕傲的詩(shī)人,那寧愿做一棵小草,默默地生長(zhǎng),“野火燒不盡,春風(fēng)吹又生。”